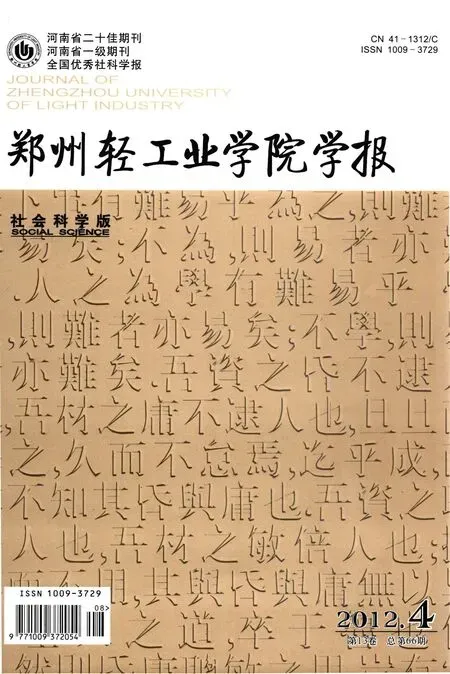论孔子的社会秩序观
王军
(1.南京大学政治系,江苏南京210093;2.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212003)
儒学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秩序思想。瞿同祖[1]曾言:儒家是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的。“五四”思想界的激进主义者往往将儒学视为维护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儒家关注社会秩序的做法也成了很多人攻击儒学的口实。之后,学界对儒家社会秩序思想进行客观研究者不多,对孔子秩序观的研究情况更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在解读相关文本的基础上,梳理和归纳孔子的社会秩序思想,并发掘其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对现实秩序的判定与对理想秩序的设定
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是社会秩序观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理解孔子社会秩序观的前提。孔子判断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2](P174)礼乐制度和战争出自天子或出自诸侯分别是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2](P174)在孔子看来,礼乐征伐如果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那么就不会长久;出自大夫或陪臣就更是如此。在西周鼎盛时期,礼乐征伐专属于天子;周平王东迁之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五霸迭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频繁出现。而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由于缺少法的有效约束,上行下效是无法避免的现象,诸侯的僭越必然带来大夫、陪臣的僭越,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就无法避免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孔子才会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P174)
依据上述标准,孔子判定春秋时期是一个无序的社会:“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2](P175)理想的社会秩序显然不是这样的。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社会秩序必须做到人安其位、各司其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P128)此处涉及君臣、父子两对关系,其中又以父子关系更为核心,这也是移孝作忠的根据。该论断虽有维护等级制度的意向,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君臣父子要尽到各自的职责。先看父子关系:“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P40)父子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平等的,对父母的孝是最基本的要求,子对父是可以“谏”的,关键是要注意方式。再看君臣关系:“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P30)虽然后儒移孝作忠,但君臣关系并不等同于父子关系,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即君以礼待臣。由于君臣之间不存在类似父子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解除:“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P117)可见,孔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绝非后世所宣扬的愚忠。当然,孔子也明确反对臣弑君的行为:“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2](P153)可见,理想的社会秩序是君臣、父子各尽其责,否则就是“礼崩乐坏”的无序社会。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君臣、父子秩序的设定只是一个比较低的要求,更高层次的要求体现在《礼记·礼运》的相关描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3]这是儒家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经典描述,也是对孔子社会理想的进一步升华。然而,现实的社会并非一个理想的有序社会,因此,如何变现实的无序为理想的有序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对传统秩序的创造性诠释
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孔子对前人的思想资源进行了一番选择,并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
第一,从周正名。作为一个十分熟悉传统的思想家,孔子重构秩序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选择、利用“三代”资源。“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P26)“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P28)显然,孔子从周,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周比夏、商两代的文献更为丰富,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孔子认为周文化比起夏、商两代有更多的优势。然而,孔子时代周文疲弊,各种僭越行为造成了名实混乱。因此,孔子提倡正名:“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2](P133-134)
孔子所谓正名,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名实一致,即循名求实,有君之名,须有君之实质;有臣之名,须有臣之实质。父子亦然”;其二,“名分相符,即依名守分,有君之名,须守君之本分,有臣之名,须守臣之本分。父子亦然”。[4]表面上,孔子的这种做法是在维护既有的等级名分,因此有人将其等同于“恢复已经衰颓的周礼中的等级名分”,继而认为其思想是守旧的——如冯友兰[5]在其《中国哲学史》中就持此观点。其实,孔子倡导正名是有其现实原因的,决非“复古倒退”,其目的是强调人们(主要是为政者)要主动约束自己的欲望以符合自己的“名分”,而非简单地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这是对制度的重整而不是简单的“恢复”,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正名,可以使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如此,各种因欲望张扬而造成的僭越行为就会逐渐消失,社会也会逐渐回到符合礼之要求的秩序之中。
第二,以仁释礼。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孔子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礼乐制度本身的崩溃,而是人们内心对礼乐秩序的忘却最终使其成为没有灵魂的、僵死的躯壳:“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6]这种拘泥于礼的形式而忽略礼的本质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因此,孔子才会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P185)为了使礼乐获得新生,孔子援仁入礼,就是要唤醒人们内心对礼乐秩序的自觉。当然,孔子所说的礼乐并不完全等同于西周初年的礼乐,它已经从外在的规范变成内在的自觉了。为了将礼乐秩序植入人的内心,孔子将其解释为人之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P24)既然仁是人之本质,则只要将仁唤醒,就可以重构人内心的秩序,而内心秩序的外化就可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
这种重构有可能吗?在孔子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一方面,孔子认为人性平等,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P181);另一方面,仁根植于人性之中,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P74)。当然,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十分复杂,但“仁之成就,始于主观之情感,终于客观之行动”[7](P57)的特征,保证了礼乐制度可以通过仁获得新生。非但如此,作为主观情感的仁,还是安顿人心、处理人心秩序的最重要的原则与手段。
三、对社会秩序中不同主体的安顿
理想秩序的实现离不开人。在孔子看来,不同的人其作用是不同的:君子是实现理想秩序的主体,是主动者;而普通民众则是需要被安顿在这一秩序中的分子,是被动者。
1.提倡君子人格
重构理想的礼乐秩序离不开君子,这一重任主要由君子承担。为什么只有君子才能承担起重构理想社会秩序的重任?这涉及到理想与现实的问题——虽然人性平等,但理想并不等于现实,现实中人与人是有差距的,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2](P61,P181)。所以,重构社会礼乐秩序的重任只能由“中人以上”的君子承担。然而,君子有什么样的规定性呢?有人认为,君子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体系中,“指称的基本对象是政治中人,而不是后来宽泛意义上的道德指称”[8]。说君子主要是处于政治上的在位者而非普通民众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在孔子那里,君子还应包括道德高尚者,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P1)中的“君子”显然不必是政治上的在位者,政治上的在位者只是其原始义。因此,理想的君子是德与位同时具备者,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所说的君子不是普通的、作为芸芸众生的百姓,而是能够担当道义的人。
担当道义的君子应如何重构秩序呢?在孔子看来,就是通过君子的“修己”达到“安人”、“安百姓”的效果:“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2](P159)君子“修己”是唤醒自己内心对秩序的自觉,这是重整外在秩序的基础;“安人”、“安百姓”则主要是通过君子恪守秩序而对百姓产生示范作用来实现的,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P11,P12)。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由“内圣”而“外王”[9]。与庄子“内圣”为本、“外王”为末[10]不同,在孔子那里“内圣”固然很重要,但绝不能取代“外王”。虽然“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但“外王”是孔子一生都未曾放弃的追求,只要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是十分乐意做官的,因而子夏说的“学而优则仕”[2](P202)也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即便孔子晚年不再求仕,一心编(著)书、授徒,也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无论是以“思无邪”为宗旨的《诗经》,还是记载古代圣王治国之政治经验的《尚书》,都表现出其明显的政治意图,而《春秋》所体现的“春秋大义”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更是十分明显;在讲学中,孔子也并非以培养有知识的人为目的,而是为了培养能够实现“王道”的士与君子。所以,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是其思想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向度,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两者缺一不可,他们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内圣”就一定能达到“外王”吗?孔子想到了这个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主要体现在其治民之术中。
2.养民、教民、治民并举
除了君子,世上更多的是普通民众,如何安顿这些人是重构理想社会秩序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孔子提出了三个策略,即养民、教民、治民。
首先是养民。养民是孔子一贯的主张:“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2](P136-137)如何养民?孔子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P4)又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11](P12)孔子之所以重视养民,一方面与其仁的精神相关[7](P60),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认识到必要的财富是德性与秩序的基础。这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2]的道理有相通之处。但孔子并不提倡以追求财富为目的,而认为财富应该是完善德性的手段,所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11](P12)。在财富分配上,孔子明确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P172)这仍然是出于对秩序的考虑。
其次是教民。在孔子那里,养民是为了给社会秩序的安定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理想的秩序并不会随着基本物质生活的满足而自然建立,因此需要对民众进行教化。孔子的教化理论十分丰富,其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以身作则,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P129)。又云:“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P138)“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P135)在位者与君子以身作则是教化民众的关键,君子、民众都做到“正”,方能实现社会的安定与秩序的重建。
最后是治民。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通过教化而遵守秩序的:一方面,有些人是不好教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P81)——此句中的“可”不是“可以”而是“容易”之意,这与孔子“有教无类”[2](P170)的主张完全一致。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人,让他照着做可能比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更容易。另一方面,总是存在一些不受教因而教不好的人,这也是事实,因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对于“不好教”(不易教)和“教不好”的人,采用强制手段即政与刑也就无法避免了。然而,孔子认为,政与刑的作用是消极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2](P12),因此政与刑只是实现教化和社会秩序重建的辅助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萧公权才会说孔子“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殆略近于消极”[7](P63)。
四、孔子社会秩序观的当代价值
孔子通过从周正名与以仁释礼对传统秩序的创造性诠释,以及通过提倡君子人格与养民、教民、治民并举来安顿社会秩序中不同主体的思想,对我们构建与维系良性社会秩序有重要启示。
第一,良性的社会秩序需要不断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孔子的社会秩序观并不是对西周旧秩序的简单重复,而是依据仁的精神对传统秩序的创造性诠释与重构。伴随着春秋时期人文精神的跃动、井田制的瓦解和现实王权的衰落,维系以礼制为特色的社会秩序的各种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改变,原有秩序岌岌可危,这是孔子改造周礼的最根本原因。而孔子改造原有礼制秩序的基本方式就是融入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精神。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社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文化观念的碰撞与交流更加频繁。因此,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必须不断地输入时代精神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
第二,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孔子重视养民,主要是强调要让百姓在经济上实现富足,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百姓进行有效的教化。这一认识十分朴素,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代社会也是如此,要想建构并维系良性社会秩序,必须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且这种需求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第三,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教育与感化。人们对物质的欲求有时是无止境的,孔子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尤其重视教化的作用,将教化作为重构社会理想秩序的基本手段。当今社会要建构与维系良性的社会秩序,亦应对国民进行教育与感化。当然,这种教育不能仅停留于标语、口号,而要变生硬呆板的道德说教为润物无声的绵绵细雨,以增强其亲和力、感染力,让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内在的德性品格。
第四,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制度的保障。面对那些无法教化的民众,孔子并没有排斥政与刑的作用。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样如此,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仍然需要一定的强制措施,而这离不开较为完备的制度保障,如此方能避免政随人迁,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第五,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榜样的示范作用。孔子认为君子在重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启示我们,社会秩序的建构需要发挥榜样的作用。政治上的在位者和公众人物的言行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网络时代这种示范效应尤为显著,因此政治上的在位者及公众人物必须自重。另外,要有意识地发现和保护那些能对社会秩序产生积极影响的榜样,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并对之进行倡导和宣传,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良性社会秩序建构与维系的示范作用。
[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270.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14.
[4] 萨孟武.儒家政论衍义[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38.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78-89.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57.
[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8] 赵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3.
[9]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84.
[10] 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8:881.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戴望.管子校正[M].上海:上海书店,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