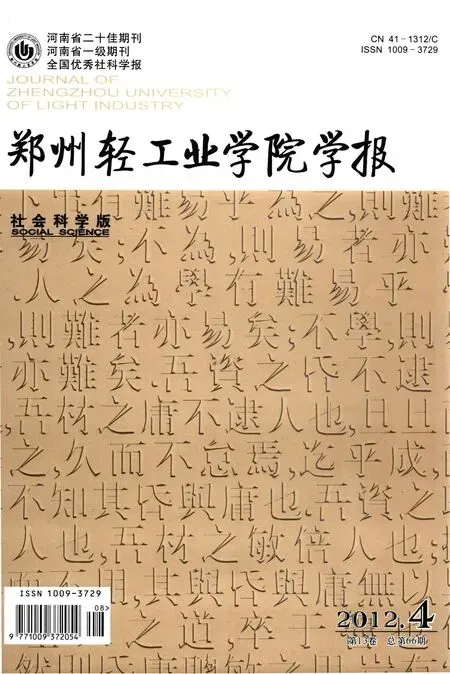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杨卫军
(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原籍德国,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它使人向非人化方向发展,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被异化,因而是病态的消费异化的社会。学界对弗洛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弗洛姆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关系、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分析和社会改造理论及人道主义与人学思想等方面,但都没有对弗洛姆异化理论的具体内容及成因作系统探讨,也较少涉及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问题。本文拟在分析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弗洛姆异化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
总体上,弗洛姆认为,人类有“自我保存的需求”和“生存的需求”,人性是一种潜能、创造性和理性,对自由、幸福的欲求是人的天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模式。如果一个人按照人性的特性和规律去充分发展,他就可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如果一个社会以符合人性的、满足真正的个人需要为基准,它就是健全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不健全的社会,它以人的病态化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人的异化。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对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病态化及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弗洛姆认为异化主要是心理学问题,是一种心理体验。所谓“异化”,就是一种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把自己看做一个陌生人”[1](P106)。弗洛姆认为,在现代社会,异化几乎无处不在,“它存在于人与他们的工作、与他所消费的物品、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以及与他自身的关系中”[1](P109),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已经在物质上进入了富裕社会,但人被异化的范围也更广泛了,已经由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手段,但消费的这一功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异化了,消费被赋予了其他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人们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消费异化使消费的主体、客体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异化。
1.人所创造的世界成了人的主宰者
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然而人却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反而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奴隶。人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越强大,人就越感到作为一个人的渺小和无能。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组织越来越庞大的工业社会中,人所创造的世界没有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确证,人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也没有成为人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必需用品,它们反而成为人的偶像和控制人、奴役人的上帝,物欲驱使使得生产者成为消费行为实现自己的必需手段,人不过是消费得以实现和持续的环节,人对物的消费异化为物对人的消费,消费异化成为社会存在的重要特征。“人所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在它面前,人俯首帖耳。他竭尽全力地安抚它,巴结它。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2](P159)
2.商品使用价值被遮蔽
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炫耀价值走向前台,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微不足道。当一个人说到“300万美元的物品”的时候,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它的用处、外观或具体特征,而是在说它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能用金钱数量形式来表达其交换价值的品质。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表了一种抽象形式的劳动和努力,它不必是“我”的劳动和“我”的努力,因为“我”能通过继承或欺诈或运气或其他方式得到它。“如果我有钱,我就能够得到一张精美的油画,即使我可能没有一点艺术鉴赏力;我能买到最好的留声机,即使我毫无音乐感。”[1](P115)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使用价值被遮蔽,商品的价值被异化,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3.消费从手段变成目的
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满足于无使用价值的占有与幻想的需要,人们的消费狂倾向已经与人的真实需求失去了正常联系。最初,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更为快乐和满足的生活,消费是使人快乐的手段,但是现在消费成了目的。“我们吃一块无味而没有营养的面包,只是因为它满足了财富和身份的幻想——它是那么洁白和‘新鲜’。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吃一个‘幻想’,与我们吃的东西失去了真实的联系,我们的口味、我们的身体,被排除在这一消费行为之外。我们在饮用标签。拿到一瓶可口可乐,我们是在饮用广告上的俊男俏女,我们是在饮用‘停下来提提神’这个广告词,我们是在饮用伟大的美国习惯,我们绝不是品尝味道。”[1](P116)今天的人们已经被他们能够购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商品的能力所迷惑,人们成了消费狂。消费行为本来应该是人类的自觉行为,人在消费中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情感的、有判断能力的人,消费行为应该是充满意义的、体现人之本质的创造性的情感体验,但在消费社会中,这种创造性的情感体验微乎其微,消费基本上是消费主体对人造幻觉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具体的、真实的自我相分离的幻想的满足。消费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人变成了商品的奴隶,整个社会趋于病态,而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消费异化的最典型特征是社会上出现了“消费人”这一性格类型的人,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普遍相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停地购买又不停地抛弃。
4.人们对商品的原理日趋陌生
在弗洛姆看来,人们被一无所知的商品所包围——电视机、收音机、留声机,它们的性能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而又神秘,我们就像是从原始文化中来的人,对于那些常见商品的原理感到陌生而遥远。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应该按哪一个按钮,但我们并不知道其所以然——除了一些我们在学校里获得的粗糙术语之外。就连那些并不存在什么复杂科学原理的东西也同样如此,“我们不知道面包是怎么做的,布是怎么织的,一张桌子是如何生产的,玻璃是怎么制造的”[1](P117)。这正是典型的消费行为的异化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丰富的世界里,而我们与它们的唯一联系就是,我们知道如何操作和使用它们。
5.闲暇时光走向异化
弗洛姆注意到,现在有90%的人都会读书写字,更有电视、电话、电影和供每个人每天阅读的报纸,然而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予人们最优秀的文学和音乐作品,而是用廉价而缺乏真实性的垃圾和偏执狂的幻想来填充人们的心灵。他会“享用”球赛、电影、报刊、书籍、演讲、自然景色以及社会的集体活动,但他不是主动地参与这些活动,而是要“享用”一切已有的东西,并尽可能多地占有文化。实际上,他并不能自由地享受自己的闲暇,像他购买的商品一样,他的闲暇时光已经被消费社会所控制,他的品位也因为他想听到和看到的东西已经预先设定而受限。这种闲暇被异化的情况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拍照行为——人们不停地拍照,但常常什么也没有看见,除了取景器中的印象;照片替代了旅游,享受旅游的过程消逝殆尽,人们也失去了充满意义的、创造性的体验。
6.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
在消费社会里,不仅人与物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而且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雇主利用雇员,推销商利用顾客。每个人都是除自己之外的别人的一个商品,会受到一定友好的对待,因为这个人即使现在没有用处,也许将来会有用。在现在的人际关系中,再也找不到多少爱与恨,人们有表面上的友好和更多表面上的公平,但在表面之下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相互的冷漠,以及大量的难以捉摸的互不信任。[1](P121)在消费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而人的价值就体现于卖者能成功地就自己的交换价值与买者达成协议,并尽可能地抬高这种价值。“既然现代人体验到自己在市场上既是销售者又是商品,他的自尊就依赖于他所无法控制的条件。假如他‘成功’,他就有价值;反之则一文不值。”[4](P145)
7.人与自身的关系被异化
弗洛姆把由于消费异化而导致的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描述为“市场倾向”,在这种倾向中,“人体验自己是一个能够在市场上被成功利用的东西,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自身权利的持有者、一个积极的作用者,他的目标是成功地在市场上销售自己。他的自我意识并不来自于作为一个富有爱心和思想的个体的活动中,而是来自于他的社会经济角色中”[1](P123)。消费社会中的人并不是一个有爱心、恐惧、信念、幸福等情感体验的人,而是一个真实本性异化的、在社会系统中完成一定作用的抽象物——这种体验自己的方式是人与自身关系异化的结果。此时,人的肉体、头脑和灵魂就是他的资本,生活的任务就是努力地投资,使之为自己创造出最大的利润,其内在品质如友爱、仁慈等成了他作为商品时的外包装,有助于他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尊严被一点点地摧毁,市场成了衡量人成功的唯一尺度,由此带来的不安和焦虑以及判断力的丧失使他更依赖于市场的认可,最终沦为“无我”的状态。过去的不幸是,人成了奴隶;现在的不幸是,人成了机器。
8.消费异化带来生存危机
消费异化必然导致人类的生存困境。在消费异化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人把占有、消费视为自己人生的真谛。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贪欲,“他”不但要占有本国的资源,还必然要拼命地去掠夺他国的资源,这就必然引发战争。弗洛姆对由于消费异化引发战争极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因为人们会顺从那些命令他们的人从而铸成终身大错,因为人们会遵从古已有之的恐惧、仇恨和贪婪情感”[3](P1)。如果任由人们的无度消费发展下去,“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不会有能满足每个人无止境的消费欲望的经济”[3](P105)。在资本主义社会,由消费带来的无限占有欲望驱动着人们对资源和能源的无限攫取与掠夺,最终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而技术的进步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更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
9.真爱和幸福逐渐丧失
弗洛姆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求得精神上的满足与幸福。“爱既不是一种飘落在人身上的较大力量,也不是强加在人身上的责任;它是人自己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人使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世界真正成为他的世界。”[4](P34)而在市场机制和消费异化状态下,这样一种出自其本性、发自其内心的爱的能力已消失殆尽,人与人之间的同胞之爱蜕变成抽象物之间赤裸裸的交易关系,人间的真情一点点枯萎,爱的能力一点点消失,真爱因为利益驱动而完全封闭于人的内心深处。而且,现代人普遍相信:生产发展无限可能,消费永无止境,技术无所不能,科学无所不知,而幸福就是消费更新、更好的商品。因此,任何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成了消费的对象。然而,消费者并没有从中得到资本与广告所允诺的快乐和幸福。一方面,消费异化中的极端享乐主义虽然也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但同时认为幸福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全部愿望或主观需求;另一方面,消费异化中的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必须鼓励的性格特征,所以现代人以利己主义的方式尽情享乐并希望把一切都据为己有,占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真正的幸福由于消费异化中的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而完全丧失殆尽。
二、消费异化的成因
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背后凸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现代性困境和自身的危机。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上进入富裕社会后一次全面的社会转型,它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弗洛姆通过重点分析19—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来分析消费异化的成因。
1.资本增殖的结果
弗洛姆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最显著的变化是技术上的变化,蒸汽机、内燃机和电的广泛使用,原子能的开始利用。这一技术发展的特征是,手工劳动越来越为机器生产所取代,甚至人的智力也为机器的智慧所取代。”[1](P92)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由于工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生产由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日益向资本增殖的方向转变,与生产和市场有关的一切都因为资本增殖链条的无限延伸而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最终导致人的性格及其生存目的的根本变化,消费异化只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这样,资本统治下的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是机器越能干,人越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于是人只有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提升主体的方法最后异化为和主体一起服务于资本增殖。
2.价值缺位的焦虑
弗洛姆认为,19—20世纪资本主义的根本变化就是国内市场重要意义的提高。“我们的整个经济机器都建立在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原则的基础上。在19世纪,普遍的倾向是节约,到了20世纪,情况却完全相反,每个人都被诱惑去购买尽量多的商品,更多的市场需求是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手段的强烈刺激下产生的。”[1](P95-96)这种由生产方式变革和需求目的变化而产生的市场法则延伸到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中,使得现代人把自己也当做物来看待,体会不到自身的价值,把人看做社会经济制度的附属物。资本市场能直接体现出来的就是所谓“公平”交换,即主体直接感知的是物欲表征的交换价值,价值本身因物和人的双重异化而隐而不现,价值缺位的焦虑导致主体安全感丧失,进而使得消费购买与占有欲望成为主体证明自我的生存方式,结果反而加剧了消费异化的趋势。
3.生产行为的延伸
在弗洛姆看来,数量化、抽象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加剧了数量化、抽象化的过程。“如果没有数量化和抽象化,现代产品的批量生产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一个经济行为已经成为人的主要职业的社会里,这一数量化和抽象化的过程已经超出了经济生产的领域,从而影响到了人对物、对人以及对自己的态度。”[1](P100)质言之,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和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由此导致了数量化和批量化的生产行为,从而为资本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为消费延伸提供了无限可能,交换行为的抽象化、人际关系的冷漠化、消费行为的异己化不过是这种可能的实践形式而已。
4.人性欲望的失控
20世纪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使它拥有了千倍于从前自然所给予人的力量,似乎一切都有可能。生产的奇迹引发了消费的奇迹,再也没有什么传统观念来阻止人购买他想要的东西。“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可能不是为了购买真正的珍珠,而是购买化学合成的珍珠;购买像凯迪拉克一样好的福特汽车,购买与价格昂贵的服装一样效果的便宜衣服,购买百万富翁和普通工人都爱抽的香烟。”[1](P97)只要拥有金钱,每件物品都伸手可及,都能买到、都能消费。当消费成为生存方式,它就不再仅仅是资本增殖的链条延伸和价值缺位的证明方式,而且成了人性底线的无控释放和欲望满足的符号能指——消费的对象甚至消费对象的交换价值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消费本身,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三、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过健全生活、如何建设健全社会的一种新思路。
1.树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
消费异化中的占有取向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典型特征,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即“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就是“我”的生存。在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有与利用的关系,所有的人和物不过是为己牟利与满足物欲的手段。而今,这种消费异化现象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国的消费现状:很多人不再满足于物品的使用价值,开始从实用消费转向符号消费甚至炫耀型的奢侈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正侵蚀着人们以人为本、注重实用的健康消费理念,成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敌。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借鉴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树立“重生存”的生活方式,让社会的生产活动回归真正“为人”的生产目的,让人的消费理念回归“生存”本身,反对炫耀型消费和奢侈消费等消费异化现象,在全社会树立起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健康消费理念,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们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与世界融为一体。[5](P23)
2.建立生态消费的消费模式
弗洛姆在对消费异化进行批评时认为,消费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应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异化消费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快乐,那种认为“我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和怎样来的以及我要用它做什么,与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要不触犯法律,那我的权利就是无限的和绝对的”[5](P75)的观点和原则是不合理的。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对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建立积极健康的消费模式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主体权利“无限和绝对”的错误消费理念和生活原则,建立生态消费的新模式,使生产活动建立在人们的健康消费基础之上。在生态消费模式下,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等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人的需求出自真实的需要而不是虚假的需要,消费行为应该对人的身心发展有利而不是相反,企业不能仅为了利润而生产,而应该以满足人们的身心健康需求和人本化发展为要旨。
3.注重精神健康的实际需求
弗洛姆所谓“精神健康的人”是指:“他与世界建立友爱的联系,他利用自己的理性去客观地把握现实;他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单个的个体,同时又感到自己和他人是同一的;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的摆布,而愿意接受良心和理性的理智的权威控制;只要他活着,他就会不断地再生,他把生命的赋予看做是他所得到的最宝贵的机会。”[1](P221)当前我国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说到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达至和谐的社会和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和实现这种生态文明,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人的精神健康和心态和谐,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培养其自由、友爱和创造性的人格品质,在反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异化消费的过程中坚持以人的发展为唯一目标,使物质需要服从精神需要,使物质消费真正服务于人的生存本身。
4.关注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
弗洛姆认为,“我们需要的收入是能保证有尊严的生活的基础。就收入不平等而言,这种不平等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制”,应建立“年保证收入”制度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1](P270)这对完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关注我国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并保证其基本生存权等具有重要意义。包含人与人的关系在内的人类社会系统,本来就是广义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广义的生态文明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进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源分配不公平、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存在的重要原因,和谐社会建设本身也说明目前我国尚存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影响生态文明双重和谐的不利因素。对此,我们可借鉴弗洛姆关于限制不平等收入的思想,结合我国国情来完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待遇,在关注弱势群体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改善其生存状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达至生态文明的双重和谐。
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是深刻的,但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对之要做批判性的分析。弗洛姆试图对以恒久和普遍的方式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界定,而忽视了其具体的文化背景;他的消费异化理论建立在他的人道主义总体人性论的基础上,具有抽象人性论的性质;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具有乌托邦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理论魅力。
[1] [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王大庆,许旭虹,李延文,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2] [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3] [美]埃里希·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M].王泽应,刘莉,雷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 [美]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 [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