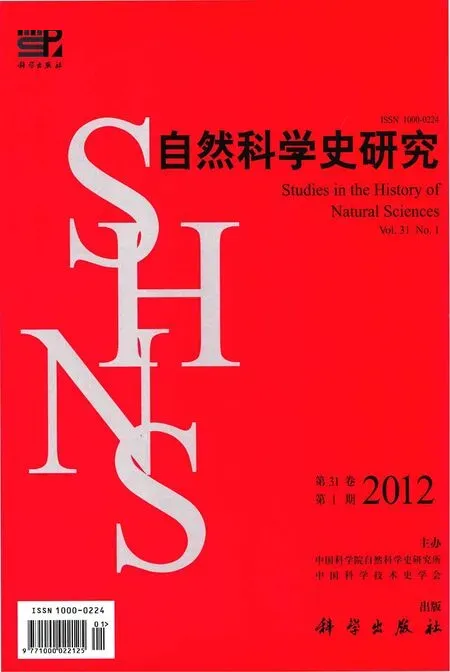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的利用与改良
杜 娟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062)
土壤作为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如何合理利用始终贯穿于我国悠久的农业历史中。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国劳动人民在识土、用土、改土、养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被古代农学家总结记载于许多古籍中。有关古代劳动人民土壤耕作的历史演进一直是农史学界关注的问题,并已开展了许多深入的研究[1—3]。但研究多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土壤耕作技术的革新,而对耕作技术的应用与土壤环境变迁的具体关系则研究较少,也缺少古代土壤耕作的区域性研究。关中平原是我国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很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于此产生并迅速传播。该区域目前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产区,其优良的土壤资源是农业高产的有力保障,现代地表广泛覆盖被群众称为“塿土”的农业土壤,学名为“土垫旱耕人为土”。这种土壤类型正是在自然尘降和人类不断耕作施肥双重作用的影响下,在自然褐土层表面叠加了厚度约≥50cm的人为堆垫熟化层,该层具有优良的生产特性,为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4]。但在原始农业向传统精耕细作农业转变的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地表尚无深厚的堆垫熟化层,那时农业耕作的土壤环境如何,人类又是如何利用及改良土壤仍有值得深入研究之处,也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区域人为土产生的历史过程提供依据。
1 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特征
古时关中平原属雍州,《尚书·禹贡》记载,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为上上”。雍州东邻冀州与黄河为界,南邻梁州以秦岭为界,其广大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厥土惟黄壤”是对覆盖于黄土高原黄土的直观描述。“厥田为上上”也说明了黄土是一种优良的土壤资源,对应全国最高的田赋等级。但在黄土高原内部,各地区受气候、地形的影响,土壤类型又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秦汉时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平原,因“膏壤沃野千里”[5]被称为天府之地。那么,秦汉时期关中平原“膏壤”的土壤环境、农业生产特性具体如何呢?
关中平原地貌形态以河流阶地、黄土台塬和山前洪积扇为主。渭河两岸的河流阶地及黄土台塬由于地形平坦,发育较为完整,成为古代关中农业发展的主要区域。由于一级阶地形成时间较晚,其上部仅有全新世两层土壤发育,二级阶地及黄土台塬上则发育有两层以上的古土壤[6]。一般认为,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全新世普遍发育了两层土壤,即全新世黄土(L0)和全新世古土壤(S0),上部全新世黄土开始发育年代为距今3000年左右,正值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下部全新世古土壤发育于距今8500~3000年左右。[7,8]而秦汉时期农业垦殖也开始于距今2000多年,正是全新世古土壤向黄土发育过渡的时期。因此,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平坦阶地及台塬上的农业垦殖大多是以全新世古土壤层为耕作层位。古土壤层粘粒含量高,质地坚硬,具棱柱状结构且大孔隙少,这种土壤质地和结构并不利用土地垦殖和作物生长。
针对古土壤层质地坚硬、透水性差等特点,古代先民往往通过抢耕,尽可能保证更多的天然降水储存于土壤当中。《吕氏春秋·辩土篇》就曾提到:“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厚)枯,必厚(后)其靹,为其唯厚(后)而及。”①该句括号中为后人校注时所改文字。孙诒让曾经认为:“此文多伪体,不能尽通。是否是后人校释有所而成,不得而知。”他将此句改为: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后)其靹,为其唯厚(后)而及。夏纬瑛先生校注时认为该句应为: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厚)枯,必厚(后)其靹,为其唯(雖)厚(后)而及。垆土层由于土质致密坚硬,往往不利于水分的下渗和储存,导致土壤内部水分缺失。而古时耕地注重深度要达到湿润的“阴土”层,《吕氏春秋·任地篇》中就曾提到“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就是强调耕地的深度要达到土壤底墒。故垆土层会因为水分少而具有深厚干枯的特征。《说文》释:“垆,赤刚土也,”实指黏性强的土壤类型,《广雅·释诂》释:“靹,弱也,”代表轻质疏松的土壤。该句是说耕地的道理,开始必定要先耕刚强的垆土,因为它水分少而深厚干枯,必定要后耕轻质疏松的靹土,因为它即使后耕也来得及。《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集其门客所编著,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当时秦国主要活动范围也位于关中平原,据此可以推断文献中所载“垆土”与“靹土”应为关中地区秦时期的主要农耕土壤类型。至汉代,氾胜之“教田三辅”,在其所著《氾胜之书》中详细记录了汉代整地、耕地的技术与方法,其中也强调“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上述文献中“坚硬”、“寡泽”而“厚枯”都符合古土壤层的特点,孔隙度小,黏性强,土壤紧致,不利于水分的流通和存储,往往成为黄土地层中的隔水层。而从靹土的土壤性质来看,质轻而疏松,应属于新近沉积物或发育较弱的黄土层的性质。
在关中平原内部,各地气候没有显著差异,地形则是造成土壤类型差异的主要因素。从全新世古土壤层广泛分布于黄土塬各级塬面及河流阶地上来看,秦汉时期,坚硬的垆土层主要分布于这些区域,而在塬区缓坡或泾渭河谷低阶地上,受地形及河流泥沙泛滥等影响,地表外源物质堆积作用显著增强,造成土壤熟化作用和粘化作用大为减缓,使剖面内全新世古土壤层缺失或发育很弱,粉砂含量高,故而形成质地松散的“靹土”土壤类型。然而,质地过于粘重或疏松均不利于土壤气、热、水、肥的疏通和平衡,大大降低了土壤的适耕性。
除土壤质地影响农业垦殖外,土壤水分与养分也难以满足秦汉时期农业耕作的需要。关中平原虽位于黄土高原最南端,可供利用的农业气候资源均优于黄土高原其他地区,但土壤水分不足仍是限制关中平原农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尤其农业灌溉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秦汉时期,解决土壤缺水问题就成为农民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故古代关中文献中不乏土壤增水保墒措施的记录。此外,“薄田”、“腊田”、“脯田”等也都是土壤肥力不足、结构不良的表现。为此,古代先民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通过一系列整地、用地技术改良土壤环境,从土壤质地、结构、水分、养分等多方面提高土壤的适耕性。
2 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的利用与改良
2.1 土壤质地与结构的改良
关中平原西部气候湿润状况优于东部,且东部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渭北平原很多地方古称沮洳之地,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关中平原内部的土地开发存在着由西部向东部、高地向低地转移的趋势。当许多地势低平的地带由于盐碱地的存在而难以利用时,关中地区的土地垦殖仍然以黄土塬、黄土丘陵为主。黄土塬及丘陵地带的地形起伏、微地貌差异也会导致上层沉积物来源的多寡及水分聚集程度的差异,进而造成土壤质地的强弱差异。这种质地强弱的差异主要由土壤中粉砂和粘粒含量的比例决定,汉代先民在其耕作体系的建立中,也体会到这种土壤的差异,并用“强土”与“弱土”区分不同的土壤质地。针对土质坚硬的“垆土”层,采取“强土而弱之”的耕作方法。《氾胜之书》载:“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所谓强土而弱之也。”[9]《说文》释:“摩,研也”,这里为摩平摩碎之意。通过这种“耕-摩-复耕-复摩”的耕作体系将坚硬的土块彻底打碎,形成细小的颗粒,使其质地变得松软。而对质地松散的靹土,又被称为“轻土”或“弱土”,于“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耕辄蔺之。草生,有雨泽,耕重蔺之。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9]。“蔺”通“躏”,有“践踏、碾压”之意,通过“耕-蔺-复耕-重蔺”的耕作体系,且以“牛羊践之”的方法使土壤变得致密紧实。显然,这种过“强”或过“弱”的土壤都不宜作物生长,人们需要采取“强土而弱之”和“弱土而强之”的方法,改良耕作土壤的质地和结构,这是形成质地均匀的耕作层的基础环节。
土壤质地除了通过直接的治土过程得以改善外,古代的治田技术也显著影响土壤质地的变化。我国古代从原始农业的粗放经营到传统时期的精耕细作,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则是由原来的遍地撒种到对耕作地块进行统筹规划。这种农田规划自周代已开始,“《周礼》所谓‘遂人’、‘匠人’之治,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遂注入沟,沟注入洫,洫注入浍,浍注入川。故田亩之水有所归焉,此去水之法也。若夫古之井田,沟洫脉络,布于田野,旱则灌溉,涝则泄去,故说者曰:沟洫之于田野,可决而决,则无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则无旱干之患”。[10]一种好的农业耕作体系或布田方法,对改进土壤透水性,提高土壤含水量,降低地表径流是有直接意义的。《吕氏春秋·任地》也提出“上田弃亩,下田弃甽”[11]的垄作方法,即在易旱的高田要放弃垄台,将作物种植在沟中;而在下湿的低田要放弃沟,将作物种植在垄台上。这正是通过改变微地形的治田方式达到对土壤水分的调节,起到高田蓄水、低田避水的作用。至汉武帝末期赵过任搜粟都尉时,又推行了代田法,更进一步改进土地利用方式,实行“一亩三甽,岁代处”[12],将作物播于甽中,待出苗后,逐渐将垄台上的土覆于苗根,且每年垄甽互换,这不仅使作物起到抗旱、抗风、抗倒伏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恢复,提高土壤的生产力。
为使得各种土壤类型都能获得丰产,汉代对商代曾出现过的区田法也进行了积极地推广与改进。区田被认为是低于地面的田畦,以此聚集水肥。具体做法为:“以亩为率,令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广四丈八尺;当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间分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广一尺五寸;町皆广一丈五寸,长四丈八尺。尺直横凿町作沟,沟一尺,深亦一尺。积壤于沟间,相去亦一尺。尝悉以一尺地积壤,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积壤。”[9]并且,根据不同作物吸收热量、水分的不同,间隔种植的距离及种植株数也不尽相同。依此方法,可根据地形地势规划数量、大小不等的地块。这使得开垦丘陵及边坡地带时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产值,而且低畦种植也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因此,氾胜之也强调,区田“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而且区田,“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9]。这也说明,汉代对于“非良田”的耕种或荒地的开发采取了直接建区田的治田方法。且从“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9]可看出,当时区田显然是为应对旱灾而作,其目的就在于将地表做成凹于地面的坑,减少地表径流,土壤储蓄雨水的能力就会增强,加之耕翻过的土壤,质地疏松,更增加了土壤的垂直入渗率。
通过土壤质地的改良达到良好的土壤结构是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一种好的土壤结构往往存在大量的团粒结构,促使土壤养分、土壤水分、土壤空气三者的协调统一,达到土壤中水、肥、气、热的平衡,满足作物对水肥等的需要。土壤耕作正是通过外力作用于土壤,改善土壤结构,调整耕作层及地面状况,用以调节土壤水分、空气、温度和养分的平衡,为作物播种、生长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我国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判断土壤的优劣,并掌握其生产性能。《周礼》中“万物自生焉则曰土,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曰壤”指出了“土”与“壤”的概念。《说文解字》关于“壤”的解释:“壤,柔土也,无块曰壤。”《周礼·地官》郑玄注:“壤,和缓之貌。”显然,人们已经了解土壤的生产特性,并认识到只有人类活动施加于土壤才能形成从“土”到“壤”的结构转变。对于改善土壤结构的方法,汉代氾胜之就提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9]“趣时”强调选择最佳的时间下种、耕翻、不误农时。“和土”是使土壤松和,调节土壤的通气及热量状况。“务粪泽”强调水分和养分的重要性。这些土壤耕作的重要原则始终贯穿于农业劳作的各个环节。
汉代十分重视“耕得其时”,充分利用气候和土壤条件,达到适耕的目的。土壤保持良好的通气状况是土壤水分、养分得以运输、协调的关键。因此下种前,适时而耕就是要保证土壤内部热、气、水、养分间的协调。古时常常提到“地气”,即是指土壤的通气状况。土壤空气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土壤水分共同存在于土壤孔隙当中。土壤空气主要来源于近地面大气层,其主要成分为O2和CO2,但经过土壤微生物呼吸过程和有机质分解过程消耗O2而释放CO2,因此土壤中CO2的浓度明显高于大气层。随着温度升高,微生物活动增强,土壤中CO2浓度会更高,导致土体膨松。据观测资料显示,土壤剖面30cm深度范围内CO2和O2的体积分数在冬季分别为1.2%和19.4%,而夏季则分别为2.0%和19.8%。[13]可以看出,当夏季气温升高,土壤中CO2和O2的体积均有所升高。地气对生物活动具有明显的影响,当土壤通气不良时,微生物活动就会减弱,制约植物根系的生长,阻碍植物根系对水分及养分的吸收。我国汉代耕作过程中曾多次强调:“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9]土壤经过“春”,“夏至”,“夏至后九十日”的三次复解过程,达到良好的温度及通气状况。不仅如此,汉代还以“春候地气始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土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9]来判断适耕的时节。
2.2 土壤水分及养分的调节
土壤水分与土壤空气一同存在于土壤孔隙当中,水分含量多少及存在形式对土壤形成发育、肥力高低、自净能力都有重要影响。土壤水分不仅能够直接供给作物生长,同时随着土壤水分的不断运动,土壤有机质和无机质才能在土壤剖面中不断迁移转化,被植物吸收利用。关中平原属旱作农业区,水分在农业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提高与保持土壤水分含量也是古代农业生产实践中经验总结最为丰富的。在难以实施灌溉的黄土台塬上,充分利用天然降水是土壤获取水分的唯一方式,因此,耕地的时间往往以伴随雨雪来时及时耕作为宜,“天有小雨复耕和之”,“有雨泽,耕重蔺之”,“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这些措施旨在降水少的季节,及时耕地将降水迅速导流收集于土壤内部,不至于形成地表径流而无法利用。当天旱无雨泽时,露水也被提倡充分利用,“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渍麦种以酢浆并蚕矢,夜半渍,向晨速投之,令与白露俱下”[9]。土壤水分收集后,减少蒸发也是提高土壤含水量的重要步骤。“蔺”,“摩”的耕作环节就有效地防止了土壤深层水分的蒸发,“耕重蔺之”,“麦田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当有雨时节,适时耕作,使雨水迅速入渗,掩入地下,同时将大土块摩碎摩平,覆于上部,有效起到“保泽”作用。
可见,关中平原汉代十分重视天然降水的利用,如果利用不好,土壤易枯燥板结,起到“伤田”的效果。秋天无雨时节耕田,“绝土气,土坚垎”,此田称为“腊田”;至盛冬时节耕田,则“泄阴气,土枯燥”,此田称为“脯田”。这两种田均是在少雨季节耕作,结果“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之”[9]。这些耕田原则均是通过充分提高天然降水的利用率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壤水分,这是汉代所采取的最基本的土壤保水措施。在接近水源地的条件下,灌溉则是更为直接有效的提高土壤含水量的方式。但受水源及地形所限,关中平原大面积的农田并无灌溉之利,仅“区种之田”,才能“天旱常溉之,一亩常收百斛”。受技术所限,当时的灌溉用水多采用流水灌溉,如“种芋,宜择肥缓土近水处……旱则浇之”;种麻时,“天旱,以流水浇之,树五升;无流水,曝井水,杀其寒气以浇之”[9],这里的流水指引河水或湖水灌溉,应当均在低平的河谷平原区,高地无流水时,则依靠井水灌溉。但文献记载反映仅在种芋、种麻或“区种之田”时述及农业灌溉,流水或井水灌溉可能仅在颇受重视的作物种植时才被采用。
随着大型水利设施的兴修,引水灌溉成为迅速提高土壤含水量及改良土壤的有效方式。郑国渠于始皇元年(前246年)开凿,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郑国渠干渠分布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最高线上,干渠自西向东,利用了关中地形的自然坡降,自流引水灌溉,从而获得尽可能大的灌溉面积。这不仅解决了关中平原旱地土壤缺水的问题,同时“用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5],1408页)。郑国渠渠道以南地势低洼,原为泾渭清浊洛诸水汇集区域,古时曾是面积广大的湖泊沼泽之地[14]。在这些地区,由于土壤排水不畅,形成“泻卤之地”,不利于农作物生长。郑国渠建成后,通过浑水灌溉淤高地面,降低地下水位,冲洗土壤中多余的盐碱成分,这种高泥沙含量的河水起到了对盐碱土壤的淤积压盐作用。太始二年(前95年),白公在郑国渠以南修建了白渠,渠成后,关中泾阳、三原、高陵一带则受益于“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12],1685页)。郑国渠和白渠引水均来自泾水,泾水发源于六盘山东麓,流域内除少量石质山地外,大部分流经厚层黄土区,流域内被侵蚀的表土层含有大量的腐殖质。由此看来,关中东部地区的引河灌溉除增加土壤含水量外,对土壤的增肥及改良作用则更为显著,这为后来关中东部成为京师的主要粮食供给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主要来自于土壤,随着作物的收获,土壤肥力会显著降低,及时补充土壤养分是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保障。在商代,我国已出现对土壤进行施肥的萌芽。至周代还专门有“草人”一职,“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15]”。郑玄注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胜之术也。以物地,占其形色,为之种[16]。”“土化之法”为使土壤肥美,因此,“草人”是专管土壤施肥及肥料的官职。古代最原始的施肥方式就是将枯草直接掩入地下或焚烧荒草后将草木灰作为肥料。因此,古时“草人”一职的名称也应与此有关。至汉代,施肥、积肥技术与方法日渐成熟,但当时的肥源以人畜粪便及蚕矢为主。“蚕矢”及“溷中熟粪”是《氾胜之书》中所载的两种主要肥源。《释名·释宫室》解释:“厕或曰溷,言溷浊也。”《汉书·燕刺王刘旦传》记:“厕中群豕出”,注谓“厕,养豕圂也”。同时,“厕”也是人们便溺之地。汉代民居中,很多厕所往往是和猪圈相连,猪圈厕就是汉代极具特色的建筑形式[17]。此种建筑形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保证人粪、猪粪的集中收积和使用。
尽管汉代已注重肥源的收集,但也难满足所有农田的肥粪需要。因此,作“区田”时更注重“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氾胜之书》中介绍区田法时,将区田又分为上、中、下农夫区,在上农夫区,“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而在中农夫区和下农夫区的种植中均未提及施肥的环节。并且在禾、黍、麦、稻、稗等大田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也未提及施肥环节,而在区种大豆时提到:“其坎成,取美粪一升,合坎中土搅和,以内坎中……一亩用种二升,用粪十二石八斗”;种枲,“布粪田”;种麻,“树高一尺,以蚕矢粪之,树三升;无蚕矢,以溷中熟粪粪之亦善,树一升”;种瓜,“一科用一石粪,粪与土相合和,令相半”;种瓠,“蚕矢一斗,与土粪合”;种芋,“取区上湿土与粪和之,内区中萁上,令厚尺二寸”[9]。可见,汉代并非所有农作物种植都有肥源保障,更多的土壤仍需休耕或轮作等环节完成肥力的调节与恢复,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对于施肥的方法,多次提到将粪或蚕矢与土相拌,共同施入农田。可见,施用土粪在关中平原自秦汉时期已经相当普遍。直至现代,关中平原农村依然沿袭着“以土和粪”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对塿土的自然土层与人为堆垫层叠加结构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结语
历史时期,关中平原一直是我国典型的农耕区,悠久的农业耕种历史为人们提供衣食之源的同时,也使得地表土壤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中平原现代地表覆盖的塿土是一种优良的农耕土壤资源,正是长期的耕作活动改善了原有的农耕土壤环境。研究表明,关中平原大面积农业开垦之前的土壤可耕性远不如现代地表,古时土质过硬的“垆土”和土质过轻的“靹土”及“沮洳之地”曾广泛覆盖于关中平原,均不利于农业生产。秦汉时期,劳动人民正是通过一系列治土、治田过程改善这一土壤环境,始终贯穿于生产过程的“趣时”、“和土”、“务粪泽”的耕田原则是改良土壤、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有效方式,也是古代土壤耕作层形成初期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以土和粪”的施肥方式自秦汉时期已广为应用,这是导致塿土剖面人为堆垫层持续堆积增厚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耕作制度的变化,耕作方式的进一步优化必然促进了地表土壤环境的人为化趋势,这也是研究历史时期土壤环境变化应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 张海芝,杨首乐,马威,等.中国古代土壤耕作理论和技术的历史演进[J].土壤通报,2006,37(5)∶994~998.
2 王在德,王爱民.中国旱地农业耕作技术传统研究[J].古今农业,1993,(2):1~9.
3 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与耕作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08.
6 赵景波.淀积理论与黄土高原环境演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5~7.
7 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的气候与环境[J].中国科学(B),1993,23(8):865~872.
8 赵景波.关中地区全新世大暖期的土壤与气候变迁[J].地理科学,2003,23(5):554~559.
9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0 王祯.东鲁王氏农书[M].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8.
11 吕不韦.吕氏春秋[M].高诱,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334.
1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85.
13 李天杰,赵烨,张科利,等.土壤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7.
14 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20.
15 周礼[M].崔记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5.
16 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4.
17 彭建.浅谈汉代猪圈厕[J].武汉文博,2010,(2):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