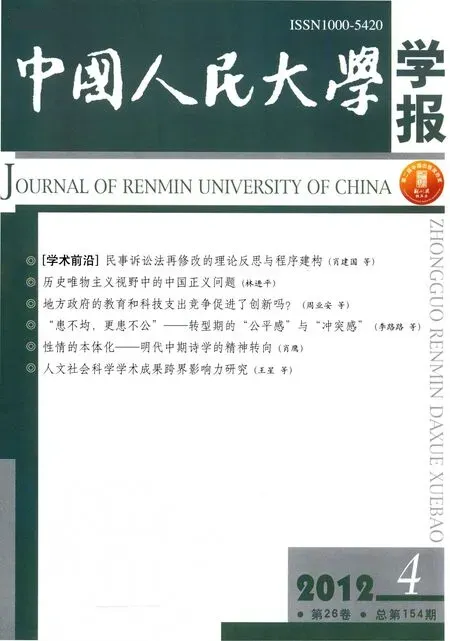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洪迎华 尚永亮
一
明清之前,除苏轼 《书黄子思诗集后》提出“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1](P2124)的观点,从美学风格层面讨论韦应物、柳宗元清淡诗风及其对陶诗的效法,并由此极大地影响了此后韦、柳诗的接受主流外,还有少数诗家从诗歌体裁层面阐发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价值和意义。如金代元好问 《别李周卿》说:“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东坡诗雅引》又云:“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馀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2]元代方回《送俞唯道序予》则谓: “五言古,陶渊明为根柢,三谢尚不满人意。韦、柳善学陶者也。”[3]可见,他们都认识到韦、柳对五言古诗的坚守和传承,其中元好问还从古今流变史的角度肯定了韦、柳五古的成就和地位。这些观点直接为明清读者所继承,并在新的诗学思潮中找到了适宜的滋生土壤,形成盛极一时的围绕韦、柳五古而展开的辨体讨论。
所谓辨体,即 “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在对不同体制诗歌探源溯流的过程中,“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高棅 《唐诗品汇序》),其行为指向是确认传统和正宗。若处理不当,则易导致崇正抑变的思想倾向和 “规古近雅,创格易鄙”(陈子龙 《青阳何生诗稿序》)的价值判断。这种观念在南宋严羽那里就已产生,其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4](P252)后来高棅在 “辨尽诸家,剖析毫芒”以确立盛唐正宗地位的诗学实践中对此予以吸收和发展。至格调说形成,“辨体别流”遂成为格调派诗学理论的核心,并对其他诗学流派和评家思想产生持续影响。
正是在这种辨体意识和推崇雅正的风尚下,韦、柳五古受到了明清诗家的充分肯定。试举以下几则评论为例:
五言古诗,实继国风雅颂之后……迨李杜复出,时道大兴,而作者日盛矣。然于其间求夫音节雅畅,辞意浑融,足以继绝响而闯渊明之阃域者,唯韦应物、柳子厚为然尔。自时厥后,日以律法相高,议论相尚,而诗道日晦焉。(吴讷:《晦庵诗钞序》)[5]
唐诗固称极盛,而五言正脉,亦无多传,陈拾遗、张曲江、李、杜、韦、柳而外,惟储、孟……尚不替前人轨则。(乔亿:《剑溪说诗又编》)[6](P1116)
汉、魏、六朝诸人而后,能嗣响古诗正音者,韦、柳也,非仅贞元、元和间推独步矣。(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 “论五言古诗”)[7](P699)
盖终唐之世,称大家者,以李、杜、韩三家为宗。古诗之得正音者,陈、张、韦、柳四家为宗,而元结、沈千运诸人为辅。(鲁九皋:《诗学源流考》)[8](P1356)
在传统诗学观念中,古诗贵质朴。所谓 “古诗正音”、“五言正脉”或 “诗道”,即指诗歌格律化之前自汉魏以来的古朴诗风,其中以汉魏古诗和陶诗为最高代表。在古代文人的经典意识和崇尚风雅的文化心理中,汉魏古诗作为诗歌史上最早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典范地位自陈子昂倡导复古、追求 “兴寄”“风骨”即已确立,而陶渊明继汉魏之后,将古朴诗风提升到更纯熟的境地,成功开辟了平淡自然这一新的美学境界,以古诗艺术的集大成者受到后人的景仰。如贺贻孙 《诗筏》云:“论者为五言诗平远一派,自苏、李、《十九首》后,当推陶彭泽为传灯之祖。”[9](P159)
明清时期,虽然各位诗家在思想倾向上有复古和求变的差异,理论建树上有主格调、重性情和尚神韵等不同,诗歌批评上也有唐、宋诗的轩轾和争议,但在接受古诗时,基本都认同汉魏及陶诗的高格和雅正。冯班云:“古诗法汉魏,近体学开元、天宝,譬如儒者愿学周、孔,有志者谅当如此矣。”[10]贺贻孙 《诗筏》云: “储、王诸人学苏、李、《十九首》,亦学彭泽,彼皆有意为诗。有意学古诗者,名士之根尚在,诗人之意未忘。”[11](P159)将汉魏作为古体代表,并将学古这一行为与诗人名士之品节挂钩,可见时风雅尚。
进一步看,韦、柳在这一五言正脉的传续上又有其特殊的位置。从前引元好问 “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的说法可知,他将汉魏、晋宋、唐代作为三个重要阶段,以代表作品和作家简要勾勒出了五言古诗发展的脉络,而把韦、柳当做五言古诗和风雅传统的终结者。承接元氏观点,明清诗家在古诗流变中赞许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将韦、柳视作殿后的两位,由此形成此一时期较为一致的接受态度。究其缘由,恐怕在于韦应物、柳宗元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正当诗史新变和转关的特殊时段。清人叶燮 《百家唐诗序》认为:“迨至贞元、元和之间……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 ‘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 ‘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 ‘中’者也”[12](P81-82),便从宏观视野阐明了此一时段的重要性。
当然,对于唐代得古诗正音的诗人,各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于古诗独尚陶之清澹和技艺,以至在唐代惟推韦、柳二人;但更多人将古质与淡远并视为古诗风韵,所以陈子昂、张九龄、李太白等人也被纳入古诗正音的系统中。清代王士祯即谓:“夫古诗,难言也。《诗三百》篇中 ‘何不日鼓瑟’, ‘谁谓雀无角’, ‘老马反为驹’之类,始为五言权舆。至苏李、《十九首》,体制大备……唐则陈拾遗、李翰林、韦左司、柳柳州,独称复古,少陵以下又其变也。”[13](P2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士祯手编了一部 《五言古诗选》,选录汉魏六朝至唐代的五言古诗。其中唐代五古也正是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柳五家入选。他在 《五言诗凡例》中称:“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 《杂诗》。贞元、元和间,韦苏州古澹,柳柳州峻洁。二公于唐音之中,超然复古,非可以风会论者。今辄取五家之作,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14]由此而言,陈、张、李、韦、柳五家便因其对汉魏风骨和陶诗风神的传承,而受到王士祯的特别青睐。
二
在明清诗家看来,韦、柳既能 “嗣响古诗正音”,同时也有 “变”的一面,只不过韦、柳能变而不失其正,所以仍为典范。王士祯的友人姜宸英在 《王阮亭五七言诗选序》中评论王氏诗学观念云: “于唐仅得五人,曰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盖以齐、梁、陈、隋虽远于古,尚不失为古诗之馀派;唐贤风气自为畛域,成其为唐人之诗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诗于唐诗之中,则以其类合之,明其变而不失于古云尔。”[15]古典诗学中,古体和近体有严格区分,李东阳 《麓堂诗话》即谓:“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16](P1369)认为古诗之所以为古,就在于它的自然和质朴,于是坚决排斥古诗中的律化和近体倾向。很多读者通常对古体诗中的雕琢颇有微词,如前引元好问所谓:“自馀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方回在 《婺源黄山中吟卷序》中亦云:“唐诗承陈隋流□之馀,沈、宋始概括为律体,而古体自是几废。然陈子昂、元次山、韦应物及李、杜、韩、柳诸公,追刘、陶、曹、谢与之伍,亦未尝尽废也。”[17]盖因传统诗学中历来存在 “体”的界定,故至明清诗家,沿波起澜,要求辨体的声浪日盛。但在诗人的创作实践中,古、近两体并非此疆彼域,往往出现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迹象。特别是在近体完全成熟且蔚为大观的唐代,身负才力的唐人往往诸体皆擅,一方面着力于开拓近体诗,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古体诗。在诸体意识杂糅、且近体成为主流并不断求新求精的创作环境下,唐代五古自然免不了“涉律”而打上时代烙印,因此有了唐代五古和传统五古之区分,韦、柳等人的古诗创作也就具有了双面性。一方面,因其古诗创作超越时代风气、力追古人,其五古成为传统古诗在唐世的余响,不失为古诗 “正”脉;另一方面,他们又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其创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古的一部分,具备了 “变”的因素。
面对这一双重特性,大多数明清诗家将眼光集中到韦、柳创作中超然复古的一面。他们认为,韦、柳等人虽不及汉魏及渊明古诗,但在其所处时代亦属上品。《诗友诗传录》记王士祯言:“唐五言古固多妙绪,较诸 《十九首》、陈思、陶、谢,自 然 区 别。”[18](P130)贺 贻 孙 《诗 筏》 亦 谓:“储、王、孟、刘、柳、韦五言古诗,淡隽处皆从 《十九首》中出,然其不及 《十九首》,政在于此。”[19](P138)由于时移事异,往古已不可尽追,所以,韦、柳五言不仅被视为古诗正格而赢得普遍称许,而且还被很多诗家作为创作中学习和取法的对象。如李重华 《贞一斋诗说》指出:“唐代五古,则自陈伯玉、张曲江至韦、柳俱可学,自后亦不必学。”[20](P924)朱庭珍 《筱园诗话》卷一认为:“盖五古须法汉、魏及阮步兵、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李、杜诸公,而参以太冲、宣城及王、孟、韦、柳四家,则高古清远,雄厚沉郁,均造其极,正变备于是矣。”[21](P2334)田雯也说:“余尝谓学诗者宜分体取法乎前人。五言古体必根柢于汉魏,下及鲍、谢、韦、柳也。”[2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外,有些诗论家对心目中的最高典范怀着一种高山仰止的心理,将价值评判与创作实践分别开来,如王士祯 《五言诗凡例》说:“《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后之作者顾求之针缕襞绩之间,非愚则妄。”[23]认为陶诗 “纯任真率,自抒胸臆,亦不易学”。这样,韦、柳作为古诗传统的继承者反而更受到诗家的重视,被当做创作中必需循法的诗人。
将韦、柳视为古诗创作的效法对象,是明至清不少诗人的一致看法。李东阳 《麓堂诗话》即谓: “惟谓学陶者,须自韦、柳而入,乃为正耳。”[24](P1379)王 行 《柔 立 斋 集 序》 云 :“朱 子 教人,为诗须先学韦、柳。韦、柳固不足以尽诗之妙,然由是而往,虽求至于三百十一篇,亦犹洒扫应对,求造夫圣贤之域。虽地位有高卑,道里有远近,往之则至,终无他岐之惑矣。”[25]薛雪《一瓢诗话》云:“犹夫学陶诗,须自韦、柳入。”[26](P706)在他们眼里,学习韦、柳是追陶和尚古的门径,“自韦、柳入”,既有迹可寻,又不失为正道。清人厉志在 《白华山人诗说》卷一中自述其学诗经历云:“予初游郡中,得遇徐敬夫先生,谓余近体如屈翁山,古诗如吴渊颖,但须取柳柳州诗尽读之。予因尽读柳诗,并上追陶公,旁及王、韦,自觉稍有进益。”[27](P2280)明 清诗家对韦、柳的认识,于此可见一斑。
三
在以上推许韦、柳 “正音”的接受态度中,虽对其 “变”的一面表现出宽容和默许,但着眼点和批评内容还是其 “正”的层面,由此充分肯定其古诗地位。明清时期,也有论者明言其变,从 “变”的层面予以评说和肯定。如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即谓:
元和诸公,议论痛快,以文为诗,故为大变。子厚五言古,如 《掩役夫骸》、《咏三良》、《咏荆轲》,亦渐涉议论矣。至如 《荆轲》结语云:“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即 《桐叶封弟辩》云: “或曰封唐,史佚成之”之意,但语较元和终则温润耳,故不入大变也。[28](P245)
又说:
唐人五言古,气象宏远,惟韦应物、柳子厚,其源出于渊明,以萧散冲淡为主。然要其归,乃唐体之小偏,亦犹孔门视伯夷也。[29](P239)
从思想源流看,许学夷仍属格调一派,论诗注重析其源流,考其正变,但其评量眼光多着眼于 “变”,并重新认识变格诗歌的价值和地位,由此颇具新意。在他看来,“变”有 “大变”及“正变”之分,“古诗若元和诸子,则万怪千奇,其派各出,而不与李、杜、高、岑诸子同源,故为大变”,柳子厚五言古虽亦涉变,但因源出渊明,故仍为 “唐体之小偏”,即 “正变”之属。他对 “正变”和 “大变”的看法分别是: “其正变也,如堂阶之有阶级,自上而下,级级相对,而实非有意为之。”[30](P306)而 “大变”则因诗人才具和时风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一味求变而难以收束,如 “白乐天五言古,其源出于渊明,但以其才大而限于时,故终成大变”[31](P271)。据此可知,在许学夷那里,韦、柳五古虽仍属于 “正音”中的 “变”者,但已没有前面论者语气中的古诗嗣响或者末响色彩。相反,因为他并不否认“变”的合理性,所以韦、柳古诗也就没有因其“变”而黯然失色。他说:“《三百篇》而下,惟汉魏古诗、盛唐律诗、李杜古诗歌行,各造其极;次则渊明、元结、韦、柳、韩、白诸公,各有所至。”[32](P317)又说: “韦、柳五言古,犹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学韦、柳诗,须先养其性气,倘峥嵘之气未化,豪荡之性未除,非但不能学,且不能读。”[33](P240)与前面把学韦、柳当做入古门径泛泛而论者相比,许学夷的评论显然要深入一步。
但是,着眼于韦、柳之 “变”时,并不是所有的诗家都认同其价值和地位。相反,有的诗家不能容忍古诗中的变格,以至于认为唐代没有真正的五言古诗,唐古俱不可学。这种观念主要以明代的七子派为代表,如何景明 《海叟集序》云: “盖诗虽盛称于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34]李攀龙 《选唐诗序》云:“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35]在对整个唐代五古都给予否定和贬斥的态度下,韦、柳五古自然得不到他们的认可,所以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四云:“韦左司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至于拟古,如‘无事此离别,不如今生死’语,使枚、李诸公见之,不作呕耶?此不敢与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谢,岂知诗者。柳州刻削虽工,去之稍远,近体卑凡,尤不足道。”[36](P1011)其态度如此偏激,则主要源于格调派论者在辨体过程中对纯正体格的过分讲究。前七子派王廷相 《刘梅国诗集序》曾说:“君子之言曰:诗贵辨体。效风、雅,类风、雅;效 《离骚》、 《十九首》,类 《离骚》、《十九首》;效诸子,类诸子;无爽也,始可与言诗矣。”[37]后七子派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艺圃撷余》亦谓:“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38](P775)辨体的意义就在于对古诗纯正体格的掌握,避免在效仿的过程中混入旁体或杂音,也即学古须尺尺寸寸之,以求达到完全逼真的境地。这种对体格纯之又纯的追求,必然导致抹杀一切创新和变异性因素。韦、柳等唐人五古完全被排斥在他们眼中的古诗之外也就是必然的了。
受七子派影响甚深的胡应麟对唐古的接受态度虽比其前辈温和,但在 “变”的价值评判上还是以否定为主。胡应麟曾探讨唐代五言古诗的源流正变,云:“陶,阮之变而淡也,唐古之滥觞也”[39](P29),具体到唐代各位作家,其传承又有不同:“四杰,梁、陈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鲍也;曲江、鹿门、右丞、常尉、昌龄、光羲、宗元、应物,陶也。”[40](P35)但他持 “格以代降”的诗学观念,认为:“楚一变而为 《骚》,汉再变而为 《选》,唐三变而为律,体格日卑。”[41](P3)既然格以时变、格以代降,那么,不仅汉魏诗高于唐诗,就是齐梁诗在品格上也高于唐诗。所以他说:
韦左司大是六朝余韵,宋人目为流丽者得之。仪曹清峭有余,闲婉全乏,自是唐人古体。大苏谓胜韦,非也。[42](P36)
多谓唐无五言古。笃而论之,才非魏、晋之下,而调杂梁、陈之际,截长絜短,盖宋、齐之政耳。如……韦左司 《郡斋》,柳仪曹 《南涧》……皆六朝之妙诣,两汉之余波也。[43](P37-38)
虽然也一定程度地承认韦、柳诗之 “妙诣”,但此 “妙诣”说到底不过 “宋齐之政耳”;柳宗元是 “唐人古体”,韦应物乃 “六朝余韵”,柳自然不能胜于韦。应该看到,历七子派和性灵派的论争之后,胡应麟在思想中力求格调和性情的调和,他不仅主格调,亦论诗歌的兴象风神。所以从风格的多样性和美的角度,胡氏曾大力肯定韦、柳等人诗歌的艺术价值,发出 “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之论,也曾以 “大家材具”[44](P186-187)对柳宗元等元和诗人进行称赞。 但论及诗歌品格,则又回到了七子派的立场,以伸正绌变的态度贬低唐诗和唐古。所以他对韦、柳古诗的些许肯定,或者认为韦胜于柳,都是建立在六朝古诗比唐古格高一筹的认识之上的。
由上可见,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柳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评论者的批评视野中得以凸显,但在具体的接受内容上则存在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究其缘由,一方面乃因韦、柳生活于位处 “古今百代之中”的贞元、元和之际,近体诗的兴盛与部分诗人的慕古意识杂糅并存,使其创作兼具五言古诗“正脉”及 “变格”的多重面相;另一方面则缘于明清各家互有差异的 “诗体正变”观,导致相关评价在 “正”“变”天平上的不同倾斜。似可认为,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或 “正”或 “变”的种种评说和争议,既是明清诗家诗学价值观的一个缩影,也为传统的韦、柳接受融入了新的气息,既丰富了 “韦柳体”的诗学内涵,也细化了对五言古诗特别是韦、柳五古的历史认知。在韦、柳诗歌接受史上,这是一个转折阶段,其所内涵的诗学意义还具有广泛的开掘空间。
[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卷三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3][17]方回:《桐江集》,卷一,宛委别藏本。
[4]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5]程敏政辑:《明文衡》,卷四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6][7][8][9][11][19][20][21][27]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冯班:《钝吟杂录》,卷三,清借月山房汇钞本。
[12]叶燮:《己畦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四四),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4][23]王士祯:《带经堂集》,卷五二,清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
[15]姜宸英:《湛园集》,卷一,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16][24][36]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26]郭绍虞编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2]田雯:《古欢堂集》,卷二五,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25]王行:《半轩集》,卷五,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28][29][30][31][32][33]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4]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四,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35]李攀龙:《古今诗删》,卷十,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37]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二,明嘉靖刻清顺治十二年修补本。
[38]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39][40][41][42][43][44]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