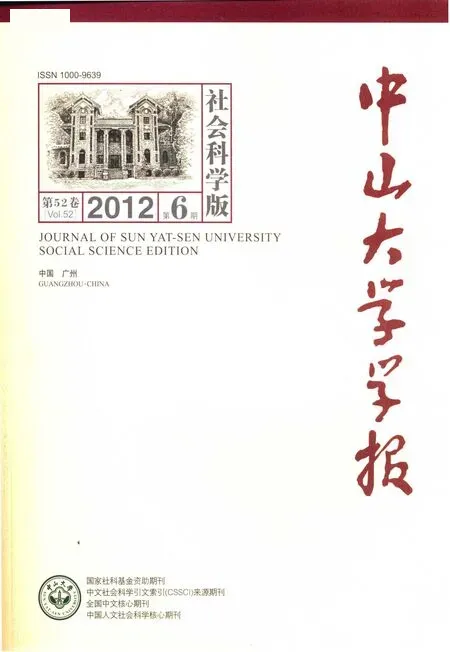人间佛教之源与脉*——从祖师禅到生活禅
张 平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
——从祖师禅到生活禅
张 平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人间佛教;祖师禅;人生佛教;生活禅
人间佛教,作为专称,确指20世纪初滥觞于太虚法师(1890—1947)孤明独发的弘教行解,而澎湃于20世纪中后期台海两地的佛教复兴运动,以及由之生成的佛教发展之新思潮和新的理论形态;但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则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或切实而言中国禅宗——的本质特征。正如星云大和尚所言:“人间佛教不是太虚大师的创说,而是佛陀的本怀;人间佛教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复兴佛法的根本。”①星云:《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氏著:《往事百语②》,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年,第70页。祖师禅将以儒道为表征的中土文化的精神土壤,嫁接印度大乘佛教之神髓,信持不二中道法则,标榜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一举打通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开出中国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起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生遭20世纪初叶的太虚大德,悯世忧道,意欲以正法解民族国家之危局,亟亟于阐发佛陀人间关怀之本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表彰“人成即佛成”的“今菩萨行”,揭橥人间佛教之现代新模式,点燃了引领中国佛教迈向复兴之蜡炬。当前,方兴未艾的生活禅,洞烛现代人新的生活样态所孳生的新的精神祈愿,赓续祖师禅和人间佛教之法脉,通过禅门,将佛法贯彻落实于大众当下日常生活的具体而微的方方面面,把佛法与生活打成一片,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祖师禅、人生佛教、生活禅三者,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它们各自在其历史境遇中,与时相谐,契理契机,紧扣时代和当下人生的问题,重释佛法,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成就了反映时代特征和要求的佛法济世度人的新范式,使中国佛教赋有了新生面。
寻绎人间佛教的起源和流脉,梳理人间佛教推展的历史轨迹,不难发见:其所以能成功地弘播流布,赢得缁素两界的广泛认同和奉持,除却其契理契机的根本品性使然外,其开展过程中,应世应时,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亦命运攸关。正由于此,人间佛教方得以逗机引教、不断创新,以新的法门为自身开辟道路,拓展觉世普济的新进境。
一、六祖革命:人间佛教的源头活水
尽管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度化众生在人间,一切都以人间为主,因而其教法赋有浓郁的人间性品格;尽管大乘不二法门使佛缘不离世间具足法理根据,但出离世间、了脱生死之解脱义,当是佛陀创教设法、弘化人间之根本价值祈愿与诉求,更是佛教之为佛教乃至佛教之为宗教之核心义理和究竟的所在。作为佛教中国化之大成的祖师禅,以中土文化——主要表现为以儒家心性论——接续大乘佛教,自然未脱其解脱观之核心义理。或可说,正由于对佛教解脱义的承继乃使祖师禅成为印度佛教的中国法嗣,也正由于禅宗六祖对佛教解脱思想所行的儒家心性论的根本性改造而成就了其佛教史上的革命壮举,开启了中土人间佛教之历史行程。
因此,有必要论析祖师禅解脱论的义蕴、特征,以追究何以祖师禅之为人间佛教的源头活水。祖师禅解脱论的思想内容概而言之有三:其一,心性观,旨在揭示觉悟解脱亦即成佛的内在可能性和根据;其二,功夫观,旨在阐明修行而解脱的方法和路径;其三,境界观,旨在论述觉悟解脱的止境。由内在根据经方法路径而终极目的,祖师禅解脱论形成了完整而自洽的逻辑体系。其中贯彻的恰是人间佛教的思想诉求,所体现的恰是人间佛教的精神特征。
(一)“自性是佛”的心性论是众生成佛的根本依凭
当年禅宗六祖求法五祖弘忍(601—674),有两段经历使其佛性论之深蕴昭然若揭。一是,六祖初拜五祖时,弘忍劈头叱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猲獠,若为堪作佛!”慧能(638—713)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①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8,29,24,31,26页。二是,慧能道出那惊撼众僧的得法偈后,弘忍暗约其三更来会,密示心要。当听闻《金刚经》所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时,慧能廓然大悟,慨然叹曰: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②《六祖法宝坛经》,台湾:毘卢出版社,2011年,第9,15页。
这两次经历表征了六祖之于佛性的深切体认与悟识,主要有三层意涵:首先,人人具足佛性,生而平等,皆可成佛,“猲獠”与佛圣并无差别,而且佛即自性。“佛性”的本质是觉悟、智慧,所谓“佛者,觉也”③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8,29,24,31,26页。。在六祖看来,“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④《六祖法宝坛经》,台湾:毘卢出版社,2011年,第9,15页。,世人皆可由智慧觉悟成佛;而世间所以有愚人智人之别,不在佛性有无,端在自性(心)迷悟。在此,六祖不仅阐释了众生本性平等,皆具成佛之因性,而更重要的是将此因性归结到现实人性(心)之自悟之上,其心性论的人间性和现实性特征已见端倪。
其次,自性本来清净,只因烦恼尘垢掩覆而不得朗现,众生无以觉入佛境。六祖喻云:
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⑤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8,29,24,31,26页。慧能并不以为烦恼妄念是外在于心性之物,毋宁说慧觉本性与烦恼妄念相即不离,共系一心,“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⑥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8,29,24,31,26页。,“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⑦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8,29,24,31,26页。。慧觉本性即在烦恼妄念之中,净即在染之中;烦恼是慧觉本性自身的遮蔽,尘染是清净自身的陷溺。是故,惟经由俗世人伦日用中的修行开发自性本在之般若智慧,方能转烦恼为菩提,濯尘染而现清净,最终成就佛果。
再次,自性含生万法。六祖阐释清净自性时,称其“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但此虚空之性正因其空而涵容万法,“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①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第30,24,43—44,22,37,19 页。。这即是说,万法在自性,而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因此,不仅涵容万法,且世间万法之种种,也不外乎自性起用的结果,“思惟一切恶事,即行于恶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②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第30,24,43—44,22,37,19 页。。一切全系于如何起用自性(心)。宗宝本《六祖法宝坛经》亦有言: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③《六祖法宝坛经》,第33,18—19,38页。
在六祖那里,要紧的是心性。只要心性清净朗明,不执不迷,则人伦日用与禅修并未二致,却反是心性安放的所在。于是,生活与修行,世间与出世间,此岸与彼岸,浊世与净土,浑然无间,圆融无碍。六祖如是说:
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流通,即名为彼岸。④《六祖法宝坛经》,第33,18—19,38页。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但无不净,西方此去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⑤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第30,24,43—44,22,37,19 页。
(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禅修觉悟的至要方法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出自《金刚经》,当年六祖甫一闻,便“言下大悟”,足见其法力之威厉深雄。可以说,此一语道出了禅要根本,更深契六祖之心解,构筑了《坛经》“无念”、“无相”、“无住”的法理础石,成为禅宗至要的修行方法。
“自性是佛”、“人性本净”明确众生各各具足成佛的内在可能性、因性,但若要这可能性化为现实,最终圆证佛果,则必要有深切的修行工夫以明心见性。既然“万法尽是自性”,自性(心)决定一切,则众生各各直须在自性上做工夫,“直指本心”。因此六祖强调“自修自度”方能证入悟境。所谓悟,正在于“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⑥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第30,24,43—44,22,37,19 页。,“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⑦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第30,24,43—44,22,37,19 页。。这可说是禅宗修行的基本立足点和着力点。如何具体开展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深中肯綮,既提挈禅宗修行之纲领,又落实了禅宗修行之方法。“无所住”即是无论何境皆无所挂碍,不著名相,了无妄念,纤尘不染;“生其心”是见性,即见那本来清净之自心。众生各各心念处处不滞不碍,不执不妄,不染不垢,清净自心自然朗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意旨与慧能“明心见性”之义蕴若合符契,故而,在此基础之上,《坛经》进一步提出禅修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⑧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第30,24,43—44,22,37,19 页。的“三无”说。
所谓“无相”,即“于相而离相”,若能离一切名相,清净性体自然显现;所谓“无念”,即“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妄念;所谓“无住”,即是于一切时中一切法上念念不住。由此可见,六祖之“无念”、“无相”并非绝除一切“念”、“相”,不承认任何“念”、“相”的存在;其要表达的真义不过是,思维主体在面对外在事物时,不可能不思不念,不可能罔顾法相之在,而是须不起虚妄分别的念想,不执著对象的相对相、差别相,使自性时时与真如相冥符而生正念,是谓“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⑨《六祖法宝坛经》,第33,18—19,38页。。六祖关于禅修“三无”的阐释,充分体现了大乘不二中道法门的善解妙用。
基于这样的主张,六祖对传统的避处荒野、安坐树下的“空心静坐”、“百物不思”的禅修方式提出批评,认为“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是著了法相,不识人念念不住,滞碍了道之“流通”,陷人于无情,令其形同木石,因而成为“障道因缘”;“看心看净”,则不识净无形相,而著了净相,致本自清净之心反被净相所缚,亦是“障道因缘”,两者均不是证入智慧解脱的正定。随后,六祖有针对性地开示其“一行三昧”的禅法:
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①《六祖法宝坛经》,第35,27,22,14,45,23 页。
六祖强调,修行时,心须无所执,无所住,在当下的行住坐卧等等日常生活活动中一任那清净自性随缘任化,自然流通。但行直心,时时可以修行;具足直心,处处即见净土。这分明是将修行融于生活之中,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于是,佛法修行与日用生活打成一片,当下的行住坐卧中方可证成解脱的佛果。基于此,六祖直言: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②《六祖法宝坛经》,第35,27,22,14,45,23 页。
(三)“顿见真如本性”:修行解脱之止境
禅修的究极目的在证成佛果而得解脱;而在六祖那里,成佛解脱既以自性菩提的顿悟为不二之梁津,又以顿悟为内蕴并由之而体现(“佛者,觉也”)。因此,顿悟是方法与目的的统一,功夫与境界的统一。而作为禅修的境界,顿悟表现为内心世界刹那间的质的升华,是精神的瞬间超脱。
佛义所谓“觉悟”,即证得无上菩提,由凡夫而佛,由烦恼而解脱。而在六祖,这只在转念一瞬便可达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他前承道生,名之为“顿悟”,尝自谓“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③《六祖法宝坛经》,第35,27,22,14,45,23 页。。何以一念悟便可立登佛境,得大解脱?盖因真如本性即是自心,本为空寂性体,它涵摄万法、包容一切,是无限性的整体之在,因而绝对待而无分别,正如六祖所示“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④《六祖法宝坛经》,第35,27,22,14,45,23 页。。对之不可取点滴累积、渐次达致之法,即“不由阶渐”,悟则彻悟,不悟则不悟;一旦觉悟,则精神世界慧光普照,通体澄明,愚染尽荡,佛我一如。诚如六祖所言:“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闇,一智能灭万年愚。”⑤杨曾文校写:《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第24页。
这样的顿见真如本性的心灵慧觉体现为两种精神境象,即了无分别、不执不迷,不滞不碍、随缘任化,自然无为的所谓“无心”,以及空寂澄澈,随时放下,洒脱自在的“无所得”。
首先,无心,脱胎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即是“无住生心”,意谓心之不住,指本性上那念念不住之心,不可在任何时候任何外境任何名相上有所住留。因此,无心不是心之死寂或死寂之心,而是不起分别,不起执著,不起计较,在应境待物时无所用心,而随运任化,顺其自然的自由自在的超越之境,也即六祖所揭橥的“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⑥《六祖法宝坛经》,第35,27,22,14,45,23 页。、“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⑦《六祖法宝坛经》,第35,27,22,14,45,23 页。的超脱空明。在六祖看来,生活于尘世,而能识其空性,禅心不染,自性清寂,才是真正的解脱。这一解脱境界观成为禅门宗嗣的传家之宝,并在其修行实践中不断光大;及至以马祖道一(709—788,一说688—763)及其弟子大珠慧海(生卒年代不详)为标帜的洪州禅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马祖道一以“平常心”解“无心”:“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做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做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⑧[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252页。这所谓的“平常心”,就是对于是非、圣凡等等不起分别的众生本来面目的心性,也是顺其自然、不加造作的心理状态。马祖道一认为,只要众生妙悟平常心是道,各自相信自心是佛,而万法唯心,一切所见的诸境名相尽是佛性之变现,处理日常物事即是修习佛法,“若了此意,乃可随时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⑨[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一)》,第375页。。大珠慧海深得乃师心要。一次,有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大珠慧海答:“用功。”曰:“如何用功?”答曰:“饥来吃饭,困来睡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解释道:“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10)[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7页。一问一答揭示了同样的吃饭睡眠、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对常人与悟者所表现的迥异的境界,而所以致此,只在于一念心的有无“须索”、“计较”、分别与执著。前者于生活每每有种种的寄托、期许、计较、取舍乃至想像,为众多的妄念牵挂所羁绊,作茧自缚,难脱尘缘。后者则心念清明,无所住亦无所用,不于诸境生其心,生活中澹然安处于不执不著、不牵不染、无分别、无取舍、无对待的超然空寂之境。
一颗“平常心”,遂将修道与生活、尘世之居与超脱之境圆融一片,浑然一如,六祖“不离世间觉”得以极致的发挥与表达。
其次,无所得,根柢处讲,实即无心;无心更侧重禅修中破外在诸境、名相的妄执,而无所得的主旨则在破禅修中禅法本身的妄执。正是在此意义上,神会称“无所得者,即是真解脱”①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1页。。六祖继承《心经》《金刚经》“无所得”的思想,标举无所得为“最上乘”的佛法。他以为,依坐禅和听闻讲诵而悟道,是他力外修,属小乘之境;经由佛教经书义理而契会佛性、成就佛果,属中乘之境;依其所理解的佛理佛法而实地参修,妙悟禅机,登达佛境,属大乘之境。三境地尽管后者对前者有所增进,但终不是究竟之境。而惟“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②《六祖法宝坛经》,第63,79页。。这一境界要求修习者“无念无修,自性自解”,以顿悟万种佛法均不在自心之外,而是圆满具足于自我一身。无所得所以被六祖奉为最上乘之境,盖因在他那里“一切现成”,清净自性世人本自有之,圆满菩提世人本自具足,既然本来自有,便非由外得来,这即意味着世人并不能由法门持修行而获得任何新东西,而所要做、也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开发自身般若智慧,涤除染垢,呈现自性本心本来面目。因此,他要求修行佛法而不执于法,悟空而不执于空。只有既不恋住“菩提涅槃”,亦不泥守“解脱知见”,才能抖落一切束缚,直下彻悟大道,得真正解脱,脱颖为“立亦得,不立亦得,来去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的“见性之人”③《六祖法宝坛经》,第63,79页。。
由上述祖师禅的解脱论释析,佛教本土化,或者更切实地说,佛教人间化、入世化、生活化的面貌和内蕴判然可见。大乘佛教的玄理奥义化约为人间修行者的实践智慧和行动南针,禅修道场从山间树下、深殿幽堂移至井边灶台,饥食寒衣、行住坐卧无非修行打禅,彼岸佛界、西方净土不外心净行善,昔日幽居林壑、飘然世外、绝情断欲、百物不思、寂静冷峻的觉者在此化为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恩孝父母、敦睦友邻、随缘任化、洒脱自在而又笑容可掬的善者。于是,佛的信仰转化为人的信仰,向佛的修行转化为人格的自我修养,成佛超脱转化为在平常生活中圆成人格善境。六祖经由对印度大乘佛教作儒家心性说的解读,达成传统佛教的创造性改造,实现了中国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蜕变。但也应看到,祖师禅在历史机缘中对传统佛教再解读而形成的一些见地及主张,其应机适变而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与风格,因其畸重畸轻不免为后期禅宗所出现的歧变乃至颓衰埋下伏机。有关于此,笔者会结合以下论析而略有述及。
二、“人成即佛成”: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
虽然六祖革命在义理上打通了大乘佛教与儒家心性论,引出中国佛教人间化的源头活水,人间佛教的合法性由是确立,但在之后的历史实践中,其人间佛教思想并未得以充分展开,遑论深入社会,普及大众,敦化人伦,救度世人,于是出现太虚大师所言之汉传佛教“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现象。汉传佛家陷此历史窘境,究其因由,其一,传统社会统治者筑就儒释道三元共轭的思想意识形态格局,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为儒家所垄断,佛家难以染指,而只能发挥由“治心”而敦化人伦、辅翼世教之作用;其二,如陈兵所言,就禅宗的整体精神而言,慧能虽打破了世间与出世、出家与在家的局限,但偏重心体性的一面、涅槃的一面,而较忽视心性用的一面④陈兵:《佛法在世间:人间佛教与现代社会》,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328页。,加之儒家对其社会功用一面的排斥,以禅宗为骨髓和主流的汉传佛教便更向出世一路用力,形成畸重出世的传统。及至清末,佛教游离于世间更为严重,其时之佛教徒,或静隐山林,或赖佛为生,非但不以深入社会、济度苍生为天职,反而自甘沉溺,结果,社会自社会,佛教自佛教。佛教遂近乎堕落为“重死度鬼”“重视死后胜进”之消极巫教。而同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新的思想学说激活民族的精神创生力,于是,教内外复兴佛教的要求风生水起。当此之际,一代宗师太虚法师应运振起,勇当慧命,遥接祖师禅真脉,秉承大乘法绪,缘机逗教,披蔽启明,掀起一场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运动,揭橥以圆成人格、建设人间净土为主旨,以今菩萨行为要津的人生佛教,赋予人间佛教以现代形态。
在重建中国佛教这一时代课题上,太虚大师凸显出鲜明的主体精神和谨严的治学风格。其思想深广圆融,高屋建瓴,总揽佛学之全体,广纳一切当机之资粮,力戒一宗一派乃至一民族文化之蔽。但同时持守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以及问题的时空规定性,立足于佛教复兴的中国主体性,强调重建中国宗教,一方面须探本于佛之行果、境智、依正、主伴,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非依任何古代宗派或异地教派。太虚本人反复申明自己并非独承某宗某派,虽主张异地学法,但反对“另寻来一种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①《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80,382页。。另一方面,须立足中国佛教传统,“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②《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80,382页。。职是之故,太虚根据其独特的判教方式,撷取汉传佛教的总体特征而得出结论:中国佛教之特质在禅。他说:“现在讲到中国佛学,当然有同于一般佛法的;然所以有中国佛学可讲,即在中国佛学史上有其特殊质素,乃和合一切佛法功用,而成为有特殊面目与系统的中国佛学。其特殊质素为何?则‘禅’是也。”③《太虚大师全书》第2卷,第13,333页。此处所言之禅,并非专指禅宗之禅,而是涵摄禅宗的广义之禅。但太虚也曾径直指出中国佛教之特质就在于禅宗:“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欲构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宝,当于律仪与教理之基础上,以重振禅门宗风为根本。”④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台湾:正闻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太虚的这一判识决定了其对禅宗的态度。虽然在宗教实践中,他并不独承某宗某派,而是八宗兼擅共扬;但之于禅宗,更确切讲,之于祖师禅,却最为钟情、最为激赏,尝言:“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个直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之骨髓。惟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⑤《太虚大师全书》第2卷,第13,333页。对禅宗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太虚于此揭示了禅宗在中国佛学乃至在整个佛学中的历史地位,进而他以为,中国佛教之复兴仍以禅宗复兴为关键,“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⑥《太虚大师全书》第28卷,第94页。。以禅宗振兴作为中国佛教振兴之核心,这是太虚对于中国佛教发展道路之根本抉择,反映了其实事求是地梳理汉传佛教历史传统之来龙去脉的客观主义精神。以太虚之睿见,考诸史实,禅宗所以能于唐宋之后在中土佛教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实赖诸多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因缘之凑泊;同样地,考诸当下,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因缘也使重振禅宗成为未来中国佛教复兴之必然进路。
实际上,从学理上讲,太虚大师在其人生佛教⑦太虚对其佛学思想,大多时候以“人生佛教”相称,有时亦称之为“人间佛教”,名或有别,但其所言内容却无二致。的建构中也正是经由批判地继承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主流佛学引出根本的思想资源的。今取最可表征太虚人生佛教旨趣的两个思想特色,以窥其大略。
(一)入世精神
六祖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将大乘佛教世间与出世间、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二的主张推向极致,由此行住坐卧不外修行、饿食寒衣无非体道之类便成为祖师禅的思想标记。对之,太虚法师是深有体会的,尝言:“佛教佛学通出世世间真谛俗谛而言,人乘正法即为人道正义。”①《太虚大师全书》第28卷,第361,275—276页。“其实禅宗与一切佛法,皆是通为出世世间的善法的……盖佛法本是透彻出世,而亦利益世间尽未来际的。”②《太虚大师全书》第28卷,第361,275—276页。其针对当时传统佛教的种种衰象而揭橥的人生佛教理论可谓通体贯彻着禅宗这一思想诉求,富有强烈的入世色彩。
首先,人生佛教是契理契机的。佛教要走进社会,契入人生,进而化导社会和人生,必先得当时当机,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以及生活其中的大众之要求。太虚认为佛学固有“契真理”和“协时机”两大原则:契真理,指符合佛教真理,即与“宇宙万有实相”相符契;协时机,谓与时俱进,佛教应结合时代变迁及信众情状适时进行相应的变革。太虚考研了当时世界文化所出现的新特征,指出,由于科学技术和交通的发达,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已汇成世界文化,表现为“现实的人生化”、“证据的科学化”、“组织的群众化”③《太虚大师全书》第3卷,第193,183—184,207,208页。。与此相适应,太虚揭橥人生佛教的“三大要义”:
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法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④《太虚大师全书》第3卷,第193,183—184,207,208页。
如此,人生佛教建设便紧贴时代脉动,反映了世界文化变迁的现代特征,从而推动了佛教的现代化转变。
其次,人生佛教主张积极的生活中的修行。《人生之佛教》⑤《太虚大师全书》第3卷,第193,183—184,207,208页。一文要求人们从现实的生活中体悟佛教,认识佛教。太虚说:“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了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这正是他一贯主张的人生佛教。他还说,所谓菩萨、佛,虽是出凡入圣的超人,但绝非是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若以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为,推动整个的人生向上进步,向上发达,就是菩萨,亦即一般所谓贤人君子;再向上进步到最高一层,就是佛,亦即一般所谓大圣人,故佛菩萨,并不是离奇古怪的、神秘的,而是人类生活向上进步的圣贤。”在《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⑥《太虚大师全书》第19卷,第318,218、219页。《唐朝禅宗与现代思潮》⑦《太虚大师全书》第22卷,第186页。等文中,他认为,“务人工以安色身,则贵简朴;修佛学以严法身,则贵真至”,力倡发扬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强调“凡学佛之人,无论在家出家,皆不得以安受坐享为应分,务必随位随力,日作其资生利人事业,不得荒废偷惰”。总之,“出家者有出家者之家务事业,即所谓‘宏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⑧《太虚大师全书》第19卷,第318,218、219页。。他谆谆告诫学人、信众:佛法并非是隐遁清闲的享受,也不是教人不做事的,而是应该对国家、对社会知恩报恩,故每个人都应当做正当的事业。例如,在自由社会里,可从事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在和平时期,则可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等,以这些作为成佛之因行。
再次,人生佛教是现世的,倡导人间净土的建设。太虚指出:“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⑨《太虚大师全书》第3卷,第193,183—184,207,208页。针对传统佛教为死向鬼之流弊,他回归佛陀本怀,强调了佛教的人生性、人间性。人间佛教的本质不同于一般宗教,将所谓理想境界寄托于来生完成,或寄于“天国”或他方世界去实现,而是注重于今生现证此解脱境界。这在祖师禅“平常心是道”的行解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太虚看来,五戒十善、六度四摄、利乐众生、庄严国土,都必须在与众生的关系中,主要是在人类社会中实践,在社会责任中完成,离开人类,脱卸社会责任,便无从成就佛果,也难以自了生死。所谓了生死,并非死后方了,并非离社会责任才能了,要在于我人生活之当下.以智慧照破自心中的我法二执,证见本来无生的实性。佛教的解脱精神应该是精进于今生的,是现生智慧地行持合于菩萨之道。即使是追求往生他方佛国净土,以人生佛教的立场看,也须佐以建设人间净土的福德之积累。单纯的美好向往终不能解决来生的归宿问题。据此,太虚以为,当下人世间固然不完美,但这并不意味着必得弃绝此恶浊之世而另求清净之世,相反,世人应依靠自身的努力改造此不完美世界,致力于在人间创建净土。他特别强调人心之于人间净土创建的关键作用,指出“若人各改造其心,为善去恶,便能转此苦恼世界而成清净乐邦也”①《太虚大师全书》第5卷,第264页。;同时他也十分重视社会政治力量之于建设人间净土的重要意义,主张发挥政治力量的作用,推进实业、教育、艺术和道德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二)人本精神
“六祖革命”将佛性由抽象的超验的本体请回了现实人生,以人心、人性置换传统佛教的自心、自性,从而实质上便将佛归结于人,还原为人,另方面亦将人变成了佛;及至祖师禅后学,更是佛即是人,人即是佛,人佛无异不二。于是,现实人性人心、现实人生及人生现实登得佛家圣坛,成为考究悟解的所在;佛的问题便化为人的问题。修行而成佛解脱,不再体现为息心灭情,遗世涅槃,而是落实为人性人心的自我悟觉,及人伦日用中理想人格的圆证。太虚“人生佛教”所彰显的人本主义精神无疑是祖师禅这一人本化佛学传统的深沉的近代回响。
依太虚之见,佛法虽涵摄一切有情世界,普为一切众生,但其主旨在觉悟和解脱人生,弘化的中心在人间,实践的主体是人,故佛教自是以人为本。他考察分析中国文化传统主流之历史赓续及近现代文化流变之特征,以为,当今之世,表彰和推展佛教之人本精神尤为当机。他首先强调,中国二千年文化传统向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儒家为主潮,文化之特点“在于本人情为调剂之人伦道德”②《太虚大师全书》第28卷,第385页。,在此文化氛围,“不得不行”以人为本之人生佛教③《太虚大师全书》第25卷,第383页。其次,他反复申说现代文化人的价值及地位日益凸显,佛教建设以人类为中心方是发展的契机和正道。在《佛陀学纲》文中,他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力求人类生活如何能够得到很和平很优美……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间,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④《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第185页。在《救僧运动》一文中,太虚还明确指出:近代思想,以人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为本,或以圣人之道为本⑤《太虚大师全书》第19卷,第95页。。根据现代社会之现实的人生化的态势,他将以人类为中心,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作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
太虚人生佛教的人本精神,突出地体现于其由人乘行直趣佛果的主张。太虚将佛教判为五乘,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和佛乘。在他看来,天乘和声闻、独觉二乘实乃人修行之“歧出”,并非由人而佛必经的次第和阶段;而且,人生是宇宙特殊部分,“佛已证到人生与宇宙一致的实性,所以佛法的法身即宇宙(人生性即宇宙性)”⑥《太虚大师全书》第23卷,第140页。,由此,佛便是“全宇宙的真相”,是“人的本性的实现”,“是最高人格的实现”;而“人类得到的最高觉悟的就是佛”,“把人的本性实现出来的”就是佛。这样,人完全可以超越天、声闻、独觉三乘而径趣佛境。太虚开出一条“由人而菩萨而佛”的路径,他有偈诗云:
仰止惟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①《太虚大师全书》第25卷,第377页。
太虚强调人生佛教以人生为起点和基础。他揭示人生相较与其他众生之殊胜处:由人向下为一切有情众生,由人向上为天及三乘、菩萨、佛。上下总依人生为转移,人是一切众生上下升沉的总枢纽。因此,最要紧的是做好人,“佛学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一个人”②《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第204,443页。,惟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学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③《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第204,443页。。这就要求首先要生活合理化、道德化,以成就“君子贤圣”之人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起菩提(觉悟)智慧,修解脱行,寡欲知足,宁静淡泊,求身解脱、心解脱、慧解脱;更要实行六度四摄、救苦救难、普利一切有情的菩萨行,依此不断向上发展,以发达人生而臻于圆满无上之人格——成佛。由是,太虚发扬祖师禅人本化之法脉,把握住做人、完成人格这一根本和关键,一则将传统佛教中被离析的佛与人生有机地契接起来,肯认并凸显人之于修佛之功用与价值,使成佛径直根植于做人之实际;一则为佛学奠基了人学之础石,从而禅宗畸重出世之偏向得以根本校正,更避免佛教重蹈“向鬼为神”之覆辙,同时也为学佛提示了切实可行的切入点,使求佛之人众有具体路向可循而趣之。
三、生活禅:人间佛教禅宗化的修行法门
(一)生活禅的历史定位
人间佛教作为汉传佛教的现代义学形态,由太虚创发,几十年来经由印顺、赵朴初等的不断充实、修正、发展和完善,其理论建构已臻于成熟,其标举的以人为本、注重济世的人间佛教的价值理念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转化为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蔚然而成当代汉传佛教之主流。而作为必以践修为根本之宗教形态,人间佛教若欲走入人间,导化人生,落实其完善人格、发达人生、利生济世之宏旨,则必要施设世人赖以修持、依法行践的方法论体系,亦即方便法门。失了方法之支撑,即世间即出世间、即人即佛云云便失了转化之津渡和门径。是故,人间佛教由义学而践修,由见地而功夫,是其教法本身的内在诉求;进而人间佛教走向生活禅乃其契理契机之必然。生活禅首倡者净慧言及生活禅来源时说:“‘生活禅’来源于祖师禅的精神和‘人间佛教’的思想,目的在于落实人间佛教的理念,进而把少数人的佛教变成大众的佛教,把彼岸的佛教变成现实的佛教,把学问的佛教变成指导生活实践的佛教。”④净慧:《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但净慧又指出:“‘生活禅’是认识到‘人间佛教’提出来一个理论框架之后,缺乏实践方法,于是在‘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方面提出‘生活禅’的修行理念。这也可以说是禅宗走到今天,禅宗要怎么样才能和今天的文化、今人的文明契理契机地结合起来,于是产生了‘生活禅’。”⑤《净慧长老访谈录》,《宗风》已丑春之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于此,净慧在揭示生活禅两大思想源头之外,还流露出两层意思:其一,针对人间佛教理论在实践方法上的缺失,创设以修行实践为核心诉求、以修行方法为核心内蕴的生活禅,以将人间佛教的理念真正向人间落实,建设大众的佛教、现实的佛教、化导生活实践的佛教;其二,生活禅是禅宗与今天的文化、今人的文明契理契机相结合的产物,以禅宗的根本禅理、禅法、禅径接引人间佛教走入当代社会生活实践,因此生活禅是禅宗的当代表现形式。
生活禅如此的历史定位,既体现了净慧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更揭橥了生活禅的价值、功用和意义,凸显了生活禅的基本特质及殊胜的所在。如果说太虚的人间佛教将慧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根本主张落实在圆满人格建设上,那么,净慧的生活禅则更深一步地将人格建设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将佛法融入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二)由重智轻悲到重悲轻智:生活禅旨趣的历史因缘
在生活禅建构的具体过程中,净慧始终十分强调禅宗和人间佛教之于生活禅的理论基础及思想本源之意义。基于历史之省思和现实之体察,净慧对禅宗和人间佛教在历史推展和演变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保持着清醒的警觉,一贯奉持中道精神,运用不二之法,谨重审慎地对待每一理念、每一观念,乃至每一口号的形成、提出和推展,并使之不断地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完善,不仅力图针治传统佛教之流弊,且希冀于理论创设中防微杜渐,以规避生活禅未来发展中的歧变和偏失之可能。
考诸史事,无论禅宗或是人间佛教,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皆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失甚至变异。
禅宗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主张直契心源,内省自证,轻忽严密的经教和事相的修习,鼓吹“无相戒”而视外在戒规如敝屣,这固然旨在破除各色执著,还原一个自在自由、空寂清净之心体,而直证佛果,但在实际的运用落实中,却因众生根器有异,而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酿成后世堕落的狂禅之风。禅宗这一流弊,一直以来,尤其是近世以来,深为教界内外所诟病。欧阳渐(1871—1943)指责禅宗后世盲者“徒拾禅家一二公案为口头禅,作野狐参,漫谓佛性不在文字之中,于是前圣典籍,先德至言,废而不用,而佛法真义浸以微矣”①欧阳渐:《唯识抉择谈》,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欧阳竟无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0页。。前述已提及陈兵指出禅宗有畸重出世之面目,而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禅宗衰落之原因时,他认为从禅宗自身看表现为四方面,其中尤值吾人措意者有二:一是背离了禅即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俗生活的本旨,偏重出世的一面,过于注重个人的了生死问题,崇尚山林办道、隐逸高蹈,较少关心社会的伦理教化和众生的现实生活;一是“背离经教,藉口‘教外别传’,不看经论,不修持戒、发心、忏障、集福等加行,不分根器利钝,一入佛门,便只抱定一句话头以为究竟,在无明眼宗师指导印证的情况下,不是久参不悟,便是迷执光影,误认法尘影事为真我,修行多年,烦恼根本分毫未动,我慢增上;或发邪解,或以解为证,堕于狂禅、野狐禅,自认本来是佛,戒定福德,无需更修,烦恼即菩提,无需离断;或如枯木死水,认世间定境为涅槃”②陈兵:《中国禅宗的振兴》,《法音》1996年第4期按,按,该文以笔名“佛日”发表。。人间佛教的思想重镇印顺(1906—2005)则更激烈地批评禅宗,因偏重心性的体证,故深邃的义学、精密的论理,都被看作文字戏论而忘却。而它虽自许圆顿大乘,但考其修行作略,所表现出的急证自了倾向、清净无为的山林气息及忽略现实、脱离社会的作风,却与小乘同。故印顺认同太虚称禅宗为“小乘行”的说法,评论禅宗为“小乘急证精神的复活”③印顺:《谈入世与佛学》,氏著:《妙云集》下编之七《无诤之辩》,台北:正闻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的中国佛教。印顺的批评,若涵盖整个禅宗尤其是祖师禅,尚可商议,然却切实描出了禅宗末流之真面相。综上,禅宗末流之根本表现,一言蔽之,重智轻悲。或亦可说,盖因重智轻悲,才导致禅宗之式微。
近现代人间佛教的产生和弘扬,不仅推动佛教回归佛陀本怀,也为传统佛教的走向人间、实现现代转型找到了当机的形态和门径,同时为佛教在当代社会推广普及和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拓展了道路。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作为传统佛教流弊之反拨,人间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极端强调教义的人间性、现世性、此岸性所致的其向另一倾向的流变,引起研究者们的忧虑与关注。李利安认为佛教的超人间性和佛教的人间性共同支撑着佛教整个的理论架构和实践体系,而佛教的超人间性是佛教最本质的特性,离开了超人间性,一切都以人间性为准绳,佛教就不成其为一种宗教,就将失去它的魅力和生命力。在他看来,当今的人间佛教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推展上,佛教的人间性被不恰当强化,乃至排斥佛教的超人间性,致使佛教的超人间性日趋淡化,人间佛教本身呈现出“过分理性化、世俗化、功利化、现世化、相对化”等特征,随之而来的是神圣性的消减,这是人间佛教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的症结所在④参见李利安:《佛教的人间性与超人间性及当代人间佛教的困境与出路》,《佛教与现代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董平对大多数人间佛教论者“都突出强调了佛教的人间价值,竭力强化其以人的现实生命为本位的固有品格及其关怀生命的人文情怀,而竭力淡化其作为出世间信仰的固有内涵”的理论倾向提出质疑,认为:“‘人间佛教’固然应以发达人生、利乐有情、建设人间净土为目的,但这种世间目的应由佛法本身的出世间的宗教目的来统摄。应重新凸现佛教所固有的超越品性,并在这一超越品性之下来重新诠释、调适佛教的观行系统,从而在入世与出世、世俗与神圣之间寻得某种平衡的基点,在保持佛教的宗教神圣性的前提下来谈论它的世间价值,而不应倒过来,为凸现其世间价值而纯粹解构掉它作为宗教信仰的超越性的、出世间的精神价值诉求。”①董平:《大陆近二十年关于“人间佛教”的研究及有关理论问题的思考》,“2005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台湾中国哲学会主办。转引自“学佛网”,http://foz.xuefo.net/show1_24787.htm.释如石更是尖锐地指责人间佛教的推展偏重社会弘法和救济活动,而忽视定慧的修行,认为“基于定慧的菩萨行才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若不先讲求出离心与菩提心的长养,和戒、定、慧的落实,便汲汲营营于社会与弘法事务的关怀,那就显得太舍本逐末而深违佛意了”②参见释如石:《台湾佛教界学术研究、阿含学风与人间佛教走向之综合省思(下)》,《香光庄严》第67期,1990年9 月出版。转引自“香光庄严”:http://www.gaya.org.tw/magazine/v1/2005/.。由此可见,如果说明清以来禅宗末流走上重智轻悲歧途从而激发太虚这样有识之士的反思,人间佛教之旗帜由此揭起的话,那么,当代人间佛教的推展所出现的重悲轻智之态势,便不能不引起教界内外明眼人之省察。
于是,我们便不难契悟何以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八个字为生活禅立宗的良苦用心了。
(三)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
整个佛法的核心理念不外悲智二字,整个佛法的根本精神即体现为悲智双运。智是自觉,悲为觉他。生活禅以“觉悟人生”解佛法之智,以“奉献人生”解佛法之悲,可谓深契佛法根本之理,是悲智双运精神的现代诠释,更是悲智双运精神的真正落实。净慧说:
生活禅的宗旨有八个字:“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佛教的精神两个字:一“智”、二“悲”。“智”就是大智大慧,“悲”就是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和大慈大悲,是大乘佛教的精神,是佛法的总体精神,佛教的一切精神都包括在这两个字当中。有大智慧所以觉悟人生,有大慈悲所以奉献人生。“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是把悲与智用现代的语言加以诠释,并且把它落实于生活这个很具体的范围之内。③净慧:《禅在当下》,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生活禅”的目的是要实现“禅生活”。从“生活禅”到“禅生活”其中要落实的理念,就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大乘佛教悲智二门就是指救度众生的慈悲与求证菩提的智慧。此二者中,智慧着重于自利,慈悲着重于利他。若配以人之两手,则悲为左手,智为右手,悲智具足,两手齐全,缺一不可,“觉悟人生”自觉觉他,“奉献人生”自度度他。学佛能以般若智慧求觉悟(菩提),即是从“生活禅”进入到“禅生活”的过程;学佛而能以慈悲精神度众生,即从“禅生活”回到“生活禅”的过程。觉悟人生即是观照当下,破除烦恼;奉献人生即是发心在当下,成就众生。④净慧:《中国佛教与生活禅》,第128—129页。
生活禅,说到底即是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禅视域,处处禅机,在在道场,故而修行未必惟有山涧林下、深堂密室,得道未必只在拜师求教、念经打坐,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动念、扬眉瞬目、举手投足、接人待物皆是修行内容,一颗平常心、一生本分事、一个自在人便是道行。在生活中,时时刻刻、事事物物皆能保持佛法的观照和化导,由生活禅而禅生活,便可实现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宏旨。生活禅的这一理念,将大乘佛教悲智并重、悲智双运的根本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在佛教的修行理念中,解脱道体现了佛法的智慧一面,以出离心为基础,以自我解脱为目标,以自受用为主,是佛法向上的、出世的一路;菩萨道体现了佛法的慈悲的一面,以菩提心为基础,自觉觉他,自度度人,最后圆满成佛,以他受用为主,是佛法的向下的、入世的一路。依大乘正法、正修,解脱道和菩萨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圆融一体的,亦即向上向下不二,自觉觉他不二,出世入世不二。但在实际修行的践履过程中,由于根性的差异、志趣的差异,修行者往往畸重畸轻、厚此薄彼,致使佛教精神难以真正发扬,佛教的社会功用不能富有成效地显示。有鉴于此,净慧更进一步揭示了修生活禅之于佛教禅修的意义。他强调:“我所提倡的生活禅,如果以佛教的解脱道和菩萨道的理念来归纳,‘觉悟人生’就是解脱道,‘奉献人生’就是菩萨道。生活禅的宗旨,就是希望把解脱道和菩萨道完美地结合起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①② 净慧:《禅在当下》,第177,178页。在净慧看来,一方面从佛理讲,出世求解脱是每一个学佛人的根本目标;只有在解脱道的熏习下,烦恼才能排除,心灵才能有所归宿而安顿下来;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佛教强调福慧具足,只有既修慧也修福,才可能在果位上福慧圆满,证成佛境,因此要求在解脱道的基础上,发起慈悲救世之愿力,奉献牺牲个人身心和生命。另一方面,入世利生行菩萨行,须以修证为基础,以出世解脱的觉慧为前提和条件,才能以“无我”、“无所得”之心,无私奉献,饶益众生,而不致亟亟于现实功利,急于求成。“所以福慧双修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有偏差。觉悟人生和奉献人生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在觉悟中奉献,在奉献中觉悟;在智慧指导下修福田,在修福田中又来开发智慧,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做到福慧双修,做到觉悟人生与奉献人生、解脱道与菩萨道并驾齐驱。修行有基础、有目标,就能稳操胜券,不至于走到误区。”②② 净慧:《禅在当下》,第177,178页。
贯彻悲智双运、福慧双修,追求觉悟人生与奉献人生、解脱道与菩萨道并驾齐驱、完美结合或可说是生活禅整个理论架构和修行体系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体现了生活禅开展的根本愿景,从而形成了生活禅的最显著的特征。此一理念作为宗纲,涵摄生活禅的方方面面,从主旨和目标的定位,到修行原则和内容确认,直至修行方法的运用,皆体现着其落实的要求,而所有这些最终又内化为修行主体从观照自心开始的由“生活禅”到“禅生活”真修实证的践行过程,从而成就了以祖师禅之道落实人间佛教精神的不二法门。
B946.5
A
1000-9639(2012)06-0130-12
2012—06—19
张 平(1956—),男,河北邯郸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石家庄050051)。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