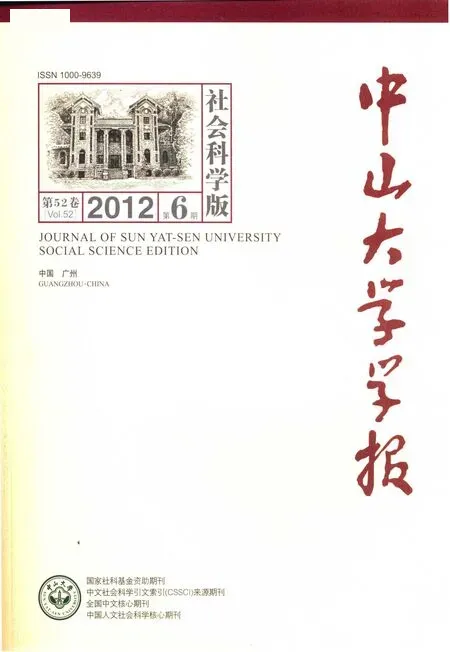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刘青海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刘青海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献赋;汉魏六朝;庙堂文学;政治体制;文学风气
献赋活动在汉代非常活跃,是汉代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它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是对汉代献赋传统的一个延续,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献赋的机制又在发展中较两汉时有所变化,由此造成献赋在功能上的明显转变,并呈现比较明显的南北分流的趋势。上述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是汉魏六朝文学的重要构成,理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学界对汉魏六朝赋的研究虽然不少,尚未见有集中研究献赋现象的。本文旨在论述汉魏六朝献赋现象的发展和流变,并且从政治体制和文学风气两个主要方面揭示献赋活动的内在体制和功能转变的根本原因,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
史传中对献赋的明确记载,最早始于汉武帝朝。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司马相如曾经多次向武帝“奏赋”①所谓献赋,即将自己所作的赋投献给君王、主司,以达到讽谏、歌颂之目的,或用以自明。《史记》、《汉书》都称“奏赋”,“献赋”的说法出现得较晚。:首献《天子游猎赋》,次献《秦二世赋》,三献《大人赋》;并且都有很明确的现实政治的指向:《天子游猎赋》和《大人赋》是谏武帝游猎和求仙的,《秦二世赋》也有以古讽今的意思在内。与司马相如同时的枚皋作《皇太子生赋》,又于卫皇后初立时“奏赋以戒终”,武帝东巡,沿途每有所感,皋即受诏作赋②班固:《枚乘传》,《汉书》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67页。。从上述史传对司马相如、枚皋献赋的记载可见,用于献纳之赋与普通赋作在创作上是有不同的,其赋作的内容与作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尤其是朝廷、帝王的动向相关,是西汉文学“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①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的集中表现。以武帝朝为例:朝廷每有大事,例如天子封禅出巡、郊祠甘泉、游猎、求仙、临幸池馆、诞生皇子、贡献异物等等,都有文人如司马相如、扬雄、枚皋、东方朔等献赋加以讽颂。显然,通过献赋这种方式,文人对当时朝廷的各种举措保持了敏锐的反应,为自己以文章经国的抱负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渠道;而朝廷也得以了解下情,并借骋辞大赋来润色帝王的伟业。武帝之后的历代君臣继续这种献纳活动,由此形成了献赋这一政治和文学的重要传统。献赋活动的展开表明,天子和文人、朝廷和文士对于所置身的皇权政治有一种明显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臣下以之为讽谏颂美,主上用其来润色鸿业。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这就是献赋的机制。
这种植根于政治的献赋机制,也可以从其更早的存在方式得到印证。《诗·鄘风·定之方中》毛传云:“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②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15页。又《国语·周语》中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③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页。正如钱志熙先生所指出的,就赋体从口诵体到书面体的发展来看,《毛传》“升高能赋”和《国语·周语》“瞍赋”正是早期口诵赋的代表。不仅如此,这里大夫和瞍所“赋”都是有特定对象的,也可以视作早期以口头形式献赋的例子。而且,“无论是大夫之‘登高作赋’,还是天子听政时的‘瞍赋’,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④钱志熙:《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而后世的书面体赋作的奏献活动,正是对口诵体的进一步发展,其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显然也包括在内。
考虑到具体的创作情境,在这一作用于朝廷和文士之间、帝王和文人之间的献赋机制中,天子是赋作特定的奏献对象,而且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因此,献赋者在创作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天子对赋作内容的接受,尤其是当其以讽谏为目的时更是如此。因此在艺术表现上,往往不直言其事,而是“主文而谲谏”,以求“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⑤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15页。。司马相如三赋就是这样⑥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73页。,并由此奠定了汉大赋欲讽先颂、寓讽于颂的传统。曲为之说固然可免于罪,然曲终奏雅,进谏的效果不免要打折扣,甚至造成献赋的最初目的与其实际效果之间的背反。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大人赋》本以谏武帝之好仙,而天子读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⑦司马迁:《史记》,第3063页。。稍后的赋家扬雄“辞人之赋丽以淫”⑧扬雄:《法言》卷2,《扬子法言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的指责,也正是有鉴于此。不免于劝,甚至欲讽反劝,可以说是两汉献赋之作的一个普遍困境。这一困境的造成,应该说正是受制于献赋这一特殊的机制,即它是在专制皇权的背景下展开的。后世的赋家在创作非奏献之大赋时,也往往曲终奏雅,这不仅仅是恪守传统,也是专制皇权作用于文学和文人的结果。
献赋始于武帝朝,而全盛于西汉。对于汉代献赋的规模、数量乃至功能和效果,班固《两都赋序》作了概要性的描述: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儿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22页。
由班固的论述可知:(一)西汉献赋的规模很大,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献赋者有枚乘、司马相如以下共61家②班固列78家,内有主名者66家,其中屈宋等6家在汉以前。。赋主的身份,可分为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夫御史两大类。前者如司马相如等人,都是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其赋作保存较多;后者如御史大夫儿宽之属,则主要以政事见长,不以辞赋创作为后世所知。(二)献赋的数量,班固这里明确地说是“千有余篇”。其中有九百余篇都著录于《汉书·艺文志》③这里采纳陈君《两都赋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走向》(《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的说法,认为《汉书》与《两都赋》的创作,前后只相差一年时间。,还有大约百篇应该是亡佚了。如董仲舒也是班固赋序中所举“时时间作”的“公卿大臣”之一,可以肯定他当时也曾有“奏赋”之举,但其赋作的具体篇目,《艺文志》不录。他流传至今的惟一赋作《感士不遇赋》也显非奏献之作。大概他所献之赋,在班固作《艺文志》时,官方目录已不见载,很可能当时就已经亡佚。(三)献赋的目的,即班固所概括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无论是将下情上传给天子,还是将上德流布于万民,都是为了让皇朝的美政显著于后世,而赋作本身作为庙堂文学的代表,也就是当代的雅颂。(四)献赋的效果,即“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除了有效地刺激汉代赋体创作的繁荣之外,献赋还直接干预如迁都、游猎、求仙、封禅等当时重大的政治活动,是汉代文人以文章经国安邦的重要举措。
东汉文人的献赋直接延续了西汉的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是班固、杜笃献京都赋一事。光武帝在洛阳建都,但关中耆老还希冀还都于长安。班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班彪传》);而同时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以效“司马相如、杨(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后汉书·文苑传》)④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1335、2595—2596,1373、2616,1991、2650 页。。二作对迁都的态度不同,但都是对司马相如等西汉赋家在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献赋以讽谕人主的传统的发扬。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后世:明帝朝,琅琊孝王刘京“数上诗赋颂德”⑤《司马彪续汉书卷四·光武十王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08页。;章帝朝,帝每行廵狩,班固“辄献上赋颂”(《后汉书·班彪传》);和帝朝,李尤因东观受诏作赋,有相如、扬雄之风,官拜兰台令史(《后汉书·文苑传》)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21、1098页。《上林赋》原文作“上林颂”,据上下文径改。挚虞《文章流别论》亦云:“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崔寔献《大赦赋》(《全后汉文》卷45);桓帝朝,马融从帝猎广成,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全三国文》卷8)⑥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1335、2595—2596,1373、2616,1991、2650 页。;灵帝朝,招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后汉书·蔡邕传》),高彪“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后汉书·文苑传》)⑧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1335、2595—2596,1373、2616,1991、2650 页。等。
东汉献赋的规模和数量,因为缺少类似《两都赋序》这样的明确记载,现在已很难具体考知了。根据《后汉书》和钱大昭、侯康、顾槐三诸家《补〈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篇目来看,其中有些赋作虽无文献佐证,从标题看也可以推测当为献赋之作,如崔骃《大将军临洛观赋》、崔寔《大赦赋》等。以李尤为例,其《函谷关赋》、《平乐观赋》、《东观赋》、《德阳殿赋》、《辟雍赋》⑨顾槐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本,1998年,第2271页。等,应该都属此类。另,尚书令阳球罢鸿都门学的奏章中提到,当时乐松、江览等32人之所以“位升郎中,形图丹青”,只因“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后汉书·酷吏传》)。这些赋作,“高者颇引经训风谕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说明既有以讽谕为本的大赋,也有以谐谑为主的俗赋,其中甚至还有“或窃成文,虚冒名氏”的伪作(《后汉书·蔡邕传》)。大约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暴露出某些作者的趣味不高甚至品性不良,同时的杨赐才将鸿都门下招会的“造作赋说”之人指斥为“群小”(《后汉书·杨震传》)。而这种鱼龙混杂的状况,也反映出汉末献赋的真实生态:日益黑暗的政治环境让文人不复盛汉赋家润色鸿业的热情,他们对现实的讽谕也不容易得到君王、主司的优容,反而有可能因此遘祸,甚至因此亡命殒身,崔琦以《白鹄赋》讽外戚梁冀,终为其所刺杀即为著例(《后汉书·文苑传》)①范晔:《后汉书》,第2499、1996、1780、2622—2623 页。。到了汉末,皇权政治摇摇欲坠,献赋的机制也面临解体的危险。直到建安时期,这种局面才被打破。
二
建安时期,“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心雕龙·明诗》,见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第478,48 页。。在他们身边,聚集了邯郸淳、杨修、王粲、刘桢、陈琳、阮瑀等一大批在汉末成长起来的文人,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这个文人集团,“首先是政治集团,然后才是文学集团”③程千帆:《重叠的文学史》,《俭腹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性质,还是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④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心雕龙·明诗》,见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第478,48 页。为主要内容的雅颂文学。吴质《答魏太子长笺》云:“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全三国文》卷30)这指出他们的身份,正是与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等人同样的文学侍从,也反映出建安文学在观念上对作为汉代文学盛世的汉武时代的文学是有所继承的。曹丕《典论·论文》赞美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全三国文》卷8)⑤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221、1098页。,这里的文章,主要也还是指以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建安时期之所以能够接续两汉的献赋传统,也正是因为二者都是在雅颂文学的繁荣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曹魏时期的献赋作者和对象,都是在汉末的政治和文学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其献赋活动可以说是对汉代献赋传统的很自然的延续。如陈琳是建安时期重要的献赋作者,建安十二年向曹操献《神武赋》,后来又受曹丕之命作《迷迭赋》、《玛瑙勒赋》、《柳赋》等。但此前陈琳在袁绍军中时,早在建安三年,就有《武军赋》之作以献袁绍⑥《武军赋》序有“回天军于易水之阳,以讨瓒焉”之句,乃建安三年袁绍讨公孙瓒时所献。以上陈琳赋作皆见《全后汉文》卷9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967—968页。。曹氏父子都是建安时献赋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同时曹丕和曹植也是重要的献赋作者。以曹丕为例,他不仅向曹操献赋,而且在未立为太子之前,还曾献赋给钟繇⑦见《全三国文》卷7《又与钟繇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88页。。这都表明,建安时代的献赋风气,不仅仅受益于曹氏父子的“笃好斯文”,从武帝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献赋传统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汉代献赋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臣下主动“奏赋”,二是臣下受诏或受命作赋。曹魏时期的献赋也可以大致分为这两类:臣下主动“奏赋”的,如邯郸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曹)丕以为工,赐帛千匹”⑧郝经撰,黎传纪、易平点校:《续后汉书》卷66下上《文艺传》,《二十五别史》本,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903页。,卞兰献《赞述太子赋》,赞美曹丕的《典论》等著述(《全三国文》卷30);受命献赋的,如陈琳受五官中郎将曹丕之命献《玛瑙勒赋》,曹植受其母卞夫人之命作《寡妇赋》(《全三国文》卷13)等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222、1125页。。但由于曹氏父子都能作赋(1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曹操撰《沧海赋》、《登台赋》、《鹖鸡赋》三篇,第1055页。,所以在建安时出现了在上位者首倡并与臣下共赋的情况,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这种风气,最早是由曹操开创的。建安十一年,曹操北征乌桓,作《沧海赋》,曹丕集中亦有《沧海赋》(《全三国文》卷4),显然是同时之作。这应该是建安时期君臣共赋的开始。建安十七年春,曹操游西园,命曹丕兄弟共赋,丕《登城赋》(《全三国文》卷4)尚存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72、1074页。。挚虞《文章流别论》回忆建安中献赋的盛况:“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②章樵:《古文苑》卷7《羽猎赋》注引,龙溪精舍校刊本。此外曹丕作《寡妇赋》,令王粲并作;作《玛瑙勒赋》,令陈琳、王粲并作;作《槐赋》,命王粲同赋;临淄侯曹植作《孔雀赋》令杨修共作等③以上曹丕、杨修诸赋,分别见《全三国文》卷4、《全后汉文》卷5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1073、1074、1075、757 页。,都属此类。曹丕篡位建魏之后,太和六年诏卞兰、缪袭等人作《许昌宫赋》。曹操、曹丕、曹植以重臣、帝王和王子的身份与臣下共赋,这对于献赋这一传统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这种带有竞赛性质的献赋活动,是文学的自觉在献赋这一特殊的文学生态上的表现。同时它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为后代帝王及其身边的文人所效仿。魏明帝曹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自言“于赋诔特不闲”(《诏陈王植》),但也能写作辞赋,有《游魂赋》(《全三国文》卷9)尚存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103、1101页。。明帝也喜诏令臣下为赋,曾命人作《景福殿赋》,何晏、缪袭、韦诞、夏侯惠同作。刘劭是明帝朝最重要的赋家,其所奏献,不但有《嘉瑞赋》、《龙瑞赋》等颂美之作,还曾受诏献“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⑤陈寿:《魏志·刘邵传》,《三国志》卷21,香港:中华书局,1971年,第618页。。无独有偶,何晏受诏所作《景福殿赋》,也是以讽谏明帝之大造宫室为旨的。受诏作赋而以讽谏为旨,这在整个献赋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却正表明了献赋这一体制在当时特有的活力。当然,这和明帝的喜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青龙元年,明帝有诏云:“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成上不封,得令人见。”(《全三国文》卷9)同年改元青龙,缪袭奏献《青龙赋》(《全三国文》卷38)。足见明帝一代的献赋风气。此后高贵乡公曹髦临朝,其《原和逌等作诗稽留诏》自言“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全三国文》卷11),朝臣钟会“植蒲(葡)萄于堂前,嘉而赋之。命荀勖并作”(《全三国文》卷25)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104、1265、1114、1188页。,亦可见当时风气。这种献赋活动一直延续到魏末,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成公绥迁中书郎,“每与(张)华受诏并为诗赋”⑦房玄龄等:《文苑列传》,《晋书》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5页。系年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则张华与成公绥在元帝朝的献赋之作当为不少,但大都已散佚,今存张华集中虽有辞赋数篇,但都非此时献赋之作。
曹魏时期的献赋活动是整个六朝献赋史上的一个高潮,随后的西晋初年活跃的献赋活动可以视作其余波。晋武帝朝去魏不远,献赋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如泰始四年武帝藉田,潘岳献《藉田赋》以美其事;泰始八年,左芬受诏作《愁思赋》。但无论是献赋的潘岳(247—300)、左芬(?—300),还是诏令左芬献赋的晋武帝,他们都是在曹魏末年的文学空气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其奏献活动,实可视作是曹魏献赋高潮的余波。左思写作《三都赋》,虽然实际上并未奏献给晋武帝,但也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写作的,而且在具体的写法上参考了班固奏献光武帝的《二京赋》。贾谧在《三都赋》序中说赋“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也不是一般地评论赋体,针对的其实是以《二京赋》为代表的这一类传统上用于奏献的京都大赋。像《三都赋》这样实际上受献赋传统的影响而创作,但事实上没有奏献或本就不准备奏献的作品,似乎可以算作一类,叫作模拟献赋。这类赋作甚多,兹不赘举。除史籍所载外,陆云集中的《南征赋》很可能也是一篇献赋之作⑧《陆云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7页。《南征赋》序云:“美义征之举,壮师徒之盛,乃作《南征赋》,以扬匡霸之勋云尔。”。另外陆云在写给其兄陆机的信中提到,他写了一篇《讲武赋》,准备献给大将军。这些都是晋武帝朝26年间的献赋情况。继武帝之后嗣位的惠帝是个白痴,据史书记载,侍御史傅咸曾受诏作《明意赋》;此外皇太子司马遹曾令潘尼(约255—约300)作《鳖赋》,令陆机作《桑赋》。
东晋一百年间,是献赋的低潮期。史书见载的献赋仅寥寥数次,基本集中在东晋初年。元帝太兴元年,郭璞“奏《南郊赋》,中宗见赋嘉其才,以为著作佐郎”①汤球辑:《东阿郭录》,《晋中兴书》卷7,光绪广雅丛书本,第110页。。可见献赋是文人炫露才华的重要手段,相较作诗,古人认为作赋、奏赋更能见著作之才。且赋本为润色鸿业而作,故作赋之才,更适应王朝政治的需要。概言之,较之诗,赋是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的文体。之后王廙奏《中兴赋》,以“宣扬盛美”②房玄龄等:《王廙传》,《晋书》卷76,第2004页。。在该赋序中他还提到,曾受元帝之命作《白兔赋》,白兔是祥瑞,此赋亦当为颂美之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谢灵运出使彭城,慰劳相国宋公刘裕,献《撰征赋》,“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③谢灵运:《撰征赋》,《全宋文》卷30,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600页。。这已是晋宋之际了,两年以后刘裕篡晋,而且献赋的对象为刘裕,《撰征赋》归到刘宋时期其实更合适。两晋献赋活动的低潮,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皇权政治的衰落,缺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以雅颂为基本性质的庙堂文学无所附丽,献赋也就无从谈起;另外,东晋的玄风大盛,文人普遍不重著述,更缺少创作大赋的热情,献赋活动无可避免地衰落了。
三
刘宋六十年间,接续了东晋时一度低落的献赋传统,基本恢复到了曹魏时期的规模。这首先要归功于专制皇权的重新建立和稳固。同时刘宋在位时间比较长的文帝(30年)、孝武帝(11年)、明帝(8年)都好尚文学,临川王刘义庆、江夏王刘义恭都能创作辞赋。与此同时,随着玄风的消退,著述的风气重新兴起,一批能作赋的文人也成长起来。这些条件都促成了献赋活动的重新繁荣。文帝朝是献赋传统的复苏期,元嘉十八年。见颜延之献《赭白马赋》④《全宋文》卷36《赭白马赋》序云:“乃诏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献赋。”又云:“惟宋二十有二载。”可知是作于元嘉十八年。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633页。,江夏王刘义恭《白马赋》(《全宋文》卷11)⑤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497—2498页。当为同时奏献之作;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献赤鹦鹉,群臣为赋,谢庄《赤鹦鹉赋应诏》深为袁淑所赏⑥沈约:《谢庄传》,《宋书》卷8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67页。。庄又有《舞马赋应诏》(《全宋文》卷4)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625、2626页。。宋孝武帝是在文帝朝的文学空气中成长起来的,自己能创作辞赋,有大明六年《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华林清暑殿赋》(《全宋文》卷5)等作存留⑧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465页。。韩兰英献《中兴赋》,孝武帝赏之,被赏后宫⑨李延寿:《后妃上》,《南史》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0页。。《全宋文》卷5录武帝《华林清暑殿赋》,江夏王刘义恭、何尚之亦有同题之作(10)刘义恭、何尚之赋作分别见《全宋文》卷11、卷2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497、2587页。。这种在曹魏时期出现的君王首倡臣下同赋的情况,可以说是献赋传统被最大程度地激活的标志。史载宋孝武帝严暴,宗室刘义恭“虑不见容,乃卑辞曲意附会,皆有容仪。每有祥瑞辄上赋颂”(11)李延寿:《宋宗室及诸王上》,《南史》卷13,第373页。。这些作品今天都散佚了。裴子野《雕虫论》序云:“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行幸燕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12)裴子野:《雕虫论》,《文苑英华》卷742引,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3页。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学风气中,可以想见“以命朝臣”的内容应该不仅限于诗歌,也应该有包括辞赋在内的文章。时风流衍,至刘宋末年,犹有江淹献建平王刘景素之《灯赋》以为讽谏①《灯赋》的创作时间和主旨,参丁福林:《江淹年谱》,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萧齐统治的二十五年间,基本延续了刘宋的传统。齐武帝萧赜的统治时期是南齐朝政最平稳的时候,献赋活动也最频繁。如武帝起旧宫,王彬献赋,“文辞典丽”②李延寿:《南史》卷22《王彬传》,第611页。;又武帝“数阅武”,王僧佑献《讲武赋》③李延寿:《南史》卷21《王僧佑传》,第580页。;武帝游新林苑,江淹、王俭同作《灵丘竹赋应诏》(《全齐文》卷9)④《灵丘竹赋应诏》系年,参丁福林:《江淹年谱》,第176页。;“琅邪诸葛勖……坐系东冶,作《东冶徒赋》,世祖见,赦之。”⑤萧子显:《南齐书》卷92《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93页。同时,诸侯王与臣下同题共赋也很活跃,如竟陵王萧子良就曾作《梧桐赋》(《全齐文》卷7),并命王融同作⑥王俭、萧子良、王融赋分别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840、2824、2854页。。江夏王萧锋亦能作赋,应该也有与臣下同赋的情形⑦李延寿《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下·江夏王锋传》载萧锋“著《修柏赋》以见志”,第1089页。。谢朓是萧齐最重要的赋家,《全齐文》卷23录谢朓赋作甚多,其中如《拟风赋奉司徒教作》、《七夕赋奉护军命作》、《酬德赋》、《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杜若赋奉隋王教于坐献》、《野鹜赋》等数篇是奏献之作⑧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918—2920页。,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献赋活动是非常频繁的。《野鹜赋》序云:“客有爱其羽毛,请予为赋。”又《酬德赋》是献给沈约的,辄所献之对象,在诸侯王、主司之外,还有和自己身份相若的“客”和友。这种投献对象地位从帝王、诸侯王、主司到客、友的下移,也说明了南齐献赋活动的普及。
梁代的献赋活动也很频繁,可以说是继曹魏之后的又一个高潮。梁武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下诏立谤木甬、肺石甬以开言路,求古乐古礼,鼓励献赋也是其为巩固新的皇权所作的诸多努力之一。就继承传统而言,萧齐时的献赋活动已经非常活跃和普及了,梁武帝本人就是在这种政治和文学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雅好作赋,今存《孝思赋》、《净业赋》、《围棋赋》(《全梁文》卷1)等数篇。武帝即位之后,其《敕答陆倕》“昔虞丘辨物,邯郸献赋,赏以金帛,前史美谈”,《敕赐费昶》“昔郎恽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全梁文》卷4)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948—2951、2969—2970页。云云,分别引曹魏时邯郸淳、卞兰献赋,曹丕加以赏赐之事以为故实,表现出对汉魏献赋活动的繁荣的向慕。在武帝的影响下,其子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雅擅辞赋,昭明太子萧统、邵陵王萧纶以及宗室萧子范、萧子云、萧子晖也都能作赋,为梁代献赋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根据《梁书》的记载:“高祖革命,(周)兴嗣奏《休平赋》,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高祖以兴嗣为工。”(10)姚思廉:《梁书·文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97—698页。显然,易代之际周兴嗣所奏之《休平赋》,其目的正是班固所说的“宣上德以尽忠孝”,客观上满足了当时巩固新的皇权的需要,因此得到了武帝的积极回应:不但对献赋者予以赏赐,而且还诏令臣下同赋并加以品秩高下。史书中这类武帝对奏献之赋予以评赏的例子颇多:
(张)率取假东归,论者谓为做傲世。率惧,乃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南史·张裕传》)
(萧子晖)尝预重云殿,听制讲三慧经,退为《讲赋》奏之,甚见赏。(《南史·齐高帝诸子上》)(刘)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在御坐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梁武帝甚称赏之。(《南史·刘勔传》)
(沈众)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徳殿。帝令众为《竹赋》。赋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南史·沈约传》)①李延寿:《南史》,第815、1076、1006、1414 页。
我们注意到,武帝不但对奏献之赋表示称赏,甚至还会手诏加以评点,这对于献赋者来说自然是很高的荣耀,而史官也将武帝的好文载入史册,流传后世,由此达到润色鸿业的政治效果。应该说,这是武帝及其臣下积极参与的结果,而天监初武帝与臣下任昉、王僧孺、陆倕、柳憕同作《赋体》之事②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3页。,可以视作是当时献赋活动达到全盛的一个标志。此外有文献可征的献赋,尚有天监十二年改造太极殿毕王规献《新殿赋》(《南史·王规传》)③李延寿:《南史》,第597,1503页。、沈约献《天渊水鸟应诏赋》(《全梁文》卷25)等;另外萧纲和萧绎同题共作的《对烛赋》、《采莲赋》、《鸳鸯赋》(《全梁文》卷8、卷15)也当是这一风气的产物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100、2997—2998、3038页。。
陈代献赋接续了齐梁的传统。陈文帝在梁末任会稽太守,陆琛上《善政颂》,甚有词采,琛由此知名⑤姚思廉:《陈书·文学传》,第465页。。陈宣帝时,太子陈叔宝赐袍江总,总献《山水纳袍赋》(《全隋文》卷10)以颂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069页。。陈后主“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⑦姚思廉:《文学传》,《陈书》卷34,第453页。。如后主听说袁朗的文名,即“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后主曰:‘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于前矣。’”⑧刘昫等:《文苑上·袁朗传》,《旧唐书》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84页。祯明二年冬,后主于莫府山校猎,虞世基受诏作《讲武赋》,序云:“昔上林从幸,相如于是颂德;长杨校猎,子云退而为赋。虽则体物缘情不同年而语矣,英声茂实盖可得而言焉。”(《全隋文》卷14)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095页。可见当时献赋,仍是以盛汉时期的传统为尚的。陈瑄是后主朝的重要作者,有《应诏语赋》等数篇。《南史》卷61《陈暄传》载:“暄素通脱,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后主甚亲昵而轻侮之。尝倒县于梁,临之以刃,命使作赋,仍限以晷刻。暄援笔即成,不以为病。”⑩李延寿:《南史》,第597,1503页。虽然仅为个例,却至少说明在陈朝,赋作者已经真正沦落到了倡优弄臣的地步。
四
从两汉到六朝,献赋的主要对象始终是帝王宗室和朝廷重臣,虽然有颂美也有讽谕,但其所献赋作的基本性质始终是庙堂文学,是润色鸿业的一种方式。因此,一个专制皇权的存在也就成为献赋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只要有专制皇权的存在,献赋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也是为什么献赋在六朝一直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当然,在皇权鼎盛的朝代,如果帝王又重视文治甚至自己能创作辞赋,那么这一朝的献赋活动就会比较活跃,甚至会达到某种程度的繁荣,如前面论述过的汉武帝时期、曹魏时期以及梁武帝朝;如果皇权比较衰落,甚至像东晋那样,皇室与士族共同统治国家,士人又缺乏著述的热情,则献赋活动就寂焉罕闻。
政治对献赋之作的形式和体裁的制约也是明显的。一般来说,主动奏献的赋作多以散体大赋为主,无论颂美还是讽谏,针对的都是当时的朝廷大事,赋作的内在结构可以视作是当时皇权政治的文化镜像,是一种从中心向四方辐射的既宏大又有序的视野。从我们熟悉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作一直到六朝王粲《神武赋》、邯郸淳《投壶赋》、潘岳《藉田赋》、谢灵运《撰征赋》、王僧佑《讲武赋》、王规《新殿赋》、陆琛《善政赋》等都属此类,可以说是献赋之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班固所赞美的“雅颂之亚”,所指的主要就是这一类作品。
与两汉的献赋传统相比,六朝献赋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这两种同题共赋的形式,给赋作者提供了文学竞技的机会,有利于赋作艺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让整个献赋活动具有了更高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而品评高下与分别赏赐的特权仍属于独尊的帝王。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六朝献赋与汉代献赋的一个重要不同,即六朝献赋在功能上,文学本身的功能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发展的结果,因此很快受到帝王与文士的共同喜爱,在朝廷上下普及开来。受诏之赋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性,如遭逢军政大事,帝王令臣下作赋以壮声势,润色鸿业,如魏文帝曹丕命卞兰、缪袭等人作之《许昌宫赋》、张率应诏所作之《河南国献舞马赋》等就属此类。这类赋作无论结构还是形式都和前述主动奏献之赋相同。另一种则更多地具有娱乐的性质,没有具体的政治背景,君王宴游之时,往往一时兴起,指某物某事为赋。如曹丕命臣下共作《寡妇赋》、《车渠椀赋》、《玛瑙勒赋》,萧子良与臣下共赋《梧桐赋》、《高松赋》等。这一类赋作,往往是即席而作,且限以时刻,所以往往比较短小,抒写也比较自由,内容上不必有明显的颂圣之语,结构上也比较随意,大多都属于小赋。从数量上看,后一种显然是六朝献赋之作的主流。我们研究小赋的发展,献赋这一创作情境的制约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是应该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
六朝的献赋活动既是政治体制的产物,也受到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在献赋之作中,大赋的比重在不断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除了前述创作情境的制约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汉末文学的自由,诗赋分流,娴于辞赋尤其是大赋写作的文人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在西晋初年已经很明显了。陆云在写给陆机的一封信中,就谈到自己在写作大赋方面所遇到的困境:
钞前日观习,先欲作《讲武赋》,因欲远言大体,欲献之大将军。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许家语,不知此可出不?故钞白兄。若兄意谓此可成者,欲试成之。大文难作,庶可以为《关雎》之见微。①陆云:《与兄平原书》,《陆云集》卷第8,第138页。
这段话中,陆云向其兄坦陈了自己欲献大赋时的看法和顾虑,有几点颇值得注意:第一,对于所献之赋,陆云称为“大文”,其内容称为“大体”。“大”从形式上来说,指的是篇幅较长,与后文中的“少许”相对;从内容上说,指的是旨趣远大,与后文中的“家语”相对,亦即不是家常言语,是有关于邦国大事的。这和我们前面对大赋的雅颂性质的论述是一致的。“大文”、“大体”的提法,或许只是陆云自己的,但却可以反映出当时一般的观念,即用于奏献之赋,须得词旨正大关涉国家大事,不可作寻常言语,这也正是后文中陆云因只作得“少许家语”而迟疑不献的原因。第二,“大文”的写作需要很专门的才能,所以像陆云这样在当时与陆机并称“二俊”的作者,而且自言“颇能作赋”②陆云:《与兄平原书》,《陆云集》卷第8,第135页。与下文“为欲作十篇许小者”连读,可知其所能作之赋乃是小赋。,也不敢轻易作“大文”。也正因为如此,陆机在听说名不见经传的左思写《三都赋》,才会在给陆云的信里讥其为“伧父”,并说“须有成,当以覆酒瓮耳”③陆机:《与弟云书》,见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9页。。而左思之《三都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的事实也再次印证了陆云所说的“大文难成”的理论。第三,“大文”是有明确的投献对象或说特定的读者的,无论是赋作的形式还是内容,“远言大体”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大将军的认可。为了保证这一点,陆云才会要求陆机帮他进行预评,如果陆机认为“可成”,才“试成之”而后进献。这和史书中所记载的王僧佑献《讲武赋》,王俭借观不与的例子一样,都说明大赋的奏献对作者和时人来讲都是一件大事。
“大赋难成”的困境,对西晋乃至整个六朝文人来讲都是普遍的。这和建安时期吴质在《答东阿王书》中“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的描述,正形成鲜明的对照。而随着诗赋的分流,以及抒情小赋写作技巧的发展,文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缘情绮靡的诗歌和短小自由的小赋的创作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作者队伍的减少以及作者构成的改变,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主动奏献大赋的作者明显减少。随之而来的,还有以为讽谏的赋作明显减少,毕竟,受诏作赋相对来讲自由度更小,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如前举魏明帝朝何晏《景福殿赋》、刘劭《许都赋》、《洛都赋》等数篇),大都以颂美为主。
与南朝献赋以颂美为主形成对照的是,北朝的文化之盛不如江左,能作赋者甚少,但有所作,则多为大赋以为讽谏。如阳固“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受诏报焉,甚见嘉美”(《北史·阳尼传》)。北魏孝武帝“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时寒,朝野嗟怨,帝与从官及诸妃主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年二十七。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手诏报焉,甚见褒美”(《北史·魏收传》);高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北史·高允传》)。北齐高纬因母后帷簿不修而幽其于北宫,母子隔绝,“周使元伟来聘,作《述行赋》,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文虽不工,当时深以为愧”(《北史·后妃传下》)。可见是更重视其讽谕功能的。又郎茂为朝臣罗织徙官,以《登陇赋》附表自陈,隋炀帝颇悟(《北史·郎基传》)①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1721、2026、1124、523、2016 页。。这种献赋之作在体式和功能上的分流,也是南北朝文学分流的一个重要表征。
要之,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汉魏六朝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揭示汉魏六朝的献赋机制,有助于我们认定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而对于晚近的唐代文学来说,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又构成了新的传统,对唐代文人的献赋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I 206.2
A
1000-9639(2012)06-0010-10
2011—12—16
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项目成果(S30403);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古典文献学”
刘青海(1976—),女,湖南华容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