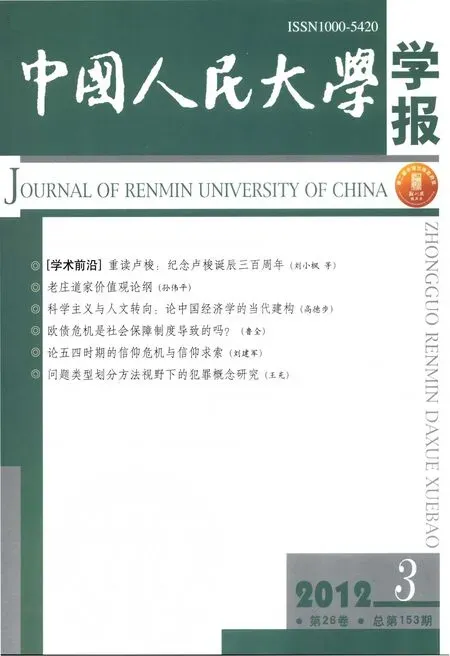论五四时期的信仰危机与信仰求索*
刘建军
考察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总得一再回到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后来的许多思想文化现象都可以在那个时期找到自己的缘由或萌芽。同样,考察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源流,也要回到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瞬间式地展现了中国人传统信仰的危机和对新信仰的求索。从此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追寻信仰的文化运动。从信仰角度来回顾五四时期,再现那个时期中国人在信仰上的危机、求索、冲突和选择的图景,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20世纪中国思想信仰史的逻辑,而且对于当前正面临信仰困惑的中国人如何思考和求索信仰不无启示。
一、信仰问题的凸显
在五四时期,“信仰”一词突然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概念。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吴稚晖等人,甚至青年毛泽东等,都在探讨信仰问题。吴稚晖还提出要建立一门“信仰学”来专门研究。这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是少见的。从历史上看,“‘信仰’一词在文献中大量应用,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1](P139)事实上,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知识分子很少热烈地讨论信仰问题。但在五四时期,信仰这一本来并不通行的词汇却成为一个核心性概念。这说明信仰问题在五四时期凸显出来,成为知识分子关注和争议的焦点。
当时的思想界所提出和讨论的各种问题,不论使用何种词语,事实上都属于信仰问题或与信仰问题有关。比如,打倒孔家店,它既是反封建的问题,又是信仰问题,是要反对和推倒传统信仰。国民性批判问题也涉及信仰,其中一个方面是责备中国人缺乏信仰。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也与信仰相关,实质上是关于从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化资源中吸取信仰灵感的问题。人生观的讨论所涉及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等问题,也都是信仰问题。“科学”问题也与信仰相关,它关系到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对待科学,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认识工具,还是要寻找科学的精神价值,让它成为中国人新信仰的因素。在政治层面上,民主问题、反独裁问题,既是鲜明的政治现实问题,也是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信念问题。丁文江在《我的信仰》中就谈论了自己在政治民主方面的基本信念。宗教的问题在当时比较突出,人们在讨论是否需要引进某种宗教,或确定某种固有的宗教来作为中国人的信仰。
那个时期充满着复杂的思想论争,而且表现得十分热烈和强烈。尽管有人力图使其保持在温文尔雅的范围内和水平上,但其思想的尖锐则是无法掩盖和回避的。尽管当时相互争论的学者之间往往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但在他们之间展开的激烈论争则没有调和取中的余地。比如,当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双方的带头人丁文江和张君劢虽然是好友,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思想上进行激烈论战。由于思想的对立,语言也就难免尖锐,语气也带上了感情冲突的特征,而且争论越到后来就越尖锐,越形成严重的冲突。之所以如此,缘于这是信仰之争。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试图为信仰的竞争制定规则,使这种竞争和冲突限定在思想意识和学术理论的范围内,并采取温和的形式。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能是善良的愿望。
二、传统信仰的崩塌
五四时期的信仰冲突和信仰选择是传统信仰衰落的结果和表现。如果说在19世纪末,作为这个信仰的载体和现实象征的清政府及其皇帝本人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完全失去了威信,国家危亡的危机感已经使传统信仰陷入危机的话,那么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辛亥革命废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传统的信仰失去了现实的载体和政权的支持。但封建势力仍然强大,企图依靠封建军阀伺机反扑,因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反传统还是最强音。尽管也有人主张重新恢复和振作传统信仰的力量,但已经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响应了。
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传统信仰并非没有合理的地方,也不是没有起过积极的社会和人生作用。但在五四时期中国人进行通盘的信仰清算和选择的时候,不应抽象地谈论儒家的积极内容。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尊孔读经和重振儒家信仰所带来的不过是帝制和复辟而已。李大钊在《圣人与皇帝》一文中说:“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很替中华民国担忧。”[2](P95)
传统信仰是历史形成的整体性存在,它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体系,而且也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对于这样一种信仰体系,要想对它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思考,进行细致的分析与鉴别、清理与剔除,使之实现时代性的全新转换,焕发出新的生机,尽管并非不可能,但绝不是一件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要想对它进行建设性转换,必然会遇到来自历史惯性力的强烈抵制。加上现实的紧迫感,生存还是死亡的最大问题,迫使中国人在急迫和实际的环境中进行着根本信仰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做的首先是把这个历史的庞然大物推倒。
一些对传统信仰抱留恋态度的学者,力图把传统信仰与封建制度区分开来,一方面承认封建制度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又大讲传统信仰的优越性,希望通过纯学理的研究证明传统信仰的合理性。以梁漱溟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提出了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主张。梁对比中外文化,从人生信仰立论,在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的比较中论证了传统儒家信仰的合理性。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向外的、纵欲的,印度文化是向内的、禁欲的,而中国文化是中和的、节欲的,故最为合理。这一做法自有其可取之处,其中也包含力图为国人保留一种信仰的真诚,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归根到底起着维护封建文化和制度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好像是设立了一个理性的法庭,一切思想和信仰都要拿到这个法庭上来加以考察和评判。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失去了优先权,不仅如此,它首先成为被严厉清算的对象。当时的反传统是以非常激烈的形式进行的。一些饱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举起反传统的旗帜。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攻击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避开孔子而抨击后学,而是直指“至圣先师”孔子。痛骂孔子,打倒孔家店,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反映了当时中国人信仰失落和危机的尖锐现实。中国人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传统信仰随着封建制度一起崩塌了。
三、能否将孔教定为国家宗教?
在中国人信仰的求索与选择中,定孔教为国教是被较早提出的一种主张。它不是简单地强化和恢复传统的信仰,而是以西方宗教的架构来为近代中国人构建新的信仰。
这个思想和主张来源于康有为。他明确地认定孔子学说是一种宗教,并将其视为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之一。尽管许多人认为儒家不是一种宗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有很大差别,但康有为一口咬定“孔教”就是一种宗教。在他看来,孔教是一种更为优越的宗教,是一种人道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是讲神道,托神道让人尊信,而只有孔子“不假神道而为教主”。他认为,世界上的宗教虽有多种,但只有孔教和佛教是更为根本的,而耶稣教、伊斯兰教以及“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3](P178)孔教是“阳教”,它顺乎天理自然和人情;佛教则是“阴教”,它逆人之情,去伦绝欲。他还认为,孔教是包容性的宗教,可以兼容其他各种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道教以及回教都可以继续存在,并不因孔教的官方地位而受到排斥。从内容上说,孔教也可以兼容其他宗教。孔教“本末大小兼养,重魂灵亦重体气”。“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粗细,无一不举”。这样的兼容性是其他宗教所不具备的。
康有为认为只有孔教最适合中国,能够救中国。他早年尊孔不舍佛,而到中老年后越加尊崇孔教,主张孔教救国。中年时期的康有为著书立说,上奏折,请尊孔子为教主,定孔教为国教。辛亥革命后,他继续鼓吹尊孔,认为“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若不敬孔教而灭弃之,则人心无所附,风俗败坏,礼化缺裂,法守扫地,虽使国不亡,亦与墨西哥同耳”。[4](P917)他认为,孔教是治与教兼备,既可以教化天下,又可以治国、救国。相比之下,耶稣虽然生于犹太,但不能救犹太人国家的灭亡,佛祖生于印度,也没有救印度于灭亡。他力主定孔教为国教,定孔子为教主,主张把“天”作为具有人格的主神来信仰,同时以孔子配天,作为教主同受崇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辛亥革命后中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的局面,也才能对抗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影响。
康有为的这一主张在实践中遭到了失败。1912年10月,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在上海发起孔教会,自任主任干事,创办《孔教会杂志》并任主编。尊孔读经活动受到了军阀政府的支持,袁世凯于1913年6月发布了《尊孔祀孔令》。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陆续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将孔教编入宪法,祀孔子行拜跪礼。这一尊孔逆流很快就彻底暴露其反动面目。传统信仰作为封建制度的护身符出现,它必须与封建皇权结伴而行,在五四时期已没有进步意义。袁世凯称帝于前,张勋复辟于后,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定孔教为国教的做法遭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反对。李大钊认为,这违反了信仰自由的原则。他说,人民有信仰的自由,古来以政治的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的,没有不失败的。在中国,历来是儒、释、道、回、耶杂然并传,含容甚广,这说明中国先民已经默认了信仰自由的原理,如果现在反其道而行之,凭空建立国教,那肯定是破坏了好的传统而会导致纷争。蔡元培认为,“孔教”一词不能成立。凡宗教都包含有某种神秘主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教育家而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不是宗教。陈独秀对定孔教为国教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反对包括孔教在内的一切宗教,认为一切宗教“无裨治化”。即使退一步说宗教有其好处,也不能只是肯定孔教一家。国家是四亿人的国家,宪法是四亿人的宪法,如果宪法独尊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就是“专横跋扈”的行为,必将引起社会的纷争甚至冲突。可见,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是矛盾百出、不合时宜的。
四、宗教信仰能否救中国?
在寻找信仰的时候,许多国人想到了宗教。梁启超从讲信仰的重要性直接转入宗教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中国,“信仰问题终不可以不讲”,“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信仰是情感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产物;信仰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有了信仰就有了奋斗的目的,也就有了追求的感情动力。在他看来,宗教信仰不可废,“信仰必根于宗教”。[5](P144)宗教有两面性:一是迷信作用,这是不好的方面;二是道德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宗教以“起信”为本,注重人的感情,而伟大事业,比如救国救民这样的伟大事业,只有在伟大的激情中、在白热化的感情和意志中才能做出来。
梁启超认为,中国必须寻找一个“新信仰”,求一个“最高尚”的宗教信仰,这就是佛教。他信仰佛教,想把“佛法”作为近代中国人的信仰,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孔教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教育之教”,“主实行,不主于信仰”。他也不赞同中国人改信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感情格格不入,而且迂腐浅薄,其教义不够深微,不能“涵养万有鼓铸群众”。他也反对以哲学代替宗教,认为哲学讲的是怀疑,宗教讲的是相信,二者根本不同,故哲学不适宜立身治事。
他从多方面阐述了佛教的优越性:佛教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独善”,“入世而非厌世”,“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自力而非他力”,等等。他认为:从政治上说,佛教有益于“群治”和“治事”;从文化上说,佛教是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是最崇贵、最圆满的宗教;从自然科学上说,科学的发展与佛教教理相暗合;从哲学上讲,佛教的哲理最圆满。总之,佛教的基本道理是“宇宙间唯一真理”。
章太炎主张用佛教信仰来增进人们的信心。他反对基督教,认为将上帝定于一尊与民主观念不合,而且基督教神学与自然科学不能相容。他宣传无神论思想,反对上帝造人说,否定神不灭论。他认为,宗教分有神教与无神教,佛教属于无神教,人们崇拜释迦牟尼就像崇拜孔子一样,是“尊其为师,非尊其为鬼神”。他还批评了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的做法,斥之为“怪妄”,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认为,孔子作为文人的崇拜对象,就像萧何作为官吏的崇拜对象、鲁班作为木匠的崇拜对象一样,不过是祖师的意思。孔子是宗师,而不是教主,如果将孔教树为宗教,就会堵塞智慧之门。
通过发起宗教信仰来振奋人民、拯救国家民族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主张无神论,认为宗教信仰并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前,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不信佛且对佛教神学进行一定批判和揭露的,主要有朱执信、陈天华、孙中山、胡适等人。
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也颇有特色的是蔡元培以哲学和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当时一些留学海外的人,看到西方社会进步,就想引入基督教让中国人来信仰。那么,中国社会的救助是否需要某种宗教?蔡元培对此做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宗教是在人类早期愚昧时期出现的,是人的认识不发达的产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将失去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他反对用任何宗教来作为中国人的信仰。
1917年8月,蔡元培做了一个《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他先从宗教的作用谈起,认为宗教不过是人的精神在知识、意志和情感三个方面的作用。在原始时期,人类的知识附丽于宗教,以粗浅的方式来解答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疑问。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知识开始脱离宗教而独立。人类的意志在开始时也是附着于宗教的,人们从宗教神学中获得自己道德观念的基础,后来,人们开始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道德问题,使道德(意志)从宗教中脱离出来。同样,人类的情感开始也存在于宗教之中,美术往往是宗教中的美术,但人类的情感也不会永远附丽于宗教,美术等活动作为人类情感的表达,也日益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他对美育寄予了很大期望,认为宗教在人生中主要起一种感情的作用,美育也可以起到此种作用。美育能纯洁人的感情,陶冶人的性情,使人的行为变得高尚,升华人的精神境界。而且美具有普遍的精神价值,超越人间利害,可以淡化人的功利心。总之,美育能够发挥宗教的感情慰藉和升华作用,而没有宗教之弊。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后来又提出了以哲学代宗教之说。他说:“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依赖鬼神的宗教。替代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这种哲学主义的信仰,乃完全自由,因人不同,随时进化。”[6](P63)他还在《简易哲学纲要》中说:“哲学自疑入,而宗教自信入。哲学主进化,而宗教主保守。哲学主自动,而宗教主受动。哲学上的信仰,是研究的结果,而又永远留有批评的机会;宗教上的信仰是不许有研究与批评的态度。所以哲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7](P462)他认为,哲学之所以能够代替宗教,是因为二者“同源”,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都涉及知、情、意三个方面,二者的研究对象也相同。他还说:“以自由选择的随时进步的哲学之信仰,代彼有仪式有作用而固然不变的宗教信仰。”[8](P226-227)
后人往往更重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而不大注意其“以哲学代宗教”的观点。其实,讲得比较通的还是后者。以哲学代宗教,有其基础,是在信仰层面上谈问题,哲学信仰代替宗教信仰讲得通。而美育代宗教其实指的是用艺术的作用来取代宗教所起的感情慰藉作用,而不是把艺术作为一种信仰来取代宗教信仰。蔡元培的意思不是以非信仰的东西来取代信仰,不是认为信仰没有必要,而是认为宗教信仰弊端太大,应该用另一种更为合理的信仰来代替,这就是哲学信仰。
胡适也反对以宗教信仰救中国。他较早地转向无神论,写有《我的信仰》一文,称自己从十一岁时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胡适用实验主义方法来看待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问题,包括信仰问题。该方法有三个步骤:一是用来确定事物的意义,二是用来确定主观的意义,三是用来确定信仰的意义。他认为,对于一种思想,应先用这种方法确定它所指的事物是否真实,接着再来考察这个观念本身是否明白和有意义,最后才来决定对它是否信仰。只有当事物、观念的意义明白确定之后,才可以进入第三个步骤。胡适批评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的《信仰的意志》一书,批评詹姆士在宗教问题上不忠实于实验主义,因为他认为只要上帝的观念能使人类安心满意就说它是真的。
当然,胡适有过一种“新宗教”的说法,但他说的是广义的宗教,认为宗教不必以鬼神为本。他在评论西方宗教的发展时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西方宗教观念中的迷信成分越来越被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且连基本观念即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也动摇了,被新宗教所代替。他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9](P314)他自己还提出过一种“社会不朽”论的新宗教。他认为人是追求不朽的,宗教追求的是神的不朽,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前者虚妄,后者模糊。于是,胡适提出一种“不朽”论,就是“社会的不朽”。他认为,个人是有限的、必死的,而由个人的“小我”组成的“大我”即社会,则是不朽的。个人只有在社会的不朽中才能找到自己小我的不朽。他反对出世,主张入世,强调社会,重视人为,主张为人、为社会和人群尽力的无鬼神的不朽论。胡适说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的“宗教”。
五、“科学主义”:朦胧的科学信仰
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发生过一次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又称“科学与玄学”论战。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断言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4月,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反驳,认为人生观应受科学原则的支配。接着,许多著名学者相继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这场论争具有明显的信仰冲突的性质,实质上是一场关于中国人应选择什么样的信仰的论战,是中国人是否应该选择科学性的信仰的论战。李泽厚写道:“科玄论战的真实内涵并不真正在对科学的认识、评价或科学方法的讲求探讨,而主要仍在争辩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信仰。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所以这次学术讨论,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思想影响大于学术成果,它实质上仍然是某种意识形态之争。科学派实际上是主张科学来作为意识形态,玄学派则主张非科学的形而上学来作为意识形态。因而这是一场信仰科学主义的决定论还是信仰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的争论。”[10](P58-59)
就玄学派来说,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中国人的“科学万能的信仰”。他认为,“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现在应该是物极必反了。科学是讲因果的,如果学生头脑中塞满了科学的观念,他自己就会被因果所缠绕,忘记“人生在宇宙间独往独来之价值”。李泽厚认为,“科学派强调科学方法、态度、精神,强调‘科学的人生观’,实际上具有建立信仰的意义。”[11](P58)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6月本院住院的88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男51例、女37例,平均年龄(49±3)岁。所有患者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空腹血糖≥7.0 mmol/L或者餐后2 h血糖≥11.1 mmol/L。排除了同时患有可以引起肾脏病变的其他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同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70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39例、女31例,平均年龄(48±4)岁,排除了糖尿病以及心、脑、肝等疾病以及可以引起肾脏病变的其他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
自从19世纪末变法维新以来,“科学”在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地位,并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朦胧信念。胡适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12](P10)这反映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情形。但在20年代初,国内思想界则出现了对于科学的反思或反动,随之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个思潮起因于梁启超的一次西方游历。1919年年初,以梁启超为首的一行人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随后在欧洲各大城市进行了旋风般的旅行。那时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社会生计的困窘、思想的混乱给梁启超等人以很大触动,使他们开始反思西方战祸和其他社会危机的根源。梁启超把这归之于西方人的科学主义信念,归结于“科学万能论”。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科学发展、工业革命以及社会变动的加剧,使人们的内心生活发生动摇,宗教及哲学失去了权威,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倒可以救西方文明之弊。回国后,他们发表一系列论著,从西方文化的热烈介绍者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来。1923年的人生观讨论不过是再次把这个问题突显出来罢了。
科学派主将丁文江力主科学万能,即科学方法万能,而且捍卫科学信仰的态度异常坚决,因其主张上有些绝对,言辞也相当尖锐,故而引起一些人对他的批评。有人说他宣扬的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哲学,是相信科学万能的信仰。梁启超批评他说:“在君(指丁文江——引者注)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在君那篇文章,很像专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学者态度,这是我替在君可惜的地方。”[13](P141)林宰平也批评道:“现在在君先生的野心可就更大了,他不但想组织一系列的学问,还要把科学来统一一切。看他口气,简直像个教主,凡是宗教都有统一的欲望,他用同一的形式同一的信仰,把人生圈入一定的轨道中,以为天地间真理一口吞尽,再也没有例外的了,在君先生想用科学的武器来包办宇宙,上自星辰日月下至飞禽走兽,敢说声不依我的科学,我都认作邪魔外道,非严重讨伐不可。”[14](P157)其实,丁氏语言和态度的尖锐,正说明他不是一般地参加讨论,而是在捍卫一种信念,一种历来为中国所缺乏、好不容易经过血的教训而在中国出现的科学信仰的萌芽。
这种论战促使主张科学的人们进一步地明晰自己的科学主义信念。论战开始的时候,问题集中在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上面,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持否定态度,而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则持肯定态度。围绕这个问题,论战面越来越宽,生出许多枝蔓,以致后来的人们认为他们的争论没有找到焦点。胡适表示对此种讨论不满意,认为讨论应该具有建设性,应该从正面展示出科学的人生观应该是怎样的。他赞扬吴稚辉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文,认为文章首次提出了一个科学化的、比较系统化的世界观(人生观)。胡适自己在这个科学人生观的基础上再作补充,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科学的人生观”。[15](P23-24)胡适认为,科学信仰并不等于都是已知的科学知识,它里面也可以有关于未知领域的大胆假设。“我们信仰科学的人,不妨也做一番大规模的假设。只要我们的假设处处建筑在已知的事实之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最满意的假设,可以跟着新证据修正的,——我们带着这种科学的态度,不妨冲进那不可知的区域里,正如姜子牙展开了杏黄旗,也不妨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16](P17)
通过这次讨论,人们心目中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信仰进一步清晰了,初步显示出科学信仰的优势,但它的局限性也日益清晰起来,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初步的朦胧的科学信仰。
六、脱颖而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五四时期,人们对封建主义失去了信仰,而对西方资本主义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再崇拜,于是,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趋向于社会主义。李维汉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7](P108-109)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他们的朦胧信念,因为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引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非常之多,可以说各种思潮都有人研究和信奉。“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涌而来。”[18](P179)
五四新一代青年不仅在思想上求新,而且在行为上也积极探索,他们想通过组织一些小团体来追求和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当时,各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小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如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的“觉悟社”,以及“工学会”、“共学会”等。“这些小组织小团体的‘宗旨’不一,大多相当模糊笼统,如‘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新民学会)等等,但在这模糊笼统中,却又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新的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的一种实践性的向往和追求。”[19](P21)当时影响最大的当属“工读互助团”,有数百人报名参加,这个团体施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从朦胧的科学崇拜到自然主义的科学信仰,再经过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信仰,最后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信仰,这是当时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信念的转变过程。只有到了这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科学信仰才进一步明晰起来,显示出真实面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脱颖而出。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现了科学主义的朦胧追求与社会主义朦胧追求的汇流,它既是科学的信念,又是社会政治的信念,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信仰体系。
科学派追求科学信仰无疑是进步的,但科学派主将丁文江是个自然科学家,其他人甚至包括胡适、吴稚晖,也都对于人类社会没有真正的研究,他们所持的不过是生物进化论及其在社会上的粗浅应用。因此,他们手中的科学工具只是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的求实方法而已。他们不可能真正拿出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因此,尽管他们主张建立科学信仰、反对非科学非理性信仰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科学信仰建构的任务。他们都不懂得并且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错过了唯物史观这样一个分析社会和人生的科学工具。而沿着唯物史观这个大方向走下去,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建立中国人科学信仰的道路。
李泽厚对于这个过程曾作出精辟的概括:“科学派强调人生观以及一切精神文明都可以通过科学分析得到说明和了解,都可以作出因果律的决定论的‘科学’解释,这就预告着以一种建立在科学的宇宙观、历史观基础上的决定论的‘科学的人生观’来作为信仰指导人们生活、行动的可能。而这,后来不就正是马克思主义么?人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来作为人生的向导,不也正符合‘科学派’的主张么?这,大概是出于‘科学派’的意料的。”[20](P60)“科玄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五四时期‘赛先生’(科学)在这里和以后日益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代称;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科学(唯物史观)成了一个东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和以后不久,便迅速被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所欢迎。它取代了上代人所崇奉信仰的进化论。”[21](P64-65)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信仰的选择走出了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的范围,日益变成了一种由不同的党派所引领并包括广大群众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运动,采取了激烈政治斗争甚至大规模军事斗争的形式。这是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所意想不到的。但这是历史的逻辑,它有自身的行程和结果。在20世纪上半期,经过激烈的思想理论斗争,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新中国的主流信仰。这是中国人信仰史上的重大转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转折,预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1]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康有为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6]罗章龙编:《非宗教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
[7][8]《蔡元培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9]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0][11][19][20][2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12][13][14][15][16]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7]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8]丁守和:《中国现代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