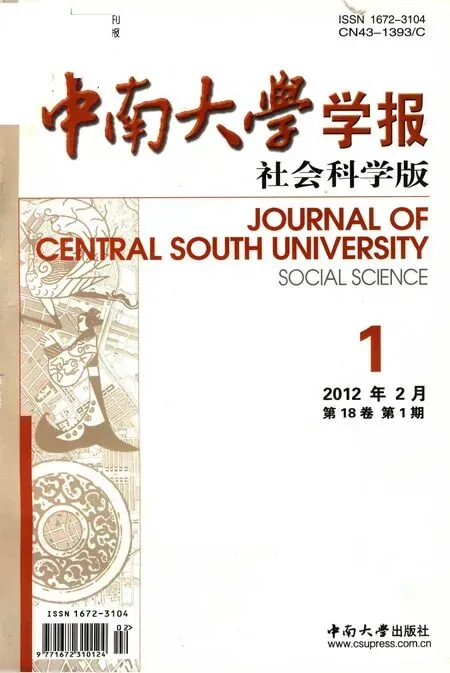论反垄断法之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的协调
丁国峰,毕金平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 合肥,230039)
一、反垄断法之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的龃龉
(一)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的固有缺陷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有对垄断案件进行调查和惩处的权力。对垄断违法行为的判定离不开相关垄断专业知识和具体技术标准的支持,其全过程完全集中于公共执行机关手中。即使对执行机关所作裁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该诉讼并非是对垄断案件本身违法的审查,而是对执行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考察和判别。因此,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在实施反垄断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现状不可能改变,这种“行政执法为主导”的模式阻碍了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促进公共利益和维护有效竞争,公共机关执行反垄断法固然为最有效的途径,但由于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存在执法人员数量有限、专业性水平不高、办案经费紧张等问题,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权配置严重不足,欠缺足够的执法能力。受到执法资源的约束和限制,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不得不集中相对有限的资源来处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垄断行为案件,而对于单个私人主体而言非常重要的案件往往得不到反垄断公共执行机构的重视,甚至被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意忽视。反垄断公共执行机构遭受财政资金的限制愈多,其在执法过程中的诚实、勤勉和尽责的表现和执行能力的发挥愈为低下,公共执行机构被迫在财政能力与执法政策目标之间寻求适度妥协,确保执行的重点性、有效性。[1]反垄断公共执行机构还时常遭受外在社会利益集团的不当干扰,或是迫于政治压力或是遭被管制者的游说,可能成为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工具,同时其还可能面临反垄断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也存在自身私利所导致的懈怠、失职,甚至消极懒惰的局面。[2]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多头执法的现状必然引发公共执行机构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不良倾向不易彻底根除。另外,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部门之间可能发生争夺反垄断执行权或“通过彼此商谈、上级协调确定执法权的归属”,[3]其结果要么恣意放弃执法权要么出现利益“一体化”的格局,必然会损及反垄断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以上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所具有的各种缺陷会明显或潜在降低反垄断法的实施效率。
在行政主导的反垄断法实施模式下,私人实施更多地被公共执行所侵吞或取代,私人实施的威慑性和必要性难免会遭到公众质疑。若私人主体人人皆想获得赔偿和惩罚性报酬,则为寻找违法行为者而付出的资源还会出现浪费,虽节约了行政成本,但其是建立在司法成本激增的代价之上。由于垄断协议的隐蔽性以及私人调取证据的困难,私人往往可能难于获得昂贵、但具社会价值的信息系统(意图垄断的电话记录和电子邮件合同等),而公共执行机关对此类执法构成天然垄断,自然公共执行在收集信息资料的手段上比私人更有效和更占优势。收集信息、举报违法者和阻止垄断行为者对私人的报复(主要表现为供货商拒绝对批发商或零售商提供货源或供应产品)可能需要运用强制力,而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私人主体无权使用强制力,更不能实施限制人身自由之措施,因此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之范围和方式极其有限,不能有效防止“政府失败”,即不能监督公共机关的懈怠和疏忽。因为根据政府管制的俘获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执法者同时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收买,从而疏于或怠于查处垄断违法行为。另外,我国竞争文化理念并未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随左右而深入民心,市场主体、社会民众对“竞争”充满着敌意或冷淡情绪,极易引发他们对反垄断法这种“公法”的私人实施方式的正当性的种种疑虑。[4]由于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把握,损害赔偿的计算具有相当复杂性,反垄断法私人实施还存在技术上的不成熟。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可弥补公共执行的不足,但私人实施也存在自身的缺陷。反垄断法多倍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会引发过度私人实施的情形,导致威慑过度与经济上的无效率,同时也鼓励了私人实施的爆炸性增长,产生各种缠讼、扰讼、滥讼的现象。“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除了可能会发生过度威慑和执行的负面效果以外,它还可能会被私人当事人滥用,以实现敲诈(extortion)和破坏竞争(subvert competition)的目的。”[5]私人实施可能被竞争对手用作战略性限制有效竞争的行为。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相关规定过于简单,根本不可能起到辅助、补充反垄断法公共执行的目的,更难以起到制衡反垄断法公共执行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为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并奠定了实践基础,但并未对私人起诉权作出任何具体明确的规定。从现有规定来看,垄断行为的民事责任与我国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步,从法律实施来看甚至还显得单薄、落后,私人当事方发动反垄断私人诉讼虽有较大空间,但必然面临许多制度性障碍。例如,当被侵害的经营者(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违法行为损害时,受害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是否能直接受理呢?由于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且私人实施依赖于公共执法,这两者之间很难协调、衔接、合作与发展。2011年4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规定(征求意见稿)》),[6]虽进一步明确了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若干具体规定,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激励性不足的难题。原告举证责任的过重、损害赔偿的非惩罚性、诉讼成本的高昂等都会使私人主体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处于得不偿失的地步,导致私人实施缺乏动力性的制度支持,私人诉讼的热情不高。
(二)缺乏合理的公私协调机制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反映的是以司法为主导的反垄断法实施模式,而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机制反映的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反垄断法实施模式。在美国,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不能直接对垄断违法行为者直接进行罚款处罚,主要是以公诉人的身份向联邦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或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法院成为实施美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力量。而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并不发达,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采取的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模式,在此种情况下,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之间并不是相互辅助、相互补充的关系,而是比较明显地表现为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相互替代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不仅规定了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的二元实施体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合理的手段对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进行适当的分工、协调与合作,来优化反垄断法的实施程序,促进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然而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与公共执行之间并没有任何在实施程序方面的分工与合作,缺乏两者之间的合理衔接与协调,可能导致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存有矛盾和冲突,最终从根本上影响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以及竞争政策目标的实现。这种明显缺乏相互协调的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的反垄断法执法局面,主要源于失衡的反垄断法公私实施机制。从我国反垄断法的条文可知,涉及公共执行的条款共有17条,它们分别是第9、10、38~49、51~53条,而涉及私人实施的规定仅有第 50条。这说明对私人实施制度 与公共执行制度的设计方面更多地偏重于公共执行,这不仅源于我国悠久的行政传统优势,更重要地是传统行政模式的惯性思维在起作用,即行政精英与行政资源的优越和丰富。从第50条的规定来看,其内容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对私人实施的主体、范围、方式、对象等均缺乏明确的规定,自然无法起到补充反垄断公共执行的目的,最多只算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文。当前,我国反垄断法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之间缺乏有机协调与配合,这两种执法方式之间还存在衔接性不足的问题。自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国家工商局、商务部及其他部委颁布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规定、指南或暂行办法共有十几项,①到目前为止,涉及私人实施的只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规定(征求意见稿)》。从这些法规的内容看,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处于优势、主导地位,而私人实施则处于弱势、辅助地位。这些法规也没有明确对这两种执法方式之间的配置与协作问题进行规定,公私协调机制明显欠缺,即并未建立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协助的具体实施条例或执法指南。缺乏合理衔接的公私执法模式将降低反垄断法的实施效率,无论是公共执行还是私人实施都不可独霸反垄断法的施行权,只有实现这两者的合作与协调、共同运作,才能有效威慑、惩罚违法垄断行为者。
《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了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具体途径与程序,但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与公共执行之间的合理边界、各自范围还模糊不清,缺乏法定的权力配置,极易引发两种执行方式上的冲突。反垄断法公私执行缺乏协调机制主要体现为:其一,未有统一明确、详细具体的私人实施制度规定。现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规定(征求意见稿)》与反垄断法第50条的规定无法全面指导私人实施反垄断法。其二,未优化反垄断法执行程序。现有的反垄断法实施程序只偏重于行政执法,私人实施规定中也同样缺失这两种执法方式之间的合作、协调与分工。[7]其三,未完善两者之间具体衔接的制度内容。《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规定(征求意见稿)》虽规定了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的相关程序,但并未设置“约束力规则”,②即并未规定反垄断公共执行机构的裁决结果或调查证据可作为私人主体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法定依据。根据当前的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裁决的结果或确认的事实对正在法院审理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原告当事方可委托专门机构或专业人员作市场调查或经济分析报告,并通过法院的审查判断来决定是否采用。缺乏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机构的在调查与取证方面的直接参与、运用,反垄断私人诉讼无法独立进行,这也不利于鼓励私人后继诉讼在我国的运用。
在行政主导的实施模式下,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往往并不发达,无法与公共执行相协调。私人实施的主要方式为对垄断违法行为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私人实施程序机制和手段方式比较单一、简单,缺乏灵活性,也无法弥补反垄断规则的不确定性或是反垄断法的原则性。在行政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性。例如,在以行政决策为基本模式的欧共体,欧盟成员国中的私人主体很少提起反垄断私人诉讼。[8]就是在奉行“公正交易委员会中心主义”的日本,有关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权的规定也没有能发挥机能。[9]在此种情况下,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已凸显出足够的威慑力和惩罚功能,私人实施的补偿、规制功能与更深层次的威慑、阻吓功能似乎显得并不重要,看上去被公共执行所吸收、所代替,进一步扭曲了设计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的应有作用。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强调的是行政权的提前介入,私人实施则强调的是司法权的重要性。对于既可以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主管又可以由私人主体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同一案件,在客观上就形成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行使认定垄断行为违法性的权力,难免在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的适用上产生直接的冲突。同时,由于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的目的、标准和理念不同,必然会导致反垄断法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在运行过程、实施程序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二、构建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合理协调机制的设想
(一)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对公共执行的协助
无论是公共执行还是私人实施,都不能对竞争法的实施进行垄断,它们必须共同运行才能有效威慑、调查和惩处违法行为者,并且赔偿违法竞争行为的受害者。[10](252)公共执行和私人诉讼相互配合和协调运转,才可能实现最优实施效果。私人实施对公共执行的协助主要表现为私人主体收集和向有关公共机关提供垄断违法行为相关信息与证据的行为。公共执行应该采用战略执行方法,偏重于对竞争产生重大影响或具有重要意义案件的处断。因为国家机关预算资金、执行机关的人力、物力都是很有限的,“政府失灵”问题时有发生,公共执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垄断问题,也不可能总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中心。公共执行可以弥补私人实施的缺口,因为反竞争行为的受害者往往不愿就那些对其损害不大,诉讼成本高而证明责任和负担极大的案件提起诉讼。由于私人主体比公共执行机关更加容易获得侵权者违反竞争法的信息,能迅速地了解供货方的垄断行为,因此应该建立和健全私人主体对反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向公共执行机关举报制度,这其实也是私人主体协助竞争主管机关执行反垄断法的行为。目前我国《反垄断法》第38条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对涉嫌垄断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举报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该规定过于简要,应该进一步具体化私人主体实施举报的形式和程序。在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司法程序中,法院既应尊重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的裁决,又应依法审查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的裁决是否形式合法。同时,法院应依法受理并未经过反垄断执法程序认定和处理的涉嫌垄断违法行为的案件,但对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终局裁决程序认定并不构成垄断行为性质的案件,则不应允许私人主体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11]
利用私人获取信息的便利对垄断行为者施加压力,这需要公共执行机关及时快速地调查被举报的案件,并且及时将调查的结果和受理的情况向私人举报者反馈。经公共执行机关查证后,对举报行为属实的反竞争案情,公共执行机关应该对举报者给予适当的奖励,并且为举报者的个人信息保密。特别是对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私人主体一旦举报或控告,公共执行机关应立即发动执行程序。如果公共机关怠于执行,私人主体有权直接对违法行为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停止违法行为或赔偿损失。通过制度设定,赋予私人举报者有权对违法的公共执行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对其失职或违法行为向其上级机关进行举报,要求监督或提出复审。
(二)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对私人实施的支持
公共执行对私人实施的支持主要是指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机关对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亲自参与,或给予的援助。在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案件中,私人主体由于信息不畅通、自身技术水平有限或势单力薄等原因,加之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限制,其在收集证据或调查取证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无法独立完成。因此,证明责任和证明负担往往成为决定私人实施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机关拥有广泛的、强有力的调查权力,在收集证据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在指控违法行为时非常容易获得成功。如果在私人主体原告不能取得证据之时,公共执行机关能及时对私人原告提供支持和协助,这将大力促进私人实施,也方便私人主体起诉,增大其胜诉的机率,增强反垄断法的威慑效力,从而有利于其权利的实现。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应与反垄断法公共执行进行全面协调与合理衔接,“建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参与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制度,以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代表公共利益表达其对相关竞争政策和具体专业问题的意见,供法院参考”。[11]
各国为了方便私人提起后继诉讼,往往在法律中规定了约束力规制或表面证据规制,即竞争主管机关认定的违法行为对法院有约束力或可以作为表面证据。[10](244)由于反垄断案件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法院一般会认可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机关裁决的效力,因为私人主体不同于公共机关,其不易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不具有强制力,更不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公共执行机关对反竞争行为证据的收集具有优势,而且对有关事实的认定也具有优势,所以行政执法机关所作的违法行为裁决在私人实施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反垄断主管机关提供相关案件意见和资料充足的情况下,更便于私人实施案件的审理。反垄断主管机关先前所作的违法垄断行为裁决会给潜在的私人市场主体提供相关反垄断法实施信息,鼓励私人原告主体提起私人诉讼。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方式赋予反垄断主管机关的先前裁决在私人实施中的效力,或者认可其裁决的效力。如美国《克莱顿法》第5条允许三倍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引用具有最终效力的裁判用作表面证据使用,以证明违法行为的存在、损害的结果及其因果关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第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但我国《反垄断法》应该对反垄断行政主管机关的裁决效力作出进一步规定,为私人当事人提起后续诉讼奠定法律基础。私人主体的后继实施主要是指私人主体借助于政府先前的裁判或调查和处理结果去控告各类反竞争行为者,以获取民事救济或损害赔偿。通过设立初步证据规则或约束力规则来实现对私人实施的支持,私人实施如果能充分利用公共执行的初步成果,将会大大促进私人实施的效力,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反垄断法的威慑性实施效果。
(三)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对私人实施的适度限制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最根本目的在于私人市场主体能从反竞争行为中获得损害赔偿,并未考虑到私人实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私人实施天生就具有片面性,很可能面临被滥用和过度适用的危险。反垄断法应赋予公共机关优先执法权,并将公共执行机关的诉讼或调查处理作为私人实施的前置程序,即规定公共主管机关优先于私人市场主体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权力,并对公共执行机关提供的违法信息承认其效力优先性,在法院审查程序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美国通过初步证据规则,而英国和德国通过约束力规则来激励私人主体开展反垄断法案件的后继实施。公共执行和私人实施的合作与协调对私人当事人的后继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反垄断主管机关的后继实施在实践中比较少见。在私人实施后,如果反垄断主管机关发现该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应该积极发动公共执行程 序,否则就是懈怠或失职之表现。总之,我国反垄断法具体实施条例或细则的制定过程中,以及将来反垄断法的修改过程中应该考虑并引入约束力规则,即明确规定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处理决定和认定的违法事实对法院具有约束力。
对私人实施的限制还表现在公共执行对私人实施的参与和干预过程中。反垄断法应该进一步规定公共执行者有权干预私人市场主体的实施活动,公共执行者有义务对私人实施的特定案情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准许公共执行机关在适当的条件下全面接管或终止私人实施法律的活动。公共执行对私人实施的干预程序,即公共执行机关可依法向法院提起驳回私人起诉的建议,有权对私人实施中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甚至依照特定程序授权公共执行机关代替私人市场主体的诉讼原告资格,在私诉过程中将其变更为公诉。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对私人实施的干预,有利于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监督,便于对私人实施或私人诉讼进行审查,防止私人实施主体的策略行为。虽然私人的法律实施从外在表现形式上可能有利于公共利益和目标的实现,但其真正目的和动机并非仅限于此,私人实施法律的行为还可能是一种策略行为,即私人实施法律的过程中,私人追求私利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很可能会置立法当初所追求的社会公益目标于不顾。私人实施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很容易被被告所收买,进而与被告达成表面的和解协议,通过该协议暗中给予私人原告大笔的好处费而维持垄断局面,甚至暗中进一步加剧垄断现状。与此相类似,一名竞争者起诉另一家企业的动机,或许是为了与对手形成某项共谋协议,或达到其他策略目的,其实施活动与促进竞争之间或许没有任何干系。[12]当然,不利于公共目标实现的策略行为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决私人实施的作用,对私人实施制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来避免的,最根本的应对策略和手段是加强公共执行机关对私人实施过程的监督和干预,避免私人实施偏离公共目标而成为滥用或谋取私利的手段。通过对私人实施制度的精细设计和严密监管,逐步减少私人实施的策略行为,同时对合法的私人实施进行引导和鼓励,避免对善意的私人实施构成威胁或打击。
为了制止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过度滥用,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公共执行对私人实施进行适当限制是合理的。公共机关主要是通过事前审查、事中参与和事后监督等制度对私人实施进行干预和限制。如,应该为公共执行机关设置某些职权,及时监管和调整那些不宜由私人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一旦公共执行机关接手垄断案件,私人实施主体不得再采取措施或进行干预;为了掌握私人实施现状,公共执行机关可对某些重大反垄断案件要求私人将实施情况及时向公共执行机关报告。在私人实施过程中,加强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机关的监管,授权其查阅私人实施主体获取的相关证据资料,参与私人主体起诉的全过程,旁听私人庭审诉讼,及时向法院提出法律请求或提供建议材料等。为了防止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不当运用,制止以要挟他人、为牟取私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滥用,应该赋予公共执行机关相应权力来处理与反垄断案件有关的行为,如对不合法或不正当调解、和解协议提出异议,处罚相关当事人,宣告相关行为违法或无效,没收违法所得等。[13]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对反垄断法私人实施进行适度限制和合理支持,私人实施同时协助反垄断法公共执行,这不仅可实现反垄断私人诉讼与反垄断公共执行之间的合理衔接与协调,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发挥反垄断法的功效。
(四)避免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之间可能的冲突
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将“实施垄断行为”作为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法律对由谁来认定垄断行为却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传统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与公共执行相比,明显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私人实施实际上指把属于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行政主管机关)管辖的案件分离其中部分,转给私人实施主体自主处理或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也可以说是司法权先于行政权介入反垄断案件或司法权与行政权平行介入反垄断案件。在行政权与司法权互相制约、关系良好的美国,司法救济使法院最终处于实施反垄断法的主导地位,美国私人实施制度运行良好,几乎很少存在问题。但在实际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在行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冲突,因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都有权认定垄断行为的违法性,这必然会导致二者在认定和行使权力上的不一致。由于实施法律的标准和理念难以统一,甚至会出现冲突的可能,这种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会使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难以充分保护。另外,司法权和行政权行使的具体程序不一致,导致其具体实施程序上不协调或者冲突。在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如果私人实施主体也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此时反垄断公共执行是否应该让位于私人实施呢?在行政争议中,为解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间的冲突,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权优先于行政权,诉讼优先于复议。但在垄断案件的审查中,是否可以借鉴这一作法呢?[14]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成熟的专业执法经验,可以对反垄断分析中的诸多技术性问题作出评判,加之我国诉讼文化的缺失和激励诉讼制度的空白,促使我国应当借鉴日本以政府公共执行为主导、私人实施为辅的实施模式。另外,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对垄断案件的审查具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行政权优先于司法权为更加可行的选择,这样我国可采用日本的做法,即推行行政程序前置制度。如果私人实施主体认为反垄断法公共执行机关的处罚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可以就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的错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启动抗告程序,对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所作的处罚结果进行司法审查。当然,行政程序前置的设计方法存在很大的弊端,需要在司法机关积累丰富的执行经验后,对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保障司法审查权优先于或平行于行政执法权的行使。无论是否设计行政程序前置的方法,反垄断法的实施都应设定终极的司法审查通道,私人主体可以基于自身成本——效益作出路径选择,决定是否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这样可把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有机地连接起来,既可免除私人当事方的故意或过失举证责任,又能节省宝贵的司法资源,同时又可减少法律实施中的冲突与矛盾。
由于宽恕制度的存在可能导致反垄断私人实施更加频繁,也会影响到宽恕制度的实施效率,从而引发反垄断法公共执行和私人实施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宽恕政策和私人后继实施之间的潜在冲突,增强反垄断法实施效果,美国国会完善了反托拉斯刑事处罚的相关法律规定,加大了对垄断行为的惩处力度。法律规定,适用宽恕政策的主体只对受违法垄断行为影响的贸易额中其所占的比例负责,并且其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仅限于单倍赔偿责任。为了实现单倍损害赔偿的利益,公司等市场主体必须与发动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原告合作。为了解决宽恕政策和私人后继实施之间的冲突,欧盟对宽恕政策的施行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为了鼓励宽恕/豁免申请者继续提供情报,委员会现在授权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申请和详细陈述案件事实。[15]欧盟委员会还在《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绿皮书》中提出了公共执行解决宽恕政策问题和私人后继实施问题之间冲突的三种方案:其一,排除对宽恕政策申请的证据开示,从而为作为宽恕政策计划的组成部分向竞争机构提交的文件能得以保密;其二,针对宽恕政策申请人提出的任何损害赔偿请求给予有条件的扣减,针对其他违法者——他们以连带方式对全部损害负责的请求保持不变;其三,免除宽恕政策申请人的共同责任,因此限制申请人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风险。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将宽恕政策申请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在与其在被卡特尔化的市场中份额相当的水平。[16]合理平衡的反垄断法公私实施体制为宽恕申请者同样提供最佳的激励,成功的宽恕申请者或告密者可获得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责任减免的激励,同时其还可获得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减轻的回报。宽恕申请者在私人实施中不可能比其他违法垄断行为者承担更多更严厉的责任,这既保证了宽恕制度的有效性,又促进了反垄断法公共执行与私人实施之间的相互协调。
注释:
①参见中国反垄断法网中学习园地栏目下的反垄断法规,http://www.antimonopolylaw.org/more.asp?channel=%D1%A7%CF%B0%D4%B0%B5%D8&type1=%B7%A8%C2%C9%B7%A8%B9%E6,2011-6-16.
②例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33(4)条明确规定,当原告根据《反限制竞争法》或《欧共体条约》第81条或第82条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时,一个竞争主管机构在其决定中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对于法院具有约束力。英国《2002年企业法》第47A条规定,公平贸易办公室或竞争委员会对违法行为的决定对竞争上诉法庭具有约束力。参见王健:《关于推进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思考》,《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第23−34页。
[1]王健.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及其实现——兼论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J].法律科学,2007(4):104−111.
[2]MATTHEW C,STEPHENSON.Public regulation of private enforcement: the case for expanding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EB/OL].http://www.virginialawreview.org/content/pd fs/91/93.pdf,p.107,2011-6-18.
[3]李俊峰.反垄断行政执法的资源,意愿与威慑力[J].法治论丛,2010(1):17−20.
[4]郑鹏程.论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之困难及其克服[C]// 王晓晔.反垄断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64.
[5]王健.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局限性及其克服[J].东方法学,2008(4):114−121.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EB/OL].http://www.law-lib.com/fzdt/newshtml/20/20110426091143.htm,2011-05-05.
[7]王健,朱宏文.构建公私协调的反垄断法执行体制——中国的问题及出路[C]//李明发.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第1辑).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22.
[8][美]戴维 J.格伯尔.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M].冯克利,魏志梅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79.
[9][日]村上政博.日本禁止垄断法[M].姜姗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96.
[10]王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基本原理与外国法制[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11]王先林.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协调[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 87−91.
[12]BRO DLEY J F.Antitrust standing in private merger cases:reconciling private incentives and public enforcement goals [J].Mich L Rev,1995(94):35.
[13]李俊峰.私人实施反垄断法问题研究[D].上海: 华东政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161−162.
[14]玄玉宝.简论美国反托拉斯法私人实施及我国取向[J].研究生法学,2008(5): 63−72.
[15]DONALD I,BAKER.Revisiting history-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priv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at we would recommend to others? [J].Loy,Consumer L Rev,2004(16): 403.
[16]GREEN PAPER-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the EC antitrust rules [EB/OL].http://europa.eu.int/com m/competition/antitrust/others/actions_for_damages/gp_en.pdf,2009-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