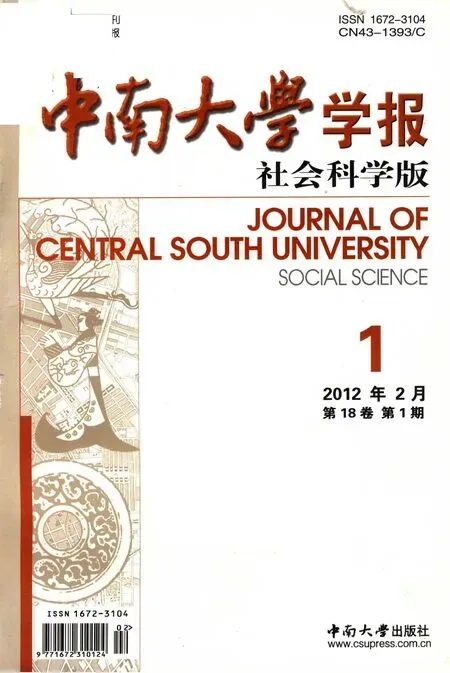论道学对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影响
吕锡琛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堪称研究、理解东方文化极为深刻的西方学人,他对易经、瑜珈和汉、藏佛教均有研究,对老庄思想和《太乙金华宗旨》等道教丹书尤为推崇。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不是从玄理的层面而是在心理学的框架中来讨论和吸收道学的智慧。但学术界对于荣格与道学之联系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其关注点多集中于荣格与道教内丹学的关系,有些评价还似显保守。①
我们认为,不应忽视或低估道学对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因子正可凸显中国哲学的特性、优长及其现代价值。荣格从道学中获得了哪些思想营养,而从荣格的探索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启迪?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对立统一思想对荣格的启示
道学的对立统一思想对荣格的研究具有解困破冰的意义。当荣格在集体潜意识理论研究等方面陷于困境之时,他读到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所翻译的道教丹书《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被这部中国著作的奇思异想深深迷住”。[1](71)故他在《金华秘旨》德文第二版前言中强调:“正是《金华秘旨》(即《太乙金华宗旨》)这部著作,第一次把我推到了正确的方向上。结合对中世纪炼金术的长期研究,我找到了在意识自我和集体过程中存在的联结点。”荣格对老子可谓推崇备至,他在自传的结语中称:“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见多识广的这位老者的原型是永恒地正确的。”[2](338)
通过《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研究,他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找到了一条实现人格整合的道路。荣格认识到,道教修炼是一个结合对立面的过程,而《太乙金华宗旨》这部著作就是一条能够“从对立面的对立中解脱出来的道路”,由此,荣格开辟出了一条整合意识与潜意识,促进精神的正常发展的道路。关于道学对荣格潜意识理论的影响我们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详论,在此我们首先从方法论的层面论述荣格思想与道学对立统一思想的联系。
对立统一思想是道家学派的基本哲学原则。《老子》第二章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恒也。”老子看到,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对立面皆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由此可以推论,对立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执着于一端、非此即彼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以这种思维定势去处理问题往往会导致刻板僵化,主观教条,激化矛盾等一系列的弊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语启示人们,如果人们一旦对于美丑、善恶产生分别之心,特别是了解到由它们所带来的一系列利害,必然会自觉地努力追求美和善,也会去争夺美、善之名,这种道德自觉意识的产生虽然有利于引导人们趋善弃恶,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亦有消极的一面,即人们会否认内心中的一些恶的东西,而掩盖自己内心的阴影。但掩盖和否认并不能真正驱除恶的阴影,反而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如此一来,岂不是“斯恶矣”、“斯不善矣”?
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智慧指引下,老子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处世之道:“不尚贤”、“和其光,同其尘”,更提供了一种可操作原则“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老子》第三章、第四章、第四十九章)这就进一步彰显了运用对立统一智慧的实际功效。如果以排斥的态度对待不善,其实并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包容不苛、不弃不离的仁慈之心才是医治心理疾病的良方,才能更好地挽救那些有缺点、有过失甚至有严重错误的人,真正化解人们心灵深处的郁结;而以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来处世治世,才有可能感化顽冥,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创建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和谐社会。
在道学对立统一思想的启示下,荣格从治疗方法上突破了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他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一书中深刻地批评西方人在这方面的误见:“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一旦从阴暗面去解释的话,那么明亮的一面已不复存在矣。很不幸的,佛洛伊德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其实,阴暗是光明的一部分,正和恶与善之关系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其逆亦真。因此,我愿不顾众人的惊愕,毫不迟疑地暴露我们西方思想的错幻和渺小……这便是一项东方人的真理。”[3](74−75)“有一千年之久的东方典籍能把富有哲理性的相对论介绍给我们。”[3](325)在这里,荣格虽然未具体指明这种“真理”出自哪一位“东方人”或“东方典籍”,但以荣格对道家思想的熟悉和推崇程度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荣格所说的“富有哲理性的相对论”的“东方典籍”当指老庄的学说。
《庄子》不仅发展了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强调“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庄子·则阳》),更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事物性质的相对性。如,在《齐物论》中,他从事物本身差异来说明事物认识标准的相对性:“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而在《秋水》中,他又从认识主体的观察高度和角度的不同来说明事物认识标准的相对性:“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这些思想的提出,让庄子成为公认的相对论鼻祖。
在荣格的心中,东方人这一“富有哲理性的相对论”有着极不寻常的分量,他称其“具有无比贡献”,“非常欣慰而且欢迎它的出现”,“根本没预料到它会对我们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力”因为正是这些思想为荣格提供了批判西方非此即彼“错误观念”的理论根据,提供了超越弗洛伊德理论之片面性的精神力量,让他认识到“阴暗是光明的一部分,正和恶与善之关系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其逆亦真”。[3](325)
在此基础上,荣格提出了著名的阴影理论,深刻指出了人类压制阴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如何正确面对阴影的思路。荣格认为,阴影(5hadow)是心灵中遗传下来的最阴暗的、隐秘的方面。它包括一个人违背道德的所有的体验和心灵内部所有最受压抑的或不发达的部分,是人格中的卑劣部分。所有个人与集体精神因素的总量,出于这些因素无法与被选择的意识态度共相并存,因此这些因素在生活中便被拒绝表现出来,因而就接合到一种相对自治的带有与相反倾向的“分裂人格”中去。“阴影将一切个人不愿承认的东西都加以人格化,但也往往将它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强加在个人身上——例如,性格中的卑劣品质,和其他不相容的倾向。”
荣格认为,对待阴影这一人格中的卑劣部分不能简单采取压抑的方式,否则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荣格学派的学者美国心理学家卡尔·S·霍尔曾引述荣格的评述,以说明这一问题:当我们心中的野兽受到压抑时,“我们心灵中的野兽只会变得更加凶狠残暴”;“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再没有一种宗教象基督教一样用无辜者鲜血的飞溅来亵渎宗教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世人从未目睹过比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残酷的战争的原因。”[2]霍尔认为,荣格上述看法的言下之意是说,由于基督教教义对于阴影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被压抑的阴影向回扑过来,以肆虐的流血杀戮来吞噬种种民族。”这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为残酷的原因,甚至在可以从历史中引证的无数其它的事件中,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继二次大战之后的种种战争亦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4](46−47)
荣格提出阴影理论是为了克服压抑阴影所导致的恶果,为了以更为理智的态度来面对阴影,最终目的是“把人类的恶根找到”,“把世上的某些罪恶铲除掉”,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关于这一点,他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一书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
然而我们能够在我们内心深处发觉到这么多的恶魔,几乎可算是一大慰藉了。至少,我们可相信,我们终于把人类的恶根找到了。虽说一开始我们不免惊讶、失望,然而,由于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最好说明,我们算是多多少少已把它们控制在我们手中,因此,我们便可去纠正它们,或至少可有效地去扑灭它们。我们想作个假设,如果我们真能成功的话,我们一定能把世上的某些罪恶铲除掉。[3](306)
荣格注意到阴影与光明的相互联系以及阴影对于促进光明的出现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他说:“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在我体内的阴影可为我唤起了有利的光明,因此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黑暗也同样可带来光明。”[3](314)因此,荣格认为,有效地扑灭人格中的阴影决非通过简单地进行压抑,而是要以宽容的态度来进行整合,这又促使荣格通向了老子兼容不苛的主张,他在为《太乙金华宗旨》注释所作的评述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迫切需要整合的人格其结果究竞如何?追求整合的必要性究竟多大?于是我们又踏上了这条东方人在远古就已走过的道路。很显然,中国人之所以发现了这条道路,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迫使人性中的对立因素分离得太远,以至于丧失了各因素间所有自觉的联系”,中国人具有一种“包容各极的意识”,“认为是与否本是近亲”。[1](81)显然,这里所说的“包容各极”的思想正是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翻版;而“是与否本是近亲”等思想亦来自老子关于善恶、美丑等对立面之辩证关系的论述。
道家的对立统一思想亦受到荣格学派心理学家的推崇和运用,将其作为“突破黑暗面”智慧。在荣格学派学者路格· 阿伯罕所著的《人生黑暗面》中,作者提到了“积极影像”这一心理训练和治疗方法与道家的联系,他说:“创造积极影像所使用的最广泛的方法,乃是将我们自己和道家的训诲调和为一体,于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坏事将全部为好事所代替。”[5](175)该书作者还指出,如果我们对自己中的黑暗面怀有敌意的话,“它将会变得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反之,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友善的——亦即了解到它的存在是自然的——则我们的将出现令人惊异的转变。”[5](175)
也就是说,如果能以道家“包容各极”的辩证思维来善待自己或他人,就会对那个“阴影与光明”并存的个体有更多的宽容,从而以友善的态度面对“不善”,这不仅能够感化不善者而实现“德善”,更能化解埋藏在自己心中的怨恨,淡忘不快,走出烦恼,让生活充满友爱和快乐的阳光。
老子的智慧给了荣格以启迪,而从荣格的理论来诠释老子思想,又让人们更主动地吸收这些智慧来善待人的黑暗面,这就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在这方面存在的简单片面做法,从而有可能找到另外一条缓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矛盾的道路,并激发人的内在创造力和生命力,促进人格更为协调地发展。
运用对立统一原则,荣格进一步指出,在生命的进程中,冲突和对立是无处不在的事实。假如冲突能够被承受,那么,它们就可以为创造性的成就提供动力,并且赋予人的行为以活力。反之则会导致人格的分裂,或者濒临干疯狂的边缘。因此,荣格努力寻找综合那些对立力量的各种途径,以图推进对立的统一,实现和谐、平衡、统一的人格的完形。[4](51−52)在此基础上,荣格提出了整合意识与潜意识、阴影与光明、阿尼玛与阿尼玛斯等一系列理论,在西方心理学领域内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宏大体系。
二、“元神”“识神”概念对荣格的影响
《太乙金华宗旨》中所说的“元神”、“识神”是道教内丹学两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它们是一对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制约的生命要素。道教认为,“元神”是人的“本来面目”,来自无极之真性,无识无知;“识神”禀太极之元炁,有识有知。元神喜静,识神喜动。识神动则情欲盛,情欲盛则耗散元精,进而耗散元神。人在出生以后,原本没有意识但能主宰生命的“元神”逐渐被“识神”所侵扰,成为人的主宰,因此人难以长生。
结合自己以往的研究,“元神”、“识神”的概念启迪荣格找到了在意识自我和集体潜意识过程中存在的联结点,正式形成了他关于集体潜意识的理论。他将“元神”看成是“潜在于集体潜意识领域深处的本来自我”,将“识神”看成是“自我意识的活动”。他认为,人格结构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又分为集体潜意识和个人潜意识两个层次。意识即是经验者自己能够知晓的心理经验,普通心理学对其有相当多的论述。潜意识是荣格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按照荣格《心理结构与状态》一书所下的定义,潜意识的内涵包括:“所有我知道,但在当时并未思考的事情:所有我曾意识到,但现在却已忘掉的事情;所有我的感觉已感知到,但并末被我的意识头脑注意到的事情;所有我不是主动地、对其不加注意地去感受、思维、记忆、渴望和做的事情,所有将塑造我,并在某些时候会进入意识的未来的事情。”“个人潜意识”除了上述内容以外,“还包括那些或多或少具有全球性的对痛苦想法和感觉的诸多压抑”,荣格关于个体潜意识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基本一致。他的独到创建在于提出了集体潜意识的概念。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并非来自个人的经验、不是个人所习得,而是人类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通过遗传而先天存在的原始意象和本能,荣格之所以将其称为“集体”的,是因为它并非由个体和或多或少有些特殊的内容所构成,而是“由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所构成,由那些习以为常地发生的事物所构成”。[2]
在为《太乙金华宗旨》注译本所作的评述中,荣格进一步指出,潜意识的心理结构是超越人类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集体潜意识的实质就是与所有种族差异无关的大脑结构全同性的心理表现”。[1](78)在自我(ego)形成之前,支配人的精神活动的主要是集体潜意识,人主要依靠本能、情感活动,潜意识决定意识。但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多、自我的成长,人的活动渐为有意识。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常常使人的精神逐渐摆脱潜意识的束缚。因此,意识过度发达的结果,却招来了集体潜意识的报复,因而产生了精神疾病。
可见,忽略潜意识的存在这是现代人产生孤独等心理问题的重要根源。荣格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一书中指出,“一位道道地地被我们称为现代人者是孤独的”,这是因为与集体潜意识日益疏离,每当他要向意识领域作更进一步之迈进时,他就和他原本要和大众“神秘参与”——埋设在普通的中——的初衷离得愈来愈远远,“每当他要举步向前时,其行动就等于强迫他离开那无远弗届的、原始的、包括全人类的”。[3](294−295)荣格认为,上述情况在西方人这里尤甚,因为西方人的精神是意识太过发达的精神,这种发达导致精神与原初状态(即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精神失常”或“意识的连根拔起”。
而我们知道,在这方面道家道教有着独特的方法,他们认识到,过度发达的理性意识和名利算计、概念逻辑、封建名教的束缚,往往使人们日益与本真之性相脱离,产生各种烦恼和痛苦,故强调要摒除后天知觉和意识,通过修炼心性以复归至清、至洁、至静的真心。老庄提出致虚守静、心斋坐忘,《老子想尔注》要人们抛却“计念思虑”“情欲思虑怒喜恶事”,司马承桢《坐忘论》中概括出“收心”“简事”“真观”“泰定”等等七个阶段,清代傅金铨《性天正鹄》告诫修炼者“施炼心养性之功,庶不以贼为子,错认识神”……
众多内丹家千言万语的叮咛嘱咐,目的都在提醒修炼者自觉地调控心理,防止意识过分发达,清除头脑中的私心杂念,实现“返本归元”。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为集体潜意识的自然发展开辟道路。
荣格力图通过意识与潜意识的融合,实现人格转化,达到完整的、统一的新人格——自性。而他认为正是《太乙金华宗旨》将他“推到正确的方向上”,促使他找到了整合意识自我和集体潜意识的联结点。何以如此呢?这就需要考察道教内丹学特别是《金华宗旨》的修炼思想,从中找出它和荣格这一思想的相通性。
从道学内丹修炼理论来看,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这种所有人类都具有的“大脑结构全同性的心理”正是修炼所说的“本性”“真性”。道学认为,“道”是生发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本源,人的真性与具有普遍意义的宇宙节律——“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相通的,心是性的载体,性由心生,当心处于无为清净的状态时,则显现出“表里莹彻……一尘不染”的本性。因此,通过炼心以求“明乎本心”乃是体认“至道”、展发本性的根本途径。张伯端在《悟真篇·自序》中指出:“欲体至道,莫若明乎本心,心者,道之枢也。”
因此,道教内丹修炼的目标就是要现出真我、真性、本性,或称之为“本命元神”。如,唐代高道成玄英就曾在《老子注》卷一中强调,修炼者就是要“复于真性,反于慧命”,这只有在守朴弃诈、排除后天意识干扰的状态下才能实现。
因此内丹家主张通过修炼主张自觉地进行致虚守静、坐忘心斋等活动以返归本真之性,现出那个被后天意识所遮掩了的“真我”。这种放弃对于意识自我的执着以回归与大道相合的本来真性的活动,其实类似于荣格所说的“原本由集体潜意识支配精神活动的状态”,建立起“意识自我和集体潜意识的联结点”。而且,这里所追求的“复于真性”并非真要回到人生初始之时,而是认识到意识过度发达的弊害因而自觉地通过修炼而超越意识自我的过程,是个体发展的更高阶段,这与人生初始还未形成自我(ego)之前由集体潜意识支配精神活动、依靠本能和情感活动的状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追求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返朴归真,是通过修养之后所达到更高人生境界。关于这一点,《庄子·天地》中“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的论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荣格的人格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个体化”,也就是发展集体潜意识,从自我过渡到自性“与我们最深处的、最后的、而且不可比较的太一相结合,实现个体化”。[2]我们看到,这一所谓“个体化”过程其实与《太乙金华宗旨》以及道教内丹所追求的“返本归元”——从后天状态返归先天状态也是非常相似的。返本归元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在人格中的潜意识与意识的对立,使得先天之气在一身之内流行,以恢复元神的主宰,恢复人之本真存在状态。《太乙金华宗旨金华·元神识神》章说:“惟元神真性,则超元会而上之,……然有元神在,即无极也。先天地生皆由此矣。学人但能守护元神,则超生在阴阳之外,不在三界之中,此惟见性方可,所谓本来面目也。”[6]
集体潜意识对人格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促进集体潜意识的发展,进而达到意识与潜意识的合一,实现自性呢?道教的心性修炼活动正是一个重要的方式。荣格看到了无为思想的心理治疗意义,并将这一思想吸收到他的治疗实践中。以下我们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三、 无为思想对荣格的启示
荣格在心理治疗实践中提出了“无为艺术”,这是他将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爱克哈特所说的“任物自行”与《太乙金华宗旨》所说的无为之道相结合而产生心理治疗方法,他认为,这一鲜为人知的艺术乃是促使精神正常发展的关键。
荣格意识到西方文化中意识过度发展对人的精神心理的危害,他看到,与西方意识片面发展的情形不同,中国人善于平衡理智和情感这两个对立方面,他说:“中国人对于生命体内部与生俱来的自我矛盾和两极性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立的两方面永远是彼此平衡的——这是高等文明的象征。”荣格毫不掩饰地批评说,西方文化中的片面性,尽管它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它仍然是末开化的标志。如今在西方发端的反抗理智祟尚情感或者崇尚直觉的这个反响,我认为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意识对专横的理智设定的过分狭窄之界限的突破。”
荣格希望采用道教的“自然无为”来抑制意识的过度发展,保持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联系,以保证精神的正常发展。他通过对《太乙金华宗旨》的研究和自己的实践,发现“无为艺术”正是道教内丹修炼的体验。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中,他画下许多作为体道象征的曼荼罗。他所创建的由“意识自我”到“集体潜意识的深层世界”的道路——“积极想象法”,与道教内丹“回光返照”,“凝神入气穴”等进入潜意识深层世界的方法在本质上多有相合。[7](76)
荣格进一步认为;人们如果要促成“自我”的解放,就必须遵循“无为”这种东方道家的处世态度。《太乙金华宗旨》的《天心》《回光返照》等多处皆强调无为的重要性,如“自然曰道,道无名相……丹诀总假有为而臻无为”,又如“惟无为,故不滞方所形象,惟无为而为,故不堕顽空死虚”等等。这也就是《太乙金华宗旨回光返照》中吕祖所说:“日用间,能刻刻随事返照,不着一毫人我相,便是随地回光,此第一妙用。清晨能遣尽诸缘,静坐一、二时最妙。凡应事接物,只用返照法,便无一刻间断。如此行之,三月两月,天上诸真,必来印证已。”[6]
文中“不着一毫人我相”“遣尽诸缘”的“静坐”方法,虽然揉入了佛教的语言,但其实质内容就是一种“无为艺术”,它与老庄“涤除玄鉴”“坐忘”“心斋”乃至道教内丹修炼的方法一脉相承,内丹修炼皆奉无为之旨。“无为”在内丹修炼中主要指毫不勉强、自然放松的调整身形的技术要求,也包含了清净寡欲的心理状态。如全真七子之一的马丹阳在继承发展祖师王重阳清净修行原则的基础上,将修炼工夫概括为“清净无为”,他告诫门徒说:“道则简而易行。但清净无为。最上乘法也。……夫道。但清净无为。逍遥自在。不染不着。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便做个彻底道人。”[7]必须排遣物欲和各种私心杂念的干扰,不断地修炼,增加定力,不为外物所动,才能保持虚静的心理状态,实现修炼的目标。这也正是《慧命经》中所说的:“务要绵绵,久久锻炼,将此阴魔②化为阳光,则身心自然安乐,情欲自然不能搅动……如法锻炼,用之得力,欲不用除而自除,心不用静而自静,所谓以道制心而心自道。”[8](222)这种通过修炼而获得的“欲不用除而自除”“心不着迹”“我与声色无干而声色自与我无涉”的自在境界,正是荣格所推崇的。
荣格看到,《慧命经》《太乙金华宗旨》等道教丹书虽然将节制欲望作为修炼的基本要求,“这似乎与基督教的禁欲道德并不相距太远”,但是,“如果认为它们阐述的是同样的事,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方式“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不同”,因为这部书的背景是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古老文化,这种文化有机地建立在原始的本能之上,因而,在这种文化中,我们不会看到专断的道德指令对本能的侵犯,而这种侵犯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征标志了。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根本不存在粗暴地压抑本能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却歇斯底里地膨胀且毒害我们的精神。与本能同在的人也能超脱本能,这种超脱与同在同样是自然而然的。[1](117)荣格这里所说的“不会看到专断的道德指令对本能的侵犯”“不存在粗暴地压抑本能的冲动”“自然而然”等对待人性、对待自然欲望的态度,正是道家在自然无为宗旨支配下的心性修炼智慧。
荣格深刻体悟到《太乙金华宗旨》中的“无为艺术”对心理治疗的意义。他写道:“为了获得自身的解放,这些人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就我所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无为),而只是让事情任其自然地发生,正如吕祖在本书令所传授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不放弃自己的俗务常事,光就依其自然的规律运转。让一切顺其自然,无为而为,随心所欲,在心灵方面,也一定要顺其自然。”
荣格看到,这种无为而为的技术正是西方文化中所没有的,“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鲜为人知的技艺”。荣格看到,在意识过分发展的西方文化中,“意识总是与心灵的发展掺合在一起,吹毛求疵,好为人师,从未让心灵在平静的环境中质朴地发展。”而如果改变这种做法,以质朴无为的态度处事,“问题就会变得十分简单”。[1](84)
荣格通过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从多方面印证了道教的“无为”原则对于保证精神正常发展的作用。因此,他治疗的指导原则是个体化的自然过程,让潜意识自发的精神在它渴求完善的本能、自发的冲动中实现意识与潜意识的调和。
荣格认为,治疗家“必须遵从自然的指导”,治疗师“不是治疗的问题,而是发展潜伏在患者自身中的创造的可能性问题”。荣格观察到:那些成功地使他们自己摆脱生活问题的缠扰,达到心理发展和整合的更高层次的患者,实质上什么也没做,只是简单地顺其自然,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们允许自己的潜意识在寂静中与他们交谈,他们耐心地倾听它的信息,并给予它们最大和最认真的关注。而只有当这一过程不受外界控制、不受治疗学家干预,自然产生作用时,才能最完满地完成。在治疗中,不要拘泥于先入之见和理论假设的影响,放弃一切方法和技巧。当允许这种心理过程平静地发展时,潜意识丰富了意识,意识又照亮了潜意识,于是这两个对立面的融合和结合,使认识增强、人格扩展。[9]
荣格运用自然无为的原则收到了明显的疗效。他在为卫礼贤所作的《太乙金华宗旨》的评述中,荣格记述了这样的案例:一位经他治疗而康复的病人写信告诉他自己所经历的重要转变:“保持安静,不压抑什么,保持注意力,接受现实——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接受它,不是按照我想要它成为的样子接受它——由于达一切,我获得了非凡的知识和非凡的能力,以前我从未想象得到。”对此,荣格十分认同,他强调:“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高层次的意识以及文化,就必须要以这样一种心态作为基础。”[1](118)
荣格不仅以无为作为治疗原则,更以自己的亲证实验,实践着“无为艺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荣格体现了“那种无为之为,也即中文之‘无为’”。这也意味着一种灵性的自发与再生。[10](196)
荣格试图借鉴道家道教“自然无为”的思想,避免西方意识片面发展或某一方面过度成长所带来的危害,对于现代中国人重新认识这一中华民族的心理保健智慧是有积极启示意义的。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人对于理性的盲目崇拜和对非理性的粗暴排斥,是否也有可能在将来再现荣格曾指斥过的意识过度发达的弊病呢?我们不应忘记,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潜意识皆是人类精神心理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既需要吸收西方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但也决不可对中国先贤的无为、直觉、顿悟等非理性智慧妄自菲薄。荣格对无为思想的评价和应用,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一道学基本概念在心理治疗方面的价值是有启示的。
当然,作为西方现代心理学家,荣格对《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以及道家道教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有误解之处。同时,荣格对于“无为”这一概念的理解又是不可能十分到位的。如他在谈及《太乙金华宗旨》的“无为艺术”时说:“为了获得自身的解放,这些人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就我所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无为),而只是让事情任其自然地发生,正如吕祖在本书中所传授的那样……让一切顺其自然,无为而为,随心所欲……”[1](84)荣格以“无为”来对治西方意识过分发达所引起的弊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里将“无为”理解为“什么也没有做(无为)”,却又是失之于简单、片面的。
在内丹修炼中,“无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既指毫不勉强、自然放松的调整身形的技术要求,又指清净寡欲、精神稳定的心理状态,更是指修炼过程中运用火候③的基本原则,所谓“采药于动与不动之中,行火候于无为之内”。[11]要求在采药炼丹时要“勿忘勿助”,注意调节火候,达到心息相依,凝神定志,不假人力又不放任的程度。
在《太乙金华宗旨》中,“无为”也决非“什么也不做”。如,该书的《回光返照》中说:“惟无为,故不滞方所形象;惟无为而为,故不堕顽空死虚。”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无为”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为”的方式,一方面,它要求行为主体在修炼中不执着、不刻意、顺应自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落入“什么也不做”的“顽空死虚”,而是有所行动的“无为而为”。
实际上,荣格在实践中也是将“无为”作为一种特有的行为方式来践行的。正如荣格心理学专家戴维·罗森所说,荣格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体现了“那种无为之为,也即中文之‘无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修炼行为中,荣格的心灵中出现了“一种灵性的自发与再生”。[10](196)这就从实践的层面证明了荣格原来对“无为”所作阐释的局限性。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苛求荣格这位西方现代心理学家,但认识这些局限,这对于当代中国人厘清对道学的误解并更准确地把握其丰富内涵也是不无启示的。
三、简短的结语
荣格在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吸收道学对立统一、自然无为等思想,开创了西方心理治疗学的一片新天地;他在东方古老的内丹修炼与西方现代心理学之间搭起了融通互补的桥梁;而通过他的潜意识理论,亦有助于我们探讨或解释致虚守静等修炼方法具有心理保健、人格发展等积极作用的内在机理,启示我们自觉地应用内丹修炼而进入潜意识层面,调治现代人类的心理问题,开发人类未知的潜能。在这一系列探索中,我们也必将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特性及优长之处的认识,进一步开掘道学智慧的现代价值,促进中国哲学智慧走进生活世界,抚慰和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注释:
①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宗昱的《荣格的道教研究》,景海峰的《试析容格评论<太乙金华宗旨>的意义》,台湾学者刘固秋的《荣格与道教内丹之心理分析──个体化》等论文;美国戴维·罗森的《荣格之道:整合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而王宗昱先生在《荣格的道教研究》中就认为:“《太乙金华宗旨》对于荣格的理论建构并未增添多少砖瓦,而是使它的轮廓蓦然清晰。”详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按《慧命经》作者的说法,阴魔,“即身中之阴气”。见《慧命经 正道修炼直论》,徐兆仁主编的《东方修道文库·伍柳法脉》第2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③内丹家将人体比作鼎炉,将真炁比作药物原料,将意念、呼吸比作“火候”,进行烹炼。故“火候”实质是指意、神、气等的运用。
[1]荣格,卫礼贤.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M].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3.
[2]荣格.荣格自传[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3]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北京: 工人出版社,1987.
[4]卡尔·S·霍尔.荣格心理学纲要[M].郑州: 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5]路格·阿伯罕.人生黑暗面[M].伊犁: 伊犁人民出版社,1998.
[6]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等.藏外道书·第10册[M].成都: 巴蜀书社,1990.
[7]马丹阳.真仙直指语录·丹阳语录[C]//道藏·正一部.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
[8]柳华阳.慧命经·正道修炼直论[C]//徐兆仁.东方修道文库·伍柳法脉.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9]戴维·罗森.荣格之道: 整合之路[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白玉蟾.谢张紫阳书·杂著指玄篇·修真十书[C]//道藏要籍选刊·第三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