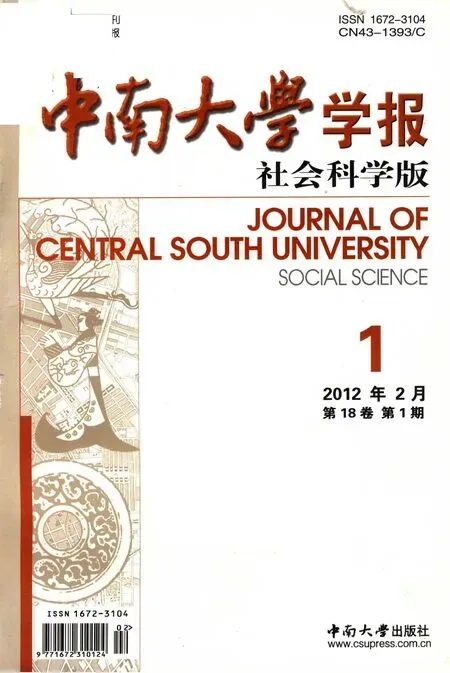唐末贯休诗歌用韵考及其所反映的方音特点
付新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贯休(832~913),字德隐,俗姓姜,晚唐婺州兰溪(今浙江金华地区)人。七岁出家,咸通初往洪州游学,稍后居钟陵山。曾漫游江西,吴越,返婺州,又避军乱至常州、杭州。后依钱塘钱镠、江陵成汭,但不被器重,又得罪于成汭而被流放黔州,后潜逃至南岳隐居。天复三年入蜀,为王建所礼重,赐号“禅月大师”。后梁乾化二年十二月卒,享年八十一岁。贯休早年即擅诗名,在当时颇有影响,同时贯休又工于书画,曾纵笔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欧阳炯观后,赠以歌曰:“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1]《唐才子传》《宋高僧传》《十国春秋》皆有传。贯休一生做诗颇多,其《偶作二首》曾云:“新诗一千首。”今存《禅月集》二十五卷补遗一卷,为其弟子昙域所编辑, 其名又作《西岳集》,乃贯休入蜀前的作品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诗》①均录,另有数首见于《全唐诗续拾》。今人沈玉成、印继梁主编的《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②则将其诗歌全部收入,共七百三十五首,押韵893次。本文主要以后者为底本,参以其他版本。
僧侣诗人用韵往往会跟通语有不同的表现,“为顾及僧、道部分之作品,在诗律方面不甚严谨……贯休之《禅月集》,自卷7至卷25,皆注明为律绝,然细考其作品,多不合诗律。”[2](193)耿振生就晚唐五代诗人的用韵做了一番考察,耿文注重从宏观上考察当时僧侣诗人的用韵情况,但是基本没有涉及到入声韵。而如果从现今作品所存数量来看,则以贯休、齐己所存作品最多,本文在以存诗最多的贯休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归纳其诗歌韵部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其异部通押的韵段与诗人方音之间的关系。对其韵部的归纳,我们采用“丝贯绳牵法”的办法对其诗歌韵脚字进行系联,参照《广韵》音系,统计押韵组合的频率。同时与刘根辉、尉迟治平所归纳的中唐诗韵26部,耿振生归纳的唐末五代僧诗用韵的15部以及鲁国尧归纳的宋代通语18部系统相比较③。至于通押的各部之间需要达到多大的比例就可以认为是不同韵部在实际语音中已经合并,我们采用刘晓南先生的观点定在10%[3]。
我们把各韵部的通押情况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统计,表中韵部一栏的名称是我们根据贯休诗歌用韵实际命名的;《广韵》韵目一栏则罗列各部所含《广韵》韵目名称;押韵情况一栏中,把各韵部间押韵的情况分为三种类型:常韵、出韵、特韵,常韵是指所押韵部符合《广韵》独用、同用规定的押韵;出韵是指所押韵部超出了《广韵》独用、同用的界限,但依旧是属于同摄韵部间的通押;特韵则是指不仅超出了《广韵》独用、同用的界限,而且也超出了同摄的界限,是不同摄韵部之间的通押。舒声韵和入声韵在出韵、特韵的表现上有所不同,前者特韵情况较少,后者则较多。在计算百分比的时候,对于舒声韵通常只计算出韵所占的比例,以10%为限;对于入声韵则同时考虑出韵、特韵两部的通押比例,也以10%为限。备注一栏记录特韵的具体通押情况及次数。现以通摄为例做一下具体说明:《广韵》中东韵独用,冬钟同用,贯休诗歌中和通摄相关的韵段总数是 85例,其中属于常韵的共有42例,如《送杜使君朝觐》叶“聪空同穷红风通功”(全为东韵字),《苦寒行》叶“毒(沃)足(烛)”;属于出韵的共有21例,如《水壶子》叶“宗(冬)公(东)”,《古意代友人投所知》叶“腹(屋)绿烛(烛)”;属于特韵的共有22例,此类入声韵跨摄通押的比较多,如《舜颂》叶“公(东)能(登)”,《少年行》叶“玉曲(烛)得(德)”。
对所有韵段通押情况的统计结果见表1。
下面就诗人用韵中不同韵部之间的通押,尤其是那些富有特色的“特韵”现象进行讨论。

表1 韵段通押情况统计
一、阴声韵
(一)支微、鱼模
贯休诗中,支微、鱼模两部通押4次,它们是:
《续姚梁公坐右铭》叶“微依(微)书(鱼)孳(之)衣(微)”;
《古塞曲三首》叶“涯(支)除(鱼)危(支)时(之)”;
《上卢使君二首》叶“墀(脂)篱(支)如(鱼)隳(支)氂(之)”;
《戒童行》叶“志易(支)地(脂)戏(支)处(鱼)⑤”。
押入的遇摄字分别是“书、除、如、处”,这些都是鱼韵系的字。明代何孟春在《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四中云:“韵之讹则以支入鱼、以灰入麻、以泰入箇,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吴音也。”[4]《老学庵笔记》亦云:“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仿此。”[5]这里的鱼韵字读开口,也就是读为跟支韵相谐的舌尖音。《南词叙录》中在谈到“凡唱,最忌乡音”的时候,指出松江人不辨“支”“朱”“知”[6](68),此三字分别是支韵和虞韵字,说的也是支韵、虞韵字在吴语区的人的口语中是不分的。现今南部吴语的一些方言中,这些韵部字的读音也有类似表现。曹志耘指出南部吴语“鱼韵[i][ɿ][ie][ei]等韵母的读法跟止摄具有明显的关系。”[7]以下南部吴语方言点的语音材料主要来自该书及《浙江兰溪方言音系》⑥(见表2)。

表2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鱼韵字在南部吴语的音值是不尽相同的,但无论怎样这些音值正如曹志耘说的那样“有明显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梅祖鳞曾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现将其所引的处衢部分方言点摘录如下⑦(见表3)。
梅先生认为同为浙南吴语的衢州方言鱼韵字的读音实际上是分为三个层次的,层次Ⅰ的韵母[※ɑ]是属于秦汉时代的,层次Ⅱ的韵母[ie][i][ɿ]是相当于《切韵》时代的鱼虞有别的层次,层次ⅡⅠ的韵母[y]是时代最晚的,同时也是鱼虞相混的一个层次。[8]可见,在南部吴语区里面,无论是婺州片,还是处衢片方言中,部分鱼韵字的读音和支韵字是很接近的,至于各方言点的具体音值不尽完全相同,则应该理解成是语音层次的问题。由此,我们认为早在唐末时代的兰溪话中读同支韵的鱼韵字应该是更多的,诗人由于受方言的影响,其诗歌中所出现的支鱼通押的“特韵”现象,是顺利成章的事情。“支鱼通押现象是宋代南方方言的共同特征之一……这一音韵特征自魏晋至唐宋(隋代似乎中断)直到明清在吴地都有较为显著地反映。因此,完全可以说支鱼通押是江浙方音历史较为悠久、个性鲜明的音韵特征之一。”[9](107)无疑,贯休诗歌中和支微通押现象是受其方音影响所致,支鱼通押的那些字在当时诗人的方音中,它们的读音是相同或相近的。

表3
(二)灰咍
贯休诗歌中有关灰咍的韵段数是64例,其中60例都是灰咍通押或灰咍独押,1例是佳皆通押,1例是灰咍和佳皆通押,两例是灰咍去声韵跟泰韵通押,举例如下:
灰咍皆泰韵通押例:
《拟齐梁体寄冯使君三首》叶“带盖(泰)辈(灰)赛(咍)”;
《上孙使君》叶“泰(泰)代外概岱(咍)淬(灰)大(泰)背(灰)会块对盖(泰)鼐塞(咍)最赖(泰)内碎阓(灰)旆(泰)薤(皆)戴(咍)桧(泰)态(咍)壒(泰)耒(灰)带(泰)辈(灰)慨爱(咍)”。
泰韵与灰咍的通押比例是3.3%,小于我们定下的10%的比例,同时诗韵同用的佳皆部总共只有两处入韵,一处即《上孙使君》中入韵的“薤(怪)”字,一处是《山居诗二十四首》中所叶的“排谐阶(皆)崖(佳)乖(皆)”。显然按比例的话,佳皆韵跟灰咍通押的比例更小,不过这里我们还考虑到泰韵字在其所有的诗歌中也只押韵两次,并且都是跟灰咍韵通押,佳皆韵系字也只通押两次,并且考虑到刘26部和鲁18部中蟹摄一二等韵都已合为一部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贯休诗韵的灰咍佳皆泰韵也已经合并。
(三)齐祭韵
蟹摄齐、祭韵总共有11个韵段,跟支微部通押的有4例,比例高达26.7%,它们是:
《怀张为周朴》叶“西(齐)眉(脂)奇(支)”;
《戒童行》叶“偈(祭)弟(齐)气贵(微)易(支)愧腻(脂)”
“衣(微)乩(齐)”;
“慧(齐)睡(支)”。
跟灰咍部则没有通押的用例,可见蟹摄三四等韵是跟齐微部合流的,而且我们发现与之通押的止摄字都是唇牙喉音字,这也跟现今兰溪方言的表现一致,都读为i韵。如“西文、眉、奇、弟、易、衣”等,贯休诗歌的支微部比诗韵的范围要大很多,但是又比宋代通语的支微部范围要小,那时的支微部包括了齐祭废灰咍的一部分。
二、阳声韵
(一)真文、侵寻与庚青
贯休诗歌中此三部大部分都是按常韵相押的,但是也出现了三部通押的现象,它们是:《春野作五首》叶“尽(真)锦蕈(侵);
《循吏曲上王使君》叶“信(真)朕(侵)”;
《闻前王使君在泽潞居》叶“名(清)心(侵)言(元)”;
《赠抱麻刘舍人》叶“绅人(真)贞(清)臣(真)迍皴荀(谆)巾仁新邻尘因津茵(真)纶(谆)频亲(真)”。
前两例是真文、侵寻通押,第三例是侵寻、庚青通押,第四例是真文、庚青通押。《循吏曲上王使君》叶“信朕”的原文是“大信不信,贻厥无朕。”其中“朕”字《广韵》只有“直稔切”一音,《集韵》则有两音:“直稔切”意为“我也”;“丈忍切”意为“革制也”,前者是臻摄准韵字,后者是深摄寝韵字。我们查看原文的解释,“……朕:形迹。”《汉语大字典》有“直稔切”和“丈忍切”两音,“直稔切”下的第三个释义为“形迹;预兆”,可见“形迹”义的“朕”字当为寝韵字。此处的“信、朕”通押是阳声韵尾-n和-m的合并。贯休是晚唐时代的人,从汉语语音史的发展来看,通语-n尾和-m尾的合并是很晚的事。王力《汉语语音史》中晚唐——五代音系所使用的材料来自南唐徐锴《说文系传》中所使用的朱翱反切,“朱翱的反切完全不依《切韵》,这就表明他用的是当代的音系。这是很宝贵的语音史资料。”[10]结果表明那时的-n尾和-m尾都是分用不混的。到了十四世纪的《中原音韵》,古-n尾和-m尾的字也都分属不同的韵部,即真文、寒山、桓欢三部收-n尾,侵寻、监咸、廉纤三部收-m尾。直到十七世纪初,徐孝的《重订司马文公等韵图经》中才把-n尾和-m尾的字作为同韵而混排在一起,表明那时的-m已经不存在了。以上是通语的情况,方言中-n尾和-m尾的分混却有不同的表现,唐朝末年人胡曾的《戏妻族语不正》云:“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针(-m)作真(-n),天阴(-m)说成“天因(-n)”,说明当时-n尾和-m尾已经相混。胡曾是湖南人,曾在四川任职,有人说其妻可能是四川人,但无论是哪里人,反映的信息就是在晚唐时代汉语方言中-n尾和-m尾已经有了合流的事实。第三例的“名”是青韵字,“心”是侵韵字,第四例的“贞”是清韵字,其他都是臻摄字,它们的通押反映的是-ŋ尾和-m尾、-n尾的合并。就以上事实来看,把三个鼻尾韵的混押认为是诗人方音的流露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同为兰溪人的李渔就指出:“吴人甚至以真文、庚青、侵寻三韵不论开口、闭口、同作一音韵用者。”[11]徐渭在《南词叙录》中也说:“凡唱,最忌乡音。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6](68)。不过现今兰溪方言中此三部合流后分为了两韵,属知章组的字读为iǣ韵;其他声母的字读为iŋ韵。前三例跟现今方言完全一致,而第四例中与“贞”字通押的臻摄字是包含非知章组字的,也许这三韵在发展中经历了合流又分化的过程。钱毅说:“宋代江浙诗韵中侵寻尽管与真文、庚青两部大量通押,但所占各自总入韵数的比例较小,均为 5%,不能将其合并,我们认为这应是江浙方音在用韵中的表现。”[9](134)可见,距离宋代未远的贯休在用韵中所出现的阳声韵尾混押的现象,认为是其受了方音的影响是合适的。
(二)寒桓、山删、仙先三部
在贯休诗歌中,寒桓、山删、仙先三部的界限是非常严格的,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偶尔跟臻摄通押外,都是完全依据《广韵》独用、同用原则的,不过有三处韵例似乎表明三部有通押的迹象,它们是:
《山居诗二十四首》叶“难(寒)山间潺(山)扳(删)”;
《曹娥碑》叶“难(寒)间山(山)”;
《咏雁山十八寺》叶“冠(桓)泉(仙)边(先)连(仙)巅(先)”。
以上三个韵段中的第一个字都属寒桓部,其他韵脚字则或属山删部或属仙先部。要说明的是此三例韵段中的第一个字都是各自诗歌中第一句的韵脚字,而我们并不能肯定首句都是入韵的,即使算作首句入韵,3例相对于总数的77例来说比例也是非常小的,因此我们认为贯休诗中此三部是完全独立的。耿15部中,寒部是包括了寒桓、山删、仙先三部的,而他所引韵例中,属于贯休诗歌的韵例就是《山居诗二十四首》一诗,韵脚字叶“难山间潺扳”。刘26部、鲁18部的寒先部都是包括寒桓删山仙先韵的,但是比贯休时代略早的皎然诗歌用韵却是寒桓、删山、仙先三部分立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广韵》的束缚,即‘唐功令’的影响。”[12]这和贯休诗歌用韵的表现是一致的,原因都是受唐代功令影响而表现出的保守的一面。
(三)元韵
元韵共入韵12次,其中10次跟真文部通押,2次跟仙先部通押,具体韵例如下:
协真文例:
《古意九首》叶“恩根(痕)尊(魂)言(元)奔门(魂)”;
《冬末病中作二首》叶“根(痕)园(元)闻(文)勤(欣)痕(痕)论(魂)”;
《赠方干》叶“村(魂)园(元)根(痕)门(魂)”;
《遇五天僧入五台五首》叶“论(魂)园(元)门(魂)”;
《魂送友生入越投知己》叶“暄(元)门村坤(魂)”;
《寄中条道者》叶“孙论(魂)痕(痕)言(元)”;
《东阳罹乱后怀王慥使君五首》叶“君(文)根(痕)言(元)恩(痕)论(魂)”;
《寄西山胡汾》叶“君(文)园(元)魂门论(魂)”;
《桐江闲居作十二首》叶“论门盆(魂)言(元)”;
《古塞下曲七首》叶“门(魂)痕(痕)蕃(元)”。
协寒山例:
《经古战场》叶“年烟(先)言(元)”;
《送越将归会稽》叶“娩巘(仙)远(元)”。
《广韵》中元韵被归入臻摄而与魂、痕同用,在宋代韵图时,元韵则被归入山摄。居思信曾指出,元魂痕在《切韵》中通押,是受了南方语音影响的结果。此三韵古代语音相同,只是由于语音的变化,现在才有了不同的读法[13]。而程垂成认为:“元与魂痕在中唐就分开了”,“元部独用和它跟山摄各部押韵共二十九次,魂部独用、魂痕同用和它们跟臻摄各部押韵共二十四次。元韵跟臻摄魂真文三韵押韵一次。”[14]意思是说从中唐以后元韵跟山摄韵部的关系更密切了。刘26部的寒先部包括《广韵》的寒桓删山仙先韵,鲁18部的寒先部包括《广韵》的寒桓删山元仙先韵。但是在贯休诗中,元韵的表现却有些不同,它跟真文部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耿振生指出:“元和及晚唐诗人将元韵与寒、桓、删、山、先、仙韵彼此合用,魂、痕韵与真、谆、臻、文、欣韵相互通押,形成真、寒二部,然而贯休对于元与魂、痕之关系,处理得非常混淆不清……这似乎显示了元韵与魂、痕韵的读音,在贯休是相同的,并且它们的读音是介于寒、桓、删、山、先、仙韵与真、谆、臻、文、欣韵之间。”[2](219)在耿15部舒声韵中,元部包括元、魂、痕三韵,而不与真部、寒部合并⑧。本文中的魂痕韵是归真文部的,而元韵也与真文部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也一并都归入真文部。要说明的是与真文通押的元韵字基本就只有“言、园”等少数几个字,此“言、园”二字属常用字,它们在现今的兰溪方言中分别属于“ye”韵和“iɛ”韵,而真文部字在兰溪方言则读“ǣ”韵,可见它们的主元音是很接近的。现在这些字有的读开口韵,有的读鼻化韵,这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可以想象在-n尾没失落的时候,它们的韵母应该是非常接近的,而它们之间的通押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四)监廉
在《广韵》的覃盐咸三韵中,覃盐属于窄韵,咸韵属于险韵,因此诗人用韵中此三韵的用字数目是很少的,所以不容易让我们对此三韵的真实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贯休诗中仅仅有8个韵段是与此三韵相关的,其中7例属常韵,只有1例是出韵,比例也已经达到14.3%,刘26部中,此三韵是分为覃谈部和盐咸部的;鲁18部中的监廉部包含覃谈盐添咸衔严凡诸韵,钱毅对宋代江浙诗人用韵的统计中,《广韵》咸摄各韵的混押比例达到了 40.6%。那么距离宋代不远的晚唐时代,诗人用韵打破覃盐咸三韵的界限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可以认为那时此三韵已经开始合并了,本文根据之前的10%的原则,认为三韵已经合并。
三、入声韵
(一)屋烛、铎药
此两部在贯休诗歌中通押5次,我们把铎药跨摄通押的四处胪列如下:
《送姜道士归南岳》叶“落索(铎)角岳(觉)著(药)”;
《寄大愿和尚》叶“岳(觉)削钥著(药)阁索霍鹤诺(铎)”;
《上杜使君》叶“岳(觉)廓铎漠薄鹤郭落(铎)削(药)渥角(觉)钥(药)壑(铎)”;
以上三例中的铎韵字是“落、索、阁、霍、鹤、诺”,它们跟觉韵通押。
《续姚梁公坐右铭》叶“薄(铎)足烛(烛)”。
此一例铎韵字是“薄”,跟屋烛部通押。
我们发现其中铎韵的唇音字归屋烛部和烛韵通押,非唇音字则归铎药部和觉韵通押,虽然例子不多,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得到现今兰溪方言的支持。在《浙江兰溪方言音系》中,铎药非唇音字正是跟觉韵字合流的,以上六字,除了霍字外,全部出现在ɔʔ韵中;而铎药唇音字则是跟屋烛合流的,“薄”字就出现在oʔ中,下面我们把这两韵的部分例字摘录如下:
ɔʔ韵:t⑧诺l⑧赂又落烙骆酪洛络乐~队⑦索z⑧凿k⑦各阁搁胳觉白角ɦ⑧鄂鹤白~岳獄学白,~习,~堂
oʔ韵:b⑧薄~荷勃蓬~:泥团□泥~薄缚钹m⑧莫膜寞木目穆牧
可见,贯休诗中铎韵的押韵事实和现今兰溪方言的情况是很一致的,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且这样的押韵和通语的情况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这同样是作者受其方音影响的结果。此种通押的现象,在宋代江浙诗人的用韵中也较常见,据钱毅对宋代江浙诗人用韵的研究,这种通押现象共有17例,如姜特立(丽水)五古《中古》第2韵段“俗坐卓”;葛立方(常州)杂古《横山》第3首第2韵段“廓屋”等等,作者拿温州、常州、遂昌三地的现代方言作验证,结果是“三地方言中,屋烛、铎觉两部字均可协韵,这是现代江浙吴语的普遍现象,反推宋代江浙方言或许亦如此”[9](151)。不过从贯休诗歌看来,这种现象其实在晚唐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显然这些都是诗人受了当地方言影响的结果。
(二)职德
《广韵》蒸登是同用的,其入声韵也是如此。刘26部中,职德部包括《广韵》的职德两韵,而此两韵在贯休诗歌中却有着不同的表现:职德两韵绝不通押,职韵有14例跟陌锡部通押,德韵则有11例跟屋烛部通押,数量都比较多。
职韵与陌锡部通押的韵例:
《寄高员外》叶“劈(锡)席(昔)吃(迄)力(职)枥(锡)忆(职)”;
《寄王涤》叶“滴敌(锡)赤藉(昔)直色(职)”;
《寄大愿和尚》叶“极(职)滴(锡)石益(昔)寂(锡)”;
《光大师草书歌》叶“壁(锡)力(职)击(锡)”。
德韵与屋烛部通押的韵例:
《酷吏词》叶“劚(烛)宿(屋)酷(沃)肉(屋)束(烛)屋哭族复(屋)北(德)”;
《荆南府主三让德政碑》叶“匐(屋)国得(德)”;
《题弘顗三藏院》叶“塞(德)束(烛)得(德)”;
《书陈处士屋壁二首》叶“北足(烛)得贼黑(德)束(烛)”。
如此的通押现象是跟通语的职德通押不一样的,鲁国尧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在吴、赣方言区词人作品中较多出现”,并且指出清代的毛奇龄在《西河词话》中就曾说过:“若‘北’之音‘卜’,则不特从来韵书无是读押,即从来字书,亦并无是转切。此吴越间乡音误呼,而竟以入韵。”[15]只是现今的兰溪方言中德韵字并不跟屋烛合流,而是跟梗摄陌麦两韵合流了;而职韵则与锡昔合流,这与贯休诗歌的用韵是一致的。相应的曾摄阳声韵也与入声韵有着相同的表现,只是阳声韵通押的韵例较少,例如:
《大蜀皇帝寿春节进尧铭舜颂二首·舜颂》叶“公(东)能(登)”;
《寄新定桂雍》叶“龙(钟)僧能罾腾(登)”;
《怀南岳隐士二首》叶“峰(钟)腾僧棱登(登)”;
《送僧游天台》叶“空(东)腾僧崩登(登)”。
由于阳声韵的通押所占比例较小,因此我们让东钟、蒸登分别独立。耿振生谈到此现象时认为“蒸、登二韵的读音,在贯休的语音是介于东、冬、钟韵与庚、耕、清、青韵之间的。”[2](219)看来,曾摄跟通摄在贯休诗中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入声韵,职韵与陌昔的通押很可能是诗人方音的流露,这从现代方言可以证明。以上韵例中的韵脚字如“劈、席、吃、力、滴、敌、藉、极、击、壁、益”在兰溪方言中的韵母都是ieʔ,韵母完全相同。而对于德韵与屋浊通押不见于现代方言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从此现象在“吴、赣方言区词人作品中较多出现”这样的事实出发,或许可以认为是语音发生演变的结果。
注释:
①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沈玉成,印继梁主编的《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③刘文的26部参见刘根辉,尉迟治平《中唐诗韵系略说》;耿文的15部只是阴声韵和阳声韵两部分,参见耿振生《晚唐及唐末、五代僧侣诗用韵考》;鲁文的18部参见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下文分别简称为刘26部,耿15部,鲁18部。
④对特韵数目的统计只考虑括号外的数字,括号内数字为通押的特韵总数。
⑤括号内标出韵脚字的中古韵部,以平声赅上去。
⑥本文所有兰溪方言材料均出自赵则玲《浙江兰溪方言音系》,《宁波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⑦所摘录表格做了少许变动,一律未加调值,原表可参看梅祖鳞《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一文。
⑧其真部所含《广韵》韵目是真、谆、臻、文、欣;寒部所含《广韵》韵目是寒、桓、删、山、先、仙。
[1]王汝涛.太平广记选(续)[M].济南: 齐鲁书社,1982:366−367.
[2]耿振生.晚唐及唐末,五代僧侣诗用韵考[A].声韵论丛(第四辑)[C].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八十一年五月.
[3]刘晓南.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通语及方言[J].古汉语研究,2001(1):30.
[4](明)何孟春撰.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四)[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四八.
[5](宋)陆游著,王欣点评.老学庵笔记[M].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2:131.
[6]徐渭著,李复波,熊澄宇注释.南词叙录注释[M].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7]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68.
[8]梅祖鳞.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A].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C].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00−201.
[9]钱毅.宋代江浙诗韵研究[D].扬州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未刊稿.
[10]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28.
[11]李渔.闲情偶记[M].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6: 41.
[12]易丽菊.皎然诗歌用韵考[D].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未刊稿:34.
[13]居思信.元魂痕诸韵的历史考察[J].齐鲁学刊,1985(4):119.
[14]程垂成.从白居易讽谕诗的用韵看元和魂痕分用的现象[J].河北大学学报,1991(2): 47.
[15]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A].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C].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