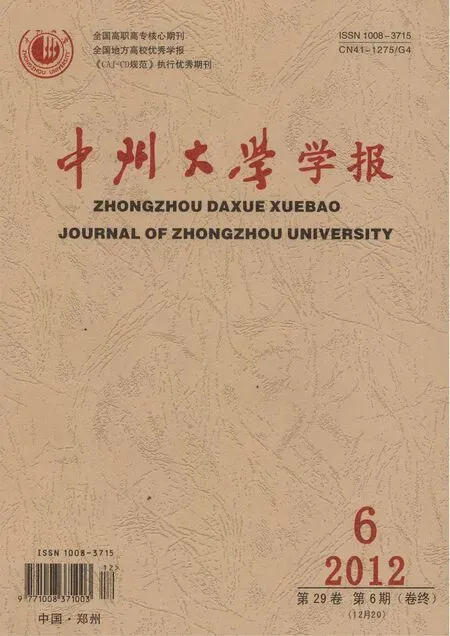思想者的责任
——艾云的写作和思想探议
黄昌成
(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 阳江529500)
一、大全大智的写作
归纳一下艾云的写作,似乎并不困难,在她天马行空汪洋恣意的文本面前,多数人都会说学者的写作或者思想随笔等,这一笼统的说法对于不熟悉艾云写作的人来说,可能会造成混淆,他们会把艾云简单地并入那些理性刻板的学院派一类。由此我想起了苏珊·桑塔格在一次访谈中关于她身份的回答:“我不想给自己贴标签。但是,如果我必须给自己归类的话,我宁愿要一个较为中性的标签。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喜欢以多种形式写作的作家。我最钟情的是虚构文学。我也写过剧作。至于非虚构文学,我觉得自己不是理论家或批评家。我觉得自己是散文家。散文对我来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我最感兴趣的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使我能感到自己有创造力、自己能做贡献的活动。大概我所缺席的唯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诗歌。”[1]苏珊·桑塔格说的是一种文学身份的认可,某种意义上,这恰恰表明了什么是真正的作家,或者说,真正作家的条件。其中,学识占有重大的比例。艾云无疑是这样一种作家。
广义地划分,艾云的文本属于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之一种。当今,散文这个原本属于最大容量的文体往往被狭隘化了,这种局限的认识一直使中国散文无法从容大度。当然,还需指明的是,艾云同时还是那种天生具有小说家和诗人气质与实质的写作者。可以这样说,艾云的作品包含着所有的文学体裁,或者说,艾云把所有的文学体裁都视作技巧,这无疑是大技巧。其中细节的文学元素,诸如修饰风格等,自然不在话下。从中可看出一个作家高超的写作能力,这才是真正的新散文与大散文。当然,这一种命名对于艾云也可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她的写作或许就是为了脱离命名而存在,她的写作就是自我的建立——一种叫艾云体的体裁。
艾云的文本极其关注事件,事件像润滑油一样缓和了理性文章在阅读上的乏味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和知识量。在她的巧妙安排之下,个人的、群体的、古今中外的各类事件遍插作品之中,既形成写作的主体又可看作文章的花絮,这使得她不少饱含学术分量的作品充满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就像小说的情节一样引人入胜。事实上,在艾云的文本中呈现的种种现象,小说的元素绝对明显。但这并不排除事件的真实性,而是一种由想象甚至虚构式的想象所支配的真实,也就是说,艾云从一开始就设置了阅读的诱饵。而在理论、观点一类文字的交错之下,文本的价值悠然如南山洞开,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文章价值的实体。“伟大的小说必须是理性直接的进驻”,米兰·昆德拉还提供了一个个案。
在《美丽的作为》一文中,艾云以事件作为写作的切入点,娓娓地勾画和还原了蓬巴杜夫人凄艳华丽而充实传奇的一生,让读者为她被疾病夺走的脆弱生命而扼腕叹惜。在事件的开始,艾云让蓬巴杜夫人的出场充满了诱惑性,这个诱惑既是对路易十五的诱惑,又是对读者的诱惑。一个清晨,在赛纳尔猎苑,一辆带有褶蓬的轻快马车在驰骋,马车上突然一闪而过一个“玫瑰般嫣红俏丽的面孔”。这一场景对于路易十五而言,真的就像一篇小说开了头,他的心被撩拨了起来,瞬间的印象比烙印还深刻,他必须追踪下去。艾云随之把事件或情节很快地转到一个化装舞会上,为路易十五认识蓬巴杜夫人制造了机会。之后蓬巴杜夫人真正的历史开始了,为了把这个美丽女人的一生更完整地呈现出来,艾云首先回顾了她的成长历程,以此证明美丽与阴谋无关。这依然是一种艾云式的叙述,其主要特征是在一些段落的“空位”上加进一些观点言论,廖廖数语有如导读,让读者在不经意间来到下一个阅读的驿站,读者那么自然地被吸引着,犹如阅读小说的感觉。这一笔法几乎贯穿全篇。成为了路易十五的宠妇后的蓬巴杜夫人,开始了她“美丽的作为”,之后的事件环环紧扣,令人目不暇接,把一个美得令人窒息又才智超人的女人短短的一生完全铺展开来。其间对环境的想像和描绘,很能渲染一种氛围,而简洁有效的对话则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
《致命的原创性》也同样呈现出这样的写作倾向。整篇文章所牵涉的人物、事件相当多,如克尔凯郭尔、卡夫卡、普鲁斯特等。最后,艾云把焦点聚集在杜拉斯的身上,事件的力度增大,并利用杜拉斯的作品作情节或插曲,一边叙述一边呈现杜拉斯的卓越写作才能和别具一格的个性与智慧,其间虚与实的描述交替进行。艾云还着意引用了一些杜拉斯言语,也可以说为完善杜拉斯这个诡异、智慧的女性写作者而让其独白,如:“如果我只属于一个男人,我就不再完全是个女人。”这种具有震撼性的语言,让人对杜拉斯产生一种绝对的深刻印象,同时隐隐觉得,杜拉斯更像是小说中的人物。
多年以前,艾云还曾经写了“南方叙事”系列随笔,这些文章以个人身份对种种事件作了详尽的剖析和回答,艾云曾告诉我,不少事件其实是她的杜撰。这里,为她的小说家气质又增加了一个例证,也指明了虚构在散文写作中同样重要。虚构是一种智慧,事实上,如果虚构得真实就不再是什么虚构了,其内里的情感资源同样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温度和感染力,这是一种能力的张扬和技巧的再生。一流的作家本身就善于创造。罗兰·巴尔特说过:“让散文表明自己类似于小说吧。”[2]
艾云的心性中有很诗性的成分,她文本中呈现的那种浓郁的诗性一度使我想到她的女性身份,当然这种联想并不具有什么科学性。事实上,你很难从艾云的写作中看到女性主义的倾向,她往往是以中性的身份说话,不知这与她认可的“形而中”概念有没有关系。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艾云对诗歌的选取与把握绝对比某些所谓的专业诗人(含诗人编辑)更准确和敏锐,她认可的诗歌有一种语言难度的标准,对艺术性有严格的苛求,她看重诗歌语句的美感和质感,希望接触和倾听到天籁之声。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遇上这样的编辑是幸福的,因为,这样的编辑从本质上维护文学的尊严。
在艾云的作品里,诗意的呈现枚不胜举,有些甚至是以章节、段落为单位,其间抒情美、张力美、智性美、哲学美的文字比比皆是,这使得艾云的文章具有一种迷幻般的气息,这些文字又起到一个写作和阅读的缓冲作用,或许艾云试图在自己理性的写作中建立一种中和反应。事实上,这是艾云注重文学的因素。随意列举如下:
透过历史的烟岚,我仿佛看到了那些身着长衫或西服的年轻人。那时的人,怎么面孔那般净朗和清癯?有些超尘脱俗的虚静,却是内心翻卷着大风暴。若是梅雨之夕,淅淅沥沥的雾帘中,他们打一把油布雨伞,迅速将打印好的传单夹在腋下又急匆匆出门了。即使在盯梢、追捕、暗杀的危机重重中,他们的脸上仍是那样平静自若,因为心里有一个大的理想,就什么都无所畏惧了。撩起衫襟,身影隐匿在叆叇密布的苍茫里。[3]
艾云善于“布景”,用诗一样的文字去营造气氛,对场景的描画精确可见,唯美的语言同样可以达到一种语义的准确,它的环境是一种如画般的清晰,并逐帧逐帧在读者的大脑里延长。当代诗歌不缺乏叙述,缺乏的是叙述中呈现出的诗意。
美,是各种理想状态下最综合的指标。美其实是一种力量。它将集中着真与善。它闪耀着钻石般璀璨的光芒。美将整合地携带出许多好东西,政治清明,经济富庶,精神洋漾,才可能创造美。美是自我描述和呈现,是精神气质。人的眸子熠熠,带出的是明智生活;人的骨骼匀称,结构着完整律令。美是深度,涵括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的整体要求。美的精神气质,其实是已经转向自身,又可以在公共空间推行,可以吸引人们前来,而不会吓跑很多人。这是劫持,却是瞬间被照亮的被虏;这也许是深渊,却是魅力无可躲匿的浮沉。美,来自力量,来自辩证,来自个人自由伦理实践,来自古希腊的阳光。[4]
这些文字带着张力,是一种诗意的评论。理性文字的非理性表达或非理性感受,或许更增加了一种理性效果。在简洁、内敛、跳动的述说中,艾云把美和美的内核和盘托出,或者说,美与思想高度统一,带来一种格言般的诗意。事实上,艾云的不少文字简直就是格言,格言是思考的结晶体。艾云是一个有格言意识和情结的写作者,她作品的生命与思想向度总是面向深远。换言之,她为经典而写作,或她的写作就是经典,她追求的是一种艺术和自我的永恒。艾云和她的文本进入未来是迟早和不言而喻的事情,她同样像那些“有信仰的人”和“志士仁人”一般,应该住进“最后的宫殿”。
如果从泛概念的角度,把艾云的写作定义为散文的一种,那么她的文本与传统散文相比,则表现在文章里的事件不是单纯性的一种叙述,而是各种文学元素的拼贴。艾云把叙述复杂化了,叙述不再是常规的有秩序的进行,而是秩序的重组,叙述的路线出现了种种可能,这无疑是一种富有生机的写作,是叙述的加强,其中的“事件”往往充当文章观点的维护角色,是绝对有力的“佐证”。与所谓的新散文相比,艾云在语言技巧的使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难能可贵的是艾云的节制,她在语言上的张扬给人的感觉总是恰到好处,其中镶嵌了一种必要的柔和。艾云作品最大的优势,是她作品中表现出的理性思考,最重要的是这种思考还是绵密而连贯性的,她破除了新散文中的那种虚无飘渺的文字游戏,那种暧昧的一闪而过的观点。事实上,理性的欠缺常常使得新散文难以展示出一种“大家风范”。
某种意义上,艾云的写作是一种纠正。真正的“新散文”或干脆说“标准”文本,必须呈现大全大智的写作事实与实力。J·M·库切在评价布罗茨基时曾有这样一个定论:“他的散文获得了一种音调——它新鲜而又复杂,苦涩中带着甜蜜。”[5]我对艾云作品的感觉则是:它新鲜而又复杂,率性中带着自然。
二、思想者或写作的责任
在艾云的写作中,寻找“失踪者”或者说“寻找”,是一个很重大的主题。失踪者本身就是一个笼统而耐人寻味的身份符号,这些失踪者可以是思想家、哲学家、知识分子、学者、作家等,也可以是流亡者、在场者、隐逸者、被遗忘了的人等,可以相互渗透。寻找他们,事实上是在寻找他们的思想、态度、观念、学识,甚至遭遇等,寻找他们的立场和行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独立与独特既可以孤立地伫立于世上,但也极有可能被历史的风尘湮灭,艾云在理清他们学说的同时,也在建造着自己学说的支撑点。这种学术的传承方式,是真正的融会贯通,是对问题和思考真正的切入,或者说,带着问题去追问和解答。诚如艾云自己所说:“思之路上,谁在寻找?谁是失踪者?我们都在寻找,我们也都可能是失踪者。如若我们不让自己失踪,那就得始终带着追问上路。”[6]没有追问则没有新的思考和阐释,没有新的体系产生与建构。这应该是一个思想者持续存在的唯一条件,也是学术获得前进的必然过程及途径。无疑,艾云在进行一种思的行动。
很大程度上,寻找也是一种还原,还原思想与学术或与这有关的一桩桩事件的真实性、价值和意义,并以此作为对比或借鉴,对照审视中国的现状,其实更多是在历史的回声中对当下作一个现实的参照,以此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一个警醒甚或修正。无疑,艾云把这当作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艾云总是善于“发现”。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文中,艾云论述了雷蒙·阿隆与萨特的论争。借此道出右翼声音与左翼思想的观点对立。由于左翼思想的浪漫主义特征,它总是受到人们的追捧,因之作为极具文学才华的萨特在这场论争中,无疑以绝对的优势压倒性地盖过了雷蒙·阿隆。而以严谨、慎重的理论方式,以经验性事实说话的雷蒙·阿隆,在被动局面之下并没有妥协,发表的依然是一种真相事实,他揭露当下的每一个问题,并认为“左派、革命、无产阶级为红色神话的知识分子共同价值观的毒害作用,这是一种类似鸦片的作用”。这对于战后的法国而言,其民众的思想原野依然流有一种枪炮与战火般的热烈情怀,则无疑撕除了一层理想的面纱。雷蒙·阿隆的清醒事实也就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但判断一件事情绝不是以人数的多少而断定。晚年重病缠身的萨特在心底承认雷蒙·阿隆是对的,最后的效果无疑就是真理,他最终站在了雷蒙·阿隆的这一边。艾云在详细分析这二人论争的过程中,还联系到当时发生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从这里我们可以探明艾云真正的意图,其实恰恰是为现实的中国情况而忧虑。在这两场性质极其相似的论争里,艾云既是一个旁观者,又充当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她灵活地搬出了一套教案或模本,可谓适时和及时,这种分析自然也就能引导现实。
艾云是那种具有忧患意识的人,艾云在还原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立场、重新为他定位的同时,还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者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良知:详尽而深度地触及,敏感与冷静地说出;不以集体倾向为主,却尊重客观规律。而在《寻找失踪者》一文中,谈到朱学勤与张志扬的一场争论时,艾云的这种“专业精神”更深入到学界内部,同样忧患的指向也隐隐现身其中。她总是最先意识到危机,而危机恰恰是思想者思想的契机。她想到解决的办法:学会划界,即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处划界,这是思想逐渐走向理性成熟的标识。中国过去一向礼法不分,这往往导致用农业浪漫主义思维去解说社会政治生活,其教训之大,有目共睹。
安·兰德在她的著作《致新知识分子》中谈及:“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社会的眼、耳、喉舌:他的工作就是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估定其价值并知会所有其他领域的人。”[7]而在观察的过程之中,知识分子也是在充实知识分子的“知识性”,学识的完善其实是一种责任的加强,而做到“知会”的尽善尽美则极可能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至少具有一种道德性。我倒是希望,学者的关注不仅仅限于学界,这样,学者的工作才充分显示其应有的价值和影响。
艾云在《谁能以穷人的名义——知识分子认知限度及分析》一文中谈到,同样是右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他“极力推重市场竞争,推重法律秩序,反对国家干预,因为他知道如此下去的循环逻辑,便是必然导致奴役之路。但多少年来,人们以为他是念咒语的乌鸦,他的话听起来那么刺耳,那么没心没肺,没有同情和怜悯,不关心没有市场竞争能力的穷人”。哈耶克的“表现”往往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他的名字与雷蒙·阿隆经常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的理智、清醒与独到的经验使他们展示出一致的形象。事实上,艾云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认知作风与洞察力。发现被发现者同样需要勇气和智慧。
艾云所关注的人,往往是那种客观看问题,敢于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以真为本的思想者,他们的观念表面上看是现实的、冷酷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是一种隧道般的深远,是人类实践光芒的必然的验证。基于此,在当时的时代里,他们更多地被人误解性地认为是不怀好意,是不合时宜的对立面。客观地看,平均主义忽视了市场经济,忽视了竞争的存在,忽视了“利益”这个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要素,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在当时环境下无疑也是一种空想。事实上,那些“打着穷人旗号的知识者,是书生气十足的认知局限者”,而哈耶克恰好是超越这一局限的人,他从实际出发,看重市场规则,捍卫市场竞争和秩序。他认为,市场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公正的,这就摒弃了一种阶层的本位主义。所以,恰恰相反,最关心穷人的便是哈耶克。为了更准确地阐述,艾云会自然地融入她研究的角色之中,事实是对所研究的对象有充分把握,艾云总是能看出他们学术和思想的“实处”或者关键的部分。艾云又善于从所研究对象的角色中走出而回复到自身,但这时,她已经把观点的刀剑磨得更加闪亮与锋利。艾云分析和肯定了哈耶克,从另一角度指出更多人的盲目心态,她其实是在作一种观念与理性的更新,也是为现今社会的发展作出一个有力的图解说明:
是谁规定了穷人一定会在市场竞争中一败涂地?芸芸众生其实最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市场可以跃过阶级的樊篱,而使机会降临到每个人头上,而不只是给有权有势者。再说,穷人不是抽象,不是笼而统之;它是具体,具体到我们每个人。谁以穷人的名义,谁就是在强奸民意,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一个统治权力集团的既得利益绞尽脑汁的维持,这只能将百姓拖向深渊。再说,若果把别人通过劳动致富而挣来的钱财搜刮而去以分摊,这叫什么公正?只能为强盗逻辑寻找充足理由。此时,法律当然必定废弛。当剥夺别人的财产成为惯性,当私产不被保护,这是富人和穷人所有人的财产都不被保护。富人被打倒了,没收了财产,穷人永无翻身改变窘况之时,为穷人的宣传,就是一场彻底的骗局与吊诡。在为穷人的名义下,多少血腥罪行横行无忌。[8]
大哲学家、知识分子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著作《知识分子论》中,有一见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9]艾云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并不是我讨论的要点,也不重要,但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出场”就有“代表”的倾向;但作为“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艾云无疑是充分掌握了的。除了以上的那两段文字,艾云在其文本中都是“在场”的,她总是让语言作为身份的替代,该出手时就出手,而这一目的更多是为了观念的放大与扩展,把额头上的光芒从容搬进纸页中,以更广度的语言景象展示一种思考与现实的透视图,恰恰挖掘和拓宽了一种哲学的内核和真相,并沿着这竭力向上实现一种理念的提升,这就是艾云的学说。最重要的一点,其中还表现出一种批判的内力——使人在信服之余必须进行全面的反思。某种意义上,艾云的写作已具有一种道路的意味。在她的文字里,启示的作用相当明显。
批判性是艾云写作令人折服的一个重点,甚至也是艾云写作的一种精华所在。批判的言外之意是深层的参照和个性的张扬,她那切肤之痛的感受也是她的观察、经验、体验和总结,它代表了个人勇敢的担当,代表了一种写作的信仰;从另一角度,也就等同于萨义德所说的“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关键是真正的思想者根本不想回避与逃避这一必然的“案底”。而在中国,批判精神正在从不少评论家的身上逐渐消失,这些评论家的立场以及鉴赏能力实在令人怀疑,他们对现实甚至文学现实的发言集体性失言。评论或言论一旦丧失尖锐性与相对的公正性,也即是违背了批判的精神,评论本身的责任进而便演变成了一种暧昧的图谋。现实中我们还经常看见,这些评论家都在为自己的言论辩护,说到底,这是并不怎么高明的掩饰,一种不言而喻的怯懦。
再细心留意一下,艾云的文字其实还饱含一种悲悯的情怀,这是一种终极关怀的情感流露,真正同情穷人和为这些底层劳动者命运着想的,是那种具有大局意识的思想者。这种意识使艾云不管在个人事件还是群体事件(其实这些事件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通过个体折射群体,群体中凸显个人的重要性)的论述中,呈现的观点都透视出一种宏观性。这种宏观性却由具体的理性细节所组成,即把哲学问题变得具体化,问题与观点的呈现清晰而一目了然,像一道数学方程式的步步解答,所以构建出的意义内涵绝对不虚无,相反一种具象的敲打让你真切地看到一种理性和它的背景。艾云进行的是一种抵达澄明之境的解读,这恰恰是理性的难度。理性的准确是一种由逻辑思维推动的激情,事实上是一个“自我化”的过程,即每一个论断更多是经验和它的集合体,以及言说的可信性,并由此完成一种预定的意义。这有别于学院派的那种晦涩,但又保留有学院派的深奥,因为它演示了一个深奥的过程,即一种理性终端的把握的合理释放。而学院派则苦于秉承一种系统的延续,漠视现实的重要性,把书本上的学术反复“抽象”,无法也不想走出教条的怪圈,自然就缺乏个性的语言和思想。因此,他们的学说具有晦涩、不可信的成分。
这里再阐释一下“艾云体”和“艾云的学说”这两个名称。这其实隐隐约约暗指了艾云的原创性。艾云说过:“原创性是致命的游戏,但从前、现在和往后,仍会有人慨然前去。”我把这句话看作是艾云的独白、宣言和守则。对于一种文体或学说,原创性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原创性代表了文体的特异和观点的推陈出新。原创既是本能也是实验,如果不是天才,原创的“创造”则往往具有瞬间的闪光或者时间之上的经验总结,一种自我观点的突兀与异类表露;对于理性文本,后一种的可能性应该更大。所以后天要转变或超越先天,无疑与一个人的学习和努力有关,甚至在任何关注点上都要保持思考的热情,触动自己的悟性,然后来一个缝合与综合,事实是穿透自己的各种过往经验。但从另一角度去看,原创也是一种危险。出师未捷而亡与对现行思想及文字秩序的杀伤,无疑是两种切实的可能,可以说,从一开始,原创就蛰伏在一个危机的层面上。但原创的目标犹如罂粟,或原创就是希望和要求一个人的思想和文本开出比罂粟更娇艳的花。所以不管怎样说,写作真正的价值是原创性,原创是一种必须,是把写作当作事业的人的意识和责任。
在《缓慢地迈向公民之路:职业及阶层的心态分析》一文中,艾云通过分析各类人物,如小百货摊主、石匠、农夫、英雄、绿林好汉,以至体制内外人等,然后提出自己对公民的理解:“公民不一定以德性为要。但他拥有个人权利,也同时负起责任。重提‘责任伦理’,并以此厘清一些混乱,可能是尝试着、逐渐缓慢地迈向公民之路的必要条件,也是走向繁荣自由国度的必要条件。”[10]艾云为了这个“写作答案”,当中可谓出尽浑身解数——聚焦对象、切片分析、旁征博引、发掘历史,对比现实等等,这就是艾云文本的又一个显著特色,也是创作的高度和难度——一种学者型的写作,其间呈现出写作的力量感与哲思元素。若撇开公民这一定义去看,我更想说的是艾云的关注面,她确实把人类群体作为自己观察与思考的对象,这体现了一个思想者的“全面性”或“人性”。只有全面,才能保证一个俯瞰的视角与姿态来进行观察,才能够真正在问题与问题之间理清思路,只有人性化的方式才能深入理解“人性”。因此,艾云的论述总是那么到位和“出位”。
这里再引用一下安·兰德的观点:“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就是研究人的科学,即所谓的‘人文学科’,但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其影响遍及了所有其他行业。”[7]以人为本,其实已关系到一个众生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而言,人是世界的主宰,构成人的“整体”则是各种各样的事件,而作为人的群体与群体事件则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群体的一种联系与连贯,是一种关注范围的再生,最终这些会跟随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命运的脉搏而跳动,并在一个思想者的认识与写作中延伸。无疑,艾云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点,她把人作了一个“还原”。
作为思想者的艾云,在思考缓慢地迈向公民之路的过程中,其实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发挥公民责任和意义的公民,或者说本质上的公民。是否可以这样界定,思想者的思考和表达也是履行一个公民的责任,这样,原则就代表了高度。
著名汉学家德国的顾彬先生在一个访谈里,一如既往地对中国文学表示失望,而我却质疑顾彬先生到底接触了当代中国的哪些文学作品?譬如,看过没看过艾云的作品?看见没看见在中国沉默写作不事张扬的那些作家?顾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敢精神严重受挫”[11]。那么他知不知道,同样也有知识分子正在千方百计地以自身精神的游历而默默地对我们的国家提供前进的良方。
[1]苏珊·桑塔格,贝岭,杨小滨.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访谈纪要[J].天涯,1998(5).
[2]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3]艾云.谁能住进最后的宫殿[J].花城,2006(4).
[4]艾云.自我呵护[J].花城,2006(1).
[5]王敖.J·M·库切——布罗茨基的随笔[EB/OL].豆瓣读书.
[6]艾云.寻找失踪者[J].花城,2006(6).
[7]安·兰德.致新知识分子[M].冯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8]艾云.谁能以穷人的名义:知识分子认知限度及分析[J].花城,2006(3).
[9]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10]艾云.缓慢地迈向公民之路:职业及阶层的心态分析[J].花城,2006(5).
[11]顾彬.中国当代文学让人失望[N].参考消息,2007-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