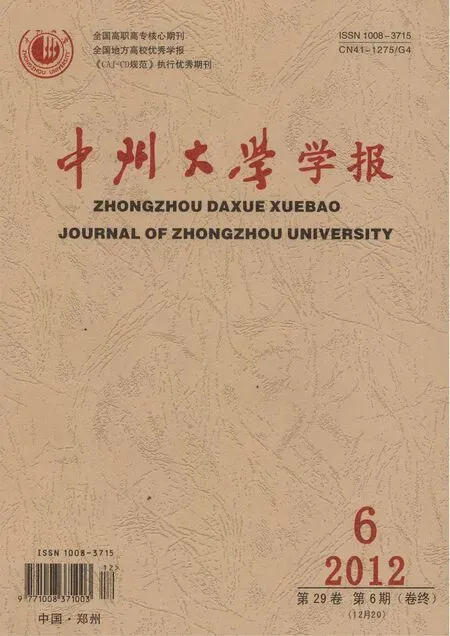一个反诗意的存在
——别尔嘉耶夫论季·尼·吉皮乌斯
耿海英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87)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介绍吉皮乌斯至今,应该说对她的关注并不算多,几篇研究性文章①和网文②,几家刊物上的诗歌译稿③和一些诗集④中收入其诗歌作品,几部研究“白银时代”的书⑤中论及她的创作,还有她的两部回忆录⑥和一部诗集⑦的译本。
在这些翻译与研究中,学者们给我们呈现的吉皮乌斯的形象是:“女巫”般诡异、伟大而清高的东正教女诗人;“彼得堡的萨福”;“颓废派的圣母”;“穿裙子的俄罗斯路德”;“俄罗斯的卡桑德拉”;“绿眼美人鱼”等。这些标签透露着对作为一位诗人与宗教活动家的吉皮乌斯的肯定。在学者们对吉皮乌斯的研究中,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吉皮乌斯诗歌的宗教性与神秘主义特征,并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吉皮乌斯诗歌中的诸多主题,如人格分裂,主体性,善与恶,孤独与虚无,苦难与抗争,自由与爱,死亡与永恒等。但这些主题如此之抽象,她如此之爱抽象,正如她的诗中所说:
我对抽象感到可亲:
我为它创造生命……
我喜爱一切远离尘世的东西
连同它们的朦胧迷离。
我是异乎寻常的梦境
和神秘的仆从……
却不知如何用此世的语言
表达唯一者的声音……
——《书前题诗》
以强烈的宗教情感表达抽象的主题,使她鲜明地区别于情感细腻、委婉柔美、充满了浓烈女性气息的阿赫玛托娃,也区别于那样贴近现实、自信豪放的茨维塔耶娃。吉皮乌斯的诗,是灵魂的求索,是上帝的追寻,是祈祷般的诗歌。别尔嘉耶夫说,“吉皮乌斯是我们富有才华的女诗人,她独具风格”,“我给予她的诗歌以很高的评价”,“在她祈祷般的诗歌中,活跃着个人紧张的情感和对上帝紧张的寻求”[1]。这也正是吉皮乌斯本人对诗歌独特的理解。她说:“人的天性之自然和必要的需求,就是祈祷。每个人都必然地祈祷或渴望祈祷,不论他是否承认,不论他的祈祷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崇拜什么样的上帝。祈祷的形式依赖于每个人的才能和习性。”[2]290“我们的祈祷,对我们而言都是活生生的诗句,诗歌……是人的心灵祈祷的一种形式,诗人……在诗歌中祈祷。每个人是如此需要、理解、珍视自己的祈祷,需要自己的诗——他心灵瞬间完满的反映。”[3]156-157吉皮乌斯把诗歌视为祈祷。祈祷是与上帝交流,是跟上帝倾诉自己最隐秘、最重要的事情。祈祷是激发个性的精神体验。吉皮乌斯的诗歌创作过程,就是一个祈祷的过程。因此她的诗带有深刻的宗教性。吉皮乌斯是关心灵魂的诗人,用诗来完成自己的信仰建构,使之成为祈祷的形式。
学者们的研究证明了,在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吉皮乌斯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她作为当时诗坛的核心人物之一,代表了“我们(俄罗斯)诗歌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安年斯基语),“作为一个有才华的、独立的、善于为我们讲述自己心灵的诗人,作为一个卓越的诗歌大师,吉皮乌斯应该永远载入我们的文学史册”(勃留索夫语)。然而,在这种肯定中,诗人的一些侧面也往往被忽视。别尔嘉耶夫作为吉皮乌斯同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则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观察、评价吉皮乌斯。
一、一个反诗意的存在
同属宗教哲学领袖的别尔嘉耶夫,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并没有太好的私交,但与其妻子季·尼·吉皮乌斯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别尔嘉耶夫在自己的《思想自传》中回忆说,他们“有过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他认为,她“是一位极其出色的人,但也是位令人痛苦的人。她蛇一般的冷漠……身上缺乏人的温情”。别尔嘉耶夫虽然“给予她的诗歌以很高的评价”,但他认为,“她并不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存在,而是像当时许多诗人一样,是一个反诗意的存在。尽管那是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但在俄罗斯复兴的氛围中却缺乏一种诗性的东西。”[4]389
时隔几十年后,在这部带有回顾和总结性质的《思想自传》里提到的吉皮乌斯,应该是她留给别尔嘉耶夫最深刻的东西:一个出色的人,却“蛇一般冷漠”,“缺乏人的温情”;可以创作杰出的诗歌,却是一个反诗意的存在。
为什么在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却缺乏诗性的东西;一个富有才气的诗人,却是一个反诗意的存在?
吉皮乌斯可算作别尔嘉耶夫不多的几位深交友人之一,不过正因了这种深交,却更强化了他们的分歧与不同。而这一切又皆因了那个剧烈动荡时代中各自不安的思考与选择。
20世纪之初的那几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夫妇一直致力于宗教-哲学探索,在当时那场热烈的探索运动中,吉皮乌斯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们组织宗教-哲学会议,办杂志,写文章,成为当时“新宗教意识”的先驱,直到1905年革命后他们迁居巴黎,在那里,他们依然是侨民的中心。
1905年革命之后的1906—1908年间,是俄国文化一个病态而深刻的危机时期,这一危机是对不久前发生的革命的亲身体验,并试图对它加以思考引起的。这次危机最尖锐的时刻是在稍后的1909年,随着《路标》的出版,围绕着作者们所表达的思想而爆发的大辩论。当时,对文集作出最激烈反应的,不是来自社会民主阵营,而是来自不久前还是同盟者的象征主义者和进行宗教哲学探索的路标派。但分裂的出现要早得多,那是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举办《新路》和《生活问题》杂志期间,他们论证的“神权政治”显然失败了的时候。当时,在这两份杂志周围聚集了不久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颓废派,索洛维约夫主义者,彼得堡宗教哲学会议的参加者,还有罗赞诺夫式的人物。他们在文学和社会生活中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团体,建立一种“新宗教意识”的渴望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新宗教意识”是一种相当流行的、内容不确定的、允许有各种不同阐释的思想。这些各不相同的阐释,正如杂志周围那些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感受一样,五花八门。将各种力量积聚在一起的革命浪潮在相当程度上仅仅是防止他们分裂的一个外在的铁钩。1905年革命失败,《生活问题》杂志停刊,其成员相当一部分侨居国外之后,这个铁钩子就不存在了,而“新宗教意识”思想,至少是1904-1905年所宣扬的那样一种思想,显然是过时了,它需要随着思考所发生的诸多革命事件而发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前的同盟者彻底分道扬镳了。
1906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迁居法国,在那里他们生活得相当积极:他们的政治-文学-神秘主义沙龙里集中了俄罗斯侨民群体,他们恢复期刊,就俄罗斯革命发表文章,准备文集,与法国政治活动家建立联系,并被深深拉进了围绕政治的活动中。吉皮乌斯的名言“我们不是被驱逐,我们是使徒”正诞生于此时。《艺术世界》的创办者阿·尼·别乌阿回忆说,在“沙龙里形成的简直就是革命的公寓-指挥部,信仰革命的各色人等都经常往来于此。”[5]444在宗教领域,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继续致力于“宇宙的三位一体”、“第三约言的王国”的思想,认为这一“新宗教”应当取代历史基督教。而在现实层面,他们努力巩固和扩大团体,其精神核心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费洛索福夫这个三位一体。
当然,他们的沙龙依然是文学性的,那里因象征主义的命运、丘尔科夫的“邪说”、勃洛克的离经叛道、高尔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而依然激情沸腾,那里思考、讨论着报刊杂志论战的战略战术。所有这些奇异地混合在一起,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形成了某种狂热的“神秘主义的氛围”。
对于别尔嘉耶夫来说,这几年更为积极的与其说是在社会活动领域,不如说是在创作和世界观方面。但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相反,他越来越远离神秘主义而走向“宗教的现实”。尽管别尔嘉耶夫一生都认为自己是“神秘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抗者,但他的反抗性从这时开始越来越不是在教会外部,而是在教会内部,在历史基督教的范畴中发展着,而不是企图建立新的宗教。
自然,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巴黎的朋友圈中引起了不快,因为,别尔嘉耶夫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认为是“自己人”,他被看作是最有可能的私人小团体的参加者。他决意不参加他们的“新教会”,强化了怨恨。相互的不满和疏远不断加深,起初是思想上的,随后是私人关系的。后来彻底决裂。别尔嘉耶夫在《思想自传》里写道:“文学宗派在我内心激起反感。我总是排斥建立小宗派式的教会的尝试,我无法在创造新的秘密(指梅氏的“圣三”奥秘——笔者)中去想象新宗教意识。对我而言,新事物不在圣礼的领域里,而在先知里。”[4]405在这个意义上,泰奥菲勒·戈蒂耶大街(梅氏夫妇巴黎住地——笔者)事件,即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费洛索福夫公开反对别尔嘉耶夫,指责他伪善,仅仅是最后的一出戏。其实决裂早已成定局,早在别尔嘉耶夫与吉皮乌斯的往来信件中就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他们的通信表明,尽管别尔嘉耶夫与吉皮乌斯私人关系较好,但是在对教会的理解上,在对新宗教意识的诠释上,他们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别尔嘉耶夫在信中指出,吉皮乌斯在宗教探索过程中要建立的“新宗教”,有宗教宗派的倾向,在这种宗派中,人的个性会死亡。这是别尔嘉耶夫所不能接受的。虽然他肯定了吉皮乌斯在这场宗教革命和宗教复兴运动中的先驱作用,也将其视为自己在精神上无比亲近的人,伟大宗教进程的蒙难者,但是,他反对吉皮乌斯将自己的一切视为宗教本身,反对她认为只有自己的圈子才是教会的,只有在她身边才会形成新的、永恒的教会,而在此外的一切都要受到审判的倾向。
在那几年里,吉皮乌斯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许多思想都是由吉皮乌斯的思想火花启发而来),她是一个“内心充满反叛的探索者”,但是,她将自己封闭于一个神秘的小圈子,试图建立一个“我们”的小教会,试图成为拯救者,试图“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塑造所有人和所有事”,把“同一使命强加给所有人”,走了一条神秘主义、宗派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道路,在这样一种近于宗教的狂热中,迷失了自己。本该成为“充满魅力、令人倾倒”的完整的人,却没有成为;本该“在自己的身边播撒快乐,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了“蛇一般冷漠”、“缺乏人的温情”的女人;本该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诗人,却在自己营造的近于修道院的冷峻、神秘、清心寡欲的氛围中成为了一个反诗意的存在。别尔嘉耶夫说:“我永远都无法容忍对哲学、文学、艺术和一切文化财富的毁灭。”[6]一直以来,吉皮乌斯过于强烈、近于狂热的宗教倾向,过于执着于“新宗教”、“新教会”的构建,损害了她的诗意。别尔嘉耶夫认为,“吉皮乌斯首先是一位富有思想性的作家,有时甚至是思想性过甚而损害了艺术灵感:她总是寻找‘意义’,有时让人觉得她爱‘生活’不如爱‘意义’。”[1]“思想性”过剩,“诗性”不足。而且,“在吉皮乌斯远不如诗歌的小说中,这种思想性更是采取了片面的形式,许多中短篇小说像是给指定的主题写的”[1]。
这看似吉皮乌斯个人的问题,却也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问题,思想性过于充盈而损害了艺术灵感的现象,并非吉皮乌斯一人所有,她“像当时许多诗人一样”。“尽管那是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但在俄罗斯复兴的氛围中却缺乏一种诗性的东西”。虽然“新宗教”意识的探索对于那个时代具有无可置疑的意义,可是极端的、走火入魔的实践,必定会带来对自由、个性、创作的损害,这是别尔嘉耶夫可贵的清醒认识。
不过,在那样一个疾风暴雨的时代,对于任何一位严肃面对生活的艺术家来说,有如此之多无法绕过去的问题,思想的紧张性恰恰是他们的创作中散发出来的一股内在力量。
虽然别尔嘉耶夫觉得吉皮乌斯“是位令人痛苦的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高度评价她作为一个诗人的独特性和价值。她本人才情横溢,思维敏捷,观察准确,文笔犀利,这从她当时的一本随笔《鲜活的面容》中可以得到印证。然而,因了她冷漠的个性(她很少感情用事,很少能感到她的激动与热情的直接表达。——别氏语),也因其不留情面的尖刻(她能高超地刺痛对手,而自己却不动声色。——别氏语),以及她总有的一种“小圈子”倾向的封闭,所以,她的价值很少有人能认识,并对其作出正确评价。尤其是,她还有着极端颓废派的名声。在当时对颓废派的一片责骂声中,更是少有人去触碰这朵“罂粟花”。然而,别尔嘉耶夫1909年撰写的文章《克服颓废主义——论季娜伊达·吉皮乌斯》,为吉皮乌斯辩护。
二、一朵罂粟花
别尔嘉耶夫的文章缘起于吉皮乌斯于1908年以安东·克莱尼的笔名(男性名字)出版的文集《文学日记》。其中收录了吉皮乌斯八年间的文章。主要有《生活的面包》,《爱的批评》,《当代艺术》,《新小说》,《我的阅读》,《两头野兽》,《我?非我?》,《关于戏剧的话》,《永恒的犹太人》,《需要诗歌吗?》,《情爱》,《论鄙俗》,《什么和怎么》,《给异口同声的批评》,《夏日里的思索》,《日常生活与事件》,《所有人反对所有人》,《颓废主义和社会性》,《世界缺席》,《诗人的散文》,《人与沼泽》,《在尖端上》,《可怜的城市》,《巴黎写真》等。在文章一开始别尔嘉耶夫就讲道:“对这位受到不公正和不正确对待的作家,我想说几句话为之辩护。安东·克莱尼有着极端颓废派的名声,他的写作被认为无人能懂也人无人需要。况且大家知道,这位敢于写严肃与深刻问题的安东·克莱尼不是别人,而是一位女诗人。除了她自己人的小圈子,没有人读过她的东西,在此之前,没有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愿意发表她的作品。而当一个人认真而不带偏见地读完安东·克莱尼的《文学日记》后,就会承认,这是位充满智慧的作家,思想敏锐,充满对生活的崇高意义的信仰,不懈地追求向上。安东·克莱尼与季·吉皮乌斯是同一人,不仅没有损害她的声誉,甚至提升了她的声誉。季·吉皮乌斯是我们时代极富天才的女诗人,她独具风格,人们对其的评价还相当不够。”[1]针对吉皮乌斯“极端颓废派”的名声,别尔嘉耶夫作了仔细的甄别。他认为,虽然季·吉皮乌斯是俄罗斯颓废派运动的先驱之一,与颓废派有着毋庸置疑的关系,但这只是其一部分,因为她在颓废派中的角色是特殊的,在她身上已经表现出克服整个颓废主义的可能性。别尔嘉耶夫认为,吉皮乌斯的诗歌是“祈祷般的诗歌”,其中“活跃着个人紧张的情感和对上帝紧张的寻求”。虽然“在一些诗歌中也感觉到某种阴暗的东西,某种魔鬼的神秘,危险的双重性,但却从未失去希望”。别尔嘉耶夫指出,在吉皮乌斯身上可以区分出“颓废期”与“超越颓废期”。在她的“颓废时期”,她超越了人的边界,因之失去了“我”与“非我”的区别,试图像爱上帝那样爱自己;但即便是在她的“颓废时期”,“她也从没有与颓废主义的印象派,与颓废主义的思想贫乏掺合在一起”。别尔嘉耶夫说:“可以感觉到,吉皮乌斯不懈地与自己身上某种阴暗的天性进行斗争,不想毁掉自己的人格,以某种准则来对抗那些阴暗的力量。这种为了拯救自己而展开的激烈的与自己的内在斗争,使她区别于其他颓废主义者。”[1]
在那样一个各种思潮流淌膨胀、鱼龙混杂的时代,严格辨别它们,就显得尤为重要。别尔嘉耶夫正是以冷静的哲学家的眼光来甄别一切。早在《论〈文学的衰落〉》一文中,别尔嘉耶夫就已经严格区分了“新艺术与色情文学、宗教-哲学探索与颓废主义、基督教与神秘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楚尔科夫与布尔加可夫、楚科夫斯基与梅列日科夫斯基、比尔斯基与弗·索洛维约夫、维杰金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7]。在这里他又严格区分了颓废主义内部的问题,将吉皮乌斯与其他颓废主义者区分开来。
吉皮乌斯自觉地实践着象征主义对诗歌的理解,因此她的诗歌大多是表达自己对宗教、世俗世界的理解。诗歌在她那里揭示事物的秘密,歌颂永恒,连接上帝。她的那些过于抽象的诗《钥匙》、《祈祷》、《神秘莫测的》、《永恒的女性》等,是通过诗歌传达某种观念。正如她所说的,所有真正诗人的诗,都是祈祷。诗在更高层次上隐喻着人与上帝的联系,所有的诗歌都不过是祈祷在我们灵魂深处迸涌出来的形式而已,我们赋予诗歌的文字、韵律、节奏都不过是人在向上帝祈祷时各种各样的变体,是美丽的祷辞。她的诗歌,体现出这位女诗人对存在所抱有的“诗意的永恒渴望”,以及在苦难中的挣扎,在绝望中的高傲。
所以,别尔嘉耶夫指出,吉皮乌斯的颓废主义本身,与那些唯美的颓废主义者少有共同之处。他说:“吉皮乌斯的颓废主义本身,与比如说巴尔蒙特的颓废主义是相对立的两极。对于吉皮乌斯来说,生活是极端艰难的,而非极端轻松的。她完全不是唯美主义者,她无法本能地、靠无法捉摸的印象、美丽的斑点、别出心裁的线条生活。……美之宗教之路似乎对她是关闭的,也满足不了她,她总是与我们的《艺术世界》培育出来的那些唯美的颓废主义者少有共同之处。比起这些肤浅的唯美的颓废主义,她所体验的颓废主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主人公有更多共同之处。这种颓废主义体验内在地必然走向宗教道路,也只有宗教可以克服。作为诗人和颓废者的季·吉皮乌斯很少有直接的幸福,生活对她来说是艰难的,她没有在艺术本身中找到意义,通向世界的道路是关闭的,于是她在新宗教意识中寻找幸福。”[1]别尔嘉耶夫在《论〈文学的衰落〉》中曾指出:“颓废主义与宗教……内在地深刻对立,相互排斥,并且在最大限度上只能是敌人。”[7]因此,他认为,吉皮乌斯紧张的精神探索正是宗教的探索,是宗教中的“自我的拯救”,而非颓废主义。他将吉皮乌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主人公”相比,认为他们“有更多共同之处”,我想这里指的是斯塔夫罗金和伊凡之类的人物。他们紧张的精神探索“必然走向宗教道路,也只有宗教可以克服”。这样,就将吉皮乌斯的“颓废”与“像是装满各种感受的袋子”的颓废者区别了开来。别尔嘉耶夫认为吉皮乌斯的努力,不仅是对自己的超越,也是对整个颓废主义的超越。他说,现在《文学日记》的作者安东·克莱尼,是“在克服过去的那个季·吉皮乌斯的颓废主义,也是在克服各种颓废主义。安东·克莱尼的整个《文学日记》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克服”。别尔嘉耶夫认为,安东·克莱尼那些似乎显得过于隐秘和小团体性的许多思想,具有普遍和广泛的意义,“是专门用来克服颓废主义的”;“文集本身已经渗透了正面的宗教世界观,作者将这种世界观独特地运用于所有的生活和文学现象”。“安东·克莱尼给我们的颓废派的无思想性、肤浅的唯美主义以沉重打击。这些打击比我们的文学保守派要有力得多。安东·克莱尼了解颓废派的秘密,了解它的弱点,又不否认它的长处和功绩”。别尔嘉耶夫认为,颓废派的功绩在于,使得“艺术的自由,对艺术价值的尊重”,“在我们的意识中获胜”。
那么,吉皮乌斯在克服颓废主义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换句话说,她在哪个层面上超越了颓废主义?别尔嘉耶夫认为,吉皮乌斯“在克服颓废主义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人和人的限度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复杂而难解的形而上学问题”。吉皮乌斯不是哲学家,没有哲学方面的素养,也许很少了解哲学关于人的问题的解决。其表述带有明显的小品文特点。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她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别尔嘉耶夫说:“这位作家天生的聪颖和强烈的人格感帮助她弄清复杂的哲学问题,告诉了她经得起严格哲学验证的答案。她敏锐地领悟到,人将毁于极端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主义,颓废主义就是毁灭,而不是个人的胜利。”[1]吉皮乌斯将自己的“我”与“非我”联系起来,也意识到并承认他人的“我”,这是安东·克莱尼深刻理解和感觉到的确凿真理,而颓废派们却没有理解、也没有感觉到的心理学和认识论的真理。颓废派们没有意识到“我”与“非我”的区别,不承认他人的“我”。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混淆和纠缠在一起,“我”膨胀到吞噬一切的地步,因而“我”迷失、消散,“我”的意识也不复存在。别尔嘉耶夫认为:“颓废主义者心理上没有任何中心,一切准则皆被否定,因而个性消散;个人死亡,瓦解于破碎的、短暂的感受和瞬间。在这个意义上颓废主义是反个性主义的,在自己身上体现出个性的消失和对其的徒劳寻找。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病态的‘唯我主义’,无异于个性的死亡和瓦解。”[1]别尔嘉耶夫的这些分析是他一贯的关于个性的思想,他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解读吉皮乌斯超越颓废主义的价值。
别尔嘉耶夫在《克服颓废主义》一文的论述中,着重评价了吉皮乌斯的几篇文章,其中之一是《情爱》一文。我们认为,别尔嘉耶夫特别提及该文是因为,关于基督教中的性问题,关于基督教应该怎样对待性问题,其实是那场“新基督教”运动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此前不仅有弗·索洛维约夫关于爱的学说,也有罗赞诺夫提出的“肉体”问题,别尔嘉耶夫本人也十分关注此问题,他认为,性其实不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个性是否完整的问题。别尔嘉耶夫在吉皮乌斯的《情爱》一文中读出了她关于爱的思想,认为“关于崇高的爱情的理想”是她“最珍爱的理想”,“这是一种非常接近弗·索洛维约夫的关于爱的学说”,而且,这一接近,不是机械的接受,而是“经过自身深思熟虑、赋予自己的经验之后”的接近。别尔嘉耶夫认为,吉皮乌斯“最敌视罗赞诺夫及罗赞诺夫思想,家族血缘式的爱,无个性的性本能”。其实,别尔嘉耶夫本人也对罗赞诺夫关于性爱的某些思想予以了批评。他说:“吉皮乌斯最独特最有力之处在于,对旧式爱情的批判,敏锐意识到由于这一无个性的生理和心理之爱带来的个性的死亡,敏锐意识到只有与基督相联的个人的爱才能拯救个性。”[1]这也是别尔嘉耶夫坚持的观点。他还发现,吉皮乌斯“也十分珍视关于性的改造的思想”。不过这一“会被当代理性认为是疯狂之想”的思想并没有被吉皮乌斯很好地表达,别尔嘉耶夫认为,她“预感到的,要比她哲学地表达的要多”。
“如果关于新型爱情的理想是她的灵魂,那么关于日常生活和事件的思想就仿佛是她的肉体”。因此,别尔嘉耶夫就吉皮乌斯的另一篇文章《日常生活与事件》也作出了评价。他发现,吉皮乌斯不喜欢日常生活,与所有日常生活脱节。日常生活对于她来说是静止,是运动的停滞。日常生活与事件、与运动、与动态相对立。真正的生活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而是在事件中。把生活与日常生活相混淆——是可怕的混淆。别尔嘉耶夫指出,吉皮乌斯渴望新的生活,旧生活及其琐碎是不能承受的无聊,只有事件才能带来新生活;她欢欣的是飞奔向前的列车,它的疾驰使人看到新生活,新天地。其实,当时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并非吉皮乌斯一人,许多人都在谈论日常生活的死亡。这其实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即日常生活的鄙俗,是精神生活的死亡。别尔嘉耶夫指出:“在她身上最为宝贵的东西是同鄙俗、同平庸、同生活的庸常化、同生活的灰色单调的不懈斗争。”[1]在吉皮乌斯这个看似极其“颓废”的诗人身上,有着正面、光明的东西。“她身上有着向前的渴望,飞翔的渴望,有着对生活意义的信仰,对生活节日(“日常生活”与“生活节日”,这里都是隐喻。——笔者)的期待”。
吉皮乌斯的《日常生活与事件》主要是以契诃夫为写作对象的,她认为契诃夫无法摆脱日常生活。她写道:“契诃夫深陷日常生活中——可又恨它,被它折磨。恨它——可又爱它,了解他。这就像有时我们恨自己的手——可它毕竟是自己的,它比其他人的手离你更近,你无法割舍它。为了拯救心脏,要割舍它,是需要罕见的勇气的。契诃夫没有这个勇气,他就这样苦恼着这一充满爱的恨,直到死。”[2]290别尔嘉耶夫说:“如果说安东·克莱尼对待契诃夫有失公正,那么对充满了晦暗的忧伤、预示着虚无的绝望的契诃夫式的东西的严厉审判是公正的、正确的、有价值的。安东·克莱尼无法忍受庸常,无法忍受绝望,不愿多愁善感,她永远希望并给人以希望。她无法忍受与无意义的生活妥协,这一不妥协性就已经具有巨大的意义。”[1]
在别尔嘉耶夫对吉皮乌斯的整个态度中,也许最不能让别尔嘉耶夫接受的就是吉皮乌斯的“小圈子”倾向。别尔嘉耶夫多处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吉皮乌斯“具有明确清晰的思维,朴素通俗的语言。但是这种看似明确和朴素,却有某种视觉上的欺骗性”。她“通俗的语言只有极少数人懂,只有被拣选的人懂”。她在写作上“仍然是一个小圈子式的作家。她希望走出私人封闭的圈子,希望走向所有人,但是在这一点上她并不总是成功”。她“在克服颓废主义,在与颓废主义作斗争,但只是在私人的、封闭的圈子里进行的。她与颓废主义的激烈斗争只有接触这个圈子的人才理解”。她“过于坚信自己道路的正确性,对于同样走向罗马的其他道路没有足够的认同。《新路》是我们的宗教-哲学探索的一环,自然是鲜明的有价值的一环。但是要知道《新路》不是探索唯一的发祥地,不是唯一的道路,不是唯一的‘新’路。这一新路应当走向共同的轨道,那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实现。而她只愿意走向‘新道路’的源头。这是小圈子的视野。如果希望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希望与具有其他源头的思想交流,就必须摆脱这种视野”[1]。在吉皮乌斯关于新生代文学批评中的小圈子倾向,别尔嘉耶夫也指出,“在文集的其他文章中可以感到对文学新生代的抱怨。安东·克莱尼关于文学新生代的说法是公正的,很好地理解了他们的病症所在。但也许少些对自己一代、对自己的圈子的辩护,会更令人愉快”[1]。而在评论吉皮乌斯的文章《世界缺席》时,别尔嘉耶夫又指出,“这篇评述《宗教问题》文集的文章,过于激烈地命名为《世界缺席》,直接触及了旧基督教与新基督教问题,文章写得十分犀利,对其中几位作者的评论十分中肯而尖刻,主要的驳斥似乎也是正确的。但是,文中有某种不明确的东西,首先是安东·克莱尼对待基督教,对待基督教中的永恒问题的态度不明确;尤其不明朗的是,她如何克服她在文集中看到的那种聚合性的不足,她是否知道通向宗教的社会性的正确无误的道路。总之,安东·克莱尼的不足是过于自我肯定,过于膨胀地相信自己及其密友们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对别人的正面价值评价不足”[1]。甚至在别尔嘉耶夫关于吉皮乌斯的《文学日记》的评论文章已经完稿,读到了吉皮乌斯的另一篇文章《白箭》时,又发现了吉皮乌斯的“小圈子”倾向,这几乎让别尔嘉耶夫否定了吉皮乌斯对颓废主义的超越,他说:“我很悲哀地感到,安东·克莱尼还没有克服颓废主义,在自身还没有战胜颓废主义的自恋和颓废主义对世界的蔑视,还没有从颓废主义的小圈子走向广阔的世界生活。”[1]
但是,别尔嘉耶夫还是指出:“原则上讲,安东·克莱尼在自己同颓废派的论战中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对当代艺术感到失望,在其根子里看到了原来的那种实证主义。在新艺术中有的只是激情,它被神秘主义的希望所吸引,而一切都以漂亮的废话告终。现在艺术发生着深刻的危机。没有任何重大的、重要的、永恒的东西。‘新’艺术很快就老化了,文学中又等待着新词儿的出现,而新词儿是不可能成为抽象的自足的艺术的……在任何时候在所有方面安东·克莱尼赞成自觉性,反对自发性。她与当下的无意识性和无理性倾向作斗争……与已经成为混乱时代的时髦的无思想的自发性的斗争,无疑是巨大的功绩。……我希望重新公正地对待安东·克莱尼-季·吉皮乌斯,承认这位引人注目的作家和人物,我们宗教探索的重要参与者的功绩。不过同样希望她走出令人窒息的小圈子,更多地重视不是经由‘新路’得到的世界的价值。”[1]
注释:
①这些文章指:季心屏.死鹰之歌:姬娜伊达·吉皮乌斯诗试析[J].名作欣赏,1988(3).
汪剑钊.“诗歌是一种祈祷”:俄国女诗人吉皮乌斯简论[J].国外文学,1997(4).
黎皓智.仇恨心理与故土情怀的奇妙结合:浅论吉皮乌斯离开俄罗斯以后的诗歌创作[J].俄罗斯文艺,2005(1).
范文艳.雪的火:浅析吉皮乌斯创作的矛盾性[J].山花,2011(12).
②孙文波.我眼中的吉皮乌斯,张柠.慌乱的回声[EB/OL].豆瓣读书.
③吉皮乌斯.吉皮乌斯诗选[J].卢永福,译.国外文学,1988(4).
吉皮乌斯抒情诗五首[J].飞白,译.名作欣赏,1988(3).
季·吉皮乌斯抒情诗四首[J].汪剑钊,译.俄罗斯文艺,1994(2).
吉皮乌斯侨居国外时期诗选[J].黎皓智,等译.俄罗斯文艺,2005(2).
④跨世纪抒情[C].荀红军,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刘象愚,主编.20世纪外国诗歌经典[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⑤阿格诺索夫.白银时代俄国文学[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王敏.与101位女作家的私人约会[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张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李辉凡.俄国“白银时代”文学概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⑥梅烈日科夫斯基传[M].施用勤,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吉皮乌斯.往事如昨:吉皮乌斯回忆录[M].郑体武,岳永红,译.学林出版社,1998.(又译: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M].郑体武,岳永红,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⑦吉皮乌斯.吉皮乌斯诗选[M].汪剑钊,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别尔嘉耶夫.克服颓废主义:论季娜伊达·吉皮乌斯[N].莫斯科周报,1909 -05 -16.见:http://krotov.info/library/02_b/berdyaev/1910_4_156.
[2]安东·克莱尼.文学日记[M].圣彼得堡:М.В.彼罗什科夫出版,1908.
[3]Гиппиус,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дневник (1899 - 1907) [M].СПб,1908.
[4]Н.А.Бердяев.Самопознание[C]// Русская идея.Москва,2004.
[5]А.Бенуа.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M].Москва,1980.
[6]В.Аллой.Письма Николая Бердяева[M].Париж:Atheneum,1990.
[7] Н.А.Бердяев.Лumитер Amурном Pасnаòе[J].Московский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1908.№49.С.39 - 53.见:http://www.krotov.info/library/02_b/berdyaev/1910_4_1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