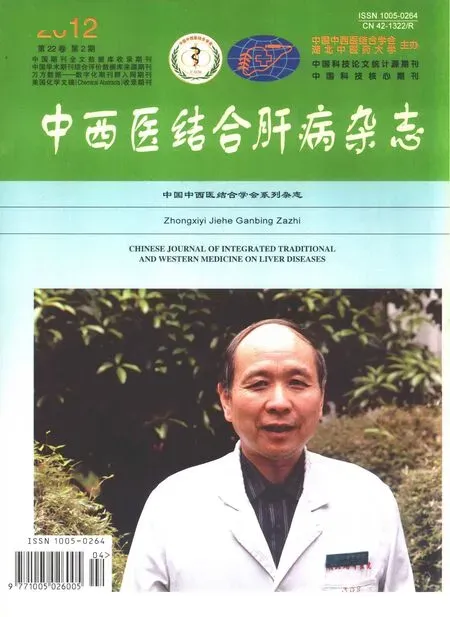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辨证分型与客观指标关系的研究现状*
刘 茹 孙建光 王伟芹
1.山东中医药大学2005级中医学七年制班 (山东济南,250011) 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病内科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CHB)是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持续感染引起的肝脏炎症坏死性疾病[1]。据2006年全国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表明,CHB现症患者约有2000万例,每年死于与乙型肝炎相关肝病者约30万例[2]。现代医学对CHB尚没有特异性治疗,目前,发挥中医中药特长,仍是公认在当前治疗中最有希望取得某些突破的方法。中医学临床的核心是辨证论治,而确定证型又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前提。但目前临床在证型划分上共有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较为混乱,这种过多的分型缺乏统一的量化和客观公认标准,给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和实施循证医学带来许多困难。因此探索CHB中医证型与客观检测指标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医现代化的要求,也成了中西医结合的热点。近年来广大中西医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笔者查阅了近十年的国内CHB免疫学的实验室检测和中医辨证关系的研究资料,分述如下。
1 中医辨证分型研究仍然缺乏统一的、权威的标准
查阅近十年公开发表的涉及CHB证型的论文及书籍,对CHB有辨证分型论治者,有辨病与辨证结合论治者,各有所长,说法不一,没有统一的规范。目前临床医家有以脏腑分型论治者,其主要证型很多且很不一致。王永炎[3,4]院士认为,证候属于多维多阶的复杂系统,应当通过降维升阶的方式,尽可能地找到能够包含对证候诊断具有特异性的症状指征的证候要素。毛德西等[5]通过对近10年来关于CHB的30篇临床资料的分析,发现在4028例中,证候分型竟有34种之多,可谓是证候复杂多变,类型兼夹不一,但其中以湿热、脾虚、肝郁、血瘀、阴虚等5种证候最为多见。于春光等[6]通过对文献规范研究认为CHB最常见证候依次为肝郁脾虚、肝肾阴虚、湿热 (蕴结)、脾肾阳虚、瘀血阻络、肝胆湿热、气滞血瘀、肝气郁结、肝郁血瘀、血瘀证、脾肾两虚。证候要素有:病位方面为肝、胆、脾、肾、胃、中焦、络;病性方面为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湿、热、气郁、血瘀、毒、寒、水、痰。苏安[7]认为乙型肝炎病机重点在湿、毒、郁、虚、瘀,以湿毒蕴遏为基本,分为湿毒蕴遏;湿毒瘀滞,肝郁脾虚;血瘀湿毒,气血亏虚;湿毒偏盛,气虚肝郁;肝肾阴虚;湿毒稽留,脾肾阳虚六型。赵晓威[8]认为CHB患者在病情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医辨证有所不同,在初感湿热疫毒之时,湿热中阻,而后肝气郁结,久而犯脾,致肝郁脾虚,气机郁滞,使瘀血阻络,脾虚运化失常,气血生化无源,到后期则精血亏耗,肝肾阴虚,阴虚则阳无以生,终致脾肾阳虚。
总之,近年来关于CHB的证型问题,众多医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于CHB的中医分型仍未形成共识,中医辨证标准仍存在异议,中医对CHB的辨证仍然停留在以医生主观经验为主的思维层面上,缺乏统一可参照的标准,因此将中医宏观辨证与微观检验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一种可行的思路。如何将中医的四诊与现代医学检测和分析手段结合起来进行辨证,这是发展中医辨证的重要内容。
2 中医辨证分型与客观指标关系的研究可为中医辨证客观化提供依据
2.1 CHB辨证分型与肝功能之间的关系 ALT(丙氨酸转氨酶)和AST(天门冬氨酸转氨酶)是主要反映肝细胞炎症损害的酶类,其升高的水平反映肝细胞膜及肝细胞线粒体损伤的程度,而ALT/AST比值有助于判断肝细胞病变程度和肝病鉴别诊断[9],TBil(总胆红素)、DBil(直接胆红素)异常主要见于肝细胞损伤时其对胆红素的摄取、结合及排泄功能降低。施卫兵[10]将183例CHB患者分为5种证型,研究分析发现湿热中阻和肝郁脾虚型患者的ALT、AST、TBA(总胆酸)、Alb(白蛋白)、A/G(白球蛋白比值)等结果明显高于其他3型,TBil、DBil值异常主要见于湿热中阻型,明显高于其他4型,麻晓慧、刘金霞等[11]对209例患者量化分析后发现CHB证候与肝功能的各项指标没有高度特异性的相关,但不同证候确实存在差别。也认为湿热中阻型与肝功能各项指标的相关性都比较高,瘀血阻络型除与凝血酶原时间 (PT)、血浆Alb和TBil,还与GGT(γ-谷氨酰转肽酶)、AST有相关性。而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则主要与TBil、PT和血浆Alb相关,说明此3个证候更多是反映全身总体状况。蒋开平等[12]研究表明慢性肝病肝郁脾虚型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湿热中阻型表现为ALT显著升高,血清Alb值正常,γ球蛋白值轻度降低;肝肾阴虚则见ALT亦明显升高,血清Alb降低,γ球蛋白升高,A/G值降低;瘀血阻络可见ALT轻度升高,血清白蛋白值明显降低,γ球蛋白值显著增高,A/G值明显降低。王振常等[13]进一步研究发现CHB患者血脂、血清载脂蛋白A(Apo-A)和载脂蛋白B(Apo-B)的水平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CHB重度患者Apo-A显著低于CHB轻度,血清Apo-A和Apo-B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肝肾阴虚型,其次是瘀血阻络型和脾肾阳虚型;Apo-A/Apo-B比值在CHB中、重度及肝肾阴虚型患者均明显异常。唐智敏等[14]研究了肝病血瘀证与血清球蛋白的关系,结果显示,血瘀证组患者血清球蛋白及γ球蛋白显著高于非血瘀证组。对病毒性肝炎患者进行血清学检测,显示临床表现湿热程度越重,血清ALT值就愈高,两者呈正相关[15]。综上所述,可认为CHB辨证分型和肝功能有明显的相关性,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湿热型患者的转氨酶、胆红素升高与其他证型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说明湿热型患者存在明显的肝细胞损害和胆红素代谢障碍,而血清蛋白的含量侧面说明了CHB病程中人体内正气的变化。肝功能指标可作为CHB辨证分型的客观指标之一。
2.2 CHB辨证分型与血清病毒学指标之间的关系 朱初良等[16]发现CHB患者肝胆湿热和肝郁脾虚患者病毒标志物有两种表型,即HBsAg(+)、HBeAg(+)、HBcAb(+)、HBV DNA(+)或 HBsAg(+)、HBeAb(+)、HBcAb(+)、HBV DNA(+),提示病毒复制高度活跃,而脾肾阳虚患者病毒标志物以HBsAg(+)、HBeAb(+)、HBcAb(+)为主,提示病毒处于低复制状态。谢磊[17]通过研究证明HBV DNA在CHB不同证型中病毒复制状态不同,高复制主要集中在肝胆湿热型,中复制主要集中在湿邪困脾型和肝郁脾虚型,低复制主要集中在脾肾阳虚型和肝郁血瘀型。陈培琼等[18]研究发现,当HBV DNA<104copies/ml时,湿热中阻型的频数明显高于其他证型 (P<0.05);而当104≤HBV DNA<107copies/ml时则相反。邢练军等[19]则认为:肝郁脾虚型患者以HBsAg(+)、HBeAb(+)为主,病毒处于低复制阶段,而肝胆湿热型患者则有两种表型,即 HBsAg(+),HBeAg(+),HBcAb(+),HBV DNA(+)或 HBsAg(+),HBeAb(+),HBcAb(+),HBV DNA(+),提示病毒复制高度活跃。蒋金仙[20]分析了142例CHB患者中医辨证分型与HBV复制程度、蛋白代谢功能、肝功能及免疫功能的关系,结果显示,湿热型患者HBeAg及HBV DNA阳性率高,HBV复制显著,但蛋白代谢正常;而肝肾阴虚型及气滞血瘀型HBeAg及HBV DNA阳性率较湿热型更为显著,且伴随严重的蛋白代谢障碍;肝郁脾虚型则为病毒复制最不显著者,因此认为,CHB辨证分型中,湿热型多为初期,肝郁脾虚型多为中期,肝肾阴虚及气滞血瘀型多为后期。文献报道,通过对205例CHB患者的统计分析,观察到实证患者HBeAg、脱氧核糖核酸多聚酶 (DNA-P)和HBV DNA的检出率明显高出虚证患者,并有显著性差异[21]。说明本病实证患者其HBV复制较虚证患者活跃。而施卫兵[10]的研究却认为肝胆湿热型HBV DNA值及HBeAg阳性率明显低于肝郁脾虚型。李晓良等[22]研究亦发现,HBeAg阳性和HBsAg,HBeAg、抗-HBc同时阳性的患者,虚证组显著多于实证组,说明虚证患者HBV复制活跃。且另有一些资料认为中医辨证分型与HBV抗原抗体系统的关系没有统计学意义[23,24]。总之,中医分型与病毒学指标的关系尚无统一认识,仍需进一步研究。
2.3 CHB辨证分型与免疫学指标之间的关系 “正邪进退”说是中医解释疾病发生发展的理论精髓。在CHB病程进展中,邪气以HBV为主,包括各种促进病情进展的不良因素(如不良情志刺激、不良生活方式等等),正气泛指包括免疫机能在内的抗病及修复能力。许多研究表明[25,26],中医各证型在CHB轻、中、重度中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它与疾病所处的不同阶段有关,随着病程进展而证型发生转化,这些证型转换与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密切相关。T淋巴细胞由不同亚群组成,是机体抗肿瘤、抗感染免疫反应中起主导作用的免疫活性细胞,是细胞免疫系统的主要组成成分[27]。国内外大量文献已证实[26,28,29],宿主特异性细胞免疫调控的紊乱是引起乙型肝炎慢性化的主要原因,CHB患者普遍存在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分布的差异 (CD4+、CD4+/CD8+细胞比值明显降低,CD8+显著升高)及 NK细胞活性的下降。因此,CHB患者T细胞亚群和NK细胞的活性可基本反映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杨宏志等[30]将76例CHB患者分为实证、虚实夹杂、虚证3组,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结果各组患者CD4+水平明显降低,CD4+/CD8+存在明显差异,CD4+/CD8+比值虚证组>虚实夹杂组>实证组,认为CHB患者存在着免疫调节紊乱,CD4+/CD8+可作为虚实变化的参考指标,CD8+可能是虚证的参考指标。李健芳等[31]将60例CHB患者分为3组检测T细胞亚群,3组患者CD4+、CD4+/CD8+均显著下降,CD8+升高,以正虚为主者最显著,邪实正虚并重者次之,邪实者更次之。王见义等[32]临床收集515例CHB病例进一步分析发现CD4+水平在湿热中阻型中最高,与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型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CD8+水平在脾肾阳虚型中最高,与湿热中阻、瘀血阻络型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血IgM、IgG水平在湿热中阻型中最高,与脾肾阳虚型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谢学军[33]研究却发现肝郁脾虚型和湿热中阻型患者外周NK细胞活跃较正常人低,说明CHB本虚的部分实质。罗国钧等[34]发现免疫球蛋白在CHB各型中都有所增高,但以湿热中阻和肝肾阴虚型为显著。总之,可以认为CHB患者的中医辨证分型与机体免疫功能之间存在相关性,相关免疫指标对辨证分型有参考价值。
2.4 CHB辨证分型与肝脏病理改变之间的关系 有关中医证型与肝脏组织病理改变的关系,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二者有很大的相关性。对CHB患者进行肝脏活检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评估肝组织炎性活动度和纤维化程度[35,36]。张如棉[37]认为中医证型与病理炎症分级 (G)、纤维化分期 (S)以及炎症、纤维化半定量计分均有明显相关性 (P<0.01),其中肝郁脾虚型炎症纤维化程度均最轻 (P<0.01),瘀血阻络型炎症纤维化程度均最重 (P<0.01)。李筠[38]总结CHB 279例病理诊断与中医证型的关系,发现CHB随着病理改变的加重,病变部位及主导证型渐由气分至血分,以血热血瘀为主证特点。肖和杰等[39]研究发现,肝郁脾虚型患者肝内Ⅳ型胶原含量最低,肝内纤维化程度轻,瘀血阻络型肝内Ⅳ型胶原含量最多,肝内纤维化程度最重,其余3型介于两者之间,认为CHB以肝郁脾虚为主,随着肝损害加重,瘀血阻络型逐渐增加。张国良等[40]研究发现肝组织炎症上,肝郁脾虚型主要为G1、G2,湿热中阻型主要为G2,肝肾阴虚型和脾肾阳虚型主要为G3,瘀血阻络型主要为G4;肝组织纤维化分期上,肝郁脾虚型和湿热中阻型主要为S1和S2,肝肾阴虚型、脾肾阳虚型主要为S3,瘀血阻络型主要为S3和S4;肝组织病理程度上,瘀血证以G3~G4、S3~S4为主,非瘀血证以G1~G2、S1~S2为主。认为,CHB的肝组织病理改变与中医证型有一定相关性,其中瘀血证型与肝组织病理关系最为密切。随着肝组织病理损害的加重,中医证型由实至虚,由气及血,瘀血阻络是其最终的病理转归。
2.5 CHB辨证分型与其他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 谢磊[17]通过研究发现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在CHB不同证型以肝郁血瘀型延长最明显,肝郁血瘀型、脾肾阳虚型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肝胆湿热型、湿邪困脾型、肝郁脾虚型与肝郁血瘀型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纤维蛋白原(FIB)在CHB不同证型之间以脾肾阳虚型下降最明显,脾肾阳虚型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肝胆湿热型、湿邪困脾型、肝郁脾虚型与脾肾阳虚型相比有统计学意义。血浆凝血酶时间 (TT)在CHB不同证型之间以脾肾阳虚型延长最明显,脾肾阳虚型、肝郁血瘀型与正常组相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王振常等[13]通过对381例患者的研究发现,AST、ALT、GGT、NO(一氧化氮)、MDA(丙二醛)在湿热中阻、瘀血阻络、肝肾阴虚型中较其他证型显著升高,Glo(球蛋白)、LPO(过氧化脂)、Apo-A/Apo-B在瘀血阻络、肝肾阴虚型中高于其他证型,而Alb、A/G比值较低,TBA、CHE(胆碱脂酶)、Apo-A/Apo-B在瘀血阻络、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型中明显低。因此认为生化及氧化损伤指标可为CHB中医辨证的客观化提供依据。汪静等[41]发现CHB中医各证型NO水平以湿热中阻型最高、肝肾阴虚型次之,肝郁脾虚型再次之,各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湿热中阻型组及肝肾阴虚型组分别与肝郁脾虚型组比较,差异亦具有显著性意义,但湿热中阻型组与肝肾阴虚型组NO水平比较,差异并无显著性意义。
3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国内众多学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CHB进行了证型分布与多项客观指标关系的研究,以便寻找出中医各证型的特异性辨证指标,来实现CHB中医辨证分型的客观化。综观文献研究,可以发现,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应该吸收现代检验医学的成就,而现代检测技术的发展也使对CHB微观辨证成为可能。微观辨证与宏观辨证相结合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的有效途径,医生的视觉、嗅觉、触觉等能力是有限的,借助于现代科学检测方法可使这些能力得到延伸,从局部或微观去搜集症状,确定证候,即微观辨证。因此,探讨本病中医辨证分型与客观指标关系的研究规律,对进一步提高疗效以及促进临床诊断标准研究的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但与此同时,这些努力虽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迄今为止,对临床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证型的特异性指标也尚未发现。因此,将实验室客观指标纳入到中医证型中来,必须进行更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循证医学验证,积极应用数学、动物模型及现代高科技手段以期建立乙型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客观化的新的诊疗模式。此外还需要流行病学、中医基础理论、卫生统计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通力协作,有助于CHB中医辨证客观化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相信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进取精神,不断努力探索,CHB中医证型的客观指标一定会日益完善,在CHB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面找到辨病与辨证、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最佳结合点。
[1]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感染病学分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J].中华肝脏病杂志,2011,13(3):21-22.
[2]计众众,姚光弼.慢性乙型肝炎的流行病学、诊断和实验室检测[J].肝脏,2006,11(2):11-27.
[3]张志斌,王永炎.证候名称及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假设的提出[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6(2):1-4.
[4]郭蕾,王永炎.关于证候因素的讨论[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7):643-644.
[5]毛德西,朱光.乙型肝炎辨证用药思路 [J].中医杂志,2002,43(2):144-145.
[6]于春光,王天芳,万霞,等.慢性乙型肝炎常见中医证候及证候要素的分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6):1-4.
[7]苏安.以六方分型辨治慢性乙型肝炎探析 [J].中医药学刊,2002,29(11):661.
[8]赵晓威.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辨证分型与免疫功能的关系 [J].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1998,(8)3:3-5.
[9]叶维法主编.临床肝胆病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747-748.
[10]施卫兵.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与客观检测指标的相关性研究[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7,17(5):275-276.
[11]麻晓慧,刘金霞.慢乙肝证侯与肝功能的相关性探讨 [J].承德医学院学报,2005,22(3):229-230.
[12]蒋开平,吴寿善.慢性乙型肝炎辨证分型与肝功能变化及肝组织病理类型的关系[J].新中医,1995(4):44-46.
[13]王振常,毛德文,黄彬,等.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与生化及氧化损伤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J].辽宁中医杂志,2010,37(3):390-391.
[14]唐智敏,茹清静,张振鄂,等.肝血瘀阻与肝纤维化关系的临床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717(2):81.
[15]汪寿鹏.病毒性肝炎辨证分型与血清TBil、TTT、ALT指标关系的观察[J].江苏中医,1997 ,(1):12-13.
[16]朱初良,殷小兰,张志杰.病毒复制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医辨证分型关系探讨[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6):705-706.
[17]谢磊.慢性乙肝不同证型与凝血相关指标、HBV DNA相关性研究[J].2006,(1):1-3.
[18]陈培琼,张金珍,田广俊,等.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分布及与HB DNA、肝纤四项关系的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9,11(16):15-17.
[19]邢练军,季光,王育群,等.乙肝辨证分型与病毒复制关系的初步研究[J]. 辽宁中医杂志,2001,28(12):710-711.
[20]蒋金仙.慢性乙型肝炎证型与生化指标关系的研究[J].苏州医学院学报,1997,17(1):91-92.
[21]杨兴中.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辨证分型与客观检测指标的探讨[J].山西中医,1991,7(2):9-11.
[22]李晓良,汪承柏,贺江平.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辨证与病理、病毒指标的关系[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6,6(2):4-5.
[23]吴婉芬.自拟慢肝宁中草药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临床观察[J].中西医结合杂志,1995,5(6):347-349.
[24]蒋传梅.200例慢性肝炎某些免疫指标与中医辨证分型关系的观察[J]. 中西医结合杂志,1992,2(3):213-215.
[25]常洁,张长法,邱蔚蔚,等.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辨证分型的量化分析研究[J]. 中华临床医药,2002,3(9):1-3.
[26]吴洁,江一平,李国贤.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辨证分型的临床发病特点探讨[J]. 福建中医药,2004,35(3):3-4.
[27]苏杭,吴晓蔓.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检测[J]. 现代实用医学,2004,16(5):288-289.
[28]FEI GZ,SYLVAN SP,YAO GB,et al.Quantitative monitoring ofserum hepatitis B vurus DNA and blood lymphocyte subsetsduring combined prednisolone and interferon alpha theraphy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J].J Viral Hepat,1999,6(3):219.
[29]朱培芳,周永列,王伯吕.HBeAb及HBcAg均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NK细胞数的研究[J].江西医学检验,2001,19(2):68-70.
[30]杨宏志,边壮,王拥泽,等.慢性乙型肝炎虚实病机与病毒复制及T细胞关系的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3,10(3):158-160.
[31]李健芳,吴轰.保元汤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免疫调节的作用[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1998(3):252-254.
[32]王见义,韩向晖,王灵台,等.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与免疫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9):35-36.
[33]谢学军.慢性肝炎中医证型NK细胞活性的研究[J].浙江中医杂志,1995,30(1):38.
[34]罗国钧,姚爱卿,程荣贵.乙型肝炎的中医辨证分型探讨[J].山西中医,1990,(1):13.
[35]KEEFFE EB,DIETERICH DT,HAN SH,et al.A treat-ment algorithm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B virus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2008 update[J].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8,6(12):1315-1341.
[36]LOK AS,MCMAHON BJ.Chronic hepatitis B:update2009[J].Hepatology,2009,50(3):661-662.
[37]张如棉.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与肝脏组织学及肝细胞核DNA含量、倍体分析的相关性研究[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08,(1):11-20.
[38]李筠.慢性病毒性肝炎279例病理诊断与中医证型的关系[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9,9(1):10-11.
[39]肖和杰,李平,张佳光,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医证型与肝脏病理改变肝内Ⅳ型胶原定量分析研究[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9,9(5):7-10.
[40]张国良,吴其恺,林巧,等.260例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与肝组织病理改变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7,27(7):613-614.
[41]汪静,谢朝良,杨华秀.血清NO水平与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的关系[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12):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