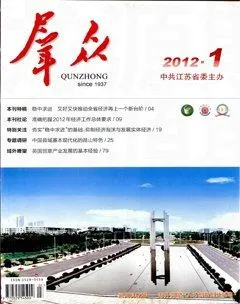社会良知何处安放?
编者:去年以来,社会道德领域的一些现象频频给人“冰火两重天”之感。合肥农妇好心载人出意外后四次主动赔偿被拒绝,南昌打工妹巩梦露危急时刻被十几名农民工营救,长春诚信经营十几载的“地瓜爷爷”遇到困难时爱心汇集,这些都使人感到暖流涌动。而与之相对,一些老人失足倒地后无人救助的场景,屡屡发生的救人反被诬事件,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等给公众善心造成的伤害,又让人颇觉寒意阵阵。其实,在“冰火两重天”的表象背后,是更令人纠结的“道德两难”问题。当道德面临现实风险,我们能否为道德埋单?如果见义勇为可能付出被诬陷的司法代价,老人倒下了扶还是不扶?如果救助伤者可能因救助不当被告上法庭,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当经济快速攀升,社会急剧变迁,各种出人意料的道德事件像集束炸弹轰击传统道德理念,我们又该如何坚守道德底线,重构道德世界?
良知缘何“沦落”?
林培:旁观是社会责任的旁落。
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我们脑海中不难浮现出一批“看客”的形象,说明当下是非分明的社会责任担当者有所减少。这给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经济发展,建立在传统血缘和乡土伦理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被削弱后,如何培养现代人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个人身份决定个人责任。每个公民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公民责任,用现代人的价值取向,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消除“看客心态”,提升自己积极向上的担当意识。位高者责重,作为社会管理者,尤其要在群体中率先垂范,为健康社会关系的塑造作出表率,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坚持正义,拒绝圆滑、推诿。责任是一种内在追求,正如康德所说:“每个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这种承担意识的培养,要从个人一言一行开始,如对本职工作的尽力、对公益事业的参与、对恶行的摒弃等。只有人人从我做起,“看客”才会越来越少,社会才会越来越光明。
周安平:陌生人社会酝酿信任危机。
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城市化大潮使越来越多人融入到陌生人社会中,原有的基于血缘的人际关系纽带断裂,人们彼此信任度降低,加之社会信息往往不透明,因而人的内心深处往往有一种恐惧和担心,对他人缺乏安全感。此外,在陌生人社会里,由于责任的分散和匿名性导致了责任主体的不清晰,阻碍了人们的交往与信任,导致社会的疏离倾向,滋长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社会心理。
佘澍:制度不公增加“善行”成本。
救人反被诬事件时有发生不得不说是“小悦悦”悲剧上演的诱因之一。挽救生命是人的天性,但另一方面趋利避害又是人的本能,是否救人本身就是人性两面的博弈。如果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却又随时存在吃官司、惹麻烦的风险,那么撒手而去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必过度去谴责那些见死不救的人,而要通过更为理性的制度设计,降低“良心”、“善行”在现今社会高昂的成本。
对“见死不救”立法可行么?
周安平:法律可以鼓励人们为善,但不可以强制人们为善。
导致见死不救的原因有自身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并且更多是社会因素。当社会本身就没有为良善者提供良善的环境,却要求人们承担良善的责任时,这就有失公允。法律可以鼓励人们为善,但不可以强制人们为善。从理论上讲,见死必救的义务对应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针对的是一般义务主体,只能是一项消极的权利,即免于剥夺生命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义务主体对于他人生命权利有尊重的义务,即做到“害人之心不可有”,也就是说,义务人只能负有不作为的义务,而不是积极的救助义务。从实践上讲,见死不救在司法实践上也很难认定,如果将见死不救入罪,可能导致更多人避开事件发生的场域,以免卷入事件当中而纠缠不清,效果适得其反。
佘澍:“法律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
通过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行为,我认为需要谨慎。法律与道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如哈特所说:法律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见到他人于危难之中出手援助,已脱离了最低限的道德要求。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立法,甚至入刑,是一种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相混淆的做法。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合乎理性的制度构建,一些经验值得借鉴。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的核心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兜底。它只为好人免责,但并不强制所有人提供援助。法律不强制人做出高尚的道德行径,但应对做出高尚行径的人进行保护。
林培:与其立法强制人们行善,不如用法律消除善举者的后顾之忧。
若一定要用“重典”,设立“见死不救罪”,那么,首先就遇到对“死”如何认定的问题。在突发事件的情境下,由谁在第一时间判定当事人“死没死”?其次,又如何认定“救没救”?到哪里去寻找人证和物证?等等。如果贸然将道德问题“泛法律化”,往往会陷入取证、审理、执行等一系列的困境之中,导致该罪的形同虚设,甚至引起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和“混战”。因此,当务之急是从制度、法律层面解决见义勇为者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焦虑,消除类似“彭宇案”的后遗症。与其立法强制人们去做义事,还不如用法律保障善举者的后顾之忧,使更多的人依从道德自觉、发自内心地去行善举,给道德留出调节内心的空间。
如何“扶”起社会良知?
林培:扶老人易,“扶”社会信任大厦倾斜难。
去年10月,首都经贸大学等3所高校联合发布的“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其中,就“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问题,有近35%的人选择“不确定”和“不扶”。这份调查应成为我们反思商业文化、功利教育,校正我们价值坐标的一把尺子。其实,扶起一位老人是容易的。但要扶正一座倾斜的社会信任大厦,还是一项经年累月的全民工程。拿农村来说,伴随城市化进程,农民走出乡村“熟人社会”,融入城市“陌生人的社会”,强调互利契约的交易原则取代互助信任的交往伦理。在此情形下,如何重建基于信任的社会伦理关系?我认为,必须充分考虑乡土时空的转换变迁,探索新形势下乡土伦理与现代道德理念有机结合的途径。如重视乡规民约在当代条件下的传承创新,强化农民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发挥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自我约束作用等等。
王小锡:让守德的人在不吃亏同时有被褒奖的机会。
我也看了“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它基本反映了当前社会的道德状况。调查中35%的人选择“不确定”和“不扶”跌倒老人,主要原因是怕惹祸上身,这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社会管理问题。要防止此类现象发生,政府要有所作为,通过更大力度的道德弘扬,让人们做好事无后顾之忧。要加强社会道德教育,让全社会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价值导向、清晰的道德观念,避免在道德价值取向上的无所适从的状况。要加强荣誉观和羞耻心教育,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让缺德者在社会上处处遭唾弃。要加强道德榜样的宣传,树道德标杆,培养助人为乐的“道德气候”。最后,还要有积极的保障举措,建立科学保障机制,让守德的人在不吃亏同时有被褒奖的机会。
佘澍:以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鼓励人们行“善”。
“小悦悦事件”中,为什么偏偏是一个拾荒者做出正义之举?这让我们反思在制度背后人所扮演的角色。儒家思想在近代发生巨大的断裂使中国人内心的道德感失去了凭依,社会的剧烈转型使人们生活在恐惧和不信任之中,尤其一些社会不公及腐败的事件效应使人们理应产生隐忍、恻隐之心时都变得异常冷漠、甚至产生扭曲心态。这些都不是纯粹地依靠制度就能解决的。道德感的缺失、对社会的不信任,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人的基本素质着眼,眼下亟待解决的是公民意识培育。中国人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公民,还缺乏一种在他人危急时刻理性施救的能力,在美国,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区教育,这种助人的意识和技能都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之一。这种技能就是一种公民意识,它的培养要比道德的批判、呐喊更为有力。如果说理性的制度设计、制度的正当运行是保护人为“善”,公民意识的培育更能鼓励人行“善”。
编者:从讨论中不难看出,“道德两难”现象的产生不仅是道德问题,也关乎法治、诚信、文明等诸多要素,其解决是一个长期过程、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令人欣慰的是,在发稿前,《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试图改善社会道德生态,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何维护社会良知,让“守德”不再难?思考在继续,行动在继续……
责任编辑: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