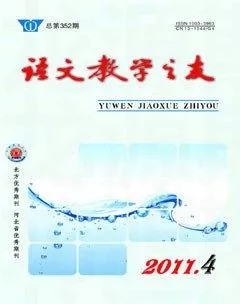“兔起鹘落”之我见
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有一句:“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高中语文课本对其中的“兔起鹘落”作的注释是:“兔的跃起,鹘鸟的降落。二者都是迅疾的动作,用以形容运笔的神速。”《教师教学用书》对这句话的译文是“所以说画竹,一定要心里有完整的竹子,拿着笔疑神而视,就能看到自己心想要画的竹子了,这时快速地跟着自己的所见去画,去捕捉看到的形象,就像兔子跃起、鹘鸟降落一样迅速。”很明显《教师教学用书》对“兔起鹘落”的翻译是受了课本“形容运笔的神速”注解影响的。
我认为课本注解所说的“二者都是迅疾的动作,用以形容运笔的神速”的说法是欠妥当的。
先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其不合理性。课本原文是一个先果后因的因果关系复句,我们可以把其理解为,作者强调“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而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是因为此时画者心中想要画的竹的形象“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兔起鹘落”所比喻的对象应是画者此时心中想要画的竹的形象,而不是如课本注解所说的“二者都是迅疾的动作,用以形容运笔的神速”。
mcBXvK4TmAts+ODnqIfHWg== 又,如果“兔起鹘落”是“用以形容运笔的神速”,那么紧接着的“少纵则逝矣”在思维逻辑上就根本连不上来,成了牛头马尾,无法自圆其说。
再从比喻运用的贴切性方面来看注解的不合理性。作者的创作灵感,或心中已酝酿好了的某一艺术形象,用一般性的文字来表达,给读者的印象有可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若明若暗,难以捉摸。苏轼用一“兔起鹘落”的比喻,可谓神来妙笔,顿生光辉,其形象之逼真,二者之贴切,可谓无可替代,不能不令人拍案称奇。
试想,如果用“兔起鹘落”来比喻画者运笔的动作,形容画时运笔的神速,不要说它不像、不准确,至少就其比喻运用的贴切性而言,与前者比较,其艺术效果就逊色多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课本对“兔起鹘落”的注解后半部分应为:“二者都是用来比喻迅疾出现又可能即刻失去的事物或现象,这里是指当时画者心中想要画的竹的形象。”
(作者单位:岳阳县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