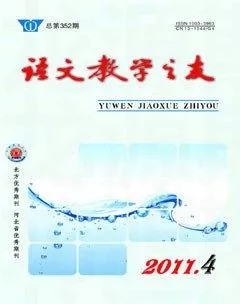意切词婉 情理俱深
在鲁迅整个杂文创作中,叙事性质的文章不仅在数量上占很大比重,而且在艺术上也同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方面尤以悼念性杂文最为显著。诸如《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此外类似的还有《忆太炎先生所想起的二三事》等,均属名篇。这类杂文,既有叙事文章擅长刻画人物的优点,又有抒情诗般的浓郁情感,还兼有议论的精警,将人生的真谛、革命的哲理蕴积在深邃的境界之中,可谓情文并茂。笔者从事语文教学已有多年,平常教学中,深为这类文章的“魅力”所折服,在此不妨就中学课本中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两文作一比较,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此类杂文的艺术特点以更好地了解鲁迅。这类杂文突出的艺术成就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情发于死,念在生者。
鲁迅这类文章跟我国古代优秀“祭文”一样,以死为引发点加以构思和展现,但又与传统的祭文不同,既不把文章做在人物死后,而是做在他生前,凝聚为对死者生前一言、一动、一个表情、一种印象的细微严谨的追忆和神形兼备的“生态”描写上。比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于柔石的描述,只是重点叙写了他生前的几个生活细节:(1)硬气;(2)迂。对于白莽,也只是淡淡地叙述了同他的三次平常的见面情形,虽然全是些平常、细微的琐事,但所蕴积的是作者对于生者生之崇敬、死之哀荣的深情,该是多么诚挚、感人!对于生者又是多么大的鞭策和鼓舞啊!所有这些,远非苍白的自我慰藉所能相比。
“一死之后,言行两亡。”鲁迅根本不相信有所谓“在天之灵”,所以,他决不代为死者设计“天堂”的美轮美奂,而是将自己的满腔思绪、情感、体验均用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事实的回忆上,艺术地再现了死者生前的“音容笑貌”。
二、如对活人,触笔于心底。
虽然文章里面的人物是早已离开了人间的“死人”,但作者仍视为“活人”,与他们娓娓而谈,神情自若。也就是说,他执意刻画的,不仅仅是死者生前的动作、言语,更是他们的心灵。
我们会留心柔石那对于世态冷酷、人心叵测的“惊疑”神态,便会明白其胸中跳动着的是怎样一颗善良、诚实的心;如果我们再细想想“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刘和珍等“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那种“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便会发现,任何“压抑”都不会“消亡”中国革命女性的“心”。以上所举,都向读者表明:“作者用如椽之笔,轻轻地伸向了人物的心底,以最俭省、最凝练的行动描写,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物的心灵深度、结构和层次,把人物的行动和心理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人物‘立体般’站了起来。”
三、于死者寄生者之情,求生者之路。
鲁迅的这类文章,都是真人真事的回忆,一般说来,是很难艺术虚构的,搞不好,便是一般的新闻“翻版”。高明之处便是鲁迅先生经过思想情感的反复咀嚼,不仅写出了曾经有过的事实,而且涌现出了可能有的“真情真感”,实在是一种艺术的创造。
比如《记念刘和珍君》就俨然像一首抒情的散文诗,对于死者事迹的简单叙述,完全成了抒情的有机内容。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
鲁迅想到柔石等五烈士是: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面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抢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这既是叙事,更是抒情。由于条件所限,鲁迅对烈士的生平事迹知道的并不详细,但他能凭借简略的事实,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突破时空的限制,用自己的心血和怒火的诗情,铸造出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青年形象,给读者捧出了一颗鲜红而真诚的心。
作者立足现实,驻望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仅于死者寄生者之情,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中探求生者之路。这中间既有对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更有对革命道路和民族前途的精心探求。
对于“三·一八”惨案牺牲的刘和珍等青年学生勇敢、果断,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但对他们的徒手请愿,作者含蓄地表示反对:“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里自然是总结教训的。
总之,这类悼念性文章不像传统的祭文那样,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牧的《祭妹文》往往重点在寄情于死者的在天之灵,将其精灵幻化为种种幻虚不实的想象,以慰作者的哀思、念情,这类传统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死者缺乏具体而深刻的了解和感知,所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往往是浓哀有余、浮幻不深。
鲁迅先生曾慨叹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种没人懂得的“伟大”,那么鲁迅自己这类悼念的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就往往被忽视。其艺术的成就就是:把对死者的往事的追忆、怀念的炽热、冷峻的情感,升华为一种政治的道德的巨大力量,把充满激情想象的构思同严谨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示人以道路前途,给人以信念、力量。
以上所述,仅是笔者对鲁迅先生的悼念性杂文的一种浅陋的看法。在新时期,有人认为对鲁迅的文章要“客观”地评价。笔者认为:杂文,尤其是鲁迅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与鲁迅不同,但是鲁迅的“民族魂”是不朽的、永存的。深入探讨鲁迅杂文的艺术成就,对于我们弘扬民族传统、振兴中华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肥西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