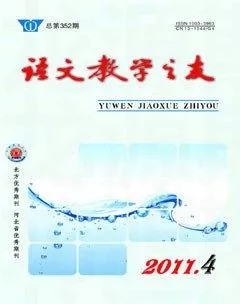浅谈阅读教学的目标意识与核心价值体现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和灵魂,在教学活动中有定向的作用。它限定着课堂教学的运作,对保证课堂教学有效开展至关重要。现代教学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有效的教学必先具备有效的教学目标。目前,阅读教学有一种走向:对话多、问题多、资料多、课件多,课堂非常热闹,教师和学生十分忙碌,教学效果并不突出。追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课堂教学目标意识淡薄,核心价值定位不准。
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基本特点的描述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同时指出语文课“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阅读教学显然是语文教学中占用课时最多、投入精力最多的重头戏。中学整个学段教材设计了许多阅读篇目,而阅读教学就要通过这些文章的学习,达到课程标准要求的目标。所以如何设计阅读教学,如何解读教材,每一课确定怎样的教学目标,就是阅读教学的核心与灵魂。但从阅读教学改革的现状看,存在如下严重问题。
一、目标不准,核心价值偏离。
新课程改革理念,受到西方接受美学的影响,认为阅读理解过程不是读者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读者再创造的过程。任何文本都具有未确定性,都不是决定性或封闭性的存在,同一文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主张在阅读教学中,尊重学生在情感、思想、知识、经历等方面的个性差异,对文本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鼓励学生敢于标新立异,言别人所未言,发别人所未发。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思考问题,获得多维理解。但是,面对阅读材料,联系写作背景、作者意图,面对教育对核心价值的选择,只一味强调标新立异,甚至以“非主流”取悦于学生,最终怎么能达到人文教育目标呢?
例如有位教师在教学《故乡》一文时,鼓励学生就其主旨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引导学生理解这篇小说的主题。有一个学生说:“《故乡》这篇小说,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表现了‘我’对眼前故乡的失望和对过去故乡的依恋。”这个解读的结果确有新意,但这个主题的归纳是很浅层也是很难立足的,它只是扣住了小说文本的字面意思。教师居然对这种归纳给予了高度赞赏,而后的“权威”评点中,也居然把它当作了整堂课的“闪光点”之一,认为这是尊重学生主体性和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其实,如果我们以一种整体的观点,切中鲁迅小说的主脉,结合鲁迅先生创作心态,我们似乎可以对《故乡》主题如此阐述:“通过对‘我’和闰土关系变化的叙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表达了对平等、亲密人际关系的期待。”当然,只要以鲁迅先生“改造国民精神”为基点,作出其他解读也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以上述学生的回答为文章定调,则恐怕已偏离了创作者的意愿,也远离了教材编写者良苦的教育用心。这不是创新,只能说是肤浅。课堂的教学价值早已游离于教学目标之外了。
二、目标过小,核心价值缺失。
阅读教学,在处理文本时,不能因为学生的视野所限,借口为了“满足学生心智的需要”,就无原则地降低作品品位或改变其价值取向。对教师来说,使作品贴近学生,走向学生的首要前提是熟知作品的文本价值,包括原生价值和教学价值,只有对这两种价值有明确的判断才谈得上进行教学设计。否则,就会导致教学目标过小、核心价值缺失。
例如有位教师执教《社戏》,整节课采用师生对话的方式,把双喜、阿发、六一公公的对话作了微言大义的阐释,并变换语气朗读人物语言。对此,授课教师在课后说课时解释:突出用语言描写来刻画人物。显然,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应合学生将作品原生价值调整,生成了教学价值,但这种调整应该建立在对鲁迅作品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从作品中寻找教学点,有违作品主旨,不顾作品的基本价值取向。虽然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较好,课堂气氛热烈,但依然无法掩盖教学价值取向错误而造成的课堂教学核心价值缺失。用对话的方式朗读人物语言,只是教学的一个点,而不是全部,选择《社戏》为教材,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训练对话语言。
三、目标不明,核心价值模糊。
由于社会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的呼声日益强烈,因而在教学中有些教师在“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爱山乐水,各掠其美”的借口和创新教育的压力下,不敢确定作品内容适当的限阈,而是当作无限开放的空间,确立教学目标不明确,总是处于两可状态,这不利于学生核心价值的形成。
例如有位教师在执教冰心的《谈生命》时,设计了一棵树和一条河的多媒体图片,试图帮助学生理解“生命是什么”。课堂上学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终不能形成概念。课后说课时施教者说,要在多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