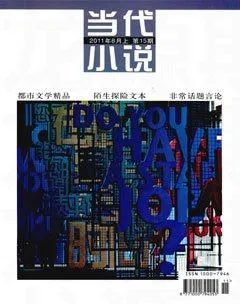红粉
她曾经跟我来过乡下老家的,我老家的父老乡亲也都见过这位叫媚媚的有些疯疯癫癫的女孩子。她大咧咧的,都觉得她很亲近人,乡亲们也没有多少反感。反正她也没有端着歧视乡下人的那种架子,让人感到别扭。她乐呵呵的,见谁都打招呼,轻易就得到了大家认可。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就不再担心老家那帮人能不能接受她。
她受欢迎程度是我没有想到的,有很多半大毛孩子还和她有了交情,我有个本家孙子还给她起了个雅号,叫红粉佳人来着。我那孙子喜欢看闲书,二三流的作品读了不少,所以也以乡间才人自居的,我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脸卖弄的神情看着我,我每次回来还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我征求意见,等我下个认可的结论。我就连连说,很好啊,不错啊,之类。他一边带着候旨一般的虔诚看着我,还时不时用余光搜寻着桌面上,并经常在我桌上顺手拿走了半包高档烟,带着一脸满足,大获全胜地跑走了。
我和媚媚所有的行为都是属于婚前同居范畴的事情,在一起玩了得有两年多,大家也都着实羡慕我拥有这么一美女女友。很多和我经历差不多的同事也嫉妒得要死。我们都是来自乡下的,凭那纸大学文凭混在城市,又进入上层建筑,在机关工作的。娶个城市姑娘是我们打小就有的梦想。我一切都那么如愿,不仅有了城市女友,还是那么光彩照人,让所有人都能看了眼前一亮。媚媚的气质形象不是学来的,是天生就具有的,是来自于骨子里,怎么能学得来呢?
和媚媚的经历让我初次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她也让我开始从一个青头青脑的大学生,一夜之间把我彻底改造成了男人。难得啊,有这么好的女孩陪着,真是上天的眷顾与垂青。在刚刚经历了上班的新鲜之后,也难免觉得机关生活的枯燥和无聊,在初看上去还有些热闹的形式,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新奇了。和一大帮俗气透顶的男男女女整天厮混在一起,说着永远也说不尽的无聊话题,真的感到了时间的漫长。难捺的时光,难捺的环境,没有半句真话的语言。如果没有媚媚的存在,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该如何面对,我的生活又该是一种什么样子,还有精神。
可是,我的领导经常教育我不要和媚媚这样的女孩在一起,而且态度严厉,几乎是命令般的不容商量。怎么呢?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呢?她究竟什么不好呢?她是我最需要的女孩子啊,再说我和她也都有了那种事,除了再领一纸证书,就是合法夫妻了。我实在找不出和她分开的理由,就痛苦得不得了,我的确也找不出她究竟有什么缺点,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的所谓前程也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我也不敢贸然得罪。就一边应着,一边把和媚媚的来往转入地下。不让她给我打电话,更不允许她来单位找我。媚媚是谁啊?她接受得了这种近乎侮辱连带委屈的事情吗。大声斥责我,说我没有男人的一点骨气,处长有什么权力干涉别人的私生活。这都什么年代了,看你还唯唯诺诺的,哪有点大丈夫的样啊。我不是看你还有些才华,就你这委琐样,我不会理你的,你就这点胆,难说有什么出息。骂完我不几天,就再也没来找我,连手机号也改了,连个道歉和解释的机会也不给我。
我就这样和她失去了联系,茫茫人海中不知她的下落。后来我就和处长的表妹谈起了恋爱,再后来,我就成了处长的表妹夫。和这个摆小摊出身的女孩就成了夫妻,然后就进入了那种一针一线也要计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感到了时间的漫长和夜的无聊。我的蜜月几乎是在高度恐惧中度过的,我不知道这种日子的尽头在哪里?我不知道和这个叫风铃的女孩磨合多久才可以正常起来?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还要耐多久?一切都是未知,我在内心几乎发疯般的想媚媚,我懦弱得可怜又可悲。
不是媚媚骂我,我有时自己也感到我窝囊不像个男人。不他妈的就是个处长吗?就这鸡巴毛般的小领导,霸道得就像土匪,我不止一次地问候了他妈妈,和连他也没有见面的先人。一句话,让我生活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旧机制的政治力量是那样强大,一己之权就可以给下属一个不近人意的人生,你无法改变,更无法拒绝。你只有努力超过他,不然,你就永远摆脱不了任人摆布的命运,所以,从那时我才真正的清醒了,这件事大于我受了二十几年的教育,比读一万卷书还管用。让我知道了奋斗,让我萌动了野心,让我顿悟了在这个场合里将来应该干什么。一失必有一得啊,我默默念叨,感谢上天用现实给我的启迪,对媚媚的歉疚和思念就渐渐地淡化了,我就要成熟了,在不可自拔的歉疚中一下就走出来,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我丈人的家世比我好不了多少,祖上是换洋火卖烟卷的出身。就是我们经常看的电影里面,胸前挂个方方格格的小木箱,里面摆满老刀,哈德门之类的牌子,然后就不住气地拉开嗓门使足力气满大街吆喝。在电影里这种人多半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之类。我也不用考证,我媳妇的爷爷肯定没做过,他们家是不具备这头脑的,也没那么开明,他们和卖糖葫芦的,蹬三轮的,澡堂里搓背的是一个阶层。但说实话,他们家人还算不坏,就是靠这些小本生意来维持生存,人都很现实,对蝇头小利看得格外重。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在商言商啊。
风铃没多大文化,在一家不太景气的棉纺厂上班,是我们本市的国有企业,企业的很多东西都要来我们处里审批。她表哥做科员的时候,她是挡车工,她表哥当了处长,她自然也就进了科室发发报纸,分分信件什么的,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活,落得轻松自在。水平没看到见长,舌头却越来越长,像个业余的新闻发布员,满脑子尽社会闲杂,鸡零狗碎的。听她说话,第一,练习耐心,第二,节约粮食,看到她眉飞色舞的嘴角泛着一层白白的泡沫,挂在嘴角就一点点外溢的样子,可没有啤酒沫那么生动,差不多像夏天堆放的垃圾,经阳光照晒的烂水果所产生的那层白白的,刺眼的,一堆苍蝇围着飞翔的沫沫,你食性再好,估计,你也会吃不下饭的。
我的功力见长很快,对她的絮叨所采取的策略是不附和,也不禁止,她也真摸不清我到底是什么态度。在单位同样如此,很难一下看清楚我对某人某事的明确态度,处长那里自然没什么问题,连委里的分管主任也开始重用我,当然,我明白这和处长的美言有很大关系,处长和主任是老乡,还是邻村,关系非同一般,属于一个最强的体系。我现在也是这个体系的一个小成员,很有必要要把这个体系维护好,我当然是尽职尽责的。这个小体系支撑着我的发展,我把自己的所有也捆绑在这个体系上,很有点儿与此共存亡的味道。我很是用心,主任也看在眼里,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好,有很多不适合跟下属说的话可以给我说,甚至连见他的那个情人也不再避讳我。我知道,我实际上已成了他的心腹。两年半,我就是正科级的科长了。
我曾经骂过一种人的,叫狗人。上大学那阵清高得不得了,见到奴颜婢膝的人就带有刻骨仇恨,并与之势不两立。连一个我们现在看很懂事的辅导员也没放过。大家那时都不叫他名字,他长得又矮小,我们都“尊称”他京巴,很形象的。私下说他的前辈不是人,估计,弄不好是狗的后代。还自编细节说,某年,某月,某天,他父亲出了远门,海员一样长达几年没回家。他妈妈就耐不住寂寞。找外人怕影响,就就地取材,和家里的一只雄壮黄毛狗苟合了,还歪打正着,有幸巧合怀上他。真的,他的眼太亮,明汪汪的,真的像狗。
现在,我也就不自觉地成了人狗,人不能太自醒,太自醒就太痛苦,有时麻麻木木的就不错,在领导跟前是狗有什么关系呢?主任见了分管市长,不也和我见了主任一样吗?下边的小科员,还有来市政府找我办事的,那诚惶诚恐的模样还真的不如狗呢。天天的酒宴也真的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事情,一醉之后,什么也就忘得一干二净。那醉酒的感觉真好,什么也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良心啊,责任啊,良知良能啊,全他妈的见鬼去了,老婆俗点丑点,有什么啊?人这一辈子最好别他妈的给自己那么多原则,那么多条条,你是谁啊,上几天大学也就那么回事,别太当真了。怎么合适,怎么舒服就怎么做,这才是最大的真理。你去追求那个概念的真理,穷其事物的本质,不把你打得头破血流才怪。
我下去到县里区里,对口的下级和见了祖宗似的,接天神般的赔着小心。在他们面前,你就真的是老子,该说就说,该骂就骂,你如果不端着,他们还不觉得你是上级呢。下去就要把脸一黑,说几句硬邦邦的话,就让那帮混小子们大气不敢喘一口,狗屁不敢放一个。乖乖的,战战兢兢的木头般立在你面前,随时听候你的招呼。所以,我没事就喜欢下去走走,周末只要主任没什么安排,就下到县里去。到空气新鲜的山村里,吃点绿色食品,鸡,鸭,狗,兔,还有乳鸽什么的,全是上好的佳品,只要别把胃弄坏了,就放开吃就是。他们看你吃得高兴,也就更高兴,似乎这样才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当然,他们更是看人下菜的。那些务虚的部门下去,他们也是能躲就躲,尽量不照面的。我呢,吃完也有任务的,就是帮他们批项目,和争取资金,每次不管多少都不能落空。
想要什么有时竟也说来就来,得了运势好事就纷纷拥入你的怀抱,挡都挡不住。跟分管市长出了次国,通知到我时就知道机会来了,我现在抓机会的能力特别强,绝对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我们分管市长可不是普通的副市长,他可是常务市长,可以参加市里最高规格的常委会,说话就可以算数的。你看,财政,人事,还有我们委,这种要害部门全是他分管,是市里除书记市长之外的大拿,跺跺脚,全市也要颤三颤的人物。开玩笑,能抓住他,我的飞黄腾达就会指日可待,况且常务市长刚刚不到五十岁,还有做市长的前景啊。当然,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傻里傻气的穷学生,我已到了可以运筹帷幄,不露声色的境界。连处长有时在和我打交道时,也觉得不太好把握。虽是亲戚。可我也明显看出来,他对我已多少有所提防。
老天助我,市长的秘书身体不适。代表团里就我一个年轻人,给大家服务就成了我个人一肩挑了。当然,在机关上,是个严格的等级制的地方,给市长的服务不可能让我一人包办了,再说,我目前做事不可能非此即彼的天真,那些看上去年龄比市长大出不少的局长们,也会在给市长的服务上争先恐后的。绝对也不会把一机会让我一人独享。所以,我的策略就是打穿插,补漏。绝对不能傻傻的冲到第一线,去让大家恶心献媚。在重点服务好市长的同时,同时也给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服务好。这样,既抓住了重点,也照顾好了全面,不然,今后的提拔,还有民主测评,公示这两道程序,犯了众怒可不明智。由于战略对头,我的这次出国给我的日后的升迁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回来后,不仅靠上了大树,还深获老同志的一片赞扬声,真是一举数得。市长还经常让一把手通知我参加他的一些活动,处长看我眼神也有些微妙的变化,角度明显地往下移,有时竟奇怪地寻摸我脸上究竟有什么。我有时也暗暗发笑,风铃也变得异常的乖,人也细腻了不少。
当年,我提了副处,是另一个处。没正处长,我就主持工作,和我媳妇的表哥一样参加委里的会议,一样指挥着十几个人做这做那,但有一点,我们处比他们处重要得多,是副主任兼着处长的。给我留了太大的空间,处长给我道喜,他内心深处的不自在已掩饰不住,多少有一些妒意。我理解他,还是口口声声地在公开场合叫他处长,老领导什么的,但也有时未免露出点居高临下的味道来。实际上目前的状态,他和我已不在同一档次上,他一个军转干部,后台就我们委里的一个第一副主任,年龄也快到了,明年估计就要下了,他的前景估计也就到头了。
两年后,我如期参加了副局级的一推双考,常务市长亲自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还破天荒地给我亲自倒了杯茶,让我也激动了半天。语重心长地和我谈了不短的时间,秘书都进来催了三次,他才让我走了。临了还说:大胆的考啊,我看没问题之类的话,让我一下就有了副局级伸手可即,一把就可以抓过来似的。那次欧洲之行的效益实在是太大了,说起来我还真的没给他服什么务,全让给老同志了。只不过发挥了我是欧洲问题专家的优势,对欧洲的历史,地理,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并见缝插针的给代表团补了好多漏而已。我娴熟的英文口语也派上了大用场,学者出身的市长一下子就和他走近了。我的沉稳又没有让我喜形于色,把前沿一直在向大家避让着。我这个小年轻拿捏的分寸让老同志也说不出什么。这次出国,还让我悟到,什么是有背景。什么是背景?背景是可以创造的啊!把祖上没有的,自己可以添上,只有弱智和简单的婴幼儿大脑的人,才整天期期艾艾骂老天不公,这些人永远也不会读懂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辩证法的。只要寻找到机会,你就拥有了进步的万能钥匙,还有打不开的门吗?
我就顺其自然成了副局级,委里想留,常务市长不许。一句话我就成了市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并且直接跟常务市长服务。一下,我成了热点人物,成了市里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整个世界全变了,变得那么轻松,见到的全是笑脸,听到的语言也更是动听,应酬也多的让我没一点空间。我好在很是清醒,做更大的事情就得把尾巴夹得更深。将来,我相信一个更大的平台已在向我召唤。
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招商引资,那个GDP把所有的官员都弄得神癫癫的,为之发狂。我们市也不例外,书记市长们整天为大项目犯愁,天天为大项目开会。经济的增长点要靠大项目拉动,流通领域的税款就不如工业项目来的直接。还有,大项目落户了,还能带动这个城市的就业,对稳定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还可以拉动消费。你想,这样的好事谁不去想啊,就变着法地出招商政策。前几年土地还可以无偿划拨,现在成了紧俏商品,中央为了保护耕地红线,下了必杀令,一般人不敢冒这个风险。就只能在免税上和服务上做足文章。可几乎差不多的地方都有这优势啊,你无资源,也无地利,所以,这项目就很难来此落户。这座城市的公安没事还喜欢到一些场所抓嫖客创收呢,一次行动中,把上午还陪着开扫黄会的政法委副书记给逮了个正着,人家正陪着一外商快乐呢。项目自然就泡汤了,把从南方来的省委书记气得鼻子都歪了。把书记市长给骂了个狗血喷头,书记市长又反过来把公安局的大小头头也骂了个狗血喷头,这所城市才变得重新歌舞升平起来。
前两天,我们在北京接待了一个香港的投资商,重视起见就由常务市长负责,当然去北京接客人就不需要市长亲自出马了,我和外经贸局的柳局长去接就可以。市长要在市里等着会见洽谈就是,把大体的口径交代下来,由我负责总协调,具体经贸局和负责该项目的人来商议具体事宜。
现在真的是办什么也快,香港到北京的飞机也是须臾之间的事情,我们还没有看几张报纸,飞机就到了,我和柳局长就恭恭敬敬地站在出口等着迎接客人。不大工夫我就看到一男一女向我们举着的牌子走过来,男的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花白头发的戴金丝眼镜的老者,而是一位器宇轩昂的小伙子,西装笔挺,头发锃亮,且纹丝不乱。好一副绅士的风范啊!后面那位穿着入时的小姐也气度不凡。我考虑着下步如何来应付客人,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女人竟然是我多年失去音信的媚媚,我人一下子就瓷在那里,练了几年的定力也全然失去了功力。媚媚显然也看到了我,只是稍一愣神就面带微笑地向我们打起了招呼,谢天谢地啊!后背湿透的我才从乱七八糟的思绪里回过神来,一边向客人伸出手,一边说着刚刚想起来的:欢迎啊!欢迎二位尊敬的客人,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二位来我市光临指导工作啊!套话都能背过,心里稍平静一点,话就说得还算是流利,好在柳局长也没看出什么,避免了我的现场尴尬。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面对一个如此理性的前女友。在接下来的很多场合里她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和我交谈,我开始还不太适应,也恨自己。一个男人,都是市里的中层领导了,居然那么放不开,居然在感情上输给一个女性?我真的成熟吗?我也在抱怨自己的农村出身,骨子里的很多东西实在是太陈旧,感情色彩太浓,成不了大事啊!在这一点上媚媚是我的老师。她的行为也真是好好的给我的现代生活补了很是有必要的一课。
在他们即将离开本市的前一天,媚媚悄无声息地把我约到离省城最近的一家酒店。那是另外的一个政府活动的主要场所。另外这所三星级的正准备上四星,现在硬件也达到准四星了,条件不错,但主要的是商务用途。我知道了精明过人的媚媚的用意。安全啊!同时,我内心又一次不争气的涌动出感激。尽管我在不停地骂自己没用,心头还是热热的,幸亏我不经商,也同时庆幸幸亏我没和她结婚,不然,我会败给她一生的。和她我们在骨子里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我也找到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本质区别。看人家处理事那叫一个大度,很男人!我呢?小家子气!忸忸怩怩的有点娘们。
吃饭没有在酒店,就随便找了个在郊外还比较像样的小店,就是那种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乡野风味的农家乐。小店为了吸引城市客人,卫生条件都很让人放心。为了一部分不带老婆出来就餐的人还准备了单间,真是让人感叹现在人真的是太精明了,为了能赚到钱什么都替你想到了。点了几个小青菜,我想极力控制我自己,尽量表现得男人些,可有些东西不是想男人就能男人的,基因在作怪。看着依然迷人的她,有点愧疚,人家实际上就没当回事;有些兴奋,她又是那样平静,略施粉黛的脸也满真实,约我出来好像就是谈笔业务那么司空见惯,根本就不像是在一起生活过的情人。
在不太明亮的灯光里,她慢慢地呷着自己带来的葡萄酒,好看的唇优雅地贴在光滑的玻璃杯沿上,有时还轻轻地用牙齿敲击,发出轻微的很是动听的声响,看我的眼神如湖水一样平静。我此时有了风铃不要说十个,就是一千个,甚至一万个也抵不上她啊!就像普通的泥瓦盆罐怎么能比得了官窑的价值连城的玉瓷呢?可我就真的需要风铃那样的一个俗得不能再俗,普通得几乎不能再普通的风铃。风铃能给我洗脚,能接受我的谩骂甚至殴打,还得给我一张笑脸相迎。媚媚行吗,门也没有啊!再说哪天她如果看上个情投意合的,她会毫不犹豫的给自己的男人扣上顶绿帽子,一般人还就真的承受不了。想到此,心里不免有点宽慰,还有点怜惜起风铃来。
我们就这样宾主般的对坐了半天她才说:你这几年很不错吧,看起来很是那么回事啊。我说:咳,迷迷糊糊的混,说不上怎么样。我不想说得太多,想听听她发几句牢骚,说些责怪我的话,甚至问一下我找了个什么媳妇,有没有孩子?她离开我后我是怎么样生活的?可她居然丝毫没有向那个方向拐话题的意思,我也不能不打自招啊!想问她点个人的事情,可又有些生怕伤害她,引人不快。这酒喝得一点也没有味道。可我还是忍不住就说:你,这几年怎么样?我想说我一直牵挂着你呢,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那样虽是句实话,可在这里就很虚伪。她看看我轻声地说:还好,日子还算开心。好与不好,不就是一种感觉吗?我点点头说:是啊!生活就是一种感觉,感觉好就好啊!觉得自己说完了,可又画蛇添足的加上那么句没头没脑的感慨,自己也觉得真是好笑。
客人大多散去了,她说:忆忆旧吧,我们曾做过短暂情人的,对于你,我还能时不时地想起,说明你还值得我喜欢,怎么样,去我订的酒店吧,这里不是省城,没有人会发现,你就放开些,要像个新郎倌一样,好吗?我没有回答她,也只好点点头。外面还有等着拉夜场的的士,司机懒洋洋的迷糊眼上来问:老板去哪里?她说:去槲树湾。就上了车,在这样的小城市,四星级的酒店对于的士来说,那简直就像在北京问天安门和故宫一样,名头绝对大和冲。
她很快走了,送她的时候我居然是那样的轻松,一点那种送别的留恋和惜别也没有,我觉得我也自豪的终于男人了一回,她在内心里也一定替我高兴的,我想我会很快把她忘却的,真的。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