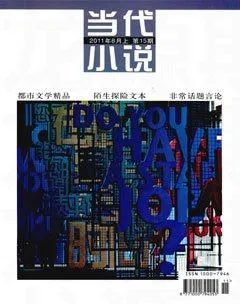故乡往事
两个不吃肉的孩子
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在一九六零年的春天,人们吃草根,吃树皮,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那年春天,谁要是看见野草长出了地面,或者,看见树木发了芽了,这才是新鲜的事情,甚至,是离奇古怪的事情。那一年,都快到夏天了,地上仍然看不见野草,树都死了大半。古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连皮都没有了,还能活着吗?那一年的春天就跟冬天似的,夏天,也跟往年的早春一样,仍是满眼的苍凉。
村子里的人饿死了三分之一,个别人,在埋葬死去了的亲人前,趁别人不注意,从死人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悄悄地,瞒着村里人,煮给家人吃。没办法呀,人的肉,也是肉不是,总比草根树皮有营养吧。父亲说,几百人口的村子,在那三年里,好多年轻的女人连月经都没有,更别说生孩子什么的了。父亲还说,不信你去打听打听,足足三年的时间里,村里连一个新生儿都没有。不仅我们村,别的村子,也是一样的。
在那个春天,死人的事情真的太多了,起初,谁家有人死了,村里的人还来吊唁吊唁,嚎几句丧,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共同把死者抬到山坡上埋掉。先死的人是幸运的,他们还能背着一口棺材上路。到了后来,谁家死了亲人,就只有家人为他安排后事了。他们的办法是,男主人把铺在炕上的席子揭了,草草地,将尸体卷起来,再找一根绳子捆住,然后,男主人独自将死者背到山坡上,挖一个坑,埋掉,就完了事。往往是,人们彼此见面打招呼:“这几天没看见你娘,她能挺得过去吗?”回答的人说:“‘一七’都已经过了。”问话的人于是叹一口气,无声地走掉。
他们都不知道,村里下一个要饿死的人,会是谁。
老人、小孩、妇女,体力差的,体质弱的,以前有病在身的,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陆续走了不少。
我在这里所要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一个吃肉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当然不是我的父亲,甚至,也不是我在小说中称之为父亲的那个人。
这一家有两个儿子,都不大。老大还不满十岁呢,老二当然更小些。
一九六零年,在一个春末夏初的傍晚,这个做父亲的,在去独自掩埋饿死的父亲时,从他父亲的屁股上,偷偷地,割下一块肉来。别的地方都是皮包骨头的样子,哪里还有肉让他割呢?他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没有办法。在他掩埋父亲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一家人用野草煮了一顿早饭之后,午饭被省略了,晚饭也是没有着落。他的老婆睡在炕上已经三天了,他的两个儿子,仿佛风中的烛火,摇摇摆摆地,是一副随时都会倒下的样子。
这个父亲回了家,煮肉给家里人吃。他的老婆不明白,这可是一块新鲜的肉,是哪儿来的?她这么问自己的男人。
男人说,你就吃你的吧,啥也甭问了。
女人吃了一口,又躺下了。她没有再吃。她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男人连一口都没有吃。
孩子们只管狼吞虎咽,他们似乎顾不上父母吃不吃。他们都饿坏了。
他们家的老大,不知何故,在第二天,“生了风湿”。
“风湿”在我的老家是有专门的指定的:人们管皮肤因为过敏之类的原因而产生的疙疙瘩瘩的无名肿块,叫做“生了风湿”。“风湿”一般过几天就好了,皮肤也是如常、如旧。这不是什么大事情,司空见惯,习以为常,除了奇痒难耐,没什么大不了的。治疗“风湿”的土办法是,找毛笔和墨汁来,将患者上身的衣服脱光了,在左右臂膀和前胸后背相对应的位置,分别写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十二个大字,就可以了。据说,这么写了,过一阵子,无名肿块就不那么痒了,慢慢地,肿块也会消失。
文字居然可以用来治病,这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最离奇古怪的事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不是真有疗效。我也生过“风湿”,也用这样的方法治疗过。总之,在这么做的时候,因为冰凉的墨汁从皮肤上划过,那种又烧又痒的症状,是暂时地,有所缓解的。治疗“风湿”在我的故乡,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药物或方子,所以,用这样的办法治疗,总比不治疗要好,是否有用,就没有人去计较了。在农村,不用治疗,也是可以忍受的,不是吗?能够忍受的病症,可以忍耐的屈辱,都得忍着,这是乡亲们的人生哲学,也是所有弱者和穷人的哲学。
因为上一次吃肉之后生了“风湿”,一年后,老大再一次有了吃肉的机会时,死活都不吃肉了。他说,我一看见肉就觉得痒,浑身的疙瘩,好像又要出来了。
他们的父亲说,人要是不吃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父亲是这么想的:虽然现在没多少肉可吃,将来一定会有的,将来有了肉,做儿子的却不能吃,他的人生,不是白活了一场?这个父亲认为,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吃,但是,不吃肉是不行的。
再说,孩子不吃肉,大人怎么吃得下去呢?
这时的日子,比起前几年的大饥荒来,已经好过多了。只要赶上逢年过节的日子,家里偶尔象征性地,还能煮一次肉来吃。每一次煮了肉,父亲都要分一半出来,逼迫老大吃了它。这一招还真是灵验,老大果然渐渐地,又吃起肉来了。
这样的事,被他们家的老二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有一天,终于又等到一个可以吃一点肉的日子了,可是,无论任何人说出什么话来,老二也不吃肉了。老二不吃肉的理由是,我一看见肉就想吐。做父亲的于是如法炮制,重新用起当年对付老大的方法来。他从小得可怜的锅里分了一半的肉出来,逼老二当着大家的面,吃了它。只是,无论怎么逼,老二还是不吃。这个法子用来对付老大还可以,对付老二似乎就不灵了。人跟人虽然看起来差不多,都长着鼻子、眼睛、嘴巴、耳朵,都是用脚走路,用手做事。毕竟,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吗?
无论父亲好说歹说,费了多少口水,哪怕是威逼利诱也好,软硬兼施也罢,做父亲的都已经束手无策了,老二还是始终不肯吃肉。最后,父亲无奈的举措是,他把老二一个人留在了家里,一家人都下地干活去了。
临出门时,父亲对老二说,你如果不把那些肉吃了,就不许出门。父亲心里明白,老二跟老大不同,老大勤快,老二却是个贪玩的孩子。不让他出去玩,兴许他会把肉吃了,再出去玩的。
天快黑了,一家人干完活,从外面回来,父亲问老二,肉吃了没有?
我把它倒在茅坑里了。
老二的回答,一点也不含糊。
大饥荒的日子过了才一年多的时间呢。做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儿子这么糟蹋吃的东西,而且,被老二糟蹋了的,不是野菜,不是粮食,是香喷喷的天底下最好吃的肉啊!何况,为了省给孩子们吃,他与他的老婆,几乎都只是尝了尝味道就没有再动筷子。父亲能不生气吗?父亲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当父亲的举起拳头来,想要教训他的儿子。可是,他把举起的手,无声地,又放了下去。
家里每一次有了吃肉的机会,父亲仍然分出一半的肉出来,逼老二吃。老二还是不吃,父亲觉得这个儿子真是太烦人了,他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只得继续逼他吃。老二照旧不吃。父亲又一次,把老二和肉留在家里,不许他出门去玩。父亲后来想,只要你舍得把肉倒在茅坑里,你就继续倒吧。父亲觉得,只要自己尽心尽力就可以了,至于老二吃不吃肉,他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了。
父亲哪里知道,他这么做,对老二来说,却是正中下怀。
老二从不曾见了肉就想呕吐,他也从来不曾把肉倒进茅坑里。
老二当然把它们都吃了。
老二太爱吃肉了。为了更多地吃到肉,老二才编造了“我一看见肉就想吐”的谎言,老二这么说的时候,心不慌,脸不红,说得跟真的似的。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分到一半的肉,吃个痛快,吃得过瘾。
老二自然不能跟父亲撒谎说,他把肉喂了狗。把自己说成了狗,老二当然不愿意。更主要的是,人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哪里有吃的东西喂狗呢?村里的狗,都在前几年就饿死了,死了的狗,全给人吃了。村里已经好几年都无人养狗了。为了给被他吃掉的肉找一个合理的去处,老二真是费尽了心机。老二想的是,如果说成是扔在了别处,他的父亲一定会出门去,要把肉找回来,洗干净了,会再吃的。说是倒在茅坑里了,大人就没办法再把肉找回来了不是?
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之后,老二就用不着这么骗肉吃了。俗话说:贼不用打,三年自招。这话果然有几分道理。老二后来甚至跟村里人炫耀说,那肉不是倒在了茅坑里,而是让我吃了。老二还说,我这么对父亲说也不算撒谎:人吃的什么好东西,最后还不是倒在了茅坑里——拉出去了不是?
老二最后得意洋洋地说,只不过,我是把倒在茅坑里的时间,说得提前了那么一点点。
这时候的老二,已经是个青年了。
在这样大言不惭的撒谎者面前,在如此的诡辩面前,任何人都会哑口无言的。
村里人把他们从老二嘴里听来的,纷纷说给了老大。老大听了淡淡地说,我早就料到老二会这么做的。他一生下来,嘴就馋嘛。老人还想替老二开脱呢。人们纷纷摇头,说,老大真是太老实了。
人们没有想到,老大居然说出下面的话来。
老大说,我以前不能吃肉,也是装出来的。
老大平静地说,有一天晚上,我在吃肉的时候,发现父亲一口都没吃。我又偷偷地瞥了母亲一眼,我发现母亲也是只尝了一小口就说啥也不吃了,那时,母亲都已经饿得瘫在炕上了,为了给我们省一口吃的,她连命都不顾了。老大接着说,到了后来,每逢有了吃肉的机会,父亲总说他是饭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母亲的理由是,我一看见肉就恶心,能尝一块就已经不错了。
老大说,可是,每当我吃得正香的时候,却发现父母正在努力地往肚子里咽口水。他们既然那么馋,为什么不吃呢?当然是肉太少了,他们才不约而同地,想把肉省下来,让两个孩子,尽量多吃一点。
老大说,我生了“风湿”之后,正好有了可以遮掩的借口,就说自己不能吃肉了,父母竟然信以为真,丝毫没有怀疑。他们哪里明白,我是想把肉省下来给他们吃呢?但是,这么一来,我得到的肉,比以往被我吃掉的,不仅没有少,却还多了很多,我怎么能继续装下去呢?老大说,我惟一能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少吃一点。老大最后说,不吃肉的办法,看来,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
老大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只能在家当一个农民。老大在村里,侍奉父母并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也得抚养自己的儿女。老大的儿女如今都大了,一个一个,都长了翅膀,飞出了农村。老大的儿子在城里工作,娶了个同事当老婆;老大的女儿也在城里工作,嫁给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城里人。老大现在跟他的老婆在乡下单独过日子。有时候,儿子会带着孙子和老婆来看他,顺便捎来些反季节蔬菜和酒肉什么的,给他们吃喝;有时候,女儿也拽着女婿和外孙女来看他,大包小包地,拿许多穿的用的,一起送了来。可是,老大和他的老婆过惯了简朴的日子,这些东西对老两口来说,真是太奢侈了,他们根本花用不了那么多。儿子走了,女儿走了,他们就悄悄地,给村里的人们,分一些,送出去。这些他们当然不曾对儿女们讲过。老大是怕说给儿女们听了,他们会责备自己。
老大和他的老婆,至今仍然种地,他们种出来的绝大部分粮食都没有人吃,老大只好把粮食弄到镇上去,卖了,把卖粮的钱存在银行里。
过完这个年,老大整整六十岁了。他忠实而又谦恭地,当了一辈子土地的奴仆。
人们说,一个人要是太善良了,就不会有什么出息。老人的一生,果然是庸庸碌碌的一生。琐琐碎碎,平平淡淡,既无波折,又无风雨。
人们常说:一岁看大,三岁看老。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个人长大了会干什么、能够做什么;三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一生将会过得怎么样。
关于老二,人们在听到他关于茅坑的狡辩时,就曾不无感慨地说,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是可以当很大的官的。
老二上过学,后来果然当了大官。更后来,在他即将光荣卸任的时候,由于东窗事发,他那一系列虚虚实实的连乡亲们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官职,被全部削去不说了,还退还了部分贪污受贿的钱物,更多被他挥霍掉的,自然是再也追不回来的了。
老二最终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他还能活二十年吗?想想他做官时那容光焕发盛气凌人的模样,再看看如今那憔悴的面容和虚弱的样子,人们对老二的长寿无不表示怀疑与担忧。他们都说,即使老二死了也难以把刑期服满,从而赎清他所犯下的罪孽。
岁岁平安
到了大年三十夜,村里终于热闹起来了。
啥也不做了,啥也不想了。没有干完的,过了年再接着干,人只要活着,一辈子都有干不完的事,什么时候是个头?没有。说是没有,其实是有的。你不干了,把什么都放下了,你歇着不做了就是了。不这样还真的没个头呢。
天还没有黑,太阳还没落山,家家户户都早早地吃了夜饭,出门去了。
到哪儿去?去做什么?
这还用问?去敬先人嘛!
先人就是家谱。年三十,供奉先人的那家,吃了午饭,早早就请了族里德高望重的人来,净了手,摆好了献饭、献食(馒头)、贡果、香炉,上了香也点了灯(蜡烛),礼仪完毕,恭恭敬敬地,把家谱打开了,就在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家谱今年过年在你家,明年过年在他家,轮流供奉,供奉的时间可以提前或推迟,但一个轮次要都轮到,一家都不落了,再从头轮。敬先人,从前是“早上清香,晚点明灯。”从除夕夜开始,正月初三花一天时间摆酒席,吃完了整整一个大家族的团圆饭,才结束。现在不同了,现在无论早晚,去敬先人的话,一律都要放鞭炮、点灯、上香、祷告、磕头、烧纸钱。仪式完毕,按老一辈传下来的习惯,要守先人,也叫守夜——在供奉家谱的那家坐到过了半夜子时,吃了宵夜,喝了酒,新年也等来了,才可以醉醺醺地,分头回家睡觉。
这大半夜的时间怎么打发?你就甭操心了!
属于这个家族的响器:锣、鼓、铙、钹,跟着家谱,都在这家搁着。平时是不能摆弄这些响器的,除非谁家搞迷信做法事,要么就是过年的时候,你才能够尽情尽兴地,敲打出一番热热闹闹的气氛来。摆开响器的,都是孩子,他们来得最早,他们憋了整整一年了,早就按捺不住了。这是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大一些的对响器没了兴趣,小一点的不能让他们玩响器——怕弄坏了。孩子们把声音整得挺大,给大人赶到大门外去敲去打了,他们也不胡敲乱打,也是有节奏有韵律的,不过简单了一些,这也好,孩子们即使不会,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学会了。对孩子们来说,合适得很。
堂屋里,十来个凳子围着火塘,这是辈分很高年纪很大的老人在坐着,家常里短,说古论今,要么直接“摆古经”——讲故事。《二十四孝》什么的,三天三夜说不完,十天半月说不完。谁爱听,谁想听,凑到身边去听就是了,没有人听,他们就自己说给自己听,有时候,一个完整的故事,你讲一段,口渴了,他又接过去,继续讲。他们都是一些守旧的人,喜欢讲,也喜欢听,百听不厌。火塘里煮着茶,火塘周边,一个一个,摆满了酒盅、茶杯,酒盅是满的,茶杯也是满的。空了,这家的男主人,赶紧又给他们续上了。
屋里还有另外一拨人,他们围在家谱旁边,是这个夜晚的生力军。
这些人,才上了一点年纪、四十岁左右的人居多,二三十岁的,五六十岁的,也不少。他们往往没有围火而坐的资格,他们召集人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无论长幼,不管辈分,想唱你就唱,要弹要拉随你便。这些“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的人,几乎人人都能摆弄乐器,他们的家里很有可能一没粮二没钱,哪怕别的一概没有,琵琶是有的,二胡也是有的。会十来首曲子的不算会,仅仅入了个门。要弹要拉的,自己找个凳子先坐着,占好了位置,这才打发自己孩子回去,转眼就把琵琶二胡什么的,给他拿来了。唱的和听的,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圈子,往往,你分不清谁在唱,谁又在听,他们都会唱。他们单等二胡琵琶把前奏奏出来,满场立刻鸦雀无声。
召集这一个群体的,年年都是一个青年人。刚开始充当召集者的角色时,他还不到二十岁,现在已经快三十了。大家都听他的。虽然他一天学也不曾上过,一个字也不认得,可是,这有什么要紧呢?他的二胡拉得可真不错!老一辈传下来的几百首曲子,就没有他不会拉的,不会唱的。大家全都服了他了。在这样的场面,他当之无愧,是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人呢。
这个年轻人来敬先人的时候,跟别人不同,他的手里拿了一把二胡,他知道自己的职责。虽说婚已结了好几个年头了,但他的媳妇还没给他生下可以使唤的儿子呢,也不知有没有毛病,是谁的毛病,反正人还年轻,以后再生也不迟,时间有的是。
年轻人拉二胡的时候,摇头晃脑,双眼微闭,他的身子俯仰有序,时疾时徐,那个忘我投入的劲儿,那副惟我独尊的神态,仿佛不是置身在人群里,而是进入到了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中去了。他的二胡拉得真是如幽如怨,如泣如诉,好得不得了。
最热闹的就数唱曲子的这一堆人。他们人数众多,最多的时候,是上百人的队伍。他们的声音又大,又响亮,又整齐,把老人们讲故事的声音压下去了,把敲锣打鼓的孩子们挤出去了,他们才是除夕夜里,真正的主角。
年轻人的人马一下子就齐备了。有人迫不及待地提议,唱《十劝君》吧。提议的人,是个半大老头。
顿了顿,年轻人的二胡一拉,琵琶跟着,也响起来了,弓飞弦舞,开了场了:
一劝君,庄稼人儿听,
庄稼人儿要认真,
薄田淡地多上粪,
皇天不昧苦心人;……
“这个谁不晓得啊?没意思!没意思!太长了。”
是村里的后生小子在外围喊。人挤着人,喊话的人还故意缩下身去,看不出是谁,也没有听清是谁的声音。拉二胡的年轻人停了,弹琵琶的人只好也停下来,有人问:唱啥好?
有人喊了一声:《十二花》吧。
《十二花》相对说来,只有十二个段落,短得多了,也更好听。就《十二花》吧。
正月里——看灯花儿打头(的)开(哎),
雕为(的)食亡人为(的)财,
蜜蜂(吆)只为(的)采花死(吆),
赵巧只为送灯(吆)台;……
赵巧是谁?是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呗。乡下还有一句谚语:“赵巧送灯台,一去永不来。”是有去无回、往而不来的意思。《十二花》每段对应一个月,歌唱一种本月即时开的花,乐曲婉转清亮,唱词工整精美,不低俗,是老少皆宜的民间经典曲子。
一曲终了,有人说,唱《月儿落西下》吧,看不见说话的人是谁。
行。年轻人说。
月儿落西下,记起小冤家,
你也不来奴家耍,心里乱如麻;
你也不来耍,我也不怪他,
写封书信带给他,奴有知心话……
一写郎无意,花园把奴戏,
哄奴上墙抽了梯,做事不在理;
二写郎不该,当初情何在?
小妹得病是你害,小郎你不该……
这个曲子的唱词所采用的,居然是民间文学里很难一见的移步换韵的手法。因为是叙事文本,较为沉闷,刚刚起了个头,就有人不愿意了。他是急着想要听听自己爱听的曲子呢,他已经等了很久,耐不住性子了。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他大声地喊了起来。
换啥?拉二胡的年轻人问。
那人说,唱《送郎》吧,这个人人都爱听。
好!好!好!大家一再地齐声附和。
《送郎歌》,又叫《打灯蛾》,“打灯蛾”是方言的叫法,其实就是灯蛾。人们说:灯蛾扑火,自取灭亡,说的就是“打灯蛾”。《送郎歌》的确是人人爱唱人人爱听的曲子。这个年轻人,人虽年轻,脾气却“不年轻”,他是有求必应,随和得很。谁要点他就听谁的,一点也不烦。
打灯蛾,满天飞,你是哪里的瞌睡客,
你有瞌睡了你睡去,不等天亮我叫你。
鸡叫了,狗咬了,和尚寺里钟响了,
和尚起来上头香,梳头打扮送小郎。
送郎送到床当头,打了灯盏倒了油,
打了灯盏不要紧,湿了妹的花枕头;
送郎送到箱子边,打开箱子取衣衫,
一件叫郎当面穿,一件给郎做替换;
送郎送到柜子边,打开柜子取两串,
一串给你做盘缠,一串给你买鞋穿;
送郎送到睡房门,一对门神笑吟吟,
我问门神笑啥子,笑我二人情意深;
送郎送到火塘边,脚踏火塘四角尖,
中间架的疙瘩柴,沿边煨的茶罐罐:
送郎送到火塘边,拨开火堆抽袋烟,
你要抽烟就抽烟,甭往奴家脸上看;
送郎送到堂屋中,手拿酒杯把酒斟,
郎吃三杯醉醺醺,妹吃三杯满脸红;
送郎送到台子边,手把柱子望青天,
我望青天下大雨,再留小郎耍几天;
送郎送到院子里,毛毛雨在下着哩,
左手给郎打把伞,右手给郎擦把脸;
送郎送到大门外,双手扯住郎腰带,
我问小郎几时来,三月不来四月来;
送郎送到十字街,十子路口好买卖,
拉住小郎不丢开,看你把我咋安排?
送郎送到石头坡,石头崴了奴的脚,
走一步来痛一阵,这个冤枉给谁说?
送郎送到椒树林,手把椒树说苦情,
甭学石榴红了脸,甭学椒籽黑了心:
送郎送到锈石崖,心想石头滚下来,
把咱二人都砸死,免得一块想一块;
送郎送到观音房,观音菩萨坐上方,
我请观音来做媒,咱们二人拜花堂。
唱词还是长!可是,它把一个女子的柔情蜜意表达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一点也不拖沓。人们都沉浸在曲子绵长的韵味里,久久地,出不来了。
拉二胡的年轻人,乘机抿了一口酒,他喜欢喝酒。发觉大家一时无语,他又咕咚咕咚喝了一气凉了的茶水。
“唱《女寡妇》或《男寡妇》吧,那些也好听。”
有更“恶搞”的,用很小却又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说:“干脆来一段《十八摸》!”
人们轰地笑了。
这更不行,《十八摸》可是典型的黄段子!这纯粹是耐不住寂寞的年轻人在瞎起哄了。守岁是个严肃的事情,这样的场合,谈情说爱的曲子还可以唱,那种黄曲子只能在非正当的场合,在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他们年轻人在场的时候,才能偶尔唱唱。
围着火塘的老人里,有人听不下去,站起来发话了:“谁再胡闹腾,把他给我押过来跪到先人跟前去!”老人的话音一落,吐舌头的、扮鬼脸的、挤眉弄眼的、缩着脖子的、矮了身子要躲要藏的,都有,但是,一齐噤了声。
只有二胡和琵琶的声音,还在悠扬。
一晃,到了吃宵夜的时间了。
吃完了宵夜,酒足饭饱,瞌睡也上来了,不时有人陆陆续续地走了。
人走完后,拉二胡的,弹琵琶的,才走。领奏的这个年轻人年年都是最后一个回家的,这不奇怪。他所从事的,是给大家领唱的角色嘛。再说,他喜欢二胡,只要还有人在拉、在弹、在唱,他就没有要走的意思,也没有一走了之的道理。
已经是后半夜了,这个年轻人终于回家去了。
大门没有闩,媳妇给他留着门呢,他想,一定是半夜起来给他开门,她怕冷,大门才没有闩上的。他又想,万一有小偷、给小偷进了屋咋办?他没有再多想。他的头疼得太厉害了,吃宵夜的时候,这个敬一杯,那个敬一杯,他喝了不少的酒呢!他摇摇晃晃地进了睡房,为了不惊扰媳妇的瞌睡,他悄悄地、轻手轻脚地,摸黑上了炕。
他把腿向热被窝里伸过去,隐隐约约,他觉得被窝里多了一条腿。这是怎么回事?他吓得一激灵,酒醒了不少。我是不是弄错了?他又想,肯定不是孩子嘛,——他们夫妻没有孩子。媳妇到现在也没怀上个一男半女的,更别说睡在炕上了。即使有了孩子,小孩也没有这么粗的腿!
他又伸了伸腿,他用自己的腿小心翼翼地,在炕的里侧摸了摸。
不是多了一条。多出来的腿,不多不少,是两条。他明白了。
在黑暗中,他坐在炕上,愣住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没说什么,躺下,睡了。拉了大半夜二胡,他真的累了,他喝得也太多了,下眼皮支撑不了上眼皮,他很快就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又醒了。
这一次是真的醒了。酒也醒了,酒劲过去了。
他伸了伸腿,多出来的那两条,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
他闭上眼睛,继续睡。
古话说得好:“正月顾头,腊月顾尾。”意思是,正月和腊月是一年开始或结束的时间,说话做事,必然有所顾忌,要善始善终才行,图个岁岁平安嘛。不这样在新的一年里,你的家里就不会顺顺当当。何况大年三十夜恰恰是头尾交接的关口,更应该谨慎忍让才对。
父母是这么教育他的,他也是这么想的。
到了夏天,媳妇的肚子一天天地鼓起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媳妇瘦了不少,脸上憔悴了,黑斑也出来了。他的脸上,却常常挂着喜庆的颜色。家里的很多事情,凡是需要出一点力气的,他都不让媳妇做。大年三十夜,炕上多出来的那两条腿,他一次也没问过她。
一旦得了空闲,这个年轻人常常独自一人,在月光下,或在大门外的老槐树底下,摆弄他的二胡。因为只有一把二胡,听起来,声音就显得嘶哑了些。他又在练习装在肚子里的那么多曲子呢,他似乎更加刻苦了。他那么用功,明年,明年的明年……应该不会有人赶上或超越他演奏的水平了。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