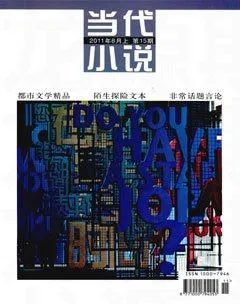无名果
“你捡到什么宝啦?”
马法官刚从路边的桃李树下直起身来,就听到一个气促的声音问他,那个声音有点迫不及待,好像是在说你捡到了宝,见者有份。幸亏马法官对这个声音很熟悉,没被突然冒出的人吓到。他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返过头,然后就看到背后站着的伍麻子。多年不见,伍麻子脸皮已皱得像一坨鸡屎。
他鼓起勇气,说:“没捡什么。”
“没捡什么?”伍麻子不信,“分明看到你躲躲藏藏,做贼一般。”伍麻子眼晴土蜂一样蜇在马法官身上,晃来晃去。马法官很不自在。
在村子里,伍麻子不是族老,也不是村长,就连村民小组长也不是,但他说话比谁都灵。特别是一些重大事情上,比如修路啊,比如谁家闹纠纷打官司啦之类,谁也不能撇开伍麻子,撇开了他,你就任何事也休想办成,事与愿违,什么也休想办成。
见到了伍麻子,马法官就记起读小学的时候,他和几个伙伴在伍麻子屋门口玩耍,伍麻子家正在煮板栗炖鸡,闻到香味,马法官就直掉口水。山边边上,马法官家有两棵板栗树,即便年成再差,每年至少也要打两担板栗。板栗外壳全是毛刺,容易刺伤人。只要打板栗,马法官就戴上皮手套,欢喜地跟在爷老子屁股后面,帮忙。打完了,爷老子就把带壳的毛板栗一担一担挑回家,马法官守在板栗树下,趁机用石头将刺壳砸烂,偷吃几颗。平常尽管带壳的毛板栗堆满半边屋子,爷老子下了锁,马法官是偷吃不到的。待到起价,马大爷就全把刺壳除掉,挑到集市上去卖。当然,每一年马大爷都少不了给伍麻子留一袋板栗送去,自己舍不得吃,更别提板栗炖鸡了。马法官和伙伴们边玩边想,这板栗是我家爷老子送的,说不定伍麻子看到了会叫他吃板栗炖鸡。心里有了期待,马法官就赖在伍麻子家门口不走,伸长半颗脑袋在门边张望,不料,伍麻子把一根啃得干干净净的鸡骨头扔出来,正好砸中马法官额角,血顿时就冒了出来。马法官赶紧用手压住血眼,缩回家。
自此,马法官就不喜欢伍麻子,有点讨厌还有恨的意思在内。但他看到爷老子平常与伍麻子走得近,也就顺着伍麻子,不敢得罪他。得罪他就是得罪爷老子。想到这些,马法官低着眼摊开双手说:“真没捡什么。”
他声音细到像蚊蝇的哼哼声。
当想到自己的工作还需要伍麻子费力时,犹豫一会儿,马法官又乖巧地问:“伍伯爷,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呀?”
“跑跑步,活动活动筋骨,锻炼身体。”伍麻子说。
农民天天有活,天天在活动筋骨,犯得着这样正儿八经的锻炼?马法官说:“伍伯爷,锻炼是城里人的事,你变城里人啦。”
“老侄,你看我像城里人么?”伍麻子得意地说。他家的地根本用不着他劳动,只要一到季节,乡亲们就抢着帮他做了。他平日坐在家里不动都呼吸不均匀,运动后就愈加胸脯起伏不止,像前生是猫投的胎。他说近年来身体老和他做对,如果不锻炼一下,身上会生起蛆来。说话神气好像他呼吸新鲜空气(新鲜空气城里当宝),比城里人还牛皮几分。
马法官读书时节,马大爷就立势,多次找过伍麻子,打预防针,说是你老侄法官宝毕业你可要帮全忙啊,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伍麻子打声哈哈,到时再说,到时再说。
马大爷以为伍麻子答应了他,就安慰儿子说:“只管把书读好,工作事就找村里的伍麻子帮忙。”伍麻子儿子在县里当县长。平素马大爷和伍麻子拢得近,不信伍麻子不帮。
马大爷喜欢看包青天,只要是关于包青天的电视连续剧,他每天追着看,随着剧情一时悲一时喜。对于包青天,民间传说有无数的版本,看着电视,好像包青天的形象就得到印证,定格成顶天立地的一个男人,有眼睛,有鼻子。马大爷最大的愿望是儿子能做法官,像包青天一样为人间主持正道,做出一番事业,所以在儿子出生后就取了这个很直接的名字。
马大爷靠种地谋生,从不会做点小买卖增加收入,他拿不出更多的钱为儿子打点铺路。他有的只是力气。因此马大爷拼死拼命地找土地要收成,咬着牙根送儿子读书,儿子每以优异成绩升一级,他就浑身来劲,鼓励说:“法官宝,争气呀。”
“会的,爷老子,你放心,我会努力。”马法官憋足劲说。
马法官的确很争气,他把别人玩的时间全部放在学习上,课外活动也极少参加。他不负所望考上了大学,读的也是法学专业,这在村里是不多的。马法官上大学时,父亲还在村里特意办了一桌酒席,以示庆贺。村里人都高兴,就如是自家孩子考上了,说马大爷风水转旺,定要把祖坟培高点,看来法官宝是个可造之材,说不准日后盖过伍县长呢。
做过酒宴,客人喝酒留下的残羹气味,还在满屋飘荡,马大爷带上锄头簸箕,拉上儿子就走。与父亲相处这么久,马法官还是首次看到他的急迫相。马法官不知他要做什么,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走了好长一段路,马法官才弄明白原来是朝祖坟的方向。这天阳光明媚,万物生发,田垅里到处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尽管水还有点寒冷,但吆喝黄牛整赶水田的,打起赤脚在水田边修田塍的,大有人在。
找到自家坟地。马大爷父子俩就忙活开了。先是烧香纸,祭念一番,然后清除杂草,父子在远处荒地取来泥土草皮,小心地培在坟墓上,直到把古旧坟墓堆成一座高高大大的山峰。
收工走在路上,父子俩暮色中回头张望,看到高高的土堆上仿佛真有灵光正在冉冉升起。
如今,马法官大学毕业回到家里,心里很犯愁。同学们谈未来谈理想,他毕业却找不到工作,回家又不会种田地,未来真的不敢想象。家里除了一个老得掉牙的父亲,没别的亲人。茫然无助的他做梦也想拥有一件宝物,换回一个适合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别无所求。可梦想归梦想,不等于现实。
儿子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马大爷却不知如何才能安排好儿子工作,又没别的门路。所幸马大爷是个有准备的人,儿子一读书,他好像就知要求伍麻子似的,送板栗,送新鲜田鱼,有了好吃的就送,自家舍不得吃。他打定主意,一个筋斗栽在伍麻子怀里,赖着他,惟有他能帮得到啊。可现如今马法官真毕了业,马大爷再去找伍麻子,伍麻子唾沫喷泉一样,说,难,铁桶一般难入。同喝一口井水长大的人,如果帮得上,不帮你,我帮谁去?其实难不难只有伍麻子心里清楚,来求儿子的人也不是他马法官一个人,不都解决了?包括一些镇长、局长,很多事情都是儿子这个当县长的一句话而已。他说并不在乎你送了什么,送礼的人多了去了。你马大爷送的礼折成钱还不如人家一条烟或一瓶酒。马大爷愈加窘迫,他说志木叶子包盐,是一片心意,礼轻情义重,你伍麻子莫嫌弃啊,你儿子没当县长时节大家彼此一样的啊。他只想着逮到机会多和伍麻子亲近,感情在于平日积累。
任凭马大爷巴结,好话说了一箩筐,伍麻子就是不上路。
你这个一生下来就顶着个法官帽子的人,还要来求我不成?甚至伍麻子还在背地里笑过,马家的先祖葬地风水不好,没有后劲,眼睁睁的一个人才出不来,把坟垒得再高也没屁用。
伍麻子心里的这些龌龊,马大爷自然蒙在鼓里,马法官也不懂。马大爷这么努力巴结他,就是指望在关键时刻伍麻子帮他一把啊。虽然马法官自小就对伍麻子印象不好,但大学一毕业,就真印证了毕业即失业这句话。马法官找老师同学,跑要用人的单位,有缝隙就钻,没任何结果。他想早知这样当初还不如不读书的好,用这一大把的时间,至少可以学会种地。在四处碰壁后,马法官还是被马大爷拉着去找了伍麻子。
那是一个傍晚时分,还有小半夕阳残留在墙壁。墙壁就像被柿子水浸泡,发出淡淡的橙红。伍麻子用一个木盆打了水在屋外水泥坪里洗脚。马大爷看到伍麻子脚晾在盆沿上,水珠子雨一样一颗一颗掉落,旁边凳子上搁着一块擦脚布。马大爷马上抓起擦脚布,说:“老伍,来,我给你擦一擦。”
看着马大爷把伍麻子的脚放到自己膝上,一点点擦拭,就像他在擦一件心爱的装饰品,生怕弄坏了似的,马法官真恨不得把那双脚给剁了,凭什么?有个县长儿子,就得把你当爷啊。马法官极力控制住自己想拉爷老子走的冲动。
伍麻子闭目享受,一边还说:“老马啊,你洗脚蛮在行啊,城里洗脚行里也没你手艺好啦。”
洗完脚,马大爷吩咐儿子,说:“法官宝,别站着发愣,去把洗脚水倒了呀。”
“嗳!”马法官听到父亲叫他,犹豫一下,缓过神来,走过去端起洗脚水。端在手里,他发现木盆就如一座山一般沉,一不小心,木盆竟挣脱掉落在地,滚到了墙角,水长了脚一样满地乱窜。
马大爷尴尬地站在一旁,脸一下苍白,狠骂儿子:“没出息的。”他担心出这样的娄子,恐怕是求门无望了。
为了他的事,让爷老子这么操心费力,自己却这样不争,马法官很难过。看到马法官难过的神情,马大爷比儿子更加急,但他经见的多,装着淡漠的样子说:“法官宝,你已努力了,怪只怪做爷的没本事,如果你是生在伍麻子家就不用着愁了。”
想起这些,马法官有些紧张地看着伍麻子,一边心里想着:“夜路走多了,总要碰到鬼,没想到今天就碰到了这家伙。”
尽管他不喜欢伍麻子,但伍麻子是要求的人,他也想像父亲一般装矮,顺着伍麻子,可临边做起来,却没想这么难,总感到别别扭扭的。
伍麻子起早床惯了,起来了就喜欢在村里村外溜,跑步,做运动。他运动起来手脚僵硬,一下就可看出他的病态。伍麻子意外遇到马法官,一怔,这小子出落得人模狗样,却是有些落魄,活该。
伍麻子四处瞅了瞅,也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便将信将疑走了。
马法官窃喜,巴不得他早走。
这次马法官是真的得了宝了。
马法官不经意在路边上发现三枚果子,果上生满毛茸茸的刺。他以为是金樱子,没在意。细一看,不是的,这果子和金樱子有些相像,但绝对不是金樱子,金樱子还没到结果的季节。不远处,有几棵矮小的金樱子树开满白花。那果子树孤单单,就生在毫不起眼的草地上,像一棵千年矮,永远长不大,长不高。它旁边全是一些高大的桃李树,桃李树上的叶子枯黄,没见到一个果子,或许是早过果子的季节。
昨天从这里路过没有发现这果子,隔一夜却让他碰到了,这不是天意么。马法官饶有兴致蹲在树边,仔细观察,想弄明白怎么突然凭空多出了这么一棵怪异的树。果子和树叶的颜色一样,绿茶色,就像灯笼草上挂着的三枚灯笼果。那树小小的,寄生在那里,几乎遭桃李树悉数覆盖,稍不留意,很容易让人忽略。马法官从没见过这果子,姑且就叫无名果得了。
蹲在那果树旁边,马法官的思绪拓展,非常阔大无沿。他放眼看天,天就在他的视域里,他的视域有多大,天也就多大。
他摘了一枚果子,在手里掂量着。面对这陌生的果物,他有些惧怕,但冥冥之中好像有神助似的,他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开始感觉有些涩,几秒钟后,微凉,遍体生津。他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出了一身微汗,竟感全身舒服极了。过去因为坐电脑多了,颈部肩周酸痛麻木的感觉尽失,神清气爽。
原来这果子有治病的功效,这不是仙果么,真真得了宝了。
马法官大喜。那果子遭他咬了一口,水汪汪的,齿痕隐没其间。既然是宝物,他生怕糟蹋了,剩下的不敢吃了,他用了卫生纸包好,接着又把另两个也悉数摘了包好,小心揣在怀里。
马法官是昨天从城里回来的,落屋时断黑了。他父亲马大爷坐在竹椅子里嗯啊呀呀,马法官把手里提的水果礼品丢在一边,赶紧跑过去,问:“爷老子,你这是怎么了?”
“没大碍,就是腰腿有点硬,年纪去了,不行了啰。”马大爷身边搁着一把锄头,锄头沾着新鲜的泥巴,泥巴里汪着水。看样式他刚从地里下来。
“爷老子啊,不知说过多少次啦,地里活多,干不了就别蛮干,你老人家只要帮我守着家就成了。”马法官说道。
马大爷没敢说,其实他是帮伍麻子挖土去了,伍麻子的土全挖完了,自家的地还没动。但他知道儿子不喜欢自己去讨好伍麻子,过分了。但是不讨好行吗?家里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去送礼,只能出卖这点不值钱的力气了。马大爷不说,其实马法官也知道,因为他回家的路上路过了自家的地,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村上能够让父亲这样卖力的只有伍麻子。
晚上睡觉时,马法官失眠了。虽是睡在惯常住的房间。但房间鲜于打扫,墙壁上粉刷的白石灰剥落得东一块西一片,透着没人居住的潮湿的霉味,闻着很难受,不太习惯了。父亲年老,腿脚不灵便,终日往返的就是厨房和睡房,别的与他日常生活起居联系不多的房间就极少光临了。马法官一踏进他昔日的房子里,森森的冷气就扑面而来,床上被子也像泡了水,一晚上也睡不暖和,粘粘的,怪不舒服。所以,他失眠了。他好奇怪,这是自己的家,过去一倒床就酣然入睡的地方,现在怎么会生出这样怪怪的感觉来呢。是不是在外面读书久了,过惯了声色犬马的城市生活,与家生分了啊。这想法一旦冒出来,马法官吓了一跳,就像小时候吃的坛子酸辣菜变质变味,这是太不应该了啊。家,就是根。外面城市闹热,与这僻壤蜗居的乡村比,虽是天地之别,但不是属于他的所有,往后像父亲一样年纪了,他终归是要落叶归根的。
父亲就他这一个儿子。他理应在身边尽孝,服侍他。可是,他那父亲读过几年书,明大体,说鸟长大了不飞,还叫鸟么。是男人就要活出男人的味,争个出息。马法官在外头一想起父亲的话,就浑身来劲,觉得眼前阳光匝地。这次他报考了县里政法系统公务员考试,弄了个前三名,就暗自有些高兴。他想把这一喜讯告知父亲,也让他乐一把。
马法官一夜失眠。本来就是来这田野的深处散步的,所以有些漫不经心。虽然此刻捡到了无名果,但欣喜过后,便又显得有些懒散了。冷淡的晨风在马法官耳边轻轻吹拂,如缱绻一起的女人呼吸,有点发痒。
昨天和父亲天上地下聊天至深夜,当然,马法官也说了自己考上了公务员的事,马大爷很欢喜,不过最后还是说道:“明天还是去伍麻子家一趟吧,如果县长能够说一句话,那事情就十拿九稳了!”当时马法官就表示了反对,但在父亲的劝说下,再联想到自己这些日子的遭遇,便也没有再坚持,只是提出先由父亲去和伍麻子说,如果有希望说动伍麻子,他再和父亲一起去。
开始泛白的天空上,星星闪烁。马法官依稀看到了父亲的身影。
他父亲马大爷鸡一打鸣,就睡不着,还有早起上茅厕的习惯。像里急后重一样,在茅厕里一蹲就是半个时辰。晨曦中,马法官看到父亲从茅厕里出来,手捧着肚子,脸烂成了一条苦瓜。痛苦折磨的形状,马法官感同身受。他慌忙把父亲扶躺在屋前草坪边的竹椅上。马大爷掏出随身携带的去痛片,宽儿子的心说:“老胃病了,无妨的,缓过一阵就好了。”
见到去痛片,马法官猛然记起那果子。父亲的老胃病,不定时发作,请遍郎中,久治不愈,已成痼疾,兴许也有效果。他把吃剩的那枚残果放进马大爷嘴里。那果子马大爷也没见过,怕是有毒果,闹人,他很犹豫。马法官用自己已经试验的效果说服马大爷。马大爷将信将疑嚼着,一点一点试着往肚里咽。
不一会儿,马大爷感到胃部轰隆一声,似有坚冰破裂。一股暖气从脚底往上蹿,直冲头顶,其劲厚实绵长,源源不绝。马大爷昏昏入睡。任由儿子千呼万唤,也没反应。马法官着急死了,万一是毒果呢,有害呢。但看着父亲脸色红润渐渐像天空一样明朗,便在一边守护,充满惶恐和期待。
看着父亲,马法官很内疚。父亲费尽艰辛将他拉扯大,并供养他上学。他自认为考上大学为祖宗争气,报效祖国,大展鸿图,没想却找不到工作。他摊开左手细细看着,看相的人说手掌中有一条事业线,马法官看到他的事业线一直通到指根,一无阻碍,他想说不定会有转机的。老师同学朋友,只要找得着的他就找,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说你认了吧,这是命,你没听说如今上海就有一些博士生毕业找不到事,去殡仪馆应聘么,何况大学生呢。
马法官这些思绪正蓬勃延伸的时候,马大爷打了个哈欠,从椅子上起来了,连声说:“仙果,真真的仙果。”马大爷不但胃病尽除,还面目精神饱满,人也见得年轻几岁。
“仙果,真真的仙果。”马法官也非常激动。
马大爷身体好了,动作也变利索了,随便对付了点早餐,便出了门。
伍麻子家在村北,水泥路修到了他家门口,还有专门的车库。跟村上其他地方鸡肠子似的黄土路和低矮的瓦屋相比,伍麻子家是三层楼仿佛地道的城市建筑,地板砖,墙壁砖,水泥吊灯像是不用电费一般亮通宵,那鲜亮简直就是一只鹤子立在鸡群里。还有,伍麻子抽的烟也不同,全是清一色的软盒芙蓉王,六十元一包,与马大爷抽的旱烟比,一包就够他抽一年。过去伍麻子也和马大爷一样抽旱烟,自从儿子当了县长,就改抽芙蓉王了,伍县长说家里烟多了,收久怕生霉,每次开车回家都要捎带一些烟洒。马大爷就想如果法官有这样的出息,该多好啊。他甚至想象着儿子马法官真的当上法官,别人求他办事,送烟送酒的滋味。他内心也并不是要和伍麻子攀比高低,只图儿子既然考上了,就应有个出息,努力也就没白忙,让盼头有个着落。如果儿子真的当了法官,他就要告诉他能帮人处且帮人,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
马大爷走进伍麻子家,伍麻子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逗猫。他把一个彩球不停地抛,那猫就不停地蹿跳,接球。猫用力过猛,收不住势,身子滑了好长一段,把球撞飞直往门口的马大爷而来。马大爷一伸手抓着球,把玩着。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凭马大爷僵硬的身手,怎么轻易就捉到球呢。伍麻子仿佛看到从西边出来的太阳,打量他在马大爷身上的发现。
伍麻子一身的养身病。先是犯哮喘,他害怕,遍寻郎中,打针吃药,无论西药中药都是一大包扛回家。反正有县长儿子做后盾,买药几乎没用过钱,只要去过他家的人,都知道他,他扛回家的药几乎可以开个药铺了。梅山县内稍有名气的郎中,都认得伍麻子。尽管他这么积极寻医问药,病却一点起色也没,好像病入膏肓,难起沉疴。他读过三句半书,就自己找来一些医书,看,钻研自己病情,自己给自己开处方,西药英文不会认,他就开中药单子,君臣佐使,相生相克,他讲起来条条是道,连那些医生也不得不佩服他,说久病成良医,伍麻子算半个郎中了啊。伍麻子以为是医生表扬他灵性,愈加起劲。结果,由于药吃多吃杂,没对路,损坏了肝功能,搞成肝腹水。
马大爷就曾多次劝说:老伍,郎中不可自诊,你别把自己当郎中搞啊,没好处的。伍麻子却不承认是乱投药的错,回道:马老弟,你也是读过书的人,你那书啊,算是白读了。每当这个时候,马大爷就不自在,自己白读那是事实,没错,如果儿子白读那就比要了他命还难堪。众所周知,村里就两个大学生,伍县长的大学是推荐的,他儿子马法官却是凭自己本事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啊。这可是他马大爷一生的骄傲。
伍麻子奇怪地问道:“老马,你在哪搞到了灵丹妙药?”
“还真让你猜着啦。”马大爷把他儿子马法官不经意拾到无名果的事添油加醋吹了一通。伍麻子将信将疑,这么久的陈年痼疾,说好就好了?但他看马大爷气色,的确又像没病,加上马大爷病愈后矫健的身手,也由不得他不相信。
伍麻子拿出一盒芙蓉王,塞到马大爷手里,说:“好抽着呢,不冲。”
“不了,我还是抽我自己的旱烟更习惯。”马大爷不接。他抽旱烟惯了,不想换,再说即便芙蓉王好抽,不冲,万一抽上瘾了,不再想抽旱烟,怎么办呢,每天芙蓉王,他是绝对消受不起的,会折阳寿。
伍麻子想了想,觉得说得也是在理,便没有硬塞,一屁股坐回沙发上,顺手抽出一根点着了,然后说道:“说吧!有什么事情?”
伍麻子没有喊坐下,马大爷也不敢坐下,便站着说道:“是啊,我那儿子马法官,读书还争气,就愁没个正式单位,现在考上公务员,想烦请你老帮忙。”
“行,我会和我们家县长说的。”这次,没想伍麻子竟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
好事连连,看来马法官好运气来啦。马大爷心情愈加愉悦。
伍麻子的声音又马上响起来,道:“你要法官带上无名果来找我,让我也见识下无名果,看有没有你说的那么神奇?”
得到伍麻子的承诺,马大爷脚步就像突然卸掉重负似的轻快,很快便把马法官和无名果一起带了过来。
见到伍麻子,马大爷恭恭敬敬递上无名果。伍麻子接了后仔细研究了一会儿,便把它放在桌角上,然后转过头对马大爷说道:“老马啊,你崽蛮精神呢。”
“托您老人家福,现在我家法官宝公务员考试,得了个第三名,请你帮忙。”马大爷说话打底边去。照马大爷想,过去马法官大学毕业安排工作难度大,现在考取了公务员,名正言顺,这个忙应是没问题了。
马大爷和伍麻子套近乎的同时,马法官站在房子里却浑身不自在,满脸堆着假笑,烦恼就像一只瓢虫在全身各个器官爬来爬去。一条五公分长的百足蜈蚣在墙根下追赶一只瓢虫。蜈蚣跑起来像飞一样,逮着瓢虫一下就钻入了地穴里。
“伍伯爷,这次可真得麻烦你老人家啦,侄子的前途都是你老的一句话了,往后我会好好报答你老人家的啊。”马法官说。
在来伍麻子家路上,马大爷就嘱咐了:“法官宝呀,现在我们是去求人家,要把自己放低下啊,你那高华的样子谁看了也反感的啊。”
“嗯,会的。”马法官嘴里满口答应,心上却想,现在我有了无名果,加上我考试也过了,只是为了稳妥起见,才去找他,却未必全是我去求他伍麻子,伍麻子不就是有个县长儿子么,至少也算交换啊,各取所需。我又没要他白帮。所以,马法官心安理得,想要挺起脊梁站起来,但一到伍麻子家里,看到父亲低头哈腰向伍麻子恳求的样子,这脊梁怎么也挺不来了,只觉得浑身发痒,手脚都不知道如何摆放。
“你崽读书是发了狠,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好事,后生可畏啊,不过这个名字稍微有点问题啊。”伍麻子取出一支芙蓉王装在嘴上,点燃,长长地吐出一个烟圈后,慢慢地说道。
“名字有问题?”马大爷小心说,像做错事的小孩。
“当然,马法官,八字都没一撇,崽没生就预先取了这个名字,一听就让人好生反感。”伍麻子依然是慢慢的语调。
“你想啊!假如你在法院,你还不是真正的法官,但别人一喊你名字就是法官,很容易引起误会的。”顿了顿,伍麻子又说道:“人家真正的法官会怎么想呢?”
“啊哟,原来这样,”马大爷顿悟到了问题的严重,慌忙说:“老伍,您说怎么办呢?”
“改个名字吧。”伍麻子说。
“这个……这个……”马大爷喃喃说不出话来。
马大爷还想说什么,马法官拖着父亲走出了伍麻子家门。边走马大爷边不情愿说:“崽啊,改吧。”
“不改,偏不改。”马法官愤愤说。“这管名字什么事,他那是在装蒜。”
“不改,你就白考了啊。”马大爷忧虑。这个时候,大家都伸长手,竞争这么激烈,会轮到你么?
“这是公务员考试,是很严肃的,相信没问题。”马法官安慰父亲。他心里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本来过来找伍麻子就是想要多加一道保险而已。公务员考试就是过三关,分数没问题,就只剩体检和政审,他自信这三关都是没问题的,一个月前他就做了一次全身体格检查,一切正常,至于政审,祖宗三代无任何历史遗留问题。
听儿子这么底气十足,马大爷就不再坚持,他也觉得改名字,做人未免做得太矮了,太没骨头了。但他脸上皱纹挤得更紧了。其时,伍麻子正在砌一条围墙,他说喜欢安静,村里的鸡狗畜生时常打扰,搞得心里烦躁,他想砌起围墙把它们一律挡在外面。听说伍麻子要砌围墙,村里去帮工的人多了。马大爷想目前有事求着伍麻子,别人都去了,自己不去怕不好意思吧。他交代儿子:“法官宝,你照管好鸡养生阿。”
“人家又没叫你,你趁热闹啊。”马法官正在看书,头也没抬说。每天没事他闲着就看书消遣,他总想着他的读书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蠢宝啊,人家没叫才更要去啊。”马大爷边说边带上工具走了。
不料,到了中午,就有村人来喊马法官:“快去啊,马大爷出事了,这样一把年纪搞成那样,何得了啊。”马法官一听,放下书,朝伍麻子家一路飞奔。
天远,马法官就看到伍麻子家附近的一堵断墙边围着一堆子人。他们见马法官来了,纷纷让开一条路。马大爷脸部手脚到处是血,口里却说:“没事的,没事的。”
原来是伍麻子请的泥工图省事,基脚没打稳就砌围墙,结果垮塌压着了正在搅泥浆的马大爷,待马大爷发现征兆,已迟,砖瓦一骨碌滚下来,腿骨折了。马法官记起无名果,悉数交给了伍麻子,既然给了人家,现在怎么好意思去要回来呢。马法官想也不想,背上爹往医院飞跑。一路边跑边问:“爷老子,你疼不?”
“不疼!”
“爷老子,你疼不?”马法官反复问,他生怕爹睡着了。
“不疼!”
马大爷住了几天院,花掉了几千元医药费,留下了一身的伤痕。马法官说:“爹,你是给伍麻子帮工才受的伤,这医药费他会报的吧。”
“你好意思说么,人家又没邀你。”
马法官就不做声了。
月底,公务员录取结果公布,马法官体检不合格,说是乙肝。听到这消息,马法官百思不得其解,恍惚全身憋起的劲力一下就泄了个精光,全身都软了。马法官觉得天旋转起来,眼睁睁看到一些不明方向的东西纷纷往他逼近,他伸出双手不知朝哪抵挡,就像一个一败涂地的士兵。
马大爷心疼地看着儿子,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跟我重新学种地吧,没看我种一生的地,不也过来了。”
还能怎么样呢,马法官就跟父亲一同下地,干活马法官力气十足,可不得法,干着干着,想起自己命运,就憋闷得慌,他禁不住一屁股蹲在地上。他想砍人,但又找不到对象,剁伍麻子么,伍麻子只是不帮他,似乎够不着那一步。他形状不安,马法官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植物,突然遭遇打击,一日一日枯萎。他感到再也找不到茁壮起来的出路。他后悔不该把他的宝物无名果由父亲送给了伍麻子,如今事也没办成,白白丢失了无名果,如果无名果还在,他是可以用来去找人做交换的啊,不信拥有这么神奇的宝物,满世界会找不到一个交换的人。想起就心疼,就懊悔,他口里不时叫道:“无名果,无名果。”
明知儿子要出事了,马大爷却想不到办法解救,无助地着急。
……
阳光暖人,伍麻子在村街上慢悠悠溜达。马法官不知从哪个转角突然蹦了出来,把嘴巴碰到伍麻子耳朵边,神秘兮兮说:“你吃无名果么,治百病成仙的啊。”
“去!”“去!”伍麻子推开他。
伍麻子看着他那傻样,有些发笑。他讨厌马法官。这小子一看就知不是做法官的料,生下来时,他父亲却做梦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荒唐名字,仿佛特地跟他家较劲。伍麻子听到村人都叫他“法官,法官”,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儿子是名副其实的县长,是这方圆数十里惟一出的一个县长,这样一来,以假乱真,岂不是把他的儿子县长叫矮了?不知情的外人听起来,仿佛县长也是掺了水分样的。
伍麻子可不允许随便诋毁他。十成的黄金兑一成假就掉色了。
伍麻子和村上人说,法官宝读书读猛了。
村庄上,到处是忙活的乡里乡亲,马法官袋子鼓鼓的,见到他们就伸出手,送出去的样子,说:“吃果子,吃果子啊,治病的神药呢。有病治病,无病养身。”他那模样,好像他真的拥有许多无名果,很大方。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