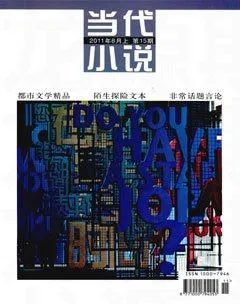出发
二零一零年农历腊月二十八的深夜,在逐渐强烈起来的新年爆竹声中,我合上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是我在习惯性的阅读中几乎很难遇到的一种感觉。这本大师之作像一盏明灯,突然照亮了我走过的路。我曾经的写作轨迹像是一条曲折的线,清晰而沉重地呈现出来。
在我十六岁决定终生走文学之路时,几乎所有的小说写作者,正沉浸在对西方文学的崇拜中,目之所及的小说无不带着西方作品的影子。字里行间,显示出的是作者在阅读西方作品时的激动情绪,而与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
我知道这样的模仿绝对不是我的方向,我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作家应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只有具备这种能力,才有与人对话的资格。只有平等地对话,才能更好地学习。“学习”时没有平等,便是膜拜。一个人,跪下,很难再站起来。
然后,我为了能够与心中的大师对话,开始积蓄属于自己的资本。
我从来都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长期阅读,阶段性拼命写作,并没有使我的创作进入到一个理想状态。焦虑像感冒一样,隔三差五便会罩在我的身上。
直到遇见《中国哲学简史》,我才知道这些年来做了一些什么。当明白曾经做过什么时,自然就知道以后怎么做。
马尔克斯说:作家,就是比常人写得好。
这一简单的说法,是对作家的最高要求。写作是一门职业,应该用职业的态度对待它。所谓职业,就像一个司机把车开好,像一个厨师把菜炒好,像一个篾匠把筐编好。任何一门看似简单的职业都不简单,有其内在规律需要掌握。司机只有很好地掌握了刹车技巧,才能把速度提高到理想的程度。厨师只有掌握了恰当的火候,才能炒出可口的菜。写作更是如此。
写作其实就是两条:一是不能怎么写,再就是还能怎么写。当对自己的写作不清楚时,往往总写些不能写的,总写别人已经写过的。因为觉得“不能写的”才新鲜,“别人写过的”才是成功的。
用普通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并不说明容易做到。普通的语言、普通的事物,简单的寒暄,曾经是极力回避的。因为普通,觉得它们缺少自己想要的力量。而小说的力量,并不是由于味同嚼蜡、看似深刻的语言。
小说的张力,来自于省略部分。正如一个雕塑大师完成一个作品,着手之前,已经清楚地知道雕出来的是什么,接下来要做的,只是剔除多余的部分。所有艺术品,都来自于对多余物的有效剔除。
写作,绝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表达,它是一种交流方式。宣泄式的写作,如同洪水泛滥,是一种灾难。只有将写作纳入理性河道,才会拥有清晰而有效的流向。正如只有将洪水合理地疏导开,才能用于发电或浇灌一样。写作,仅是给人提供一种视角,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一视角可以对别人有所改变。有时候,正因为视角的单纯或残缺,恰恰可以留给他人更大的空间。
“乞力马扎罗,海拔19710英尺,山顶终年积雪,据说为非洲最高峰。马萨伊人称西峰为‘鄂阿奇——鄂阿奇’,意为上帝的居所。西峰附近,有一具风干冻僵的豹的尸体。这只豹究竟在如此高的地方寻找什么,没有人知道。”
这是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开头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用另一种字体,表示与其他文字的不同。显示着海明威的别有用心。那只豹究竟在找什么?海明威说“没有人知道”。我相信,海明威一定知道。任何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疑问或不解时,他自己早已有了答案。那些明明知道而不说出来的部分,恰恰成为作家写作的根本动力。
我终于找到了进入所期望的那种状态的方式。用得时间不算短,显得特别可悲、可怜,但绝不可耻。我确信自己的“曲折”是值得的。如同一个在山中苦苦寻找石灰石的人,却捡到了一堆宝石。这笔意外的财富,给了我另一种感觉,另一种头脑。我会愈来愈接近并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状态。那种状态不是揪着自己的头发妄想飞离地面,而是“上帝握着你的手”。
现在,我可以对自己下达一道命令,一道早就渴望发出的命令:出发!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