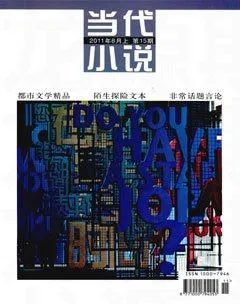流浪者
这个叫黄果树的男人之所以对我产生仇恨,因为一个叫苏烟的女人。他说苏烟是他妻子。一年前,苏烟被残忍地杀害了,娇美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块块碎肉,扔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这桩案件当时相当轰动。三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进行了深入报道,再加上形色各异的嘴巴添油加醋地描述,使本来安静、温馨的街道到处充满了血腥味道。恐怖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通过鼻子,浸透了女人们脆弱敏感的心。天一黑,稍微年轻一点的女人便不敢在街上走动。整个城市虽然灯火依旧,因为缺少了女人的身影,显得干巴巴单调了许多。那段时间,真是苦了我们这些在娱乐厅门口“趴活儿”的夜班出租车。收入直线下降不说,还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因为从娱乐厅走出来的男人们,脾气突然坏了起来。
黄果树认为苏烟的死跟我有关。而我并不认识她。当黄果树像影子一样飘进我的车里,冷着面孔说要干掉我时,我一时竟不知如何辩解。他将一个旅行包揽在怀里,尖利的目光直视着车窗外冷清的街道,一只小巧的流浪狗,正夹着尾巴、瘸着后腿,步履缓慢地穿过马路。他的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像是在嘲笑那只无家可归的狗。
他又平静地说: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
我当然不认为他是开玩笑。如果他拿着凶器穷凶极恶,我会适时握紧座椅左侧暗藏的改锥,在他扑过来的刹那间,准确地刺进他的胸膛。可他自从坐进车里一直很平静,双手很随意地揽着旅行包。说话的口气轻描淡写,好像在转达别人委托的一个口信。将明确的杀戮掩藏在平静的面目之下,传达给我的只能是无所适从的恐惧。我的左手轻轻动了一下,并不是去找改锥,而是准备开门而逃。
他朝我转过脸来:你要跑吗?说着,笑了。瘦削的脸庞右半边沾着昏黄的路灯光亮,左半张脸则涂满了黑暗,使他的笑看起来愈发怪异狰狞。我的手停在了门把手上。他盯着我微微颤抖的左手,说:别害怕,我今天不会杀你,只是通知你一下,如果你死了并不知道是我杀的,事情并不能算是真正了结。
这种说法让我略感欣慰。因为我坚信,只要他下了车,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
他见我的神情稍有松弛,满意地一笑。接着,换上一副略带羡慕的口气:你应该比其他死人感到荣幸,别人都是糊里糊涂死去,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死法。说着,他的右手轻轻拉开了旅行包,掏出一把明亮的匕首,匕首反射出一道光亮,划过他的脸庞,他微微眯起眼睛,问:喜欢被捅死吗?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他说:你很聪明,被捅死,这种死法看似简单明了,其实死者相当被动,完全取决于匕首使用者的腕力和准度,如果握匕首的人技艺稍差一点,不能一刀致命,那死者难免要挨第二刀第三刀及至第四刀,四刀啊,想一想便惨不忍睹。
他将匕首放进旅行包,又摸出一个小巧的玻璃瓶子,他拿着瓶子在我眼前晃了晃,若干银色的颗粒欢快地跳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我不由问:这是什么?他说:药,喜欢被毒死吗?
他的旅行包好像是个百宝箱,里面的内容层出不穷。他让我看了无数件准备应用到我身上的凶器。有长达二十公分的钢钉,可以钉进我的头顶,在一滴血都不流的情况下安然归西。有细软的绳子,可以勒住我的脖子,致命而又不损伤我脖子上的皮肤。有样子很夸张的锤子,可以击打我的太阳穴,这种死法最为容易,只是感到一种轻微的晕眩,再无其他痛苦。他居然还掏出了一颗美式手榴弹,效果当然不用再解释了。
每掏出一件凶器,他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所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都是我的摇头。随着凶器的不断变化,我的头摇得愈来愈厉害。脑袋几乎成了一个澥了黄的鸡蛋,我清楚地听到了脑浆与头骨的碰撞声,浑浊而沉闷。
直到一辆警车缓缓开过来,我才骤然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报警器就装在方向盘下方一个隐蔽位置,只要我的手轻轻一摁,便会有110巡警根据我的方位及时赶来,我却坐在这里跟一个准备杀死我的人探讨自己的死法。
警车并没有拉响警笛,只是车顶上的警灯在旋转着闪亮。它离我的车愈来愈近,警灯的红光闪烁进我的车里,一下一下扫描着黄果树瘦削的面庞。他没有慌张,像个到达目的地准备下车的普通乘客一样神色坦荡。我的左手食指已经放在了报警器上,准备招呼警察将他带走,单凭他旅行包里那些物件,足以让他解释不清。正在我将要按下报警按钮的时候,他轻轻拉上了旅行包的拉链,说:既然你不能确定自己喜欢的死法,那就由我帮你决定吧。说完,打开车门下了车。我如释重负。可他并不急于离去,像是将东西忘到了车上,又打开了车门,躬身将脑袋探进车里,说:我要杀你并不是为了给苏烟报仇,而是你葬送了我杀死她的机会。
我喜欢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城市。十八岁那年,因为难与人言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家乡,踏上了流浪之途。我不同于那些留着长发、长着络腮胡子的背包客。他们那所谓的流浪,其实是旅游,是对在城市呆腻了而又没办法离开的人吹嘘的一种资本。对于真正的流浪者,流浪是一种宿命,是无法逃避的一种生活,我们最大的渴望是稳定。十三年来,我在十五个城市生活过。每到一个城市,都力争将其当成永久居住地。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总有不期待的麻烦找上身来,迫使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离开。
刚到这个城市时,我已经不敢再有永久居住的奢望,随时准备奔向第十六个城市。没想到因为一份职业,居然住了下来。我从一个出租车主手上租到了一辆车,他跑白班,我跑夜班,每天给他六十块钱。这份幸运的工作,给了我前所未有的稳定感。眼看手里的钱逐渐增多,开始有了在这儿娶妻、生子等等更为长远的人生计划。
我喜欢这个城市,更喜欢这个城市的夜晚。
此时正是子夜,黑暗征服了一切,全城大都进入了睡眠状态,到处都是死寂一片,连“后宫”夜总会门口炫目的彩灯也暗淡了许多。我之所以在这里等活儿,因为从里面出来的人个个出手大方,上车时的情绪往往还沉浸在奢华的消费里,在他们看来,我所收取的那点出租车费跟无偿服务差不多。
我半躺在靠背上,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透过车窗看着夜总会门口那些遮挡了车牌的高档轿车,猜测着车主的身份,试图发现一两个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名人。渐渐地,眼睛有些酸涩,正要收回目光,忽然发现从“后宫”的侧门出来一个人。一个女人。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台阶,猛跑了几步,又疾速低下身去,再站起身,长发飘舞着从昏睡的车群里穿插过来。当一团香气涌进我的车子时,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大了好几倍。不是因为香水的浓烈骤然制约了我的呼吸,而是她居然没穿衣服。她坐进车里,匆忙地命令:快!开车。
说她没穿衣服,当然是我的错觉。只是穿得太少,仅仅勉强包住了女人的隐私部位,全身百分之九十的皮肤都裸露着,一大团肉色让我的心和眼都变得恍惚起来。她两手各拎着一只鲜艳的红色高跟鞋,像握着两把怪异的武器。车启动之后,她不时回头看一下,似乎随时准备应用她的武器。我透过后视镜看到有两束灯光远远地尾随着。她催促道:快点开,我给你双倍的车费。
我心领神会,同时心底涌上一股莫名的兴奋,麻利地变换着挡位,将车开得飞快。原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没想到后面那个司机太菜,我在铁路医院旁边随便钻了条胡同,后面的车灯便消失了,我有点失落,怀疑后面的那辆车到底是不是追我的。她往后仔细地瞅了一会儿,长出了一口气,躬身将鞋穿好,双手当梳理了理蓬松的长发。她身体的每一点动作,都将车内的香气搅得翻江倒海。她偷偷瞟了我一眼,下意识地往上揪了揪胸衣,又欠身抻了抻短裙下角,力争使肉体暴露得少一些。
我适应了香气和肉色之后,才想起问她去哪里。她愣了一下,好像一时也想不起去哪儿。我将车速放慢,打开右转向灯,准备随时靠边停车。她没有下车的意思,舒展着身子,将右腿盘到了左腿上,选择了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问:能借我一根烟吗?我将烟递给她,她接过去,先将车窗摇下,点上烟,深吸了一口,将烟缓缓吐到窗外,看着被风吹散的淡淡烟雾,说:去高新区。
高新区是出租车最喜欢去的地方。距离远,几乎相当于另外一个城市;马路宽阔得像广场,平滑得像镜子,红绿灯少得可怜,是出租车司机很能放开手脚的一段路途。看着计价器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我的心情颇为愉悦。一路上,与她攀谈的念头冒了又冒。我三十一岁,尚无女友,全身每个细胞都洋溢着与女人沟通的欲望。她却将头枕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蓬松的长发堆满了肩头,遮住了她的脸。
车快到高新区时,我叫了她一声。其实我非常希望一直开下去,她散发着香气,坐在我旁边,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才好。她似乎是睡着了,对我的话没有回应。我用右手轻轻推了她一下。手指一接触她的皮肤,好像摸到了电线,半边身子都麻酥酥的。她睁开眼睛,坐直了身子,像灵猫搜寻食物似的朝车外看。高新区里虽然高楼林立,却到处都透着一股人气不足的苍凉。她朝前一指:前边路口往左拐。
在她指示下,我将车停在“山南水北”的一座别墅前。这是一座欧式三层别墅,庞大得像个城堡,不是一般人能住得起。她对这个别墅区相当熟悉,进门时,面对着问询的值班保安,她竟然叫他小李。这座别墅肯定不是她的家,因为她脸上丝毫没有到家的从容与欣然。她并不急于下车,而是拿出手机打电话。我很诧异,她的手机刚才放哪儿了?电话打通了,手机里回荡着一曲悦耳的民族音乐,同时,别墅里也响起了电话铃声,在子夜的天空下,铃声显得尤其响亮。这显然是一座无人居住的别墅,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无人接听。她不死心,下车围着别墅转了两圈,白亮的身体时而被绿树遮住,时而暴露在昏暗的灯光中。她在不同的角度驻足,仰头审视着别墅黑暗的窗口。重新上车时,她缩着身子,紧抱着肩膀。初夏的夜晚,还有着很深的凉意。
她跟我要了一根烟,点上,又拨了一个号码,手机里的回应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她吸烟的力度大了起来,烟头的红光深深地红了两次,一根香烟便化成了灰烬。她将烟蒂弹出窗外,冲我一伸手,命令道:把你的手机拿来。尽管我不喜欢她的口气,但内心却不自觉地承认了她颐指气使的权利。我乖乖地将手机交到她手上。她用我的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依然是无法接通。她丧气地将手机扔给我,说:往回开。
我倒车时,发现她将自己的手机插进了深深的乳沟里。
回城的路上,她一直大瞪着眼睛迷茫地看着前方,似乎沉浸在一场梦幻里。到了外环路,我问她再去哪儿。她扭头看我一眼,问:你会打你深爱的女人吗?这个问题有点突然,我想了想,说:绝对不会。她又问:你会骗一个深爱你的女人吗?我说:为什么要骗呢?她说:你是个好男人。我轻轻一笑,并不敢承认自己是好男人。至于会不会打女人,会不会骗女人,只有实际经历才能证明。
她让我将车拐进了一个开放式高档公寓区,在三号楼四单元前停下。不锈钢防盗门在夜色中显得锃亮。她敏捷地下了车,左右看了看,那神情好像一只探路的牝鹿。她步履轻快地走到单元门前,按响了对讲门铃。我的心提了起来,深怕她再次失望。她将身子靠在不锈钢门上,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神态疲软地又上了车,蔫蔫地说:送我去柳家沟吧。
柳家沟是个城中村,全是破旧的民房,它好像这个城市心口上的一块烂疮,龌龊而醒目。等待拆迁的村民们,随心所欲地改造、扩展自己的房屋,将村中的马路蚕食得狭窄扭曲,像一节节猪大肠。一靠近村子,扑面一股臭气。天渐渐亮了,有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拖着疲惫身子,踮着脚,谨慎地走在脏水横流的街道上。
我的车行驶到“猪大肠”中段,一堆沙子挡住了去路。我将车停下,拉好手刹,说:就在这儿下吧。她问:多少钱?我指了指计价器,上面显示232元。她说:那我应该给你464元。我笑道:不用那么多。她说:那怎么行,怎么说的就怎么办。我说:谢谢了。她忽然惊呼道:唉呀,我身上没钱呀。我看着她半裸的身体,还真没有放钱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一个不缺钱的女人,一点也不急,拿过烟,递给她一根,她没要。我自己点上,等着她想办法。她说:要不你跟我回家吧。说着,指了指“猪大肠”末端一座楼房。那座房子底座很小,愈往上愈粗,像座倒置的宝塔,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我说:你去拿吧,我在这儿等着。她忽然有些忸怩,说:其实家里也没钱。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那怎么办?她脸上忽然带出一股凛然:我可以陪你睡觉。
我脑袋一晕。我确实很想跟女人睡上一觉,无论漂亮与否。我确实对她的肉体有着很深的好感,手指头一碰上都麻酥酥的。可转了半夜,如今再看她,忽然有种上当受骗的恶感。她见我没表态,以为我心里在进行微妙的斗争,继续说服道:我出一次台是八百,今天是你赚了。说着,用胳膊蹭了我一下。我缩了一下身子。赤裸裸的肉体交易,我这是头一次碰上,没想到这么不舒服。她的身子又靠了过来,我将身子缩得紧挨着车门:别这样,我对你没兴趣。她身子在空中一僵,随即冷笑:你说这样的谎话就不脸红吗?我愣了愣,我脸红什么?她一笑:今天我如果实在没钱怎么办?我果断地说:报警。她一听,笑了起来,捂着嘴,笑得在座位上扭动着身子,整辆车都在发颤,胸衣坠了下去,手机伴着肥乳裸了出来。我懵懵懂懂,报警有这么好笑吗?
她好不容易忍住了笑,整顿了一下表情,说:我先给你打个欠条吧。说着,不待我同意,便打开了储物盒,自顾在里面翻了起来。她找出一支圆珠笔,又从计价器上撕下发票,铺在车窗玻璃上,在发票背面写道:今欠到464元,欠款人红梅。她的字相当难看,像是火柴棍搭出来的。写完,她拿起来端详了一下,好像觉得不够郑重,将右手食指探到嘴唇上,狠狠蹭了几下,然后重重地按在自己名字上。她将欠条递给我:拿好,我一定会还的。我看着欠条上模糊的指纹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打开车门,一只脚探了出去,回身冲我一笑:如果你报警,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她嘴上的红色有些凌乱,好像被打出了血。
黄果树的出现,让我陷入难以自拔的回忆,力图在曾经坐过我车的年轻女人中,找出苏烟的影子。首先想到那个半裸的女人,并不是觉得她是苏烟,而是留给我的那张欠条。当时我看着她步履蹒跚地迈过沙堆,拐进一条胡同之后,才意识到这张欠条跟废纸差不多。她如果不还,我根本找不到她,她如果想还,也很难找到我,那个模糊的指纹印,简直是留给我的莫大讽刺。之所以没有撕掉欠条,因为我想到了那座欧式别墅。只要别墅跑不了,就一定能找到她。
真没想到她是个说话算数的女人,还没轮到我登门拜访那座别墅,当天夜里,她便委托一个保安将五百块钱给了我。钱是崭新的,连一点折痕都没有,每张钱上都醒目地写着两个字:谢谢。字很难看,像是小孩用火柴棍搭出来的。她没有收回欠条,不知是不是忘了,欠条至今还在我手上,总想归还,可我再也没有遇上她。
当时我挺惊讶,她怎么能找到我?
保安一笑:你不是有车牌号吗?
是啊,车牌号。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渺小,就像游在浑水里的泥鳅,随便一钻,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想到也会到处遗留独属于自己的信息。顺着车牌号,谁都能准确地找到我。
为了躲避黄果树的袭击,我换租了一辆车,由夜班换成了白班,虽然每天忍受着堵车的煎熬,但看着滚滚人潮,感到安全了许多。每天我自己都不确定将车开向何处,他更不容易知道我的位置,即使偶然遇上,他也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冲上来捅我。
我在记忆深处不断挖掘,寻找自己与苏烟的关系,除了那个半裸的女人给我留下了鲜明印象,其他乘客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苏烟也许就隐藏在模糊不清里。
杀死苏烟的那个人,刀法相当精湛,肢解她时相当冷静,有着足够的耐心。将零碎人肉到处抛撒的做法,颇有创意,甚至还带有跟警察开玩笑的乐趣。那不同地点发现的不同部位的人肉,很容易被当成多起凶杀案。聪明的警察没有被误导。他们将居民上交的黑色垃圾袋保存在冰柜里,当收到第八十二个垃圾袋时,苏烟被拼了出来,身高、血型、职业等等信息,都像白纸上的黑字一样清晰了。
一个月后,凶手被逮住了,是她丈夫。
想到这里,我不由毛骨悚然。黄果树即使没被执行死刑,目前也应该呆在监狱里,怎么会背着装满凶器的旅行包找上我呢?
我决定离开这个城市。尽管黄果树还没有找上我,但已经有了非常不利于我的信息。我原来承租的那辆车,在一天凌晨莫名其妙地自燃了。我的继任者,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刚刚来到这城市,对道路都还不熟,选择晚班,是因为晚班的租费便宜。他在匆匆赶往火车站的途中,车头忽然冒出了火苗,停下车,却发现无法打开车门。他是用那把大号改锥捣碎了玻璃爬出来的。让我更为不安的是,经过查明,车不是自燃,纯系人为。有人在机箱盖下偷偷安放了轻型爆炸装置。警方已介入调查。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火车站,夕阳将我的影子投射在嘈杂的车站广场上,任由别人践踏着。我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只知道买最早的一班车票。
我是最后一个检票上车的人。
进了车厢,还没找到座位,列车便缓缓启动了。眼看着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城市被甩在身后,骤然轻松的同时,还有种怅然若失。
列车终于进入了我所熟悉的节奏。乘客的情绪都现出难得的轻松。要去的地方还没到,刚刚离开的地方,一时想回也回不了。想前想后都没用,干脆什么都不想,甘心享受着眼前。有人拿出了各类零食,有人开始玩手机,有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更多的人在南腔北调相互攀谈,说的都是自己的事,那口气又似乎是说与己无关的事。车窗外匆匆闪过绿树和庄稼、城镇和农村。我被车厢里的特有气氛感染了,出租车、半裸女人、黄果树和他的旅行包,都好像是前生的一场梦。
我身旁是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正在电脑上看电视,一档法制节目。画面上一个剃光头、穿黄马甲的犯人正在监狱里接受记者采访。犯人的气色很好,根本不像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光洁的皮肤,微胖的身躯,儒雅的谈吐,说明他入狱前是个相当优裕的上层人物,即使面对着记者,也是一副高高在上,回答问题时,都不屑于用普通话,那口音恰恰是我刚离开的城市所独有的。我不由朝前凑了凑身子。
犯人栾中华,入狱前是肉食集团的董事长。十七岁进入肉食公司,在门店当营业员,身上拥有上进青年的所有品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刀法精湛,只要顾客报出所要的数量,一刀下去,上下差不了几钱,人送外号栾一刀。他所在的门店,每天排着长龙,许多人都是慕名来见识一下他的刀法。他入狱的原因是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而记者之所以采访,却是因为那桩碎尸案。
我的头皮一麻。
他入狱后,主动坦白了杀死苏烟的过程,给司法机关带来了意外收获,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尴尬。他的坦白也正是记者关注的焦点。
记者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慵懒地将戴着手铐的大手拢在腹部,平静地说:我太爱她,内心不允许让人将她的死因跟别人联系起来。
年轻的记者挺懵懂:既然爱她,为什么要杀她?并且还用那么残忍的手段。
他说:正因为太爱她,所以只能杀死她。
年轻的记者被绕得有点晕,她紧抿着嘴,低头看了看手上的本子,故作深沉地说:你这想法很难被常人所理解。
他轻轻一笑:不需要理解,我现在只想跟她尽快见面,在另一个世界。
对话还在继续,我已经听不下去了,脑子里盘活了苏烟死亡的全部情节。发现自己只是偶然被搅进来的一个小角色。黄果树像一匹受了伤的野狼,正在将整个生命投入到一场没有尽头的报复之中,即使杀了我,对他来讲也仅是刚开始。我很庆幸及时离开了那个城市,就如一只蚂蚁,往往能更早地感受到灾难的信息。
太阳将要落山,像一只装满鲜血的气球悬挂在西天,大酡红色染透了一切,每个人脸上都布满了红光。我在一片血色中,仰在靠背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车厢内的喧哗忽然离身而去,只听到车轮碾轧铁轨的轰隆声,我默默等待着所喜欢的夜晚来临。
睡梦中,又见到了故乡那片碧绿的湖水,湖心小岛茂密的芦苇丛中,是不是又有了野鸭蛋?年少的我,将自己脱得赤条条,正要欢快地跳下水去。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您旁边有人吗?
我睁开眼睛,只见黄果树背着青色旅行包站在我面前,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不待我说话,他便紧贴着我坐了下来。我毛骨悚然,正不知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幸好看到一个警察从车厢的一头走了过来,他后面跟着两个乘务员,嚷道:查票了。
乘务员先看了黄果树的车票,然后看我的。我从裤兜里掏出车票递过去,同时计划着,查过票后,跟随他们离开这节车厢,再找机会下车。乘务员看过车票,正要递给我,忽然我的车票像一个小本子一样打开了,车票底下还贴着一张纸,纸里夹着五张崭新的钞票。乘务员好奇地展开看了一下,回身叫警察。警察走过来,接过那张粘了口红印的欠条,原本模糊的红印此时显得特别鲜亮,钞票上的“谢谢”骨感地突出。他意味深长地问:怎么回事?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