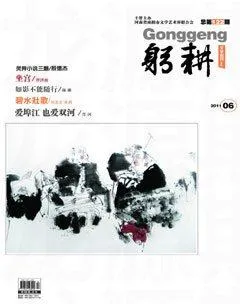在历史的余温中寻找与重现
把过去当作一个实际的存在,当作一个处所来看待,而那些被遗忘的回忆则留存在这个地方,重忆也是从这个处所把它们挖掘出来。
——保罗·利科《过去之谜》
历史真实地存在在时间与空间之中,在时空的流域之外,其存在是客观真实的。小说作为进行中的生活的生动体现,它是生活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演出;而作为演出,它是我们自我生活的一种扩展。
将小说和历史相互贯通,反映在文学中,则有了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的类型。如果把这些宏观范畴在小说中具象化、具体化,那么在同时抒写着历史和生活题材的小说中,通过小说体式的文字所要传达出的历史,以及透过历史所渲染的文字,在主体创作思想方面,则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其对历史的关照度有关。
面对一个城市,面对城市的一部历史,在这个众生都擅于遗忘和知足的年代,作为心思细腻的作家,裴指海的深沉思想与他的历史良知促使他写下沉痛历史中苍凉的真实,以及在这些真实中渗透出的对人性的拷问和反思。作为军人,作家裴指海在操作这样的历史真实的思想脉络时,其关切度显得更为深刻,他能关注到历史和战争的残酷,能关注到人性擅于遗忘的特征,能关注到世人对历史的淡忘。而对于多样性极强却又渗透出悲凉性的人性描写,他将其放置在真实的战争中,其说服力不仅仅是透过博大的想象来体现,还有作者自身体悟的真实感触的渗透。除此之外,作家还关注到传统的认知问题,大众对于军人,历史的评判对于国军,世人对于英雄,以及当下对于历史和战争的诸多认知。如果说他对小说中历史的重现是在揭示着作家对历史的关注和反思,那么对于各种认知的续写,则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思考。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实中切实存在的世人的诸多认知,才使小说在背对历史的真实层面上,反应出更深层的思想光芒。
小说《往生》有两条大的线索,一条以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连长李茂才为主人公,在这条线索中,作者集中反映的是战争前后以及惨烈的战争中李茂才所经历的历史,描写了许多令人钦佩的英雄人物,作者力图还原历史和战争的真实场面,其中充斥着战争的残酷性和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条线索则以“我”为出发点,如果忽略小说中的虚构手法,似乎可以将这部分看做作者自身的描写,“我”就是作者自身,去采访,去缅怀,在感知到历史真实的时候感伤,在面对麻木的大众时的无奈何愤怒,以及落入时空的回旋之中,借着过去了的历史进行着的情绪喷发。这部分运用了一些魔幻主义的写作方式,与灵魂战斗,时空重叠而又交错之间进行着生活,虚虚实实之间,抒发的是作者对于历史的沉痛关照以及对于现实的无奈和呐喊。
在两条线索的交叉落在现实的层面上,“我”去采访被大众遗忘的英雄,以及在参访过程中“我”和老英雄之间的精神交流,作者同为军人,对于战争和历史的伤痛有其深刻的理解,对于大众对军人身份的认知,也有其相似经历的深切性。诸多相似的背后,作者所化身的“我”在对于英雄的尊重、对于战争的认识则是令读者大众有所学习的。作者有着深刻的反思意识,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反思着我们生存的当下,作者用越来越沉痛的口吻描述我们精神生活的现状。作者在充当历史的反思者和忠实记录者时,还是一位有良知的军人。他的身上有着深邃的无奈,“我能做的,就是把我所看到的写下来”,可以看做作者沉痛之余的精神写照。
大众的心灵
大众的心灵,意在反映认知。对于战争,对于英雄,对于一段历史,大众的精神境界上的认知,能反映出大众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小说中,作者的用意在于警醒和批判麻木的大众。同样的认知问题不仅仅是当下存在着,在历史上,也同样有着这样的问题,这种延续性的民众认知,势必是一种麻木心灵的世代沿袭,也正是这渗透其中的悲哀,成为作家警醒世人的武器。
作者在文中写道:“能被普通的百姓认可,这是身为军人的骄傲。”含蓄的几个字,将军人的心态表现了出来。然而在生活真实中,大众对于军人的认知却远离着军人的心愿。战争前夕,李茂才他们要征用几间民居,得到的是市民们强烈的反对和误解。以及在赵二狗的家中,他的家人不问赵二狗的死活,也不问他的英勇与否,关注的则是他是国军还是解放军的问题。作为当下的军人,“我”遇见的也是同样的情况,大众的不屑和不尊重,作者无奈地写下,“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1937年在南京的国军和2009年在南京的解放军的遭遇是多么如出一辙”。这些相似回归到大众之上,大众的心灵是冷漠的,这些冷漠的延伸,以及作者对于这些认知的揭示,我们读者大众应该意识到,对于英雄们,对于军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该去做什么,才能慰藉那些需要被理解的英雄们的灵魂。
而在战争的面前,不同于对军人的冷漠态度,大众反应出的则是无知,深刻的无知。在自卫战前夕,老百姓面对侵略者说的是“我们不惹他们,他们总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吧”,修身养性的僧人的一味的宽容和豁达,汉奸们谄媚的嘴脸。直到战争来临,大众才能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大众对于战争的无知,一方面是在抒发大众的无辜,战斗的残酷,另一方面,也是激发读者思考的地方,在家国被侵略的时候,大众为何还如此无知。
时空退回到眼前,售票员问“我”,会不会有战争?在网吧和游戏厅,热血沸腾的少年们大喊着打打杀杀,他们都是远居在战争之后的民众,面对曾经的战争,少年们看似热血沸腾,然而在他们的灵魂之中,他们的疯狂和无知更甚。作者写了令人深思的话:“我们赶走了野兽般疯狂的侵略者,随之又培养出了比野兽更无知更疯狂的后代。他们甚至比他们所要反对的走得更远,更加反动”。如果说这些内心无知并且反动的青年人是青年人的一部分写照,那么作者还写到了一部分人,“他们世世代代长的都一模一样……他们早已经学会了如何忍受,如何沉默地生活,如何沉默地死去。”作者的笔触触动的几乎是全部的众生的类型,他们要么变得更加反动,要么像历史中一般一如既往的软弱,大众从血液深处体现出来的特征,是触及到大众世界观的部分。
作者还描写了大众对于英雄的认知。李茂才作为历史上的英雄,平庸的生活于世是一种豁达,而这种豁达背后则是大众对于英雄的忽视。老人在一吐心中的历史之后去世,而在他的墓碑上要刻写的字句,笔者认为可以看做是对老人身份的界定,他的儿子说道:“我在墓碑上能写什么呢?写民族抗战英雄?可谁承认?他就是一个农民啊。他当过解放军和志愿军,写革命历史,可也不是那么回事……”难以界定的身份不是因为老人自身的身份难以界定,而是因为大众对于老人的认可问题,没有人去尊重这个英雄的作为,只有“我”喃喃地说到,将军歌刻写在墓碑上,老人一定会赞同。同为军人,同为被忽视的人,惺惺相惜。这也是一种无声的呐喊,英雄和军人同样需要大众的认可。作者再一次将笔触渗透到无声的批判之中。
时空的回旋
小说中有个很吸引人的部分在于时空的回旋。作者将过去的和叙述者经历着的时空相交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描述叙述者“我”和侵略者以及国军军人们的相遇,这些构成一个虚幻的关系脉络,在不同的相遇对象中,“我”和李茂才的相遇是真实的关系,两部分虚虚实实地交叉在一起,其基点是作者自身的情绪辐射和思维走向。
叙述者“我”跳进历史的回旋之中,很多场面实际上都是在进行一种救赎,而这种救赎只能是身体意义上的救赎,这样的救赎对于当时的历史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将这救赎折射到现实中的精神层面上,对于当时的民众,对于当下的遗忘了历史的人们,其意义都隐藏的状态之中进行。作者要表露的是不动声色的批判,对于无知的冷漠的人们的深刻批判。
作者在叙写“我”穿插在历史中的时候,“我”和历史中存在的人进行的平静的交往,以及“我”的不慌不忙,经过了长久的历史积淀,之后冷静下来的精神写照,也可以将“我”还原到一个现代人身上,在回归历史的时候,眼观自然比身处战争中的人们,多一份冷静,这种冷静,是现代世界的历史性关照。
主人公“我”在历史状态中刺杀侵略者,日本兵却只是毫发无伤,对于历史,“我”是无力更改任何一部分的。历史中的死亡,是生命和战斗中最真实的截面,战争中难免死亡。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除了一遍遍地沉痛和无奈,并无任何力量去阻止。
在战争中被杀掉的人们对于“我”提出的诸多问题,有僧人提出的关于神性的问题,作者的话语体现出对神权的一种反思,面对残酷的斗争,除了迎头战斗,一切都是虚幻的,空假的。
在写到“我”和侵略者的战斗时,战争场面血腥,作者也透露出一种救赎,是救赎身体还是救赎内心,救赎心灵还是救赎生命,救赎历史还是救赎追忆,在这种种救赎与覆灭之间,隔着太多的无奈。而且在这部分中,很多没有了生命的人都在追问侵略者的良知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何等的无力和无知,并将无知的可悲做了辐射状的折射。然而回归到现实,面对同样的事,很多年之后的大众,何尝不是同等的无知和怯懦,这种深入骨髓的悲哀,是整个民族的沉痛。
作者有意对死亡的人授予了话语权,用这些残损的身体来说出以前未来得及说出的话,说出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东西,是最接近其灵魂的语言。然而这种悲哀之处在于,一定要等到他们的身体残破或者死亡之后,才能真实地倾吐。对于人性的虚假和真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互相依存,还是相互替代,作者试图在寻找一个可以共同存在的连接点。
文中还有一个日本亡灵所说的话,“我们还从你们汉文化里吸取了忠诚、朴实、敬业、苦行、服从等精神。我们对外霸道,但对内讲究的是忠诚、良善、上下尊卑、团队合作,我们从来不会窝里斗。看看你们自己,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你们的人性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吧。”这句话,体现着作者对于文化的思考。文化作为大范围内的范畴,在其承接过程中,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文化的借鉴者得到的又是什么?相同或者相似根源的文化带来的人性的巨大落差,带来的灾难,究竟是谁之过?而当我们对于文化的遗忘和缺失成为侵略者的把柄,我们的历史就留下了巨大的耻辱。对于历史对于未来,对于现在,我们该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是作者给予我们留下的巨大思考空间。
在大众擅于遗忘的当下,作者重提一段历史,翻出历史和城市的旧痛,不仅仅是提醒麻木的当下,还在引发思考。面对一段血淋淋的历史,面对伟大而又被遗忘的英雄,我们该持着怎样的态度去看待他们,我们该用怎样的作为来面对历史?现在我们生活的时空很快也将成为过去,成为历史。面对我们自己在经历的“历史”,我们的心灵是否还会一如往常一般空白,我们何去何从?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拿什么来警醒麻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