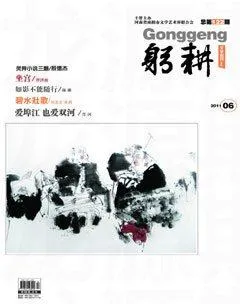也说“出书”
最近,架不住朋友游说,整理了这些年零零星星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的文字,打算出一本自己所谓的“作品集”了。屈指算来,从1985年在《奔流》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在文学这个“圈子”里也混了二十多年了,虽然前后也发表了上百万字,但总感觉并没有什么得意之作,加上经济条件等因素,出书的想法一直没能付诸行动。
由出书想到了一些社会现象,有了不吐不快的话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虽久不废。”“三立”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是许多仁人志士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人生理想。写文章,虽然未必如曹丕所称颂的那样,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毕竟是雅事,特别是读书人,视文章传世为“名山事业”,终其一生孜孜以求者不乏其人。可看看当今文化圈和官场上,许多人著作等身,却留下了不少笑话。遥想当年本地的一名县官,将在任期间的讲话、文件等汇集一册,名曰“启示录”,实则是一堆垃圾,用来敛了不少财。近日,山西省阳泉市副市长王敬瑞积多年为官经验,出了一本名为《芝麻官悟语》的书,书中提出了做官的“七要义”。且不谈这种做法对为官者有何意义,最起码从中透射出了一种堪忧的政风:虚!办虚事、求虚名、玩虚套。还有近日被查处的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贪污受贿,非法经营的总案值高达1700多万元,其中一本由他撰写的书籍单本就卖到566元的天价。由此看来,官员出书,不仅是浪费出版资源,制造文字垃圾,更有害的是它竟成了某些贪腐官员大肆敛财的手段。
国学大师黄侃曾立誓50岁之前不著一字,原因是怕自己读书太少,成书后谬见流传。可惜天不假年,黄先生49岁就病逝,没有留下一本书。黄侃虽未出书,但片言可令日本汉学巨擘吉川幸次服膺终身,再不敢妄言“中国学术界没有读书人”。和上述出书官员相比,黄侃虽无书流传,却能留名青史,而那些出书官员,最终留下的只能是一堆笑话和罪证而已。种种利益至上、道德沦丧造成了如今更为恶劣的一种局面:文化垃圾泛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这也是吾辈揣揣不安,不敢将浅陋之作贸然结集刊行的原因之一,生怕步了别人的后尘,糟蹋了圣洁的文字。
古人认为:德是一个人的立世之本,有了德才能立功、立言。古代无论是皇家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德作为处世之本,在生活中,从不肯放弃立德的点滴机会。历史规律总要以人性温暖打动人心,所以,古代统治阶层才会以德治国、以孝治国,而且古人都是以真诚用人品用人心来做的。如今世道轮回,几经篡改,人都学精明了,走捷径,直接用表演来秀道德。这就延伸出了权利、金钱、美色等各种秀,视道德为垃圾。
几年前,一个朋友想出一套文集,其中有部散文集,想请本地一位著名作家写个序,我受朋友之托找到这位作家,并送去了文稿,可是苦等了四十多天,就是不见成文,催问两次,作家均以公务繁忙为由拖延。后来,还是朋友精明,托我奉上一个大红包,没过三天,序文即告完成,并且还夸张地将朋友的作品称赞一番。此事令我感到很恶心,自此再不看这位常说要提携文学后人的著名作家的任何文章。
还有更令人不齿的,写了几篇花草虫鸟的文章,出了两本小册子,便以“作家”自居,处处显摆,招摇过市,却尽干些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舔沟子的勾当,这些是文人中的败类,何德可言!
由出书说到这些,实则不吐不快,并非标榜自己清高,文字水平有多高,作品如人品,成败得失自有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