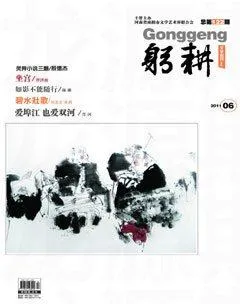坐宫
梅妮结婚前没有病,是个漂亮活泼爱唱戏的小女孩,梅妮结婚后就得了病。梅妮的病不痛不痒,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不影响生孩子下地干活儿。梅妮的病是夜里爱做梦,梦还是得劲梦,既往不咎舒心又快乐。梦醒来就算不上什么好梦了,就不得劲了,是羞于启齿的梦,这就影响心情。心情是能藏起来的,能藏多深是多深,即便是藏不下了,不好的心情悄悄爬上了脸,脸上也没写字,谁能知道她又是咋的了。
梅妮十六岁的时候,乡下兴唱老戏了。镇子里几个上了点岁数的老头,坐在镇东头的大杨树下“嗞嗞啦啦”吸了半晌旱烟,烟袋锅朝杨树根上一磕,说,整。锣鼓家什“叮叮咚咚”一敲,一杆子男男女女围上来,一个小剧团就成立了。
那时候,爹刚给梅妮找好了婆家。婆家也是本镇的,一兴做生意婆家就在镇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搭了个肉架子,干起了杀猪的营生。梅妮的爹是个半路岀身的厨子,别看是半路岀身,那时候能干这种活的人在这个镇子上可算是凤毛麟角,红白喜事、老人寿庆、孩子满月,就得弄几桌菜,就少不了梅妮她爹的身影。厨子多半是要和肉架子打交道的,梅妮的爹又好喝酒,经常和李屠夫在一起,弄个小炒、凉拌个猪肝拧两盅。一来二去梅妮的爹和开肉架子的李屠夫成了好朋友。李屠夫的儿子李毛蛋和梅妮是同岁,跟着父亲杀猪卖肉,很是伶俐,只是人长得黑,脸上还长了很多的毛,毛蛋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两家是爱好儿结亲,逢年过节毛蛋就会给梅妮她爹送只刮净了的猪头,翻洗好的猪大肠,或是一挂猪心肺,一挂猪油,惹得梅妮爹甚是高兴。
剧团的活动场地就在镇东头的老寨墙上,老寨墙早就被平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了点轮廓,上面盖有茅草房还丛生着些杂树。单甩就住在老寨墙上,两间破旧的泥屋,泥屋边是用斑茅搭建的猪圈,猪圈里养着一头雄壮膘肥的白色公猪。单甩已经五十多岁了,爹娘早己去世,是个单身汉,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胳膊落下了残疾细得像根麻杆似的,走起路来像根麻杆似的胳膊不受控制,一荡一荡的,镇上人都叫他单甩。单甩是靠养公猪给人家的母猪配种过日子的,日子好呆还能过得去。单甩年轻时好看戏,做唱念打他都不行,他耳音很好能听懂曲调,还懂得点工尺谱,就找了张蛇皮自己用竹筒糊了杆弦子,无聊寂寞的时候就吱吱呀呀地学拉弦子。虽说那条细得像麻杆似的胳膊有点不受使唤,但那只手却能把弓抓得紧紧的,一推一拉,出来的声调也算有板有眼。老戏不让唱了后,他那把自制的旧弦子就挂了起来,后来有了京剧革命样板戏,收音机里整天唱。单甩有一台小型的“红灯牌” 收音机,能挂在脖子里听的那种,单甩就又跟着收音机的曲调学拉弦子。他特别喜欢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 那段导板音乐。他经常学拉那段导板,把那段导板拉得高昂激越,虽说音符不太准,那种韵味还是有的。
单甩住的地方离镇子较远又偏僻,排起戏来就方便了许多。
这个镇子地处汉水流域,早年就流行“二黄戏” 。“二黄戏” 的学名叫汉剧,这里人从不叫汉剧,都叫“二黄戏”,称“二黄戏”为细戏。“二黄戏”十分讲究,演员分一未、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音调幽雅,唱腔婉转,道白柔和,语言风趣,表演细腻,纯朴大方,是个古老剧种。胡琴拉着月琴弹着锣鼓家什儿敲着,一腔一字有板有眼,楚腔汉韵,直逼人心,像呷了浓茶,酽酽的,又像喝了老酒顿时涌上了脸,有了淡淡的醉。这个镇子里的老人爱听“二黄”,爱看“二黄”,还爱唱“二黄戏”, 上点岁数的人人都能哼上几句。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这个地方的“二黄戏”绝了迹,没几个人会唱了。
梅妮家离老寨墙不远,单甩在老寨墙上弦子一拉,锣鼓家什儿一响,细细的唱腔就传到梅妮的耳朵里,梅妮就在家坐不着了。梅妮不顾母亲的阻拦,撩开脚丫子朝老寨墙上跑。母亲就会说,这爷俩都疯了,一个整日扎在那儿,—个听见弦子响就往那儿跑。梅妮的爹也喜欢“二黄戏”,年轻时就学过,还经常登台演出,拜过唐河汉剧名角曲白唐为师,是个唱大红脸的。他最拿手的戏是《空城记》和《哭头》:“孤王酒醉桃花中……”一腔二黄导板唱得如痴如醉。众人都推举他为团长,他也不推辞,就自任团长了。
一开始梅妮没敢说她要学戏,她只是每逢老寨墙排戏她就去看。梅妮聪明灵秀,许多女旦的唱段她一听就记下了。这时侯能唱两下子的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了,特别是上了岁数的女人衣着邋遢,身材臃肿,嗓音也大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扮个老太婆,扮个花旦扭两下大屁股,捏着嗓门唱几句,逗逗台下的观众还行,也能说得过去。要是扮演青旦,年轻漂亮的女子,妩媚娇美的小媳妇就让人嗤笑了。于是都觉得得培养接班人,男孩女孩只要有点模样的都要,培养接班人成了这个草台班子的一项重要任务。
梅妮个头不高,一副红扑扑惹人疼惹人爱的圆圆脸蛋,都说梅妮生就是个唱戏的料。她爹却说,是啥呀是,十七八了吃了铁一样就不长个,要个头没个头要扮相没扮相。梅妮不服气就偷偷地报了名,她不敢找他当团长的爹报名,她找了拉弦子的单甩报了名。单甩问,你会唱啥?唱两句我听听。梅妮说我会唱《四郎探母·坐宫》一段。单甩就取岀弦子咯咯哇哇地调了琴。梅妮就唱了起来。
听他言不由得咱背地嗟叹
十五载才吐岀木易根源
走近前与附马重把礼见
尊一声驸马爷细听咱言
你本是杨家将驾海擎天
咱虽是番邦女略知圣贤
…………
梅妮唱起来音调悦耳,声腔婉转,像模像样的。单甩越听越高兴,弦子拉得越有劲,麻杆细的胳膊竟然也腾挪自如,把弓拉得妙趣横生。早有人拥进了院子闭了气儿在听,不由得有人喝彩叫好。梅妮的爹正在附近的一家人家忙着做菜,这家人家明天要娶媳妇了。满院子唧唧嘎嘎的人声被传来的唱腔一下子冲刷得无声无息,所有的声音都静了下来。一开始都怀疑是收音机里在唱,人们用目光在院子里四处巡找,屁股大的院子里哪有收音机的影子。有人问东家,你家的收音机夹在裤档里了,只听声儿不见东西。东家说,我家就没有收音机,这不是甩“先儿”院里传过来的嘛。单甩因为会拉“二黄”弦子,人们都戏称他为“甩先生”, 简称“甩先儿”。梅妮她爹仔细一听,他也听岀来了弦子还真是单甩拉的弦子,好多音符他都没能拉准。东家说,谁唱的呀!真好听,住这么近,这妮子的戏从没听见过,没一点印象。梅妮她爹也没听过,也没一点印象。东家问,赵大厨,你是团长哩,这是从哪儿挖来的角儿,晚上我备上礼让邻居们热闹热闹。梅妮她爹带着两手油,急步朝老寨墙单甩的院子里走,走进院子他就看到邻居们三三两两,有站着的、有蹲着的,也有靠了树靠了墙的,一脸惊奇看着梅妮唱戏哩。哦——,梅妮,是梅妮。李大厨李团长吃了一惊。梅妮还在唱:
早晚间休怪咱言语轻慢
不知者不为罪
你的海阔量宽
………
梅妮把这一段唱完了,院子里立即掌声爆起。梅妮她爹也鼓了掌,满手的油拍起巴掌来,那响声带着闷气,不够响亮。梅妮见到她爹,脸刷地一下变成了白色。梅妮生怕他爹不让她学唱戏,生怕她爹打她,就求救似看着“甩先儿”。单甩见梅妮她爹一脸的高兴,并没有责怪梅妮的意思,就对梅妮说,你爹巴不得你会唱呢!这回你爹有角儿配了,将来你演铁镜公主,你爹演杨四郎,台上是夫妻,台下是父女。院子里的人轰地笑了,梅妮的脸也红了。 梅妮她爹骂“甩先儿” 不是个东西,就是屁话多。
梅妮从此学起了“二黄戏”,越学越好越唱越好,有时还真跟他爹演起了夫妻。这种事情看怪不怪,演戏演戏这就是演戏。李屠夫本来就知道梅妮她爹会唱戏,当年还唱响过,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梅妮她爹的外号“赵大锣”,唱戏时老要锣点,锣点跟不上了他就要骂人。只是后来不兴唱老戏了“赵大锣” 变成了“赵大厨”。梅妮学唱戏的事情李屠夫家也没提过什么反对意见,老子就是个唱戏的,女儿也唱戏仿佛名正言顺,并没谁说三道四。就是父女俩在人家院子里唱乱弹时(不是正式上台演岀)演夫妻,镇上人看了戏茶余饭后说说,也只是个笑谈。李屠夫家也从没往心上放,梅妮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况且唱起戏来更显得乖巧伶俐,小模样一副可疼可爱的样子。
梅妮她爹厨子的营生是不能丢的,厨子的手艺关乎着他们一家人的生计。除了剧团学戏演戏的事,镇里镇外有了红白喜事还要请他去做菜,有的人家需要和村里人热闹热闹弄个场面了,他还要把剧团也拉去清唱清唱。
剧团里收了许多男孩子女孩子,大多是本镇上的,也有外村外乡人。剧团里能教戏的几个老人肚里戏少,教起来就力不从心了。这个时候拉弦子的单甩也把他养的那头,养得白胖白胖的大公猪给卖了,专心致志地拉弦子。又从胡北那边请了老师,老师姓林,是旧社会大主家开办的娃娃班学岀来的,唱了一辈子戏,一辈子狐苦伶仃无落无靠,就是一肚子的戏。林老师己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有了老师来到镇上教戏之后,镇子上就热闹了起来,像模像样办地起了戏校。镇子上办的这个戏校是不收钱的,只是图个娱乐。林老师教学生也不收钱,说大了是传承“二黄”文化事业,说小了就是混口饭吃。镇子上的人对林老师也很热情,饭是到学生家轮着吃,也有争着请林老师到馆子里吃的。这一杆子学生中,林老师最喜欢的女孩是梅妮,最喜欢的男孩是冬瓜。他认为梅妮是天生唱旦的,冬瓜是天生唱生的。在他心中梅妮和冬瓜就天生地造的一对金童玉女,他愿意把肚子里的戏全教给他们。他教学生们段子的同时还给梅妮、冬瓜吃小灶,教他俩全本的《四郎探母》,梅妮的唱腔好,身段好,虽说个子矮些扮相却俊美,人见人爱。冬瓜生就长着一副生角脸,高高挑挑的身材,小嗓拿捏得很亮,小时候还学过武术,戏把子一教就会,大翻小翻翻得溜溜转。
就这样,忙月季来了,学戏的孩子们在家帮家里人干干活。闲月里,锣鼓家什儿咚咚响,弦子吱吱叫,孩子们都聚拢起来吚吚呀呀地唱。年终了孩子们也快学了一年戏,该给全镇人来一个汇报演岀。林老师看好梅妮和冬瓜,镇子上的人,梅妮的爹“赵大锣” 赵大厨赵团长也都看好他们。《四郎探母》这出戏他们己经不知排过多少次,“坐宫” 一折戏梅妮己滚瓜烂熟,该是他们展示的机会了。
小年刚过,镇子里开始忙乱起来,为过新年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乡里人也都朝镇上拥,带着地里产的,手工做的,家里养的,山上逮的,外地贩的来换钱,集镇上白天像起了潮人浪涌来涌去。梅妮的婆家李屠夫准备了一满圈大生猪,杀猪声夜夜响起,凄惨的猪叫使年味有了腥气,也使年味更浓更深了。这天晚上,李屠夫家凄惨的杀猪声刚刚在镇子中心响起,镇子东边的锣鼓家什儿便敲响了。锣鼓家什儿的响声震天撼地,盖过了镇子里任何一种声音,也压过了凄惨的猪叫。这晚毛蛋显得格外的心神不定,手脚毛里毛糙的,给父亲打下手扯猪腿就没了力气,惹得猪蹦蹦跳跳就是上不了杀猪的案板。李屠夫就骂他是吃货。吃货的心被镇子东头的锣鼓家什儿敲得很烦乱,他的两眼有了饥饿感。多天没见着梅妮子了,即是偶而碰了面梅妮她也不情愿抬头多看他一眼,显出很陌生的样子。那些猪头猪下水让她家白吃了,他连她个笑脸也没看见到过,就觉很对不起猪头猪下水,对不起自己刮毛猪头翻洗臭烘烘的猪肠子下的力,心里就有些发慌。 他听说梅妮今晚要和冬瓜配夫妻唱《四郎探母》,就急不可耐地想看看她是如何在戏台上和别人配夫妻的。他听说过唱戏的男女在戏台上配了假夫妻,下了戏台就成了真夫妻,即是成不了真夫妻,往一个被窝里一钻,也会干起真夫妻要做的事,毛蛋很害怕梅妮和冬瓜做了真夫妻要做的事。
毛蛋帮他爹李屠夫杀了两头猪,浑身脏乎乎地沾着油污和血迹,慌里慌张地往戏台场里跑。戏场里的人远远看见毛蛋,就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气,一个个躲了。老远还给毛蛋打招呼:毛蛋,来看你媳妇唱戏了,这回她不和你老丈人扮夫妻了,她和人家冬瓜扮夫妻哩。冬瓜那娃长得,啧啧,就是人俊。
毛蛋才不管冬瓜人俊不人俊呢!毛蛋就是想离戏台近些,看看媳妇梅妮脸上搽了粉穿了戏装是个什么样子。锣鼓家什儿响了起来,他看呀看呀,就听到冬瓜在台后唱:杨延辉坐宫院愁眉不展……梅妮上台的时侯怀里还抱个布娃娃。毛蛋一见梅妮抱了个布娃走路还一扭一扭的,毛蛋就禁不着笑了,心里还美了一下子。美了一下子后心里就不美了,原来梅妮怀里抱那个娃娃是冬瓜的,不是他的。虽说是布娃娃,但看戏的人们都把布娃娃当成了真娃娃,他有点懊丧和失望。梅妮和冬瓜在台上演得很投入也很动情,梅妮眉目顾盼含情脉脉,可惜不是对着他的是对着冬瓜的。有一场戏梅妮抱着娃娃和冬瓜都跪在台子上一替一句地唱,像是在赌咒。那是《四郎探母·坐宫》一场,本来唱到这个时候杨四郎赌个咒就中了,江湖老师们却把这个地方做了很大的改动,加了一些热闹。让铁镜公主怀抱着孩子和杨四郎一起下跪盟誓,铁镜公主还有意挑逗杨四郎,使台下的观众看得有滋有味。毛蛋觉得梅妮不应该下跪,梅妮演的是公主,公主也下跪就有些下贱了。
这晚的戏演得很成功,比那些老家伙们演得更岀彩,演到精彩的地方还有人拍手叫好。曲尽人散,毛蛋想到后台见见梅妮,他却一眼看见冬瓜和梅妮连戏装都没脱,在大幕后面搂着亲嘴呢。
毛蛋就很生气。毛蛋摸了摸怀里,怀里没有揣把杀猪刀,要是怀里真的揣把杀猪刀,他就会像他爹杀猪一样,蹿上去捅冬瓜一刀子,把冬瓜的骚血放出来。后来毛蛋还是悻悻地走了,毛蛋觉得以后不能再让梅妮唱戏了,这“二黄戏”有啥好的,嘴里唧唧溜溜地像被人拤着了喉咙,台下就没有几个年轻人看,都是些该死不死的人在看。
快过年的时候,李屠夫让毛蛋去给他老丈人家送猪头和猪脚,毛蛋苦丧个脸说啥也不去。李屠夫问为啥?毛蛋说我还没有跟梅妮亲过嘴哩,冬瓜就亲上了。李屠夫笑了笑说,你知道吃醋了,戏台上的事不能当真。毛蛋说,老戏哪有台上亲嘴的,又不是新戏,他俩是在大幕后面亲的嘴,我看见了。又恨恨地说道:这个冬瓜,早晚我要把他的冬瓜蛋子给劈了。李屠夫惊了一下,觉得事态严重,决定自己去给亲家送猪头猪脚,并顺便说说以后不能再让梅妮唱戏了。
赵大厨这天正好在家拾掇年货,一见亲家李屠夫掂了猪头和猪脚过来,脸上立即炸开了花,心想这过年的东西算是备齐了。李屠夫问咋没见着梅妮?赵大厨说梅妮在“甩先儿”那儿吊嗓呢。李屠夫说,亲家,我今儿有个事要给你说说,这梅妮不能再唱戏了。赵大厨听他说不让梅妮唱戏了就吃了一惊,脸上炸开的花又立时败了。赵大厨问,咋啦?有闲话啦?李屠夫说,甭管有没有闲话,梅妮算是有家的人了,总免不了人家笑话。赵大厨是团长,他不能让他闺女说不唱就不唱,再说闺女唱得挺好的,许多人都在夸她。赵大厨说,不就是娱个乐嘛!这就叫好者好,恶者恶,说两句闲话叫他们说去。李屠夫说,不光是闲话,我还担心呢!赵大厨看了看刮得干净白亮的猪头猪脚,生怕李屠夫再掂走似的,大声说道:你担心个啥!咱是啥关系?咱俩是老朋友,两家是铁打不断的亲家,梅妮早晚都是你的儿媳妇。李屠夫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儿大不由爷,女大不可留,我看过罢年就把他俩的婚事办了吧!赵大厨愣了一下说,恁急!咋说梅妮也得过了十八岁。李屠夫说,不能等了,还是过罢年办吧!赵大厨又看了一眼李屠夫带来的猪头和猪脚,狠了狠心说,过罢年就过罢年,看你黄世仁一样把人能逼死,要是不答复你,怕是年都过不去了。李屠夫哈哈一笑,说道,我也不是黄世仁你也不是杨百劳,没人逼你,年总是要过的,谁也隔不断年这墙。
日头晃一下一天,晃一下一天,每过一天就是上一天的重复和复制。年很快过完了,到了农历的二月份,日子就不一样了。风也变细了,太阳也变艳了,树梢上吐了绿芽,田里多了些忙碌的身影。小镇上最显眼的地方贴了很多的海报,都是些附近的镇子、村庄要起会,有的地方称物资交流大会,有的地方则是庙会了。镇子上有了“二黄”剧团,就吵着叫着也要起会。“二黄”剧团这个时候忙了起来,那些老的小的演员们都聚在了一起,整日的排戏练嗓。梅妮最喜欢和冬瓜一起排演《四郎探母》。冬瓜现在很像个大演员了,排起戏来十分投入,总是带了感情来排练,好像自己就是多年不见母亲的杨四郎。
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
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萧天佐摆天门两国交战
老娘亲押粮草来到北番
贤公主若容我母子相见
到来生变犬马结草衔环
梅妮接唱道:
你那里休得要巧言谎辨
你要拜高堂母我不阻拦
…………
梅妮也不差劲,做功唱功越练越佳,俩人配合得很是默契。这时候,冬瓜在梅妮的心中播下了种子,冬瓜籽儿发了芽长出了藤蔓,藤蔓越长越壮,缠缠绕绕地缠在了梅妮的心尖尖上。梅妮的言谈举动有了变化,眉毛鼻眼对冬瓜都含了情。如果说被毛蛋无意间撞见的那次大幕后面的亲嘴,是冬瓜和梅妮演岀成功高兴所至,梅妮还有些勉强有些被动,现在的梅妮可说是长大了还长出了风情。有了风情是要表达出来的,梅妮就主动得多了,戏里亲呢得就像自己真的是铁镜公主,冬瓜就真是杨四郎了。戏外梅妮总是心尖尖疼着冬瓜,一颦一笑都对着冬瓜,冬瓜真的成了她的夫君她的男人。梅妮这时候到了夜里就常梦见冬瓜和她亲嘴,后来就又梦见冬瓜趴在她身上,压得她舒服得要死,醒来后就一脸的潮红,羞怯得走路就低了头。再排戏场见了冬瓜好像夜里的事是真的,就不敢拿正眼看冬瓜,眉低着眼瞄着,情丝在心头一点一点地扯开,把冬瓜网在心里。排戏中既怕冬瓜渴了又怕冬瓜累了,看冬瓜认真起劲的样子,梅妮就会在心里唱一句:——你个小冤家呀!
梅妮的变化没能逃过林老师和“甩先儿”的眼,他们倒是希望她俩就这样好下去。梅妮她爹赵大厨、赵团长却警告梅妮说,你可是有婆家的人了,今年人家就要娶你过门。梅妮认为她爹是跟她说着玩哩,唱一句:你那里休要巧言谎骗……就把他爹给打发了。他爹真想让她把吃下去的猪头肉和猪脚都给人家吐出来。
这些日子肉架子消闲了许多,过了年还不是太久,人们的嘴还不太馋,毛蛋也没多少事情可做,就晃晃悠悠地去看梅妮她们排戏。拉胡琴的“甩先儿”撵了他几回。毛蛋一看梅妮排戏,梅妮就有些不自然,不知道是讨厌毛蛋还是自己心里发虚,脸色也不好看,有些发愣发恼。“甩先儿”见不得梅妮不高兴,就撵毛蛋走。冬瓜也见不得梅妮不高兴,就用两眼瞪他,像是见了仇人。有时冬瓜还故意气毛蛋,对着梅妮叫道:哎——,夫人呀……。
毛蛋就很生气很恼火,一会儿摸摸腰里,一会儿摸摸腰里,像是腰里有个虱子在咬他,很是痒的样子,原来毛蛋是腰里摸刀。毛蛋腰里没有揣刀,他自己就很失望也很无奈。后来毛蛋怀里果真揣了把刀,是把剔肉的尖刀,事情发生在镇子上办的物资交流大会上。
物资交流大会的会址是在镇北的河湾里。这个季节河滩上只剩下了细绳一样的水流,宽阔的河滩成了物资交流大会绝好的场地。办大会的人不光请自己镇子上的“二黄戏”搭台演出,还请了县里的“曲剧团”。那时的农村物资交流大会不像现在,各种文艺演岀都有,很是丰富多彩,什么歌舞团、飞车走壁、光肚舞,杂七杂八的让人眼光缭乱。“二黄戏”的台子搭在河坡上,正对着物资交流大会的中心位置,按说这样的地势挺不错的。开始前两天“二黄戏”的台下还人山人海,到了第三天就不行了,戏台下坐了稀稀拉几个人,还都是些本镇子上的“二黄”迷。任凭锣鼓家什儿敲得再响,演员们唱得再卖力,也吸引不来观众了,梅妮和冬瓜的《四郎探母》也遭受了冷落。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你一个镇子上乱攒班子的娃娃剧团,无论身上穿的头上戴的,戏装都显得破旧寒碜,比不了人家县剧团不说。就论专业性而言“二黄戏”也远远比不了,人家有布景、有灯光、有音响,演员是专业的,举手投足,舞台经验演唱声调更不必说了,就剧种而言也附合大众口味,这都是“二黄戏”比不了的。这天下午没有梅妮和冬瓜的演岀,梅妮她爹、林老师、“甩先儿”都嚷着要让梅妮去“曲子戏”的台下看看是咋会事儿,梅妮就偷偷地叫上了冬瓜。
大会上人群涌动你挤我扛,很多少男少女穿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花布衫。有些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或者是有了婆家的男女对象,趁着大会期间约到了一起,越是人多越是胆大,没有了先前的顾忌和羞怯,手挽在了一起,有的还紧搂腰肢,亲热得让旁人看了直打冷颤。梅妮见人家赶会的青年男女,旁若无人亲热的样子,梅妮就很眼气。梅妮在涌来涌去的人群里,毫不犹豫地挽起了冬瓜的胳膊,俩人亲热得像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人。这时候毛蛋也在涌来涌去的人群中,他透过人流的缝隙早已看到他们亲热的情景。毛蛋挤过人流挤到了他们俩的身边,把手抻到怀里摸出了那把已经揣在怀里多天,被他暖得热乎乎的剔肉尖刀。毛蛋脸上的黑毛支叉了几支叉,那把带着他体温的剔肉尖刀刺向了冬瓜的肚子。冬瓜只感到有一个硬梆梆热乎乎的东西进了肚子里,并没有特别疼痛。只是,这时人群莫名地向前推了他们一下子,差点把梅妮推倒在毛蛋的怀里。梅妮猛一抬头看到的是毛蛋一脸愤怒和惊恐的毛脸,毛蛋脸上所有的毛都直直地竖立着,手里的那把尖刀在滴着血。梅妮撕扯着嗓音尖叫了一声:杀人了!赶会的人群立时炸了窝,向不同的方向挤挤扛扛蜂涌般地逃奔。
就因为当时的人群莫名地把梅妮和冬瓜向前推了一下子,那把被毛蛋暖得热乎乎的尖刀刺偏了,才没要了冬瓜的命。
后来毛蛋去县城里坐了两年大牢,“二黄”剧团随之也散了。不散也没有多大的前景,除一些上了岁数的老戏迷,再也就没什么人看了。形势发展得太快,各式各样的娱乐涌进了镇子上人们的生活,小青年们掂着盒式收录机,身穿喇叭裤,扭着腰身满大街地跑,邓丽君的歌使人们的耳朵里灌满了糖。电视也普及了,新鲜事儿一浪涌过一浪,使小镇人应接不暇,这种又陈又旧的戏很快被人们淘汰了。教“二黄戏”的林老师,不知云游到何处去了,或者做了古。拉弦子的“甩先儿”干脆把他那支破弦子摔了,又养上了他的公猪。冬瓜肚子上的伤不是太重,治疗了一段时间好了,就随了打工潮去南方打工去了,再也没见到回过小镇。
戏的虫子在梅妮的身体上不断蠕动,蠕动在身体上的虫子总是让梅妮的心里发痒,痒起来还挺难受。梅妮闹过几回要和毛蛋退亲,赵大厨想到猪头猪脚猪下水,说啥也不让。赵大厨当不成团长了,也唱不成大红脸了,还是个厨子,生怕再也吃不到李屠夫拾掇得白白净净的猪头和猪脚了。梅妮和她爹赵大厨生了一场恶气跑掉了。梅妮不去城里打工,她专找草台班子给人家搭伙唱戏。会拉碾就会拽磨,梅妮在草台班上学会了梆子戏、曲子戏、越调戏,这一带流行的戏没有梅妮不会唱的。梅妮和别人唱戏的时候怀过三次孕,打了两次胎,还和一个唱曲子戏的黑头生下一个小男孩。
二年之后毛蛋出了牢,掂着猪头和猪下水到梅妮的家里找到了赵大厨。毛蛋这回送来的猪头就没有拾掇那么干净,花花搭搭地留着一块块的毛,像个秃子头。猪大肠也没怎么拾掇,还是原汁原味就掂来了,一股恶臭直往赵大厨的鼻孔里钻。让赵大厨最感吃惊的是——秃子头样的猪嘴里还噙着一把剔肉的尖刀。毛蛋吊着一副毛脸对赵大厨说:这是“甩先儿”喂的那头骚郎猪,让我买回去杀了,留下猪头和猪下水让你尝尝。赵大厨一下子恶心得要吐,不知说什么才好。毛蛋甩着手吹着不成调儿的口哨走了。
赵大厨领着李屠夫下足了劲,跑遍了四镇八乡,终于把梅妮给找到了。这时候的梅妮己经像个成熟的少妇了,她二话没说,随着父亲和公公回到了镇子上。梅妮跟毛蛋拜了堂,结了婚。毛蛋杀猪卖肉,梅妮烧水翻肠,日子像白开水一样过着。到夜里一沾到床,梅妮就会做那号梦,梦见冬瓜或是其他的男人趴在她身上,她幸福得要死。就是毛蛋趴在她身上的时候,她也觉不出那是毛蛋的身子,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和她唱过戏的男人。梅妮做了那号得劲梦还老叫床,叫得毛蛋眼里闪着狼一样凶恶的绿光。毛蛋就很想拿剔肉刀把她给杀了。梅妮的肚子很争气,梅妮怀上了毛蛋的孩子,毛蛋就没杀成梅妮。
梅妮和毛蛋结婚后,梅妮晚上做了那号得劲梦白天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了梅妮也不往脸上挂,像平时一样帮毛蛋收拾猪头,翻洗肠子。只是毛蛋不在家外出收猪时,梅妮逮着个空闲就朝野外跑 ,跑到野地里就披头散发吚吚呀呀地唱起了她最喜欢的那段“二黄”《坐宫》:
听他言不由咱背地嗟叹
走近前与驸马重把礼见
尊一声驸马爷细听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