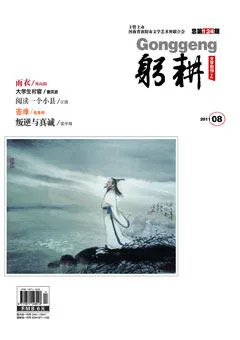叛逆与真诚
清瘦的诗人崔鹤,在我眼中消失至少已经有十年了。最后一次与他在南阳见面,记得谈话中他批评了我对南阳作家作品所作的评论——大概是他觉得那些年我对南阳作家作品的评论过于宽容了吧。这两年在网上偶然相遇,才知道“梅溪路上一棵树”、“梅老邪”都是他的网名。今年金秋十月,收到了他从郑州遥遥寄来的新出的诗集《中国狐狸》。这是继《流浪一百年》、《现在》之后,我再次读到他的作品集子。无论是他的网名,还是他这些年在经商之余的诗作,我觉得都体现出了矛盾的文化心理,一种是叛逆,一种是真诚。
“梅溪路”是他生活多年的家乡城市的一条路的名字,“一棵树”是自然界中普通平常的生命之一种,以“梅溪路上一棵树”作为网名,透射着他对故乡的热爱与寄托。“梅老邪”的网名,想是他借用了《射雕英雄传》中“黄老邪”的名字吧,这“梅”字既透露着他内心的高洁清雅,也显出他对故乡虽离不弃的缅怀,而“老邪”两字就有了叛逆的意味——但凡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大抵都知道,黄老邪实则并不邪,反倒是以孤傲与直爽居多。
作为诗人,崔鹤的叛逆除了自身形象的与众不同,如年轻时的留长发、狠命地抽烟、狂放地喝酒、愤世嫉俗等等——当然现在我已不知道他的形象是否有所改变,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在他的大量的诗歌文字中,常常出现着粗俗的语言,体现着自我解嘲、自轻自贱和决绝与无奈的反抗。但在他的另外的一些诗歌中,又常常充满着温情、温暖和对世界与生命的热爱。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这对于一个民间诗人来说是痛苦的,但也是生活给予他的深刻印记,更是孤独而又向往自由的诗人不可逃脱的宿命。
在《中国狐狸》这本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崔鹤曾一度将“狐狸”作为诗眼,反复挖掘与抒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狐狸”是狡猾、多疑、怯懦、反复无常等等多种贬义词汇集于一身的反面典型。但诗人却一反传统文化的论调,把“狐狸”作为寄托自己多种情感与向往的精神指向,不住地去透视与歌咏。在崔鹤的诗作中,“狐狸”的所指往往是多变的,有时可能是指代自己,有时可能是指代别人,有时可能是指代情人,有时可能是指代事物,有时可能是指代脑海中的意念。但无论如何,诗人诗作中的“狐狸”是充满着人性、人情的,因为她会忧伤,她会流泪。在诗人笔下,“狐狸”变得有血有肉、多愁善感,让人同情与怜惜。
崔鹤诗中这种叛逆的情感表达是多角度的,有时体现在愤世嫉俗上,他期待着“快意恩仇,笑傲江湖”(《亲爱的,老子不爽已经很久了》);有时体现在放荡深邃上:“花儿,一生/草儿,一生/猫儿狗儿啊,也是一生,/做不做一个狐狸,都是一生。”(《每一个狐狸都知道,不劳而获才是一种真正的光荣9TjZ4wYxLYphO82mEhPhkZgDRYWv6exEbXCfSM+xxEc=》)——这其中,闪现着他对生活与生命本真状态的大彻大悟。也就是在这同一首诗中,他在深味了时代生活的深层底蕴之后,又语带诙谐地写道:“今天不是狐狸的节日,/那是劳动者们的玩笑,/每一个狐狸都知道,/不劳而获才是一种真正的光荣。”他的叛逆有时体现着对世界的仇恨,但这种仇恨不过是意念中的仇恨,或是语言中的仇恨而已,有时这种仇恨又带着几分醉意:“春天到来之前喝掉你所有的酒吧/笑过、哭过、醉过/把一只青瓷花瓶摆在房间/插进一把又一把明晃晃的刀”(《狐狸的花瓶中插了一把又一把明晃晃的刀》);有时这种仇恨又带着血淋淋的语言的暴力:“很久没有杀人了,/手起刀落,血流成河,/取下那面镜子,/作船渡你回家。”(《我知道远处的那个人,当的响了一下》);有时这种仇恨又带着重组世界的大胆想像:“铺天盖地的天花板/从半空中倒挂下来/悬挂在一根生锈的铁钉下面”(《你是否看见了那几片碎瓦》)。他的叛逆又常常撕去了伪道士的假面,道出了一个男人隐秘内心的暗影:“我是梅村唯一一个不泄的男人/梅村的女人都这样怀念我”(《我是梅村唯一一个不泄的男人》)——此时的诗人,又把自己当成了一位英雄。
崔鹤的这些叛逆之作,其写作常常是低姿态的,低于生活之下,有时甚至达到了自我作贱的程度,他常常自虐自己,说“我是一个贱人”。在《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不喝酒的时间就是一个人渣》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你以为做一个人渣容易吗,你以为我这些年容易吗/真希望在某一天,你落在我手里,成就我的威名”。这些自我作贱的诗歌,看似是对自我尊严的亵渎,实则是对做人尊严的维护。诗人内心的血与泪,我们从他的这些诗作中是应该能够体味得出来的。这个世界之上,我们看到的“贱人”和“人渣”还少吗?!
崔鹤这种诗作中的叛逆或曰玩世不恭,又常常为世人所诟病,但深入他的诗歌内部,再反观他的生活历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内心的真诚。无论他表面上是如何的放浪形骸,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内心深处和诗作底里,依然是个天性纯良的孩童。如果我们被“狐狸”的表面所迷惑,那只能说是我们对诗人的诗作产生了误读。我们需要佩服的是,诗人的这些叛逆之作中,充满着对生活的切肤的痛楚,颠沛流离的人生,漂浮不定的命运,不能不使诗人常常在这种语言的表述中狂欢与放肆,而他的心与诗又何尝不是在流泪、淌血?!
如果我们再看看同一本诗集中他另外的一些诗歌,也许我们会更直接地贴近他的真诚。他写乡野的自然之美:“深深的野草,埋住了我的膝盖/小虫子爬上来,蚱蜢飞起来”(《六月,我需要一个郊外的黄昏》);在同一首诗中,他写母爱的温馨:“农家的黄昏,多么金贵/母亲一定在庄稼之间/她一定在给庄稼说着悄悄话/我知道,她想我的时间,就会和庄稼诉说”;他写让人陶醉的爱情:“我的狐狸/那个单眼皮狐狸/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喜欢躺在她的怀中/然后闭上眼睛”(《那个单眼皮的狐狸》);他对友情、爱情都是无限珍重的,他渴望“有几个朋友,/刘关张那样的。/有一份爱情,梁祝那样的。”(《其实我该知足了》)诗人又常常显出几分对回望乡情的执拗和对追求自由的放纵:“老子家的月亮就挂在树枝上,/想什么时间看就什么时间看”(《你以为想疼就那么容易啊》);“我要祝福那些断了线的风筝/会在远方变成一棵小草/想开花就开花/想结果就结果”(《我要祝福那些断了线的风筝》)。
历经人间冷暖、生活沧桑的诗人,又常常显示出生命的坚忍和执著:“这个七月我活得很烂,这个七月蜘蛛都跑得那么快。/这个七月我还没倒下,这个七月我还在苦苦地等。”(《七月》组诗之十)诗人对生活又常常是充满着向往和希望的:“我想找到一棵有鸟巢的树/窗外是满城灯光,窗外什么也没有/我知道在很久之后,会有一个又一个狐狸/举着火把,跟我一起寻找”(《狐狸的故事四处流传,没有人知道狐狸的快乐与痛苦》)。寻找,就是对希望与幸福的追寻啊!而诗人对幸福指数的要求其实并不高:“酒也足了,饭也饱了/是不是再给我一根烟/我什么都不需要了。”(《七月》组诗之十二)或者是:“找一个窑洞/冬暖夏凉/门口打一眼井/种一畦青菜/喂几只下蛋鸡/养两只下奶羊/看看书/下下棋/哄哄孩子/晒晒太阳。”(《我想给我的女人说说》)在这看似平凡日常生活的想望中,诗人有对生活的物质需求,也有对生活的精神需要。前一首诗中,酒、饭是物质的,烟是精神的。后一首诗中,井、菜、鸡、羊是物质的,书、棋、孩子、太阳是精神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谁能离开这两类食粮呢?何况是一个诗人!
全面地解读崔鹤的这本新作,我们就会看到,他有时是个性情孤绝的诗人,摆出一副与世界对敌与大战的姿势,有时又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诗人,散发出浓郁的人间烟火与情爱。也许矛盾着的诗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我也相信,无论是他的叛逆也好,还是他的真诚也好,两者都不是隔离的,而是悖离而又统一的。诗人诗作中的哀伤与欢乐、痛苦与幸福,于这个世界而言都是毫发无损的。但我丝毫也不怀疑,崔鹤的诗作在诗坛上必定是独异的,就看你如何从他的诗作中进入与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