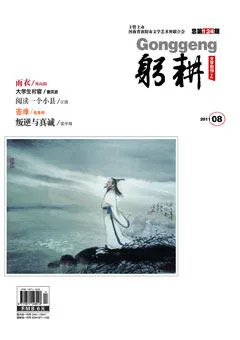江河有缘
小时候,同小伙伴一起,在丹江河里嬉水弄沙,摸鱼逮虾。稍长,便涉越丹江,到空旷的河滩割草、拾柴。乘舟过渡,看小船如竹叶般在河心打转,不是害怕,而是好玩;趟水过河,两手把衣裤高高举起,淹过肚膝的流水,扭动着身躯,流沙在脚下蠕动,如千百只蚂蚁给脚底按摩……抑或,我站立长满芭茅和刺槐的河岸,呆呆地看流水淌淌,望远去帆影,幼小的心灵会随江水流向远方。
家乡人称丹江为大河,大河有多长?有多远?时而,它清流碧水,静如处子;时而,它洪水暴涨,狰狞可怖……在我童年的懵懂里,丹江是一个谜。不曾想到,若干年后,命运真的把我推给了丹江,推给了船与水亲近的时光。丹江——留给我的是那段铭记在生命河流里的深深印痕。
船厂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是我高中毕业在故乡土地上耕耘青春的时候,忽然接到父亲所在企业一纸书信,让我去他们那个叫航运公社的企业上班。那是一个丹江岸边名曰马蹬的地方。丹江大坝的修建,移民迁徙,作为千年古镇的马蹬已沉入水底。可那俨然“水泊梁山”的航运船厂,就成了我跳出“农”门的第一个人生驿站。
航运公社,是个标志翻身船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名字,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那年,跟航运公社一起,由老县城迁移于此地的船厂,是公社的下属企业,也是丹江船舶的“大后方”。修理木船造钢船,是丹江水运赋予船厂的使命。由外仰视,这是一处生长着土石和杂树的冈丘。由老县城拆运的青砖土瓦,建成的厂房、仓库、宿舍、食堂,随山就势,参差排列。清一色的筒子房环冈而建,形同古人驻兵的山寨。敲敲打打的木头和钢铁的撞击声,成了这里张扬和放大的特殊音符。
行走在通往航运公社的江边小路,让人有种破碎的感觉。蜿蜒的江岸,停泊着装卸的船只。一片较大空地,几只上岸大修的木船,被翻扣过来,一边用木头顶着。修船木工正用凿锯斧头,给“病”了的船只开肠破肚:换下腐朽木板,嵌上新木条。
船厂有打船钉的铁匠炉,碾石灰的碾子,捣灰泥的铁板。修船人将石灰麻絮与桐油混合,锤砸调和成如手擀面似的“面团”,用凿子使劲往船板缝隙填塞。这样,“哐当,哐当”的敲击声,便汇成合唱,在空旷的山水间激荡。我觉着,这合唱,如同昔日响彻丹江的船工号子,是丹江的生命进行曲。
时逢正午,烈日如火。泊于河岸打油的木船,由于有了一侧的木石重压,斜歪着身子,大半船底露出水面,几个头戴草帽、赤脚光背的船工,正全神贯注,将金黄透亮的桐油,涂刷于被炎阳烤得滚烫的船身,黝黑的脊背滚动起汗珠的溪流。这边油好了,那边再侧过身来……一年一度,船工都要用十天半月,为辛勤一年的木船披上一层光亮金衣,都要选定太阳爆烈的正午。只有这样,油出的船才结实、耐用。
这种热闹场景,我并不生疏。幼年,随父亲去还在老县城西门外的船厂见过。不过,那时修小木船,这时修大木驳和装上机器的机帆船。同时,不远处,建造钢质船锤打钢铁的锐利之音,由石棉瓦盖顶的大车间传出,与河岸敲击木头的钝声,合为一起,音韵更为高亢、粗犷。
如今,这高亢粗粝的音响,已沉没于历史的河流。也许今后就再也听不到那震荡山川的历史绝响。那曾经从分布于丹江及其支流沿岸大大小小的修船场发出的敲击声,支撑了丹江的千年航运,撑起了让汉唐皇室都不敢忽视的山河帆影。有时候,在修船、油船现场,我真想上前帮他们剔几凿,锯两锯。非常想,但却从未尝试过。不是没时间,而是没那个劲力,没那种耐性,也没他们那种对船舶的情感。心里想着,正是这些人,创造了丹江的历史,丹江的未来——那曾经的绝响,是丹江船工行走江河、开发丹江的心灵呼喊。
我成为航运一员后,写材料,干杂务,如此待遇,是学校毕业就写点“豆腐块”的缘故。那时材料不仅靠笔写,还常常用腊笔,在垫着矩型钢板的腊纸上刻字,用抹上油墨的印机,印生产简报。字虽写得歪歪扭扭,每次却也印几十份,下发船厂、船队、装卸队。那时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夺高产”。领导要求:青年人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到火热的生产实践中锻炼。因此,除机关事物,得空是要到造船车间劳动的。搬木头,抬钢板,抡大锤,擦铁锈,遇什么干什么。一天下来,灰头灰脸,浑身就像散了架。与工人接触多了,我就发现:那些识字不多的师傅不简单。虽然都是拿斧子锯子或撑篙拉纤出身,却能凭着一股创造热情,完成了由木帆船到机动船的跨越,造出可乘坐好几百人的大客轮。
在丹江的视线里,丹江大坝的修建,使一线流水的山河,变成一望无际的“人造海”。这样,那些在古老丹江行走了几千年的小木船,便渐渐被大水库所疏远,所淘汰。船工认为:只有改变船型,实现水运机械化,才是丹江航运的出路。
然而,船厂的全部家当,就是一盘打船钉的烘炉和一台老掉牙的皮带车床。几把铁锤,几根吊绳,几个氧气瓶和堆放于墙根的铁皮钢板。靠这些东西,凭这些文化不高的造船人,硬是让古老丹江听到了机器的鸣响,听到了千船竞发的笛音长鸣。也让我这刚走出农村的船工子弟,惊异过好一阵子。
难以想象,搭建船台,工人们是将一块块方木,像小孩堆积木,垒成大半人高的原木花墩,铺上铁轨……没有天车、吊车,几吨重的钢板焊不上去,悬垂的绳子会把钢板吊在空中,用一种叫土拉丝的自制工具固定焊接。钢板硬度大,缺少让钢板折弯的设备,他们就在地上铺半尺厚的沙,几厘米厚钢板放在上面,用枣木大锤,砸出所需的弯型……
在我认识的造船人中,那个弯腰驼背,走起路却精神十足的老书记让我钦佩。他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八路”,银发锐目,不苟言笑,是个干什么都喜欢用带兵打仗口气表达情感的军人形象。船型改革的战役打响,识字不多的他,从省里弄到一本《造船规范》,便如获至宝,立即让技术员抄写一本,白天一线指挥,夜晚一啃就是半夜。两寸厚的大书,他竟能复述如流。干中学,学中干,竟然成了丹江河道的“造船通”。
同老书记一样,土生土长的造船人,像一幅幅刚收笔的人物肖像,一直鲜活于我的脑屏。
他,一个有十多年驾龄的船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上大学又中途退学的大学生,也是地主子弟的困惑,让他走向丹江。作为丹江唯一进过大学校门的驾船人,建造大钢船开始,破格由木船队被请“出山”。几年历练,他出息了:船舶设计,船台施工,直至580客位的“胜利号”客轮下水,使他成了让丹江感动的亮眼人物。
先钉秤后驾船的他,是船用螺旋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我亲眼所见,他摆弄螺旋桨的工具,是一柄打铁的锤子和装在身上的一把卷尺。在熊熊的烘炉前,几块指头厚的铁板,经他烧烧打打,比比量量,挫挫磨磨,与碗口粗钢筒一焊接,便成了电风扇似的螺旋桨。用这种办法,他给丹江大小船只,安上了“腿”,让一艘艘钢木质客货轮,走江过海,驰骋江河。
还有木工、铁匠出身的他们,都凭拿斧子、铁锤的手,成了丹江钢木质机动船建造的土专家。
今天,近30年时光过去了。但我还是忘不了那样的氛围,忘不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在那个条件艰苦,不讲科学、狂热得离谱的年代,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小船厂,竟然躲过气势汹汹的浊浪袭击,干出这样的大事业,咋说也是了不起的事情。
那个时候,职工收入不多,义务劳动却少不了。天寒地冻的岁末,竣工的船只要下水,机关、车间,全员出动。所有人都迎着寒风,跳入刺骨的水中,推呀,拉呀,硬是把几百吨的新船送入深水;水泥趸船浇铸,几支200瓦灯泡一挂,鏖战的总是一个通宵。没人喊累,没人要加班费。平时,煤船来了卸煤,沙船来了卸沙……义务劳动带来的是体力的消耗和心志的磨砺。
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我就像丹江的河石,被大浪淘洗着。义务劳动让人有了种“集体感”,或叫“合群感”,套用老作家杨绛先生说的:觉得自己是“我们”“咱们”中的一员。本来,自己一进企业就是“机关人”,与工人有了“距离”。所以,那种劳动也真让我有了与老工人建立“阶级感情”的机会……
船工子女
航运公社在进步,也在衰老。渐渐衰老的船工希翼:能把在农村的子女拔出来:呼吁,要求。于是,一批船工子女就加入到船工队伍来了。名份上虽说是临时工,但毕竟给古老航运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同父辈一样,能吃苦,肯下力,可普遍就是个初中毕业。这些人进入航运后,有的留在船厂,从事车工、焊工、电工之类。有的去船上开机器,学舵把子。女孩子则大多集中在两间筒子房内,为捕鱼船队编织渔网。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承继着父辈的劳动,成了丹江水运薪火相传的事业接力。
1970年代末,航运公社更名航运公司。
航运公司所在的马蹬,是丹江的大码头。由于库区水位时消时落,这里便成了沧海桑田的交替更迭。水位上涨,碧水千顷,舟来船往;水位下降,古镇遗址裸露的黄土、杂草、庄稼,会默默诉说起古镇的以往。水位落了,人就少了,热闹的船厂便冷清下来。本就不多的年轻人,就更不显眼了。除时而由筒子房传出织网姑娘的说笑,进出船厂的大多是中老年造船工人。铃声一响上班,铃声再响下班。沾满铁锈和尘土的清一色劳动布工作服,成了公司和船厂的主流色调。一片沉闷冷寂的冻土,让年轻人似乎WkiDTiWwFOTYOFGYlBRwaQ==成了蛰伏的秋虫。因此,织网姑娘便调侃说:“俺的青春都掉进网眼里了。”
生活水平低,是那时的普遍现象。一月30元工资,本来就让我捉襟见肘,还要拿出三分之一,给老家的生产队交口粮款。粮食不够吃,要买些玉米、红薯干补贴。用煤油炉自炊,是件无奈的事情。买煤油要“开后门”。有时,也到职工食堂去吃。虽说食堂伙食好些,却要多花钱,要交粮票。临时工的粮票是从黑市买的。遇上出差,没粮票就寸步难行……然而,少年不知愁滋味。正是那段困窘的日子,厚重着我的生命底色。工作、学习、读书、散步。闲暇时光,也过得有欢有乐,贫而自足。
要说,丹江水运已有四五千年历史。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一代又一代船工,在这条经历过夏商、阅读过唐宋的河流里,漂泊、流浪、挣扎,到了父辈这一代,大多又经历了两种社会的变革。虽然他们朴实耐劳,但旧时代留下的观念,或者说蜗居一条河流的封闭意识,成了一种固执与偏见。这就让生活在他们之中的年轻人,有了“另类”的感觉。在他们眼里:“没有不吃腥的猫,没有不燃柴的火”,男女一起是非多。所以,青年男女多说几句话,或穿件亮眼衣服,也会被指指戳戳,C1jMHN38VlXpYbzVW0sTSQ==议论一番。对年轻人来说,这种氛围,带来的是心理障碍,是无意中的伤害。在我身边,就有一位女子,因夜晚私会了男友,被送交了“公安”。约会男友,似乎成了伤风败俗见不得人的事情。后来,这女子虽然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风言风语,与相爱的人结为连理,但终因心里郁结的病灶,旧病新疾,最终离开了人世。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像绳索捆绑着年轻的手脚。在呆滞的小船厂,上演了不大不小的悲剧。张姐是先我进入公司的船工子女。人都快30了,也没遇上意中人。她人清高,喜欢读点书。在人生最美的花季,服从长辈“工作第一,恋爱第二”的训诫,很少与异性接触。结果,年岁一长,却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岁月的流水匆匆流淌,嫁不出去的姑娘,也只能坚守孤独,面对迷惘的江水,吞咽着难以言说的苦水……
这些发生在1970年代的事情,让今天的人不可思议,难以置信。
当然,也有让年轻人开心的时候。大约是为了释解呆滞环境的沉闷空气,也是那时贫乏的文化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公司会邀请电影队来放场电影。《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朝阳沟》、《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来了,职工食堂门前的小会场便兴奋起来。白色影布往两根杆子上一挂,笑容写在脸上的职工家属和小孩,会早早把小板凳放在看电影的最佳位置。一场电影给年轻人提供了难得的相聚机会。青春的火花便会在这时碰撞到一起。草草吃过晚饭的青年男女,换洗了干净衣服。因为有了附近村庄青年的加入,小小会场就显得格外拥挤。青年人既看电影又看人,左顾右盼,挤挤挨挨。我觉得,此时的船工子女,心灵的翅膀才真正展开,天性才真正回归。
随着退休接班的实施,又一批船工子女走进了水运企业。这样,老态龙钟的公司船厂,便悄悄发生着嬗变,平添出几分青春气息。夏日来临,丹江的水位又上涨了,山寨似的厂区,被清凌凌的江水环抱着。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村庄,被水汽氤氲得格外青翠。下班铃声响了,吃过晚饭的年轻人,看看太阳还在西边山冈上逗留,便不约而同,走向细浪轻吻的水岸。女的端着洗衣盆子,或蹲于河岸,或荡起小舟,平静的江水,如镜鉴一般,映照出姑娘们戏水浣衣的倩影。男的则光起膀子,一个猛子扎进墨绿的江水,泳水嬉浪,释放着劳累一天的愉悦。他们一会沉入水底,一会钻出水面,时而也泳推着浣衣姑娘的小舟,在水中旋转嬉笑。年轻人的浪漫天性,仿佛此时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水载小舟,随意荡漾,优哉游哉。夕阳把广阔的江面涂上闪亮的桔红,鱼鳞似的细浪,泛着金光,在天水间铺展出一幅优美画图。是时,一条放慢了速度的归航船只,“突、突”轻吟,缓缓驶来,从机舱钻出的小伙子,炫耀似地站立船头,向着浣衣小舟,远远递一个媚眼,做一个鬼脸。姑娘的脸上便会荡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传唱了几千年的古老《诗经》,用于此时情景,倒也贴切。开放的春风一吹进古老丹江,古板冻结的河流,便化作一泓春水。年轻人天性的复苏,让这些流动着船工血液的船工儿女,摒弃着父辈的偏见,青春的热度不断上升。他们江岸聚首,码头相会,河汊港湾,水畔月下,交谈着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秘密……热恋之后,便是新婚的花烛。老船工成为亲家,新一代结为连理。在我的印象中,好几对船工子女,就这样成双成对,心满意足地走进了婚姻殿堂。
我曾被这样的情景所感染,写过一首叫《网船恋》的小诗。大意是:小小机船进港,织网姑娘心动,船头相约,港湾相会,感情上相亲相爱,工作上互勉互励。小诗登在县文化馆的《淅水文艺》上,为开放的新一代船工留下一幅剪影,也为自己曾品尝的苦涩,找一条释放的出口。
行走江河
生活流水,无声无息。春意浓过,夏日来临,我的心也随夏日的燥热而驿动。
那是恢复大学考试第三年,希翼走进大学校门的我,请假躲入县城的朋友家,啃书本,习功课,意在为改变命运做青春最后一次冲刺。可是,三个月的“闭门修炼”却失败了。高考二次落榜,让我跌入人生低谷。无奈之下,又回到那个倾洒过汗水和情感的地方。可是,房子有人住,事情有人干了。我只好与同事住到一起,在船厂干起杂活。流汗劳累不算什么,但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讥笑非难,却让我有点晕了。有人建议:离开是非之地,换个环境,驾船去!
有人说: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一种裂变与再生。现在想来,也是那时年轻气盛,待人处事喜欢以自己好恶所付出的代价。
那是个碧水盈蓝的日子,我提起简单的行李被褥,由马蹬上船,行客济济的“丹峰号”客轮,载着我的失意与惆怅,顺风顺水几个钟头,来到处在湖北境内的丹江口河南码头。
我报到的3号铁驳,正停在码头外的港湾里。人还没下船,老船长就接我来了。我望着这位50来岁的郭姓汉子,浓眉下的双目,刻写着江河的风霜;敦厚的双唇,黑硬的胡茬,诠释的是丹江船工的粗犷与善良。他满脸堆笑,向我点点头,接过行李,扭头就走下客轮的甲板。
我跟随船长,在崎岖水岸走百余米就是我们的船了。船上还有一名船员,40来岁,姓王,他站立船头,以微笑示意。驾船人大都不善言谈,尤其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踏上颤动的桥板,向船艉小屋走去。老船长将行李往右边空床一放,才嗡声嗡气地说:“你睡这张床。”
我仔细打量这高不足两米,大约十多个平米的船屋,干净整洁,一尘不染。几张睡床宽不满三尺,铺盖都很简单。过去,我也上过船,却只是过客而已,这一次要住下了,就是说,我成了这条船的正式一员,成了名副其实的丹江船工了。
这是一艘自身不带动力的钢质货驳,200吨载重,同火车车皮一样,行走全靠火车头作用的拖轮拖带。是时,在广袤的丹江水库行舟,已不同老船工在礁石险滩重叠的山河激流撑篙拉纤。机械化的发展,让“一条竹篙船为命,栖风餐雨船是家”的老船工们欢喜着。从小木船到钢质船的过渡,让世代走风行浪的他们,满足中有了希望。老船工告诉我,当年,他们在山河行船,涉水过滩,攀岩拉纤。隆冬,要赤身跳入冰冷水中,将沙石壅堵的航道,用锄铲扒出一条行船的沟来。半天过去,腿脚僵硬,不能站立。夏日,遇上洪峰暗礁,一不小心就会船破人亡……
“说起当年的罪啊,背心还透出一股凉气。”
“昂——昂——”,随着几声船笛鸣叫,丹江号拖轮,耕波犁浪,从水天一色的茫茫水域驶来。一与货驳靠拢,我便跟着师傅,跳上河岸,拔起岸坡上的大锚,然后用钢丝绳将货驳与拖轮紧紧捆为一体。又是一阵机器轰鸣,我们的货驳便在拖轮的鸣笛声中,徐徐离开港湾,向着水天连接的深处驶去。
丹江货船,装运沙石、煤炭和粮食为大宗货物。一条货驳二三百吨,比昔日小木船增加一百多倍,相当几十辆解放牌卡车。这在公路不甚发达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水上运输还颇为可观。此时的我,与父辈一样,开始了“水上漂,船为家”、浪迹江湖的船工生涯。依照规矩,刚上船的小青年,要先“熬伙计”。熬伙计必先从烧锅煮饭做起。过去小木船用的锥底圆柱型鼎式铜锅,已被煤灶替代,烧柴变成烧煤。船工饭食很简单;煮红薯玉米糁,或蒸米,蒸馍,手擀面。船到码头,买粮买菜,小扁担一扛,就去了集市。因此,淘米洗碗,续煤戳炉,锅碗瓢勺便成了我生命琴弦的一段小小插曲。
晨起,捅煤炉,铁火棍往炉中一戳,淡淡的蓝色火苗,便轻舔锅底,小厨房就蒸腾起乳白色的云雾,游弋着飘出门窗,很快被晨曦微露的江风吹散。这时,我的心,也会像港湾的碧水般平静。
吃过早饭,编好队列的好几只船整装出发。好多船系在一起,在拖轮推动下,犹如碧空的雁阵,呈“一”字或“人”字前进。长龙似的船队,在绿地毯般的水面滑行,那种感觉真好。我们船队航行丹江,也走汉水,去郧阳。今天还在楚国始都丹阳之上行进,明日可能就在汉水的古均州城水域游走。船行江河,时有白色水鸟,几只野鸭,或盘旋于船队左右,或游弋船队前方。我站立船头,淼淼碧水,江风拂面,蓝天在上,青山飘移……那种惬意,那种感受,比沈从文老先生描写的湘西风光,还要爽目。
那时,我还不知道,楚国最早的都城就沉没于脚下这片水域。后来知道,考古部门在这里挖出许多震惊世界的青铜器。不知道,汉水下有文化悠久的均州古城,驾船后才听说:包公虎头铡杀的那个忘恩负义,意欲杀妻灭子的陈世美,就是均州人。均州人有自己的说法,他们绝不允许《铡美案》在均州家乡演出。原因很简单:真实的陈世美,讲情义,守信誉,是均州山水养育的好官。
这日傍晚,日朗气清,船队由马蹬启航,穿过奇峰峻拔的小三峡,已是明月升天。初升的圆月,金盆似地跳出水面,缓缓升高。把远远的江水映照得金光闪烁。碧月如洗,山河朦朦,“江清月近人”。诗意的江月,让我有了种凌空蹈虚的幻觉。不由想起了杜甫,想起他《旅夜抒怀》的诗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又想起苏轼、陆游、欧阳修和范仲俺,想起许许多多在生命过程中,“形在江海,心存魏阙”的千古贤者。他们的人生,都有“处江湖之远”的郁闷与放达;有于心不甘却既来则安的矛盾心理。当然,我不能与先贤相比,但放舟江河,亦有被贬的意味。因此,那种晴天丽日、碧水青山的心境,不是每天都有,更多的则是:失落、寂寞、惆怅、茫然。
舟行江湖,居无定所。船靠江岸,泊舟落锚,装货卸货,清点数目,手续交接,泊于热闹码头的时候毕竟不多。多数情况:拖轮将货驳送往一处荒凉的沟河港汊,便调头而去。一条并没长“腿”的船,停下装卸,要冷清好多天。遇上刮风下雨,大雪封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种清冷,何一个愁字了得。这些天里,除装卸货物,我只能跟师傅,一遍遍擦洗甲板,刷扫舱室,会把偌大的船舶内外,角角落落,擦洗得明光锃亮。
白天好过,夜晚,江天如漆,油灯一盏,人在一条船上,如同蚌在壳中。躺于窄窄床板,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起风了,初冬的大风卷起高浪,擂鼓般撞击着钢铁船底,砰砰作响,使夜深人寂的旷野荒水,也难安分。枕水待旦,不如披衣起床,悄悄走出船屋,目视茫茫夜空,感觉芸芸众生都被江河淹没了。远处看去,几点灯火,明灭闪烁,有点江枫渔火的意境。这便想起了落魄的张继。张继坐船至姑苏,不也是此般夜色增添了他的愁绪吗?“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江枫是他旅途的一处孤岛,可愁怅的张继会把灵魂融入江河,并随江河流淌了一千多年。诗人的生命便在江枫洲的钟声里得到提升……
我开始学着平衡自己。闲暇,一个人坐于船头的缆桩上,面对汪洋成翡翠的江河,去寻找河流的脉络,便听到了江河的呼吸……。时而,我读书、品浪,或漫步江岸,吟诵咀嚼唐诗、宋词、元曲……遇几条船在一起,就热闹了。我会加入到那些跑几十年江湖的老船工中间,侃大山,讲当年,听他们说些粗俗不堪的笑话。
船工说:“世上有三险:行船、跑马、上刀山”。“地下挖煤是埋了没死,水上行船是死了没埋”。当然,他们所指,是过去小木船行走的丹江山河。而今舟行烟波茫茫的丹江大湖,安全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在机关工作那些年,总会听到一些船工遇险或落水淹死的坏消息,也参加过遇难船工的丧事处理,亲自抬过落水船工的僵硬尸体……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溺水而死,在哭天抢地的家属面前,我的心会疼,会经受一次生与死的灵魂撞击。事隔多年,那些逝者的音容和姓名,仍留存于我记忆的书页。
起初上船,我曾为被矿石煤炭重压的船只,甲板与江水呈一个平面而担心;会为风浪颠簸的船只,浪花高高溅落船舱而惊骇。可看看身旁的老船工,竟闲庭信步般沉着,吊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驾船人忌讳说“翻”。船上时间长了,我也会“入乡随俗”,决不说“翻”这个不吉利字眼的。“船是三块板,转眼就翻脸,说句平常话,也像在吵架”。这是船工的性格写照。也难怪、常期的“水上漂”,危险随时都会降临,自然养成了他们嗓门大,话难听,出口就戗碴的脾性。可我发现:他们直来直去,不耍心眼,狠话、恶话说过,转眼就没事了,相互间又情同手足。
与他们接触,开始不习惯。时间一长,我觉得,这些人特别可爱,可交。遗憾的是,这样的船工生活只经历了半年。就是这半年,却让我读出了丹江船工的思想情感,爱恨苦乐;读懂了他们粗犷、坚毅,敢与大风浪一决高下的顽强。
在结束本篇文字之际,听说因南水北调搬迁于马蹬古镇遗址的航运公司,又要迁徙了。我在想,能写下这点文字,也许能告诉人们,不要忘了那曾生活在千古丹江上的一代代船工,不要忘了会产生历史故事的江畔水湄所发生的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