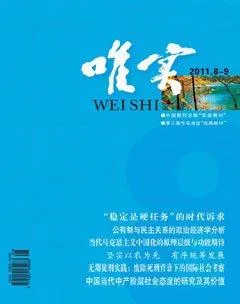转型时期农村信仰文化与道德秩序的重构
摘 要:目前,广大农村出现宗教返热现象,其本质是农民对实际生活幸福感和质量的一种功利性期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转型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态势密不可分。引导农民建构科学、合理的信仰文化和道德秩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途径。应因势利导,加强农村社区建设;遵循规律,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立足根本,健全农村保障机制;积极引导,使农民信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
关键词:转型时期;信仰;道德;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068-04
作者简介:高德群(1971- ),男,江苏启东人,中共启东市委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为深入了解农村集居地公共文化建设和新时期农民的心理状况,中共启东市委党校《东部沿海地区农民集居地社会学研究》课题组先后走访了启东近海镇、吕四港镇、启隆乡等乡镇和如皋、连云港等县市,展开专题调研共计6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然而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相左的是,很多农民在物质相对产生满足感的同时,幸福感却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文化的孤独感和价值取向的茫然带来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困惑和与之俱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部分地区出现宗教返潮现象,部分农民开始在教堂和经书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
一、农村宗教信仰现状分析(以启东市为例)
广大农村出现宗教返热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启东市宗教事务局的统计,目前,全市有佛教活动场所7处,僧职人员62人,相对固定的居士3000多人,善男信女60000多人;基督教堂所14处,信徒20000余人,教职人员20人;天主教堂所10处,教职人员12人,信徒12000多人。而道教和众多民间宗教信仰者,因其组织的松散、活动的原子化,难以统计出一个确定的数量和比例,但数量应更大。目前,信教群众数量有提速增长的趋势。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当下信教的农民表现出了与传统教徒很大的不同,他们很少真正地将信仰根植于生活、用于灵魂安顿,而是将几乎所有的心智和追求都放在了世俗生活和现有社会秩序的关注上,甚至不再相信来世。他们对宗教往往并不是真正地完全投入,而是多仅停留于相对比较实际、易操作化的层面,只是希望通过信仰上帝、神佛能带来现世的幸福生活和公正待遇。2010年12月25日,我们到启东汇龙镇北郊天主教堂调研,当晚共有1000多人次参加了该教堂举办的圣诞联谊会。随机调查其中36人进教堂的原因,有9人因好奇而来,占25%;陪同信众来的2人,占5%;相对虔诚的信徒25人,占70%。而问及信教缘由时,信徒中有超过80%的人答复是因病因灾或经商遇到坎坷,通过亲友介绍而入教。这种集未知性与现实性于一体的诉求,本质上是农民对实际生活幸福感和质量的一种功利性期望。
二、农民宗教信仰原因探析
马克思曾说过:“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1]毋庸置疑,当前农民宗教信仰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转型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态势是密不可分的。
1.社会保障因素。这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那些信教的村民在向不信教的村民传教时经常会用“信了精神好,不得病”、“保佑全家幸福平安”之类的理由来企图说服他们入教,而事实上这些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当初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加入教会的。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尤其是农村保障,总体上处于过度分割的状态,这是现阶段这一制度建设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农村保障体系含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五保户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以及计划生育夫妇养老保险、老年津贴制度、优抚制度等,过度分割的现实格局造成了制度“碎片化”现象;同时,保障水平太低也是一大顽症,尤其是农合、农保,其所产生的救济效应微乎其微,这也使得农村部分弱势群体在遇病遇灾之际的对抗力量弱化,因而试图通过宗教救济来缓解困境。
2.社会文化因素。一方面,家庭结构出现变化,并带来对传统家庭生活模式的冲击。由于社会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人群的不断流动等原因,传统的大家族聚族而居、大家庭阖家生活的模式基本不复存在。相当一部分父母不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代际之间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等互动行为迅速减少。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使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走出乡村,接触新的城市生活,而老人、妇女和孩子则多留守家园。无论是流动出去的打工者,还是家园的留守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多是空虚的,需要抚慰的。如果这时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群体予以他们必要的关心,那么宗教信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部分人的选择。
另一方面,社会单元的巨变带来对传统公共秩序和文化的冲击。农民在基本温饱满足之后,对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就会越来越迫切,对参加社会交往与得到社会认同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和需要。而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农民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机会大大减少,村民之间的日益疏远以及血缘关系的局限性使很多农民常常感到“边缘化”的弱势。农村社会传统上是熟人社会,村庄不断合并形成的大村失去了原有生产队性质的基层组织的向心力,各地兴建的村级服务中心虽然也设有棋牌室、图书室等活动场所,但因村庄太大、场所太小,而对绝大多数村民失去了亲合力。
3.宗教变革因素。宗教作为人类价值观的心灵构建,并非是脱离现实物质基础运作的文化体系,相反,它往往深深扎根于现实世界,与时演化,是人类对日常生活身心感受的另一种映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其在中国的发展尤其表现出贴近国人生活实际、甚至不惜改变原有教旨、教规的特点。比如,佛教近年来的发展与其世俗化、“人间化”的趋势密不可分,而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国化甚至地方化也是其近年来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4.农民心理因素。在当今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由贫富落差导致的巨大的心理失衡。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有力传播极大地刺激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但与城市居民或周边富裕农户生活状况的比较又使他们感到尴尬和痛苦。他们有了强大的物质需求,却没有实现这些需求的物质条件;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文化追求,却找不到表述的平台,对生活的无奈和乏力的心态就自然产生了。在这样的心态下,人们追求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幸福,而是自己如何比别人幸福,安贫乐道的恬淡心态在很多人身上已渐行渐远。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逐渐增强。而面对转型期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性”,诸如生活状态的不确定性、信仰价值体系的不唯一性、社会道德标准的模糊性等,又使很多农民感到无所适从和无助、孤独。当他们无法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信仰系统和文化系统对自己的价值观、生存观进行建构以理解世界的变化时,其中部分人往往就通过宗教获取解释。
三、宗教信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变动期,全球化浪潮冲击、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利益格局冲突加剧,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失衡,我们将随时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难题,和谐社会是在妥善应对和化解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构建完善的。宗教在此期间的规模化延续,尤其是信仰者人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明显增加,既是这些挑战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众多挑战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显示了社会应对和化解这些挑战的可能方式,其中,包括一些社会成员个人通过“信仰救济”而适应和纾缓某些困境、挑战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环境的宽松,在广大农村,宗教和民间信仰成为非常活跃的现象,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趋势,并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宗教信仰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华文化,包括新农村文化的有机组成。某些宗教信仰在特定的人群联谊工作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如民间祭祖、祀神活动已成为加强乡人联系的一个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宗教信仰成为促进各地经济社会对外联系的平台之一。“信仰搭台,经济唱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大规模的经济社会交流活动中往往可以看到文化交流活动的因素,文化与经济形成联动共生的局面,而文化交流中,宗教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往往会成为当地开展文化经贸活动的重要场所,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和发展旅游经济。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活动弥补和丰富了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发挥了部分道德教化功能。从总体上看,宗教信仰蕴含了教人敬畏感恩、惩恶扬善以及同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总体精神目标和理念,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诚信品质,倡导悲悯、慈善情怀,引导民众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因而能产生一定的社会伦理价值。而且,在当前仍然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状态下,宗教信徒中的捐献和义工劳动,以转移有形物质和劳动的形式,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贡献。对此,我们应予以承认并适当引导改造,使之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内涵,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
不可否认,宗教信仰具有消极的、迷信的成分和因素,并会淡化、冲击社会主义主流信仰,因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消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仰悄悄地发生了嬗变,原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信念、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精神有所消解。尽管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宗教信仰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需要引起关注。同时,随着信仰环境的宽松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乱建、滥建庙宇,浪费土地资源、社会财力的现象有所抬头;加之宗教信仰容易被利用来进行迷信活动,甚至与邪教鱼目混珠,误导部分农民;大型活动如组织不当,易引起突发事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负面影响。
四、农村信仰文化与道德秩序重构途径
农村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精神信仰为导航,信仰文化、道德秩序的长期被忽视将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引导农民由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跨越,引导农民建构科学、合理的信仰和道德秩序,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途径。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就整体而言,当代中国农民的主流信仰方向仍然是进步的、健康的和积极向上的,是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农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尤其是近年来的中央农村政策具有广泛的认同感。对于农民宗教信仰热,我们不必忌讳,但也不必过分担心。应有的态度是,透过宗教信仰的薄纱,感受当代农民的精神世界,理解并改变他们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来袭时所表现出的无助和迷茫。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受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
1.因势利导,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是在集体生活中完成和实现的,一个失去了健全集体生活的社会不可能拥有完整的道德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社区包括农民集居小区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在农村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居民组织,代表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另一方面,作为行政末梢组织,也是自上而下力量最为具体的承载体。它既指具体办事的组织、人员,也指作为群众活动中心的空间场所。中国乡村社会构造中存在着多元公共空间的发展时空,不同的村落社区既存在着以庙宇或宗族、宗祠为中心的祭祀仪式类型的传统公共活动中心,同时,还存在其他多种多样的公共空间表征形式,诸如村部、商店、红白喜事,等等。当前,乡村结构的变动典型表现为民间乡土多元社会公共空间和社会组织的不断萎缩,原有的家族式或行政式、区域式认同逐渐走向以个人关系为主的网络认同,农民的社会活动和行动关联日益减少,陌生化、原子化正逐步取代农村原有的乡土气息。
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