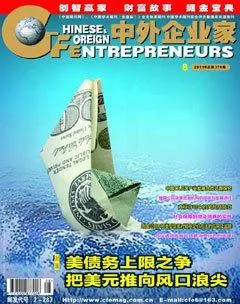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防范:利比亚危机的启示
2011-12-29 00:00:00程燕
中外企业家 2011年8期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来,已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但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海外企业除了承担商业风险外,还必须对政治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并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
利比亚危机给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如何应对政治风险提供了案例式的警示作用。本文从如何在投资前进行投资国的政治风险评估,如何在项目实施中进行政治风险的预警和政治风险的规避,如何在政治风险发生后妥善处理相关问题等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政治风险现实:
中资在利比亚损失严重
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发生战乱以后,中资项目全部搁浅。据统计,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工程项目的有75家企业,包括中国中冶、中国建筑、中国铁建、葛州坝集团等多家企业,其中大型项目50个,主要集中在基建和电信领域,涉及到的合同金额达188亿美元。在多国部队空袭前,有27个企业的工地、营地遭遇袭击与抢劫,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涉及到固定资产损失、承包工程垫付款损失、3万人员的大规模撤离等大量费用。更为严重的是利比亚战火纷飞,项目复工遥遥无期,将来的新政权是否接受原合同,都很难预测,所以利比亚战乱给中国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非洲,亦有大量的投资,2009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93.3亿美元,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仅安哥拉就超过30万人。至2006年底,我国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已超过3万起,至少有558名中国公民在海外被羁押或受当地社会动乱波及。因此,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关注政治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
政治风险评估: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指南
企业不仅要有经济风险评估,更应注重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政治风险一般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变化或触犯东道国的国家利益,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对国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评估由来已久。西方银行投资时往往有“好国家”与“坏国家”区分,并由此产生了国家风险评估理论。如美国人斯特芬·罗伯克(Stefan H· Robock)、杰夫利·西蒙(Jeffrey D.Simon )等人都有过专门的论著,提出了两组测试的指标, 一是政治制度稳定指数。该指数旨在为政治风险提供一个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个分指数构成: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和政府作用指数,其中社会冲突指数有三个分量:社会不安定、国内暴乱和统治危机。这些指数分别根据各类指标测定,从年鉴或政府文件等出版物中获得。二是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量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或10年的情况。它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
我国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经过2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已基本成形,但侧重点仍然在经济领域,对政府风险的关注度不够,许多企业在用好第三方咨询机构的风险评估结果上还不到位。其实,非洲所发生的政治动荡不是一天产生的,有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检索信息可以发现,这些出现动荡的国家,无一不是强势领导人长期执政的政权,有20年、30年的,利比亚的卡扎菲执政已达41年。长期执政、强势、独裁、严重腐败、失业率高企等,都会形成较高的政治风险。然而正是国内企业和机构缺乏风险意识,在迈向国际市场之初的急功近利心理,以及对两国关系及项目国领导人看好的盲目乐观态度,在多数人的“没想到”、“没想到”的惊叹中产生了“应该想到”的重大损失。
政治风险预警:企业稳定发展的风向标
一国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变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出现突变的事件,也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建立一个监控和预警系统,跟踪东道国及相关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化,使企业在政治风险到来之前赢得时间,并在突变发生时采取果断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东道国当地的民众认为外国公司抢走本地人工作的心理,往往会导致外国企业成为各国政治骚乱中民众民族主义情结宣泄的对象。此外,政治骚乱具有扩散效应,往往会从一国波及周边一些国家。从埃及的动荡到利比亚发生骚乱,中间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利比亚的中国企业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对局势进行判断,并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好准备,提前转移人员,保护好各种生产设备和资金,这将尽可能地降低骚乱给企业经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应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政治因素变动的机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企业、公民在海外的经营状况和安全问题,外交部专门设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相关部门也对各国投资环境进行了动态性的跟踪分析,并把信息向企业进行了通报。当前应加强权威性的预警系统,鉴于目前海外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的情况,或可在国务院增设海外投资监管部,与国资委平行,专司海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建立央企与各政府部门的海外投资纠错机制,作为企业内部监管与国资委等部门的外部监管衔接联动。政府可设立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专门机构,海外企业也应注重对当地情报的收集和汇总,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和信息的分析应用。各国有企业集团,应是海外国有企业的监管主体,应加快董事会制度建立的步伐,通过现有董事会、监事会在海外设立监事办公室等负责相关的预警工作。
政治风险规避:确保经济利益的安全阀
购买保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降低政治风险更为经济的一种选择。这种保险是海外企业以购买保险和担保的形式,将政治风险分解给保险公司。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旨在保护本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安全的保险机构。在美国,承担投资保险和担保的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它承担的政治风险有四种:(1)货币不可兑换;(2)没收;(3)战争、革命、暴乱和内战;(4)政治暴力事件。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承保企业的数量少。中国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方面的承保机构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信保)。在利比亚承包工程的数十家中国企业中,有7家向中信保投保,其中6家为国企,1家为民企,承保的范围非常有限。中国铁建选择的投保单位则由中外多个保险公司组成。二是法规不健全。198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投资风险(政治风险)条款》没有规定相应的为国内投资者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投保方式,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也仅限于商业保险关系的规范,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和保护尚没有相应的措施。因此,有必要形成完整的海外企业政治风险的保险机制。
要筹建亏损准备金制度。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同时在70年代专门设立了资源海外开放亏损准备金,以弥补其国内资源缺乏短板。我们国内也必须利用外汇储备、国有企业利润以及公共财政资金作为资金来源,设立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以缓解海外投资企业失利所造成的资金短缺。
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目前我国已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今后,一方面要扩大与世界各国签订协定的范围,另一方面,把重点放在一些容易产生政治动荡的国家,推动东道国政府对中资企业提供足够的保护,依靠国内立法与国际双边和多边协定的紧密配合来为我国境外投资提供担保。我们的企业和员工也需要与当地社会搞好关系作为自己的外部防卫,以便在危机出现时尽量减少损失。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需要切实保护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防止这些国家政权更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外资企业国有化”行为,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企业利益。
架构起严厉的问责机制。加大对投资责任人的奖惩力度,做到权责分明。如投资获利,则给予责任人相应奖励。投资失败,如果决策程序合法,至少要负领导责任,或调离岗位或引咎辞职;而若决策程序违法,则要负刑事责任。
政治风险善后:从被动中寻求主动
出现政治危机后,应制定和完善在东道国的资产保全方案,首先开展资产清查和损失评估工作,包括在东道国的资产总体情况,直接和预期经济损失,我国企业开具的各类保函情况,要求企业人员在撤离时及时撤出或妥善处置与企业资产及应收款等有关单据、凭证等资料,确保今后对外交涉时有据可依,并对项目现场遗留的设施、车辆、材料等资产采取先期处置措施。通过我国驻外使馆,要求保护我国的资产安全,与当地政府或业主进行沟通,寻求他们对我国资产的有效保护。密切跟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形势,制定出分国别的应急预案。坚持中立立场,不干涉他国内政,尽量少评论东道国政局,静观其变,在适当的时候与多方接触,展开对话,以期在将来无论谁胜出,都能按照国际惯例继承上届政府的债务。在确定基本的损失后,即可向有关的保险机构启动理赔程序,申请保险赔付。3月18日,中信保已向葛州坝集团、中建材集团支付利比亚工程承包项目信用保险逾2亿元。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