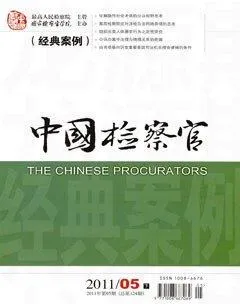威逼\\骗取银行卡及密
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刘某系恋爱关系。交往中,王某经常花刘某的钱。2009年6月19日,二人在某旅馆开房,当晚发生性关系。次日,王某又向刘某要钱,取钱时,王某一直想看刘银行卡的余额和密码,刘某不让,王某很生气,二人分开后,王给刘打电话、发短信叫刘回旅馆,刘都无反应。后王又发短信,称“已将二人发生性关系的过程用手机录了像,还给刘拍了裸照,如果刘不回来,就将二人发生性关系的录像寄给她父亲”(其实王某所说的“录像”并不存在)。8时许,刘某回到旅馆,王某逼问刘银行卡的下落并对刘某搜身,刘告诉王银行卡锁在宿舍,王用刘的手机给刘同宿舍的朋友赵某打电话,谎称刘某病了,托赵某快把刘某的银行卡送来。王某取到卡后,又继续追问银行卡密码,并威胁若王某不说就把性关系录像寄给刘的父亲,又说只想看看卡内余额,看看刘是不是真心喜欢他。后刘某告诉了王银行卡密码。王某一人到取款机处取出4900元。卡内仅剩几十元。取钱后王某逃回外地老家,挥霍赃款。刘某报案。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理由是:王某以向被害人刘某父亲发送性关系录像及裸照对被害人进行要挟,迫使被害人交出银行卡及密码从而取得钱资。其采用威胁和要挟的手段强行索要财物,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诈骗罪。理由是:刘某之所以告诉王某银行卡密码,是相信王某所说的查看卡内余额,检验自己对王某的真心。王某利用感情因素进行欺骗是其取得财物的主要手段,应当定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罪。理由是:王某前期取得信用卡和密码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实现侵财的目的,其到ATM机上取款的盗窃行为才使其实现了对刘某钱资的非法占有,故本案应定盗窃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一)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信用卡”类犯罪的定罪思路纠结,对适用不利
从现有的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信用卡”类犯罪的规定可以看出,以获取信用卡的先行手段行为确定犯罪性质,如盗窃所得即为盗窃罪,抢劫所得即为抢劫罪,其后的冒用行为被先行的手段行为吸收。而由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非犯罪的手段行为,无法界定犯罪,则以其冒用行为定罪,即定信用卡诈骗罪。照此思路,如果仅仅以单一的行为获取银行卡,认定犯罪和计算犯罪数额尚可,但如果行为人获取银行卡时采取了多种手段,综合奏效获得信用卡,究竟以何种手段行为为全案定性,就难以裁夺。况且,除获取银行卡外,获取银行卡密码也是需要相应手段的,又如何评断呢?如本案事实,王某与刘某系恋爱关系,王某软硬兼施,连哄带骗,恐怕不能单独以敲诈勒索或诈骗来界定全案的手段行为。因此,这种定罪思路是不科学的,往往造成无谓的分歧。
(二)应以侵财犯罪诸实施行为中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来界定财产犯罪的性质
我国刑法将犯罪分为不同的构成要件,就是要个别地分析诸多行为中哪个是造成危害结果的真正行为:在侵财犯罪中,就是要查明哪个行为造成了侵财结果的发生,该行为的性质就是犯罪的性质。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中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所以,银行卡只是财物凭证,银行卡的损失并不就等于财产损失。如果行为人获取银行卡后,并未使用,所有人的财产也不会受损。因此,行为人得到银行卡后,获取钱资行为的性质决定了犯罪的性质。本案中王某不论是以敲诈勒索的手段还是以诈骗的手段获取了银行卡及密码,如果没有后续的取款行为,刘某的财产都不会有所损失,所以,敲诈勒索或者诈骗都表征不了本案的性质。如果行为人在获取银行卡的过程中造成了其他侵害后果,如伤害、杀人等,与获取卡内钱资的行为应予并罚。
再从侵财犯罪的构成特征来看,认定敲诈勒索罪或者诈骗罪也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前期行为所得与实际侵财损失并非同一,本案敲诈勒索或诈骗行为所得仅为银行卡,而非卡内钱资,而侵财的损失则是银行资金。其次,犯罪行为与获取财物无直接关系。行为人实施敲诈勒索或诈骗行为后只依赖于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就能获得财物,而不需要再另外实施其他违法行为,方可构成该二罪。而本案王某又实施了去ATM机上取钱的行为才实现了非法占有,故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不能成立。
(三)王某获得刘某银行卡,通过ATM机取款挥霍,应定盗窃罪
对于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提款的行为如何认定,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冒用持卡人的身份骗取银行钱资,是典型的诈骗行为,应定信用卡诈骗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获取财物的行为实际上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应认定盗窃罪。笔者同意定盗窃罪的观点。
对此类行为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行为人在柜台取钱,就定诈骗罪,在ATM机上取钱就定盗窃,认为前者欺骗了银行工作人员。笔者不敢苟同。通过银行工作人员和通过ATM机提款,二者都是在业务规程的范围内加以判断,工作人员的大脑分析逻辑和ATM机的工作逻辑是相同的。如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第7条第1款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交易的,发卡机构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各类结算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也就是说,只要提款人提供了密码,银行工作人员或者ATM机都要支付现金,而该章程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未使用密码进行交易。则登记持卡人有效证件号码及签字的交易凭证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则进一步说明,银行工作人员对于取款人的审查仅只形式审查,无需分析判断提款人持有信用卡是否有犯罪或其他不法背景。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因错误认识而交付的情形,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明盗或晴盗,都应定盗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