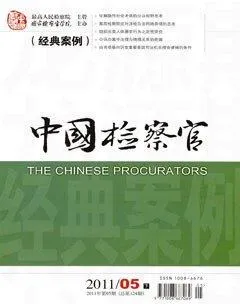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中的两个问题
[案例一]林某等走私案(简称“熊胆案”):2010年1月19日,中国公民林某、齐某出境至俄罗斯境内。从一俄籍男子处分别购买11只熊胆和4只熊胆,并由林某将15只熊胆委托殷某帮助带回国。次日,林某又交给殷某10只熊胆。殷某于21日将熊胆藏匿于其驾驶的货车发动机与扶手箱间的夹层内,从虎林口岸走私进境。齐某还于当天从虎林口岸旅检通道进境时携带虎牙2枚。经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黑龙江省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批熊胆总价值人民币50万余元;2枚虎牙价值12万元。本案中,辨方提出,俄罗斯境内允许珍贵动物制品交易,且被告不具有牟利目的,以及价格鉴定过高。法院判决,三被告人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并分别判处了相应的有期徒刑和罚金。此外,案件中认定的证据全部由我国公安机关在本国境内取得。
[案例二]吐尔迪尤夫走私羚羊角案件(简称“羚羊角案”):吐尔迪尤夫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公民。2002年9月23日,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入我国霍尔果斯口岸。在通过海关检查时,在其地毯中发现藏有羚羊角。后经鉴定,被告人携带入境的羚羊角有2公斤,价值36万元。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吐尔迪尤夫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1万元。吐尔迪尤夫提起上诉,辩称其过境时已向他国海关申报过自带的羚羊角,不应认定为走私。二审法院认为其仅向他国海关申报,而没有向中国海关申报,应认定其行为是走私,对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但考虑上诉人所在国对羚羊角管理和其走私羚羊角数量较少等特殊情况,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故撤销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吐尔迪尤夫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驱逐出境。
一、两案的比较分析
两案案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处理结果却有很大差别。两案所凸显出的主要法律问题有两个:(1)实体法律问题。购买地国家未将买卖、走私某种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进入我国后还应否作为犯罪来处理?(2)程序法律问题。应否将外国法的规定作为走私案件的证据?刑事案件中如何查明外国法?
两案相似点很明显,都是违反我国海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珍贵动物制品走私进中国境内,且数额很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条第4款第2项规定,两案均属“情节特别严重”,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熊胆案中,被告人走私熊胆总价值逾50万元,法院考虑到被告人有自首等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因而判处林某等被告人不等之有期徒刑。羚羊角案中,被告人走私羚羊角总价值36万元,一审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二审法院改判为驱逐出境。
除了最终处理结果之差异悬殊外,两案主要还有三个差异点:
第一,珍贵动物制品产地国的法律上存在差异。熊胆案中熊胆的产地国为俄罗斯,其刑法并未将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作为特定的犯罪对象加以保护,走私上述物品价值较大的,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88条规定的走私罪处罚。但未经许可经营珍贵动物制品,如果价值不大的,虽不属犯罪行为,但仍具有违法性。上述这类对象保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政府部门性文件中,公民经许可,可以按照许可证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依法猎获、收集、豢养、购买、出售或邮寄珍贵动物的制成品、躯体的部分或派生物;如果违反规定,也只是给予行政处罚。羚羊角案中,被告人本国吉尔吉斯斯坦并未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未视其为违法行为。二审法院改判的理由即是:吉尔吉斯斯坦并没有将羚羊列入珍贵野生动物的范围,在立法上也没有关于保护羚羊的规定;在吉尔吉斯斯坦,野生的羚羊比较多,羚羊自然脱落在地上的骨角也很容易找到,价值并不高,因此,其国人将羚羊角带出本国不那么受限制。
第二,被告人国籍不同。国籍因素,并非走私犯罪的要件要素,不过,由于不同国家法律规定不同,其公民对其本国法律认识,会影响到他对在其他国家行为是否合法的认识,即违法性认识。当然,国籍不同也会影响到刑罚适用上的差异。对外国人刑罚适用存在显性和隐性的差异:显性差异,就是对外国人可以适用驱逐出境(《刑法》第35条);隐性差异,就是对外国人量刑时有特殊的政策考量。
第三,被告人对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认识不同。熊胆案中,被告人作为中国公民,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走私熊胆行为为国家所禁止;而在羚羊角案中,被告人为吉尔吉斯坦公民,如二审法院裁判理由,其本国并不认为购买、走私羚羊角为犯罪,且被告在通过其本国海关时,并未受到拦阻、查获,因而其辩解不知道中国法律对该项行为予以禁止,可以认为其存在法律认识错误,进而应考虑是否影响到其犯罪故意的成立。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案情介绍看,在羚羊角案巾,二审法院改判理由中提及,羚羊角在被告人本国的价值并不高。二审法院提及此项理由,其意图并不明确,即究竟想表明,被告人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要素(即犯罪数额)存在认识上的差异,还是想说明其行为客观的危害程度不大?由于法院是在量刑时考虑该因素,因而其很可能还是将其作为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一个事实因素。
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才导致两个看起来相似的案件,其处理结果存在巨大悬殊。
二、实体法问题:走私案件中的违法性认识问题
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条规定:“珍贵动物制品购买地允许交易,情节较轻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如果达到《解释》第4条第3款、第4款规定的量刑标准,一般相应地要从宽处罚。”该条解释性意见的根据究竟为何,有必要加以考虑。具体而言,该条认为“一般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是因为如此影响到刑事违法性的成立,还是属于《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抑或是因为行为人可能缺乏违法性认识,而影响到定罪和量刑上的处理?还是单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
走私犯罪属于行为犯,走私行为所历经的国家,都可以主张属地管辖权。就上述两案而言,法院的管辖权依据都是《刑法》第6条的规定。因而,即便是走私物品的流出国不禁止或者不限制该物品流入外国。但只要违背我国法律规定,即具有违法性,如果进而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一走私犯罪的犯罪构成,就应当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无论珍贵动物制品购买地,对该问题是何种态度,根据我国刑法进行判断时,都不影响走私该制品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的成立。
该解释性意见的根据,也并非《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的第一个法定刑幅度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起刑点比较高,即便制品购买地允许交易,这一因素也不应使该行为的危害程度就降低到无罪的程度。
从违法性认识方面来探讨该条解释性意见的法理根据,与该条规定的内容并不符合。具体而言,如果行为人因为“购买地允许交易”,确实没有认识到该行为在中国是违法行为,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行为人知道中国相关法律的情况下(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那么,这一错误认识足以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进而不认为该行为构成犯罪。不过,该条解释性意见的内涵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理论分析:首先,该解释性意见并没有强调行为人的认识问题,换言之,只要“购买地允许交易”,情节较轻的,即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其次,对于情节严重的行为,即便“购买地允许交易”,也应定罪,只是相对于“购买地不允许交易”的情形,要从宽量刑。而按照上述理论分析路径,即便情节严重,也应做无罪处理,因为根本就缺乏犯罪故意。
当然可以用刑事政策的考量来理解该解释性意见的意旨,但这样并不能说明其合法性问题,在法理上也难以予以澄清。比较而言,以违法性认识是否属于不可避免的欠缺,来重新诠释这种情形下,对行为人作无罪处理的法理根据,更为妥当。但是,如此就要对该解释性意见作重新表述,如“珍贵动物制品购买地允许交易,且,行为人不知道走私该制品行为为我国法律所禁止”。
三、程序法问题: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中外国法的查明
对于多数“由外向内”走私的案件而言,只要有物证、书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将某种物品向中国境内走私,即便所有证据都在国内取得,一般也都可以认定行为人走私事实的存在。但对于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而言,由于《意见》中明确规定,购买地法律规定影响到定罪量刑问题。因而有必要查明购买地国家相关法律的内容。熊胆案和羚羊角案的审理过程中,辩方都提出这一辩护意见。在熊胆案中,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并没有直接对该问题作出回应,在证据目录中也未列明俄罗斯刑法及有关行政法律的规定。
我国法院对某一案件裁判关涉到外国法律的规定时,该外国法规定属于事实部分,应在证据目录中列明。就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刑事案件来讲,购买地国法律(以及流出国法律)的规定,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在刑事判决书中列明外国法的规定,以及取得渠道。
对于外国法律规定的获取问题,在国际司法协助中被称为“外国法的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于涉外民事案件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但在涉外刑事案件方面,尚无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对此,如果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缔结有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应根据该条约所确定的方式获取该国法律规定。此外,考虑到司法协助的周期漫长且程序繁琐,由我国驻外国使领馆取得,和外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也可以作为查明外国法的一种方式予以采用。
至于是否可以由中外法律专家来提供,尚有讨论的余地。我们考虑到目前国家间法律合作的现实情况,可以有条件地采纳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的方式。具体而言,法院在通过上述途径无法有效查明外国法,或者我国与相关国家之间没有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乃至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要求有关专家提供外国法的内容,在无有效之相反意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最后,考虑到刑事案件采取较高的证据标准,由当事人提供有关外国法的规定,难以排除合理怀疑,因而当事人自行提供的方式应当不被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