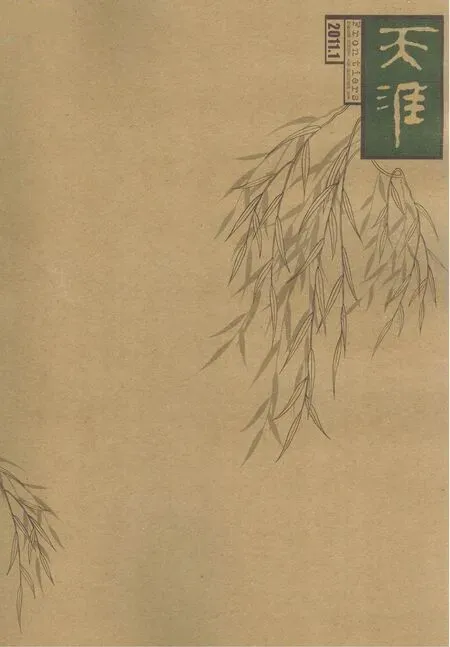总有一天
曹明霞
老派是警察,可他那歪戴的帽子和略显肥大的衣服,使他像个超市门口的小保安。特别是腮上两块永不褪色的红脸蛋儿,怎么都摆脱不了进城农民工的样子。而事实上,老派来这个城市二十多年了,如今已经混出了不错的身份,裕东区派出所的副所长。
老派慢着步子来到贵妃洗浴城门前,门前的广场很空寂,一辆汽车都没有。这里刚被扫过,且这一次扫得比较重,半个月的时间了,周遭还像秋风扫过的落叶,一派凋零。人,也都霜打了一样,没多大精神。
贵妃洗浴城的老板娘胡长花,此刻正倚门远望,像个多情又闲愁的妇人,“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看着眼前走来的一歪一歪的老派,胡长花忙晃掉眼神儿里的企盼,凑出一脸合适的笑容:“老派,您可有日子没来了。”
老派背着手,淡淡地说:“又开张了?”
“不开张吃什么,这年头儿。老派,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干这个,搁从前,洗脚剃头,这都是下三烂干的,算下九流啊。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干这个呢?”
老派径自向里走,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胡长花这才看清,老派不是帽子戴歪了,而是他的脖子有点歪,是歪脖子带动了整个身子,才显得歪的。
胡长花赶紧回过身,跟老派进来。她冲屋内的一女子使眼色,让她快些招待老派。胡长花平时跟老派没什么交情,她一直受正所长的保护,老正才是铁杆朋友,有近十年的关系了。正所长来这里,就如同回到家。正所长有时不来,打个电话或让来人持条,胡长花一律免单的。而副所长老派,是没这个基础的。不幸的是这次扫黄,正所长栽进去了。胡长花怀疑是老派干的。恨归恨,胡长花也不敢慢怠老派,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做生意,谁给你使个绊儿,都不得消停。阎王要怕,小鬼儿也得敬,不然指不定哪就穿帮儿漏水,翻船。
“老板娘”——老派坐了下来,从自己衣兜里掏出一枝烟,点上。而另一小女子送上的烟和火儿,被老派挥挥手,谢绝了。
胡长花没有丈夫,她带着儿子寡居多年,儿子现在正上着本市的一个什么大专班,花销很大。贵妃洗浴城的一半收入,被儿子花掉了。但是没办法,这也比放到社会上强,胡长花知道,把儿子放出校门,让他趟进社会,就完了,他离监狱也就不远了。胡长花到底是哪里人,没有人猜得出。她偶尔的方言里,带着东北口音,但胡长花否认自己是东北人。胡长花是这里的真正老板,谁都没见过她丈夫,可人们习惯叫她老板娘。
“老板娘——”老派向后仰了仰身,力求舒服一些。他说我今天来,主要是调查你们这儿的小吴,叫吴梦梦吧,她到底哪儿去了。一个大活人没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胡长花又冲小姐使眼色,一旁侍立的小姐赶紧拿出一双消过毒的拖鞋,蹲下了身,准备给老派换鞋。
“别!”老派两脚被烫了一样高高地擎起,他说别别,别这样,我今天不是来洗澡的,我有公事。
“老派,有事你就说嘛。怎么翻脸不认人了?莫非你是中央派下来的巡视检查团,拒腐蚀永不沾?在我这儿免费洗个澡儿,就得丢乌纱帽?”胡长花说起话来蹦豆一样咔巴溜脆,那双月牙一样好看的眼睛,黑白分明。虽然年过四十了,白净的皮肤还不老,瘦鼻梁,尖下巴,瓜子脸,属于巩俐版的美人。
老派心有所动,但脸上尽量保持不动。
胡长花知道老派对她有意思,这份意思好像都胜过了那些年轻的女子们。别的男人来了都是直奔小姐,而老派一直对胡长花情有独钟。但胡长花为人还是有些技巧的,她把和老派的关系,维持得像远房的表兄妹:有热情,有招待,但热情和招待里,分明是一种界线分明的客气,是这份客气,使老派一直不得造次。胡长花知道,吃这碗饭,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身兼二职啊。
老派内心很愤恨,装什么装啊,你靠了老正这么多年,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嫌我官小嘛,嘁。女人啊,你们的名字是鼠目寸光!是唯利是图!
其实老派只猜对了一半,女人除了唯利是图,在贪色上,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她们也愿意挑漂亮的、好看的、长得顺眼的。老正除了比老派官大一级,相貌也要比他堂堂多了,一米八的个子,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高挺的鼻梁和那双陈道明式的小眼睛,又狠又硬,是当下女人都看好的硬派风貌。哪像他老派啊,瘦小枯干的,走道还一歪一歪的。
看着胡长花风情的柳叶眉,老派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一点,不那么紧绷绷的了。他说:“我真是来找吴梦梦的,有群众举报,说吴梦梦失踪了。”
“失踪?怎么会。她回老家了。不信,你问小保。是他亲眼看着她上火车的。”胡长花回头喊了一声“小保”。
小保从乡下来没多久,按辈分,他管胡长花叫姑奶,现在是洗浴城的保安。听姑奶要他作证,他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蹭地一下从门里冒出来,说:“派所长,我是看见她上火车的,她说她回老家。”
小保说完话,乡下女孩儿一样两手捏弄衣角,两只脚也扭来扭去的。
“她老家是哪里?”
“谁知道,一会儿说四川,一会儿说东北。”
“到底是哪?”
“真不知道。”小保看向了他的姑奶。
“你不是看着她上的火车吗?开往哪里的火车呀?”
“火车我没看见,我看见她进候车室了。当时人多,我一眨眼,就找不见她了。”
“吴梦梦,鬼得很,是个天生的撒谎精。哪儿是她老家,全国各地,都被她说了个遍,就差没说中南海了。谁都逮不准她的老家到底在哪里。”胡长花接过小保的话,对老派说。
“你们不是押她身份证了吗?”
“唉,老派,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也知道,要她们身份证,是没多大用的。现在人的全身器官都能造假,做几个假身份证,还不跟玩似的。对她们,我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没事儿的时候你可以睁眼闭眼,现在人没了,你闭眼,上边的人闭眼吗?这次严打,上边有精神,从重从快。当然,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现在,一个大活人没有了,又有群众盯着,我不好交代。”
吴梦梦是去年秋天来到贵妃洗浴城的。当时洗浴城的门玻璃上,贴着一纸招工广告:本店诚招服务员,技工最好,待遇面议。
招工广告写得如此简单,宽松,没有要求个头儿,也没有年龄限制,真是好哇。吴梦梦知道,就是一般小酒店,招工也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高一米六零以上的。而这里什么都没提,吴梦梦就来了。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五,可她的容貌长得非常靓丽。
面试那天,她的对面只坐着老板娘,也就是胡长花。胡长花刚跟她要证件看,门推开了,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孩。男孩走到胡长花面前,什么都没说,胡长花就递到他手里一沓钱。男孩拿完钱,该转身出去的,可是他没走,停了下来,深深地看着吴梦梦,说咦,你叫什么名字?你长得可真像我一个女同学。
吴梦梦淡淡一笑,她不用胡长花介绍,就能看出这是母子了。孩子的那双眼睛,太像他母亲了。没等她说什么,胡长花严厉地看了一眼儿子,说忙去吧,妈妈正谈工作。
男孩转身走了。
“老板,我没有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丢了。”
胡长花第一次听人管她叫老板,而且是眼前这个矮个儿女孩。胡长花感到了她的不一般。同时她还想,这小女子,连个假身份证都懒得做,上来就说丢了,算个老江湖。“证件丢了,押金也行。一千块。走时退。”胡长花说。
吴梦梦两手在兜里抠动了半天,胡长花以为她在掏钱,她掏出的是一粒瓜子。嘎巴儿一声,嗑掉皮,吃了。她说我一分钱都没有,有一千块钱,我就不来你这了,一千块钱,我可以自己干点什么了。吴梦梦说这话时脸上白白的,一点都没有脸红。
“五百吧,五百也行。我是看你长的挺好,才拦腰斩的。换别人,少一分,我都不留。”
“我真的没有。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你没看,我就剩这一粒瓜子了。”吴梦梦用手举着半瓣瓜子皮,她的小手擎在空中,就是那一刻,胡长花决定把吴梦梦留下的。就是给她倒发工资,胡长花都不让她走了。胡长花没有文化,如果她读过古诗词,一定会想到“红酥手”这样的词句。吴梦梦的手指,象牙一样尖润,饱满,这样的手,天生是干这行的。
胡长花算得上伯乐,她没有走眼,她把吴梦梦留了下来。只一个月,冲吴梦梦的这双手纷至沓来的客人,已经排队候着了。吴梦梦的手就像搂钱的金耙子,给老板娘搂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民币。
可是,前不久,也就是春天的时候,说是北京的哪位大人物要来,突然扫了一次黄,连折了胡长花两员大将。而往年,春秋扫,年节扫,都是有规律的,说是净化环境。这一规律就像三八要过妇女节、八一建军、十一国庆一样,胡长花心里都有准备。另外只要有大规模的行动,正所长都会提前通知她的,让她收拾好,可是这次,连正所长都不知道。
那天,那些人天兵天将一般,呼啦啦就冲进来了,他们撞开门后洪水一样涌进,保安小保被冲得球一样满地咕噜,录像的录像,逮现形的逮现形。这些人逮这个很有经验,他们不进走廊两侧光明正大摆在那儿的门,而是直扑墙一样的暗门,一下子推开一番新天地,一对一对的男女,一点准备都没有,原生态地亮给了他们。第一对儿揪起的,是吴梦梦和黄处长。黄处长是市政府的,他叫什么,没人知道。他是什么处的处长,也一直是个秘密。反正黄处长是正所长的客人,一般情况,正所长都会亲自陪同。至于黄处长是个什么官儿,看正所长对他的那份恭敬,就知道孬不了,不是管干部的,就是管人事的,最次是个管钱的。
黄处长的头发平时都用摩丝固定,那天因刚洗过澡,就进入了下一环节,没有打理头发。被突然的闯入者,搞得很狼狈。好在他眼尖,看到了扛摄像机身后的那个人,他认识,那个人家的孩子去年择校就是他帮的忙,人情很重的。当时那人一看是黄处长,正想退后一步溜走,躲开,可是黄处长的眼睛钩子一样钩住了他,使他不得脱身。
那人只好说:“咱们文明执法,让人家把衣服穿完。”
黄处长和吴梦梦,就把衣服穿整齐了。
那天最冤的要数正所长,他什么都没干,只是把吴梦梦领给了黄处长,就被以皮条客的罪,也抓进去了。
后来黄处长被罚没罚钱,关了几天,大家不得而知。吴梦梦是在关了十三天后,老板娘用一千五百块钱赎出来的。按行情,吴梦梦要罚五千块,是有人帮忙通融,给讲到了三千块。可是胡长花说,三千我也拿不起,三千不行。关的人说,再拿不出钱,超过十五天,人就送走了,劳教。你一分钱都挣不着了,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胡长花又去求了人,最后价钱讲到了一千五百块。对方说不能再少了,再少,我们这都说不过去了。就是自己家人,碰到这种事儿,该出点血也总要出血的。
胡长花带着一千五百块钱,亲自接的吴梦梦,交钱领人。
回来的路上,吴梦梦的脸还是白白的,不知这十多天她是怎么过来的。胡长花吃这行饭,对监狱、看守所,包括黑白两道,都是有些了解的。她听说,进了犯人的堆儿,啥都不论,先挨上一顿好揍,饭和水都用屎尿顶替了。可此时,吴梦梦的脸上白白净净,光泽也有,好像她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
胡长花这一场损失惨重,损兵折将,还被抄走了一些东西。东西没了可以再置,胡长花最心疼的是这两个人。吴梦梦好歹赎出来了,而另一个小姐,因为被发现她还吸毒,强制送到戒毒所去了。拿多少钱,都赎不出来的。
“梦梦,这次赎你,我给人家交了三千块钱。”胡长花把金额多说了一倍,看来她也是要挣一点的,她不甘心羊毛出在鸡身上。
“用我的押金顶吧。我头俩月不是白干的嘛,你说扣了我一千,我问过客人了,他们的小费你一共扣掉我两千块还有零头呢。”
“行。那也行,就算两千。顶账了。这回,你好好干,这一扫,咱们损失可大了,机器拉走了三台,真他妈狠。这回你卖点力,头一个月,有多少算多少,就当押金了,是那个意思。以后的,咱们就按规矩分。”
“老板,你再扣不着我的钱了,我不干了。”
“不干了?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干了。”
“你不干了我的三千块钱怎么办?”
“不是让你拿押金顶嘛。”
“那两个钱,够吗?你在我这混这么长时间了,是那两个钱儿就能顶的吗?”
“老板,你要这么说,我就没办法了。你也知道,这一进去,没让我光着出来就不错了。你看,我的耳钉、手链儿都没了。够不够,就那些了。再不行,你找黄处长要吧,找正所长也行。”
“咦,你个狼心狗肺的,我赎的是你,你却让我找他们要钱,你可倒挺会指派。”
吴梦梦不说话,打开车门,跳下去,步行着向贵妃洗浴城的方向走。“小保你跟上她,看看小妖精又做什么。我自己来开。”胡长花上了小保的驾驶员位置,小保则下了车,跟在吴梦梦身后。
吴梦梦进到洗浴城,直奔走廊尽头自己的柜子,那个一尺见方的柜子里,锁着她的全部家当。柜子上的锁,全部都豁了,里面的东西,零落的散在那里。她掏出一件黑纱裙,前胸已经被撕开了,再看鞋子,跟儿也掉了一只。那只装化妆品的小包,立在角上。吴梦梦仿佛看见了当时的情景:柜子里的东西全被扬到了地上,杂乱的脚步踏过之后,就缺胳膊少腿成了现在的样子。
吴梦梦蹲了下来,她有点头晕。蹲了一小会儿,两手握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拳头,支着脑袋。她说:“跟着我干什么?我又不偷东西。”
“偷倒没什么怕偷,主要是怕你跑了。”小保说。
“我跑,我又不欠你们钱,跑什么。”
“我们白赎你了?”
“押金顶了。”
“真没良心。就欠把你送回去,劳教你三年,让你蹲死里头哩。”
“有能耐你送?你送?”吴梦梦噌地站起来,直视着小保,鼻子快顶到了小保的下巴上,“小土包子,才来几天,长能耐了,心也练得狠起来了,还要送我。”吴梦梦的近距离把小保逼视得眼皮儿直哆嗦。
小保这些硬话,都是跟姑奶学的。他的内心,是舍不得送吴梦梦去劳教的。他刚来到这灯红酒绿的世界时,不但对梦梦,对所有的小姐都算得上一见钟情。有一段时间,他差不多爱过所有的女孩子,尽管他知道这些女孩已经都不是女孩了。小保想,如果有钱,他就把她们都娶回家去,救她们出水火。可是小保知道,自己不但没有钱,自己挣的,就是把她们送进屋里去的钱。那时看着梦梦跟客人进屋,小保曾气得流下了眼泪。是老板,他的姑奶,一个脖溜子打醒了他,姑奶说:知道为什么不能让黄鼠狼给鸡看家吗?他会把窝儿里全祸害喽。你小子要是想吃窝边草,赶快给我滚蛋!你爹那病也就别治了。
现在,面对吴梦梦的鼻子,小保没有退步。他说,冲我瞪眼睛,没用。老板让我看着你的,有事你找她。
胡长花回来了,她没有理吴梦梦,进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打理干净,才出来。老板胡长花是不怒自威的,不然也吃不了这碗饭。她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叫吴梦梦,还有另几个女孩:“吃饭吧。吃饭。”
吴梦梦把自己的包收拾好了,一塑料袋都没装满。她知道自己不该来桌前吃这个饭,这饭她吃得很没意思。可是她实在太饿了,不是她坐上来,是她的胃,把她拱到了座位上。
老板说,过去的事儿,咱们不提了,晦气。咱们向前看,国家还在向前看呢,咱们有什么理由向后看?从明天开始,重新打鼓另开张,把那帮阎王小鬼儿们给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了鼓励你们好好干,提成上咱们改一下,我少挣点。三七,改四六了。大家有本事使吧。
小姐们多数露出了笑脸,只有吴梦梦,像没听见一样。
吃完饭,吴梦梦拎着她的塑料袋子,哗啦哗啦走到老板跟前。不等她说话,老板说,梦梦,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你走不了。
吴梦梦立在那里,不说话。但她的眼睛说了很多,胡长花都听明白了。
胡长花看着她的脸,语气有所缓和,说:“梦梦,你实打实地再帮我挣上半年的钱,仨月也行,我就放你走。真的,我说话算数。”
“我家里出事了,一天都不能再呆,真的。”
“什么事?不是你爹病了吧,或你妈瘫痪在床?”老板娘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我弟弟病了。”
“你怎么不说你家炕上还躺着个急等钱用的老奶奶?——可惜呀,这些话你应该对那些嫖客说去,让他们可怜你!还能多弄点钱。”
吴梦梦的眼睛变成了两把刀子。
“你先给我写张欠条吧。这次赎你的钱,这个账你认吧?”
“可是你那儿还有我两千块钱的押金呢。”
“一码是一码,你先给我把赎金打个欠条吧。”
“写完让我走?”
“梦梦,你不要得寸进尺,拿我的好心当驴肝肺,以为我没办法治你。告诉你,你如果不写,我照样把你送回去,信不信?”老板半边脸沉边半脸笑地看着她,“你要是觉得那里的日子好过,我也不强请你出来。”
吴梦梦坐了下来。
胡长花看她动摇了,接着说:三年劳教,出来的小姐都说就是卖上一辈子,都不愿再迈那个大门。这十多天,你还没尝到滋味?——看守所这几天和劳改队相比,那可是天堂地狱!
吴梦梦说我写,写,你不用再吓唬我了。你不就是公安局里有人嘛,我知道你本事大,把那些人都喂好了。可是,你也别太狂了,这次扫,你不也没接到通知嘛,也有不灵的时候。天下很大,公安局也不是你一家开的。
小保递给了吴梦梦纸和笔。
吴梦梦的欠据写完了,老板拿上条儿,说你想招儿吧,还上钱,就走人。不然,走不脱这个门。
我又没卖给你,你凭什么囚我?比旧社会的老鸨还狠呢。呸!
一个星期过去了,别的小姐都开工了,该干嘛干嘛,可吴梦梦还是干吃饭,不干活。她也知道,这样下去,饭钱又要欠一大笔。
她走一步,小保就跟她一步。就是上厕所,小保都堵在门口。那天,吴梦梦已经跳上了窗子,她看着楼下的水泥地,知道跳下去,就可能摔死。可不跳,难获自由。她脱下了外衣,把头包住,这样可以防止落地时摔破了脑袋,她还脱下了鞋子,捆到了腰上,也起一点保护作用。她准备跳了,可是她的裤角挂住了窗外的空调,她的尖叫叫进了保安,小保救下了她。
老板这回没客气,狠狠地把她揍了一顿,打完,老板说,姓吴的,你要是把我的钱还上,我再留你,就是你养的!有志气你把钱还上!
胡长花是打算放她走了,因为出了人命,也不是好办的。但从目前看,吴梦梦没有切腕上吊的形迹,她只是想跑,还没打算以死相挟。
你不放我出去,我哪里给你弄钱?
打电话。打电话跟黄处长要。
人家是嫖客,又不是民政局,打电话就给你救济。
黄处长那天做的是白活儿,出事儿了,他总该出点血嘛。
吴梦梦掏出她的小本子,找到了黄处长的手机号,她对这个手机号基本不抱指望,可没想到,两声,就通了。
黄处长听出是她,以为她想重温旧梦,正想婉拒,没想到吴梦梦没有嗲声嗲气,而是语气很冲,老婆一样跟他要钱,三千,给不给,不给别说我告你去。
黄处长愣了有一分钟,他可能在此之前,半辈子过去了,还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吴梦梦说你必须给。
黄处长明白过来了,小婊子想敲诈?
他掐灭了烟,爽快地答应了,说行,行,可以,可以。
就定下了交钱的地点。
吴梦梦说出去取钱,老板批准了,但小保仍是她身后的专职保镖。
黄处长到了约定地点,有些兴奋。他和公安局的某个领导关系很好,甚至称兄道弟。吴梦梦的电话一挂,黄处长就给公安局的哥们报了案,说被敲诈。公安局就派人暗中陪他去约定地点。可等了好久,吴梦梦一直没出现,黄处长叹了口气,拿了几包好烟塞给帮忙的警察,走人了。
小保回来后,他姑奶逼问了一个晚上,吴梦梦到底去了哪里?小保的口供非常混乱,一会儿说她说肚子疼,进了厕所,从厕所跑了;一会又说吴梦梦在警察手里,怎么跑的,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吴梦梦使了美人计,招安了小保,放她跑了?小保的眼神发直,啥也不说,胡长花只好一遍遍告诉他,如果有人来问,问吴梦梦的去向,就说看她上火车了。回老家了。
小保记下了。
胡长花还在心里打算,过了这阵,等小保的苶症劲儿过一过,就给他拿上点钱,送他回乡下,照顾他爹去吧。这里,不适合这样的孩子过活。
老派隔三差五地来,调查吴梦梦失踪一事,说有群众举报。胡长花就奇怪,吴梦梦不是本地人,没爹没娘,更没有什么亲戚,谁会管她的失踪不失踪呢?谁能吃饱了撑的举报这个事儿呢?她脸上陪着小心,心里极度厌恶,心想老派你个小屁副职、土鳖,老正不在了你就这样趾高气扬?谁没有个沟沟坎坎,等老正完事的,看他回来,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就在副职上熬到退休吧。
老派知道胡长花在笑里藏刀,死心等她的老情人,老派是有些道行的,他不慌不忙,背着手,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这看看,那走走,他走到了堆放杂物的储物间,这里也是小保的卧房,姑奶从不进来的。老派伸手掀了掀床铺,只有薄薄的一床褥子,下面就是硬板,硬板和褥子之间,掖着一个小本本,老派拿了起来,小保蹿上去抢,老派把他的手挡开,胡长花伸上脖颈,他们同时看到:
举报电话是我打的,我恨姑奶奶她们这些人。
梦梦是跟姑奶家的表叔同一学校的大学生啊,却干了这个……她走的时候,说她爱我,我告诉她我也爱她,从见到她的那天起。她说我是好孩子,还伸手摸了我的头,说总有一天,她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