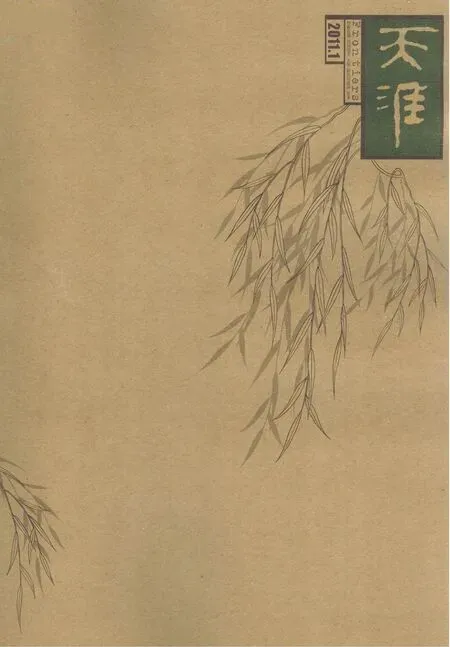豆瓣,你好
林白
一
滚滚人流中,豆瓣的历史性时刻降临了。
还不到七点,天就已经黑透,北京西客站北广场上人流稠密得像泥浆。谁都像没长眼睛,你撞我我也撞你,大人叫小孩哭,一片黑呼呼人头的汪洋上,浮动着巨大的蛇皮袋,那里面鼓鼓囊囊装着被子、衣服、年货,既像逃难,又像赶集,一种车站特有的气味黏糊糊地粘在空气中,越发乱得让人晕头胀脑。
叶含春四处看,她让豆瓣也瞪大眼睛,看看谁最先找到她的妈妈。豆瓣踮起脚跟才到大人肩膀,往哪个方向看都是人背人胸口,人流不断地过来过去,含春担心她被冲散,紧紧地揽着她。
最后还是含春最先看到香娥,他们是在一个厕所跟前,一行四个人,刚刚赶到。男人的前胸后背各搭了一只超大号的蛇皮袋,那袋子大得简直能装进一头大肥猪。他一只手扶着胸前的蛇皮袋,另一只手还拎着一只旅行包,那包满得几乎拉不上拉链。香娥背着一只大双肩包,一只手牵着六岁的男孩航空,另一只手,拎了一袋吃的东西,面包、玉米、苹果、太子奶饮料,还有几袋方便面。看样子,是准备上了火车再吃晚饭。他们下午三点半就动身,到西客站都快七点了。
女孩柏芝站在父母之间,不过才十四岁,却差不多长到了妈妈香娥那么高,她只冲含春看了一眼,就矜持地扭开脸。她拉了一只拉杆箱,怀里抱着一块电脑上的键盘,那是香娥当清洁工的那家银行里的员工淘汰下来送给她的。笨重的显示器和主机被分别用棉被包着,塞进了两只大蛇皮袋里。
三个小孩中,还是豆瓣长得最像妈妈香娥,都是桃形的脸,尖下巴,眼睛细长。如果不是皮肤粗,香娥是很好看的。女孩柏芝像她爸,颧骨高,航空虽然也像香娥,毕竟是男孩子。
怪不得,他们要把豆瓣要回去。
谁能阻挡血液的流动?一滴小小的血滴,越过了满广场黑黢黢的人头,也越过了九年的光阴,汇入了那腔子相同的热血。
这真是豆瓣的历史性时刻。
安检的人流已经很长,含春应该就地把豆瓣交给她的亲妈香娥。她把一直捏着的小手松开,提着的双肩包也只好由豆瓣背着了。豆瓣站在四个人当中,谁都没牵着她。含春就觉得她孤零零的。当然,没有人能腾得出空手;又当然,她也不是三岁的小小孩非得要人牵着。
男人又扛又提地走在最前面,柏芝紧跟着,香娥让豆瓣挨着她身边走,“走吧走吧,那我们走了”,她一边催促豆瓣一边跟含春道别。而人流轰隆隆地滚过来,仿佛洪水即将没顶。
看到豆瓣晃动的小身子,叶含春忽然想起前一年春运,一名回家的女大学生在站台上被踩死,她掉了一只包,去抬,一弯腰,后面的人就把她踩着了。人流永远是失控的,任何一点停顿都会被淹没。在人流汹涌中含春仿佛再次看到了那幅报纸上的新闻照片,一只女鞋,饱经践踏,脏兮兮地歪在一摊鲜血旁。含春感到,如果她不把豆瓣送到火车的车厢里,这个小人儿,没准就会变成那只歪着的女鞋了。
于是她又牵上了豆瓣。
几上几下,过天桥下铁梯,终于到了一列绿皮车的跟前,又一路走到最尽头,这才算到了他们的硬座车厢。
站台上黑黢黢的人头像脏水那样被列车吸干净了,含春不让豆瓣再出车厢,而且当着豆瓣全家,她也不好跟豆瓣单独再说什么。她在出口处一闪,再一闪,就不见了。豆瓣扁了嘴想哭,一看,柏芝正望着她呢,她就使劲吸鼻子,没让自己哭出来。
二
火车虽然是一路向南,车厢里却是一路的冷。是春运期间加的临时客车,没有暖气,脚冷得生疼,没一时就冻木了。香娥把男孩航空搂在怀里,两手一时搓搓他的脸蛋,一时又搓搓他的脚丫,嘴里吸着气道:“我伢冷哦我伢冷哦。”
车开出不久豆瓣就开始流清鼻涕,还没到石家庄,就把她的北京姐姐给她的面巾纸用光了。香娥翻她的书包,写了一半的作业本有好几本呢,就让她撕本子的纸擦鼻涕:“回去这些本子都没用了,还惜它做么事!”
豆瓣不撕,那是她的作文本,有三篇得了九十分的呢!她不撕,她使劲吸鼻子,想把流到嘴边的鼻涕吸回去。
香娥看不惯,拿出本子“哗”的撕了一张,她用这纸顶在豆瓣的鼻孔:“擤啊,擤擤鼻涕!”豆瓣的鼻涕擤不出,眼泪却哗哗的淌下来,怎么止都止不住,哭得那个委屈,用柏芝的话说是“一路哭到郑州才睡着”。
三
九年前,香娥在北京生下了豆瓣,一看又是个女孩,就说:“算了,送人吧。”
豆瓣满月第三天,就送给了叶家。香娥仍然当她的清洁工。
又四年,香娥在北京的航空医院生了个男孩,取名航空。又两年,被人告状,过年回村,被罚掉了超生款一万二千元。
香娥以为,不要豆瓣,仅柏芝、航空两个,不算超生,却不知谁个嘴尖,把豆瓣供了出来。一共三胎,超了一胎,只好认罚。
“罚都罚了,干嘛把伢给别个!”一年两年过去,香娥觉得这亏吃大了。
中间人去跟叶家透出这意思,叶家说,好,那就把豆瓣还给她妈妈吧。在豆瓣之前,叶家已经捡了一个女孩叫含春,豆瓣的户口就一直上不了,叶家正发愁呢。
这年豆瓣八岁,已经在北京上小学。又拖了一年,豆瓣仍旧读她的小学三年级,吃住也仍在叶家,学费也由叶家出。香娥觉得,叶家两口子简直是菩萨。
四
含春常常说,豆瓣的名字最好听。
但是王榨的大人小孩却不这样认为。
豆瓣?这叫么事名字?女孩子,嘉玲、曼玉、柏芝、咏琪……这才是好名字。若是男孩,当然了,嘉诚、家辉、朝伟……这才响亮气派!港澳的明星富豪,在电视上多威风,噼哩啪啦地响着,这样的名字简直是生着光的,富贵呢。
香娥认为,只要是姓王,不再姓叶,叫什么都无所谓。
改名字要到湾口镇,改一个字花五十块。五十块呢!买肉都能买四斤多,还能买三箱方便面!改两个字,那是一百块,要卖掉四十斤棉花才挣得着这个钱。改三个字,就是一百五十块!简直是巨款。没有人傻到要改三个字。
改一个字的却不少。当初人口登记,找的是学生来帮忙。学生都是乱写的,王榨有两个人姓王被他们写成了姓李,有一个姓李的媳妇又被写成了姓王。名字倒是无所谓,姓是万万不能随便。
叶豆瓣就成了王豆瓣。
五
开学了,豆瓣上了三观乡的小学。老师上课讲方言,不讲普通话,豆瓣听不大懂。她的功课拉下来了。
豆瓣不高兴,就跟妈妈说,老师不讲普通话是不对的,全国人都要讲普通话呢!香娥正在喂鸡,她敲着搅拌米糠的木棍应道:是啰是啰!
豆瓣又跟柏芝说,柏芝正在灶间往两只广口玻璃瓶给自己装菜。她住校,每周回来一次,做两件事,一是洗澡洗衣裳,二是往学校带够一个星期吃的菜。两只玻璃瓶,一只用来装梅干菜,另一只原来是装辣椒酱的,现在用来装炒黄豆。柏芝觉得,炒黄豆固然不错,但没有梅干菜好下饭,尤其是这一次的梅干菜,放了很多猪油煮的,里面甚至还有好几坨香浸浸的猪油渣。柏芝一边用筷子使劲往瓶子里捅,夯得越实装得越多,她一边捅一边还飞快地往嘴里塞进一筷菜,真是香死了!
听见豆瓣说普通话普通话的,柏芝嚼着梅干菜说:“普通话普通话,滚吧!”
六
豆瓣喜欢跟人说“我北京的姐姐”。王榨的小孩,有人拿一袋炸薯片在村口吃,豆瓣见了就说:“炸薯片是垃圾食品,我北京的姐姐说的。”
外出打工女人回村,脚上穿了长长的尖头高跟鞋,时髦得亮锃锃的,人人围着啧啧称好,豆瓣就说:“我北京的姐姐说,穿高跟鞋对骨骼不好。”
过年了人人回家,女人们,有空没空,聚在一屋说闲话。
谁都爱吹嘘自己的那点见识,“天安门广场,那跟电视上是一个模子……排队看毛主席,那队长得,差不多把纪念堂都包围了,人人伸着脖子四处看,广播里喊:大包小包都不能带!喝的水也不能带,枪支弹药更不能带,穿拖鞋的也不让进……”一个没讲完,一个又抢着说:“那次都怪她,毛主席也没看成……”“金水河,金水河的水根本不是金的,跟我家门口塘的水一个样……”
有人问,见过皇帝坐的龙椅没?哑了,全村都没人进过故宫。五十块钱的门票,谁去烧钱?
豆瓣不但去过故宫,还去过新盖好的国家大剧院。一只巨大的蛋浮在水面上,要从水底下进入,下沉的台阶,走走走,下下下,穿进去,一抬头,满天的水就在头顶呢!天上的光透过水照进来,一波一波的水纹在头顶漾漾荡荡,简直是一个龙宫!
“我北京的姐姐还带我去看了大鸟巢!”王榨谁都没有去过国家大剧院,“头顶上满天的水”,他们将信将疑,这哪像是真的,八成是哪部电影里头的吧,“电影里反正什么都有”。
豆瓣又从家里拿出来三枝铅笔,笔杆上印满了奥运会的福娃,她指给邻居的小孩看,哪个头上是藏羚羊,哪个头上是燕子、风筝。村里人见了就说:“这个伢,王榨还能养得了她?”
七
家里每个人接电话各有不同,妈妈拿起电话总是说:“哪个咧?”爸爸上来就大着嗓门“啊!”的一声,好像有人冷不防当胸给了他一掌。柏芝伶俐,她比父母进步多了,但她对人总是有些凛冽,她拿起电话,“喂”的一声,声调是下降的,好像是谁在她睡觉的时候在窗口大声唱歌,她说:“喂,别唱了,都几点了!”
豆瓣接电话,是像城里人那样的腔调,“喂——你好”声音悠悠地往上扬,细声细气的。
电话一响,豆瓣就赶着去接,“喂——你好”,她真像一个城里的小人儿。
但除了刚回家的那阵子,后来就再也没接到北京姐姐含春的电话了,到后来,连她留给豆瓣的照片也找不到了。
“说不定,她忽然就来了”,等不到电话,这样的念头就闪出了来,像蝙蝠,飞快地撞着她的脑门。含春从前说过的,“说不定有假期我就去看你”。
“她坐上飞机,呜的一下就到了”,豆瓣的念头滚动着,飞快地壮大,飞快地,越来越结实。
豆瓣决定,既然含春要来,她就要把枕巾洗干净。
她睡觉磨牙,又流口水,柏芝呢,不磨牙,但也流口水,两条枕巾不但有很重的口水味,而且还有黄黄的一摊摊口水印,脏兮兮的。
她在河边把枕头弄湿,涂上肥皂,搓一搓,往斜坡的水泥地甩甩打打,再放进河水里荡荡,枕巾里含着的污水就被带到下游去了,枕巾的粉红色干净地露出来,像一朵下雨后鲜艳的大荷花。
豆瓣每次都是把衣服晾在灌木丛上,小灌木跟她一样矮,枝杈杂生,把湿衣裳往上一铺,枝杈齐齐伸出手,她的衣裳裤子高高低低地就顶在了枝头上,东一片红,西一片黄,似乎是这片灌木忽然开出了花。在太阳落山之前,把衣裳收回来,那上面沾着一丝草,两枚叶子,太阳和草叶的气味使衣裳更干净、更爽手。
洗干净的两条粉红色的枕巾就晾在了后门的灌木丛上,豆瓣绕着它们来回走了两圈,仿佛那不是洗了晒的枕巾,而是她布置的一处花圃。
八
晚上豆瓣睡得香甜,梦见含春在屋外推门,怎么推都推不开,门轴吱吱直叫,但就是推不开。豆瓣在屋里帮着使劲拉门,嘴里喊道:一、二、三——一用力,人就醒了。
天黑着哪,原来是老鼠爬到床上来了,几乎到了耳朵边!
豆瓣把柏芝摇醒,柏芝说:“老鼠早就咬过我了,这回该咬咬你了!”
一起床又赶紧告诉妈妈,正是双抢大忙时节,香娥呜噜呜噜喝着粥说:“怕么事?我倒情愿让老鼠咬我一口,好让你爸回来帮我插秧!”
又告诉爷爷,爷爷说:“我伢不怕,等爷爷寻寻,看哪家的猫下了猫仔,给你讨一只回来。”
哪里有下仔的母猫呢?整个王榨的猫,差不多都被人偷来卖给武汉的餐馆了,剩下的,加起来不超过三只,都是当宝似的拴在家里。
豆瓣想起来老鼠的天敌是蛇。
她在叶家有一本叫作《我的动物朋友》的书,上面有大照片,一个外国小姑娘,鼻子翘翘的,侧身仰头,坐在一匹大象身上,她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金黄色的头发飘着,还有一幅照片,是这个外国小女孩跟一条大蟒玩。
于是豆瓣就要找蛇。
她拿了墙角的一根棍子就出门了。田岸长长的两边满是芭茅,这么长的芭茅这么密,这么密这么长,蛇在里头,就是它的深山密林,好得它怡怡逸逸的。人要找到它可不容易。
又去寻豇豆地,一垄又一垄,豆架支棱着,豇豆也像长长短短的细蛇,上上下下挂下来。豆瓣跳下地垄,从地头走到地尾,她拨着地上草高的地方,“蛇呢?蛇呢?跑到哪里去了?”她像问地,又像问草,又像问架上的豇豆。邻家的雨仙也跟着学:“蛇呢蛇呢?你在哪里呢?”她是直接问了蛇。
没有找到蛇,但是一条大蚯蚓拱拱动动的,从地里冒出来,身上亮亮的沾着土。两人蹲下,捉着棍子和石头,把蚯蚓切成了两半,腥气忽的飙进鼻子,它肚子里的血原来是一些黑糊糊黏兮兮的泥汤!两人都是头一回玩蚯蚓,正愣着,断了的蚯蚓又爬动了,两人手忙脚乱地,赶紧又切一截,再切一截,一条蚯蚓终于弄成了肉泥。两人带着满身的腥气,回家了。
九
含春没有来,豆瓣洗净的枕巾重新又睡得涎痕斑斑。床底下的小老鼠,吱吱的叫得更壮实了,有时它飞快地从墙根窜过,你一看,它竟长大了呢!
爷爷饮完一小杯酒,教给豆瓣一支童谣:唱个歌(哥),唱个嫂,唱个青蛙穿绿袄!
豆瓣却想起了蛇,问道:“爷爷,蛇都到哪里去了?”
都收走了。收到武汉卖了。卖给谁呢?卖给餐馆,杀给城里人吃掉了。
狗他也收,猫也收。他骑着摩托车,后座绑了两只铁笼子,一只又圆又扁,搁在下面,上面那只是方的。扁的装蛇,方的装狗和猫。蛇们伏伏不动,狗则狂吠,它不知自己被谁偷来卖掉了,离村越来越远,一个孩子奔跑着大喊,摩托车上了路,呼啸而去。猫呢,在白天它懒洋洋的被抓了去,到夜里睁开眼睛一看,主人和村庄,一个都没有了。
全王榨只剩了三只猫,两只狗。
卖老鼠药的就来了,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后座一只纸箱,是装方便面的,却装了老鼠药。他骑车骑得特别慢,几乎像杂技。他边骑边唱道:
有钱不买老鼠药,啃你的箱子四个角。
无钱来买老鼠药,给你药得一条索。
豆瓣不明白什么叫“药得一条索”,爷爷说,就是药得很多很多。
老鼠不药不行了,这些“烂嘴的”没一样它不吃的,稻谷、麦子、芝麻、绿豆、门、柜子、衣服、被子、纸,连电线它都啃呢!
它沿着房梁从灯绳爬下来,下下下,一下下到爷爷的床上,“噗”的一下,爷爷就醒了。爷爷到田岸上寻来一把狗儿刺(一种植物),他把这些叶子长着刺的木枝缠成一团绑在电灯的开关盒上,好了,害人精,这下下不来了。
老鼠又从窗缝进来,窗子钉了一层尼龙膜,裂了条缝隙,大老鼠在那里嗅嗅晃晃,晚上香娥起来喝水,一错眼,以为是个鬼站在那里,吓死了!
它又打洞,沿着墙脚,打洞打到灶柜里,嘎嘎嘎,又啃木头又啃柜里的衣裳。门口的一条缝,仅手指粗细,“滋溜”,一只老鼠挤进来,却有拳头那么大。
一关灯,老鼠就出洞了,吱吱叫得欢乐。啃门啃柜,高低一片嘎嘎声。谁都睡不着,香娥拉灯一看,柜子和墙中间正蹲着两只耗子呢,打又够不着,喝又喝不退,两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着它跑跑跑,从这边跑到那边,那边跑到这边。
妈妈说,这只老鼠这么忙,肯定是有小老鼠!挪开柜子,喔哗——果然,真是一窝小老鼠,红红的皮,眼睛是紫的,还睁不开,肉肉嫩嫩跟小猪仔似的!
五斗柜都被老鼠打通了,每只抽屉它都打了洞,抽屉里面洞连着洞,简直像北京的地铁。一敲一侧,满地鼠窜,有只老鼠跑不了,它急得眼睛直翻,它搞不明白怎么死活就是跑不动。大家笑得要命,原来这耗子的尾巴缠在棉花上,拖住了。
豆瓣跟着忙前忙后,她跟爷爷一起,要堵住墙脚的一溜老鼠洞。用土填,不行,它扒扒扒,今天填上了,后天它又扒开了。用沙子行,爷爷挑来一担河沙,豆瓣用大海碗盛满一碗,哗啦一倒,沙子顺着洞口沙沙漏下去,漏光了,用小钎子捅几下,再捧一大捧沙子,地下的洞真不小。
放老鼠药的时候,要等鸡睡觉了,鸭子睡觉了,细伢也睡觉了,再放药。“不能吭声,老鼠听见,它就不吃。”原来,老鼠其实也真能听懂人说话的。
十
插下的秧苗长起来了,一兜一兜的连成了线,在亮汪汪的田里,排得齐整。棉花、芝麻、黄豆、绿豆,先先后后的,都开了花。棉花的花桃红艳艳,像大朵的喇叭花;芝麻呢,白花,细长,顶上开花;绿豆花像槐花模样,却是粉黄的,挺好看;黄豆和饭豆,都是白花,饭豆花含苞时,像一粒碗豆,开了是两瓣,底下连着。
含春一直没有来,也没有她的电话。“豆瓣,你好!”她那透亮的声音就像渗进了灰尘,闷在远远的地方了。
香娥背地里跟人说,别再跟豆瓣提北京的事了,是她让叶家那边不要再打电话,省得这个傻瓜老想着要回北京上学。“这个苕伢,老想着她的北京姐姐!”
傍晚时分,“砰”的一下,“砰”的一下,“砰”的一下,烟花不断地升上空中,开出绿的、红的、黄的火花,烁烁闪闪,一朵又一朵,全村都看见了。各家的孩子听见响声跑出门口,烟花的闪光把他们的脸也照得一阵红光一阵绿光。
这是雨仙的姨婆从北京来了。当地风俗,来客人要放鞭炮,普通的客人,放个一千头的鞭炮,郑重的要放一万响,最最郑重的,就要加上烟花。雨仙说,她家来的是贵脚客呢,从北京来的。
十一
雨仙家的猫下了小猫,一窝两只。爷爷说:“嗬,一龙二虎三狗四鼠,一窝两只的猫跟老虎一样厉害呢!”
等小猫断了奶,豆瓣就用旧毛巾包了一只回来,给它喂粥,喂米汤,汤里有时搁一点腥荤。它喵喵叫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洞里的老鼠听见了,一愣,出入小心多了。
收蛇收猫狗的人被蛇咬了个半死,听说有三条土地蛇同时飙到他身上,一条咬手,一条咬腿,一条飙得最高,往他脸上喷了一口毒气,虽然没把他喷死,但再也不能到处乱跑收蛇狗了。
村里又开始有猫狗奔跑追逐打闹,跑得嗖嗖的,跑过塘边,跑过稻场,追着一只蝴蝶跑进了棉田。
棉田叶子密密的,暗了一成,但棉桃裂开了呢,亮白的棉花一簇一簇的闪出来,收棉花的季节到了。
豆瓣帮着剥棉桃,又跟妈妈下地拔花生。她每拔一兜就拣一只大的剥开往嘴里送,嚼得她满嘴白汁。新拔的花生让她吃得上瘾,比红薯脆,比莲藕香,比梨更有嚼头。
割下的芝麻挑回家,靠在墙上,比豆瓣还高。香娥在家门口铺了一张油布,把芝麻铺在上面晒。豆瓣就更忙了,她坐在门口写作业,一会儿起来轰鸡,一会儿又起来轰狗。天空亮蓝亮蓝的,太阳正大,青青的芝麻荚晒着晒着就收缩了水分。“叭”,裂开了!用竹竿一打,豆荚里的芝麻粒簇簇脱落,油布凹处,一窝一窝的。
雨仙告诉豆瓣,她家的芝麻等晒干了,要捎给北京的姨婆。“我家的芝麻……”豆瓣咕哝着,想起了含春,不说话了。
片刻,她对自己喃喃道:“……我家的芝麻,要做又香又甜的芝麻粑!”小小的人儿,仿佛若有所思。
十一的时候电视上又放起了烟花,荧屏里的北京烟花闪烁,连绵不断,闪成火的大树,亮成金灿灿的大花,一排笑脸齐齐升上高空,红的绿的黄的,每只笑脸只来得及笑一笑,就消失在黑暗中。
含春的脸也在这片烟花中闪闪烁烁,一会儿明了,一会儿又灭了,停上几秒钟,最终,直接从夜晚的天空上,掉进了又远又深的地方。不过,没有掉到底,而是在很深的某处地方安静地呆着。
十二
现在豆瓣的普通话仍然讲得不错,但她的家乡话讲得更流利,简直跟一个生下来就在王榨长大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她在湾口镇中学上初中,她的数学平平,关于她的作文,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老师不以为然,但从城市来支教的年轻老师却认为,王豆瓣如果参加《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没准能拿上一个好名次。
豆瓣的作文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豆荚开始鼓起来,如果你掰开一只,就见里面的豆子淡青的,安静得嫩嫩的,紧紧连着豆荚,用手一捏,一泡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硬了,它日夜灌浆,生长力气。等到秋天,你就再也捏不扁它了。风一响,满田野里的豆荚都在摇晃,仿佛一使劲就能摇响似的。沙沙沙,分不清是叶子响还是豆壳里的豆子响。
2012年秋天,我在香娥家的堂屋看到了豆瓣的这篇作文。
2012年尚未到来,我提前登上它的屋顶,看到河边田岸沟坎里,野草繁盛,芭茅艾草丝毛草野菊花狗儿草芸芸涌动,庄稼和百草连成一片,苍苍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