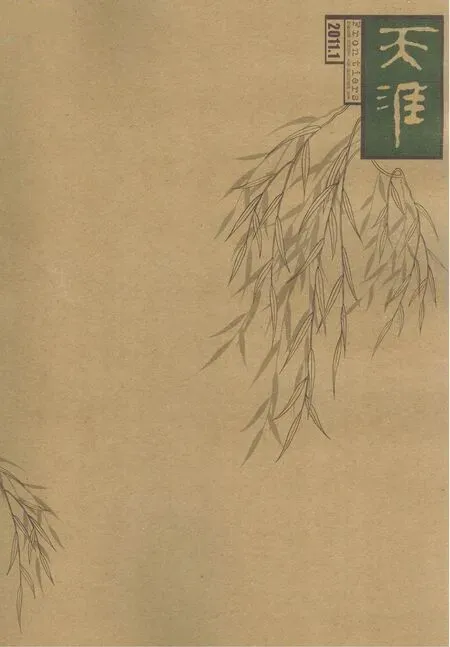近乡情更怯
江少宾
天宝来了,父亲说。我哦了一声。父亲又说,给你带了一只鸡。我又哦了一声。电话那头的父亲沉默了片刻,希望我能说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的沉默,我懂,而父亲也懂得我的沉默。
我明白天宝的来意。天宝是堂哥的儿子,刚在一所民办高职学了三年的会计,那只长途跋涉的鸡,是请我帮天宝找工作的。——我怀疑这是父亲的主意,在父亲看来,送任何东西都不如送一只鸡,我也不会接受比鸡更值钱的东西。堂哥是个老实人,黑而且瘦,因为长期抽烟的缘故,一口痰始终呼啸在他的喉咙里。堂哥说:咳、咳……你要找一个能坐办公室的事;堂哥还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咳、咳)你知道的(咳、咳、咳)……我低头抽烟,偶尔抬头,看着堂哥咳得通红的脸。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半百年纪的堂哥显得比父亲还要苍老,他在等着我的回答,脸上漾着乡下人常见的那种卑微的微笑。白白净净的天宝其时正靠在门框上抽烟,嘴角含着胜券在握的微笑。然而天宝的胜利遥不可及,他的父亲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办事能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中部城市,我无法帮一个高职学历的会计找到一间属于他的办公室,事实上,也没有一间办公室在等着一个高职学历的会计。然而这些话我说不出口,一旦我说出这些话,等着我的,将是堂哥的更为剧烈的咳嗽。我不忍再听堂哥的咳嗽,堂哥再这么咳下去,迟早会把肺咳出来的。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堂哥,除了答应,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会说什么。堂哥于是满意地走了,他把天宝留了下来,仿佛只要我今天打一个电话,天宝明天就可以上班。我苦不堪言,捉着手机发了一整天的呆,一个电话也没有打。我不知道这第一个电话到底应该打给谁,我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承认自己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但事实几乎是明摆着的,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算起来,堂哥已经是第六个找我办事的乡下亲戚了,这还不包括那些八竿子也打不着边的同姓族人、远房亲戚和拐弯抹角找来的村邻。他们托我办的,不是找工作,就是上大学;不是上大学,就是找工作。乡亲们当然也知道一些“游戏规则”,他们说,需要花钱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但乡亲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钱确实能办成一些事,但有些事,钱未必办得了。大前年,马术的女儿考了三百分,连最低的那一档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达到。马术说:需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但一定要上正规的大学。这事,我办不了。马术是看着我长大的,照说这个忙我应该帮,但这个忙我肯定帮不了。财大气粗的马术于是接连说了三个“够不够”,最后一次报给我的,是六位数,“我不相信十万块都搞不定一所学校!”马术的语气显然是生气了,事实上,我一拒绝马术就生气了。在这些乡亲们面前,我似乎不能拒绝,也不该拒绝,我一拒绝,他们就有足够的生气的理由。可不拒绝我又能怎么办呢?——在乡亲们的眼里,工作就等于一间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冬暖夏凉的办公室,等于每个月的工资不少于四位数,还等于一个城市户口,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的话,那就还等于一个城里的媳妇或女婿……在这个城市,我已经混了十五年,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我确实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但我的人脉关系还办不了乡亲们要办的大事。在我用十五年时间积累的关系网里,有商人、自由职业者、新闻工作者、编辑、作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唯独没有乡亲们需要的那种关系。我搞不来乡亲们需要的那种关系。事实上,我的手机里也有“关系们”的电话号码,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没有给“关系们”打过一个电话,甚至没有发过一条短信息。对我这个人来说,“关系”只是手机卡里的一组组数字,和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为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没少挨父亲的责骂。父亲说:山不转水转,你不找人家,事情怎么能办成?父亲骂: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别忘了你也是乡下人……如此等等。在乡下的亲戚们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以至于不愿意为他们去办这些事情。这些背后的责难不难想象,而父亲,根本就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背负这样的骂名。父亲其实是知道一些的,在短短的几年城市生活里,父亲多少体察到一些城市的冰冷和无情。几棵小白菜就要一块钱,少一毛钱都不行,而在父亲的牌楼小村,小白菜遍地都是,谁家要吃谁去挖,甚至不需要告诉主人。小村里剩下的,净是些妇女、病残者、老人和学龄儿童,地里的菜蔬和稼禾,家里的钱财和物件,没有人担心。担心其实也是多余的,岁月都老了,小村没有进过一个陌生人。牌楼似乎被世界给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一批黯然老去、默默离世的老人。乡亲们享受着这样的被遗忘,被遗忘仿佛是一个安宁的梦,直到儿女居然也考上了大学,他们才猛然惊醒。哦,祖坟终于冒烟了,祖坟冒烟的人家于是做起了另外的梦。
另外一个梦里冬暖夏凉,另外一个梦里衣锦还乡。乡亲们不知道,梦想其实是代价的同义词,梦想和代价通常是一个意思。小曾说:大学不都在扩招吗?小曾只知道大学在扩招,却不知道在大学扩招的背后还潜伏着重重的危机——扩招确实使更多的学生迈进了大学的校门,但同时也使得失业大军不断扩容。天宝就是扩招的受益者之一,但天宝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料峭的春天,我看见一大批“天宝”挤在人才市场的过道里,他们表情茫然,不知所措,在几场招聘会之间来回奔波,连一个机会也不愿意放过。和“天宝们”抢饭碗的,是“80后”、“90后”农民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批新生代农民工比“天宝们”掌握着更多的技能,他们知道待价而沽,适者生存,知道从“珠三角”转战到“长三角”,乃至一些正在崛起的中部省份——“用工荒”,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技工荒”,正是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的杰作——而“天宝们”却不懂得这些,他们刚刚走出象牙塔,盲目到无知,自信到无知。在“天宝们”眼里,“世界”就是他们在象牙塔里看到的那番景象,一迈出校门,他们就开始指点江山了,广阔天地,他们必将大有作为。广阔天地,要是没有他们投身其中,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十五年之前,我和“天宝们”没有任何区别,在“天宝们”身上,我清晰地感知到了那份茫然、焦虑与疼痛。但我比他们幸运,在十五年前的合肥,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机会,我不过是发表了几首小诗,就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新闻单位。然而即便如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依然让我产生出巨大的苦闷感与挫败感。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理想中有胜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中也有胜于理想的地方。唯有把这两者融为一体才能获得完美的幸福。”经年之后,当我读到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句话时,我已在现实中彻底释然,一切都成了过去式。现实原本如此。人生原本如此。然而对于“天宝们”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这个用四年时间培养出掏粪工(济南)、猪倌(广东)、菜农(合肥)、船娘(扬州)以及环卫工人(上海)的教育时代,现实的酷烈和无情,才刚刚开始。我无意于指责高等教育的失败,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高等教育还没有完全和市场需求相接轨的今天,对于另外一批人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而这批人,大多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孩子,他们对市场需求几乎一无所知。
这不是教育的悲剧,而是孩子们的悲剧,或者说,是乡村的新一轮悲剧。
一个星期之后,堂哥按捺不住了。按捺不住的堂哥开始隔三岔五地打我的电话,起先是在上班时间,发展到后来,居然是在凌晨或午夜。天宝的工作已经成了堂哥的一块心病,我一天不落实天宝的工作,就意味着堂哥要多失眠一夜。堂哥没把我当外人,电话里的堂哥说得非常直接,他说你不要不当事(咳、咳、咳),他说你就把天宝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咳、咳、咳、咳)……堂哥咳嗽的时间过于漫长,约等于我们之间那条漫长的电话线。堂哥的咳嗽,让我心如刀割。我唯一会说的,就是“正在办”、“快了”、“还在等消息”……好在堂哥看不见我的表情,每次对堂哥撒谎,我握电话的手都在颤抖,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想扇自己几个耳光。
谎言总有戳穿的一天,即便是善意的谎言。大约二十天之后,我终于接到堂哥打来的最后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堂哥异常的寒凉,但也异常的平静,他和风细雨的,竟然没有骂。那次短暂的通话,堂哥居然没有咳嗽,他其实是咳嗽的,他一直咳嗽。在后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给堂哥打一个解释的电话,我希望他能骂我几句,还希望他能咳嗽几声,但我一直犹疑不定。时间久了,越发缺少这个勇气。在天宝这件事上,我确实做错了——至少我应该给天宝指一条可能的道路,而不是一味地欺他和自欺。今天想来,那时候的天宝其实也仅仅只需要一条路,“天宝们”也仅仅只需要一条路。
天宝后来在老家学了裁缝,没错,是裁缝,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做的裁缝。我在小说里详细叙述过做裁缝的天宝,他似乎天生就是一块做裁缝的材料,一出师,就做得活色生香、风生水起。这对已然老迈的堂哥来说,多少是个安慰,天宝虽然没能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美梦,反倒“浪费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光阴”(堂哥语),但天宝终究还算听话,还算是争气的。天宝的现状大大消解了我对堂哥的愧意,在冰冷的城市生活里,我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和城市一样冷血的人,很容易就原谅了自己。
另外一些“天宝”,我大多已经不知所终,我一旦拒绝,乡亲们从此便杳无音信。在乡下,父亲几乎抬不起头来,几乎难以做人,那个“德高望重”、“教子有方”的四爷忽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风烛残年、教子无方的老人。毫无疑问,这是我给晚年的父亲留下的最大的罪孽,我努力过,然而我力不从心。父亲是希望我能办成一些事的,他一度热衷于传播我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奖项,这些乡亲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荣誉和奖项,编织成一个个巨大的光环,曾经持久地笼罩在父亲的头上。然而当所有的光环最后一一散去,父亲就老了,哑了,父亲终于知道,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只是个作家,一个只会写字的作家。
曾经,父亲试图代我向乡亲们解释,但父亲的解释,乡亲们根本就不信。他们在电话里冷笑,和父亲打哈哈,仿佛我们父子已经预谋好了,而他们也已经心知肚明。我告诉过父亲,解释是多余的,没有任何作用。几次自取其辱的解释之后,父亲终于死了这条心。他不再轻易告诉乡亲们我的电话号码,在关键的季节甚至也不再上街和串门。父亲是怕了,担心惹祸上身。父亲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对于门路有限的乡亲们来说,唯一的指望常常被无限放大,当那些被无限放大的指望一一瓦解之后,我终究要背负种种不堪的骂名。
早春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年久失修的老屋已经坍塌,比父亲更像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小村还是我熟悉的小村,尽管它早已楼房林立,又多了一拨新鲜的面孔。不断有人和我招呼,发烟,第一个说我老了,第二个说我胖了,第三个只是看着我笑,接着便和我聊起了最近的天气。他们的闲聊愈是不着边际,愈是让我手足无措——置身于生我养我的小村,我竟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在乡亲们不着边际的闲聊里,我甚至有些急于逃离。这种感觉真让我诧异——牌楼,生我养我的小村,仿佛成了一块伤心地。
上车的时候,我没有回头。父亲站在小村的路口,孤零零地,像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热泪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