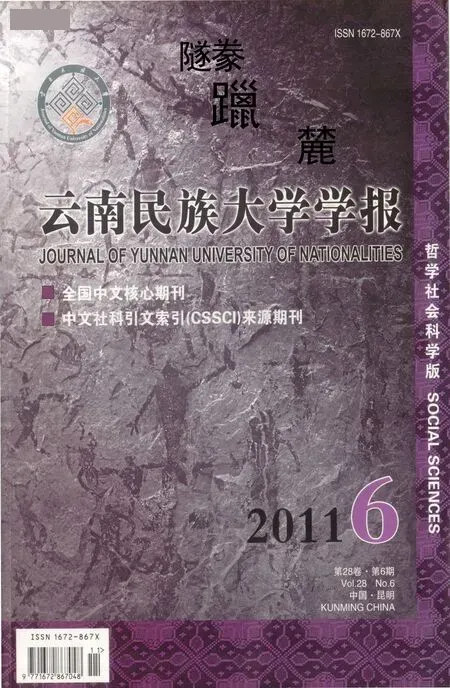田野无界——关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的思考
邵京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3)
一、田野得做,光说不行
演员在台上明处做戏,观众在台下暗中看戏,小丑上台,插科打诨(专业用语叫“旁白”),对着看戏的挤眉弄眼,打穿了台上台下的界线,这就是无界的境界。做人类学的有点像演这小丑,一只脚踩在台上,另一脚蹬在台下:两脚都在台上叫走火入魔,往而无返(英文里叫“gone native”,自己变成了“土著”);两脚都在台下,算不得做人类学,说得难听些叫以我之心度他人之腹,戏是戏,我是我,也就是所谓“我族中心观”(“ethnocentrism”),戏算是白看了。做田野是为了写“人志”。需要说明的是,用“民族志”来译“ethnography”不准,因为“民族”是一个政治与学术范畴,而人类学描述的文化不都是,或都不只是以这个分析范畴为界的。文化的主体是人,而不仅仅是被标识的“民族”的成员。够格的“人志”要有两个不同视角的融合,即人类学导论类的书总会讲到的“内省”(emic)与“外察”(etic)。(通常译作“主位”与“客位”)“人志”的书写者要有小丑的自觉。小丑的旁白都是双关语,这里一关在戏中说,另一关在戏外做。书写不仅是说,同时也是做。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行文的腔调不太学术,这种感觉正是自觉。坐电梯或搭地铁就常常会遇到同行人的“自觉时刻”:面对“镜子”,很多人都会整理一下头发,甚至“排练”一下自己在将要见面的人面前的笑貌。这种生活中的小事我们都见过、做过,非常具体,一点也不深奥。要是用学者们爱用的什么“文化自觉”、“文化的阐释”这些大而抽象的概念来讨论,反会给人一头雾水。
所以,20多年前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读人类学时就没修过“田野方法课”,人家从来不教这门课。后来这个系新出炉或快出炉的博士找工作,去别的学校面试时总要碰到如何教方法课这个问题,多数都会卡壳,系里才无奈开出此课,教自己的学生如何去教别人的学生如何做田野。当时我早就过了修课阶段,所以躲过一劫。当然这不等于在那里学人类学就根本不学田野方法。在学校里学方法的最好途径就是阅读师长、同行写出的“人志”,这是每门课里都占有很大比重的内容。而更为直接的学习就是自己做田野,因为别人的做法,别人的窍门,顶多只能拿来参考,自己如何做,做不做得成,则要在自己的田野里去摸索。说穿了做田野就是跟人打交道,一点也不神秘,是我们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做的事。
其实,做田野比说话要容易多了。说话也是不用学的,但等到长大了再要学另一种话就费劲了。而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能力却并不会因为年龄而减退,只要不老是觉得自己熟悉的、习惯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成。善解人意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有的本事,是做人类学做田野的根本,而愿解人意则是我们可以做出的选择。管家、秘书因为饭碗、工作需要必须做出愿解人意的选择,而主人、领导则不然。按理说,做秘书出身的领导个个都是出色的人类学家,可惜他们出去调研视察时只会见到下级和群众,犯不着拿出做田野的看家本事。想听见什么,想看见什么,自有下面的人提前张罗。我们去做田野时却不能把人家看做是“报告人”,预先准备一串问题问完了事。这样做人家多半会糊弄你,专挑你想听、爱听的话说,结果你带去的想法比你拿回的心得还要多,很难算得上经验研究。如果我们向秘书学,把田野里遇到的人当领导看,细心观察揣摩,田野就很少有做不成的。
反过来,非要把不费劲就可意会的东西费劲地拿来言传,漏掉的恰恰是人类学田野的灵魂。很多东西是可以传授的,也是可以程式化,甚至自动化。亚当·斯密说,如果把一块铁敲成一个钉子要十个动作,让一个人敲,一天或许能敲出一百个,但让十个人敲,每人只重做一个动作,日产就远远不止一千了。天天只做一个动作,工人可能变成了卓别林电影中那个下班了都停不下来的小丑了。跟敲钉子这活正好相反,做田野不能程序化,碎片化,更不可能自动化。几乎所有人类学教科书都会强调的整体观(holistic approach),就是这个道理。
二、田野不是一个场所
我们习惯上把做田野看作出门旅行,在平日生活与田野工作中间人为地划出一条界线,这样才会想到需要方法。这种比喻对,但也不应该全对,关键要看你心目中理想的旅行是什么。差不多10年前,我刚开始在中原做关于农村有献血员HIV感染的田野调查时,经常和一位十分出色的独立摄影记者结伴而行,跑了不少村庄。我们坐经常会把你转卖几次的依维柯,会在泥泞中翻倒的摩的,吃泡面加塑料皮的双汇火腿肠,住无星级小店,住在村里人家中。但我们觉得,这样做我们接触到了丰富的生活,这是晃一下就跑的记者无法得到的。我们俩都不喜欢旅游,只用眼去观看,不用心去感受,跟坐家里看看照片有什么区别。最近,我跟昆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小张医生到山上去看两位曾感染麻风的康复者。路上我又对他说我不喜欢旅游,他说,你这不是最好的旅游吗?
当然,做田野跟旅游不是一码事。旅游是人家搭了一台戏让你去看,谁去看都是一样。我们现在让学生去社会实践,多半会有一个基地,这是为了方便的安排,无可非议。但你每年都让一茬天真可爱的学生拿着小本本问人家同样的问题,人家也就会变成“民族园”的演员来尽职地担当“报告人”的角色。没准当地说话管用的“导演”还会在你不在的时候给他的演员种种交代,你的学生也更加像是游客了。反过来,我们不妨把旅游当成田野来做,这时旅游的质量就不同了,我想这应该是小张的意思。
这正是田野为什么是个慢活的原因。同样一件事,你得从不同人的嘴里听到,你才能确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不同时间说出的话也不会一样。譬如两夫妻家里住下一位客人,开头几天夫妻间一定相敬如宾。客人要是多住些日子,也就不是外人了。当着客人的面,夫妻也会拌嘴。这并不是说拌嘴就比客气真实,客气就一定是在做假。客人要真正了解主人,两者缺一不可。做田野就像去人家家里做客,刚去时是客,不到一定时间,就很难听到“拌嘴”,就不可能真正体验到田野里的生活。我自己做田野的体会是,一般开头几个月根本找不到路,也只当是白费了。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带着急迫的心情一定要在很短时间内有所收获,收获的只能是你自己带去的“行李”。相反,开头一段时间内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而是带着好奇去关注你所看到,看到听到的有趣的事情,你才可能满载而归,说不定还会全部扔掉你带去的“行李”。也就是说,我们去田野是带着问题去的,但问题还可以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不断修订,增补,更换。田野应该是我们提出新鲜问题的地方,而不应当仅仅是验证我们已经形成的想法的场所。”
三、做田野别忘了自己是“小丑
究竟要在田野住多长时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又要修课,又要做田野,又要写论文,时间是很紧的。结果很多学生的田野时间加在一起也就个把月,还要分几次去,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去真正认识、了解一大群不同的人,难度不小。人类学本来就是个冷门,社会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做人类学的。我想,如果是硕博连读,硕士不做田野,博士论文则在至少一年的田野基础上去写,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因为:第一,用心记,不用笔记。既然去做客,就不要摆出一副做人类学家的样子,手里拿个小本本,老让人家把手里的活停下来,听你发问,等你写字。但每天下来,写田野笔记就成了十分关键的作业了。回忆一天遇到的事,事与事有何关联,每天晚上花几个钟头写一篇笔记,老实记下当天的事,当时的感受,也就等于记载了你作为人类学研究者进入田野的历程。田野笔记不应当是流水账一本,每篇笔记都要当成一篇小品或素描(vignette)来写。回头不断地读这些笔记,我们就会发现,当初对事情的分析判断会跟后来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不一致,这种差异就是最好的田野材料,因为记载的不仅仅是故事,而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眼光一步步挖掘出来的故事。这样,参与生活的节奏没有打断,思考观察的角度没有放弃,既不全是演员,也不都是观众,保持田野无界的境界。如果田野跟我们自己生活很贴近,我们会觉得什么都没多大意思,写笔记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点距离感。如果田野跟我们自己的生活遥远,不去机械地记录,可以让我们去体验,去思考。不必担心漏掉什么细节,因为当时你想不起来的细节,也就是当时对你来说没有意义的细节,记下来也没多大用处。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有感悟了再记也不晚。
现在一个手机就比早先人类学家用骡子驮的整箱记录器材还要管用。多带几块电池,几张存储卡,你就可以把一天的所见所闻都拍下来,录下来。但我想凡是用过这种办法偷懒的人都有体会,机械记录最后整理到头来还是要花大气力整理,一点也不比空手做田野省时省事。一个钟头的录音没有七八个钟头是整理不出来的。就是变了文字,没有了当时谈话的语境、表情,意义就远没有在场时感受得到的那么真切。再把整理出来的文字大段大段地用楷体塞进论文去折磨读者,让读者去猜其中的意思,就更是得不偿失了。作为“人志”的作者,人类学研究必须在书写中呈现自己的理解,解释和判断。
第二,如果有条件,最好不要仅以人类学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田野。如果是经济学、社会学,你一说人家都明白你是干什么的。人类学则不然,不同的地方人们会有不同的误解。在美国,你说你是做人类学的,一般人马上会问你在哪里挖坑,把你当考古的了。中文里人类学很直白,却更让人迷惑。人类之学,听起来象是在吹牛、开玩笑。稍微知道一些的人则会说,你是研究人是怎么进化来的吧。所以我很少跟人家说我是做人类学的。更为相关的问题是,你去做田野,凭什么就这么闯进人家的生活,不仅要观察人家,还要碍手碍脚去问那么多人家自己也没有想过的问题。我知道有不少同行都想办法给自己找一个不是人类学的差事作为由头去做田野。这样参与时才不至于造作,观察时才顺理成章。
我就曾经给自己找了一份教人家如何坚持服药的差事去做田野。当时国家开始向农村有偿献血员HIV感染者免费发放抗病毒药,但配套的医疗服务却无法及时跟进。抗病毒药的疗效在很大程度上与服药依从性的好坏有关,如果不按时服用,经常漏服,或经历服药初期的出现毒副反应后自主停药,都会产生耐药性。了解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从一个基金会申请到了一笔经费,与当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和一个国际医疗救助机构合作,设计出一套以感染者集中的社区为依托的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同伴教育与支持方案。这项工作的前期调查,试点与实施过程中有不少地方涉及人类学的应用。我自己当时也觉得做好这个项目是正事,人类学倒更象是副业。不过,要是没有这件正事,人类学也很难做得下去,至少不会做得深入。
第三,访谈要放在田野将结束时做。刚去田野,对当地的社会生活没有体验,对社会场境里的人不了解,很难选对好的访谈对象,也很难问出好的问题。真正值得我们了解、记载、分析的东西也不是在集中的访谈中可以获得的。而生活场境中的只言片语,要是我们能够欣赏,善于捕捉,才是最好的材料。对这种材料的分析也应该是在流淌的生活中实时进行的。这时往往动静不大地追问一声,人家的回答不用多繁复,就能十分管用。也就是说,做田野时我们时刻都要记得自己的双重角色。这样的日常积累多了以后,我们也就自然琢磨出在那个特定的,我们已经熟悉的社会场景内我们该向谁提问,怎么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坐下一本正经地访谈,任务就没有那么重了,目的主要是核实你的分析,澄清你心中仍然存在的疑惑。
我做这种跟进式的访谈时还是会录音的,但现在已经很少再去花时间把录音整理成文字了。录下来心里踏实,记不清的地方回头听听,没有问清楚的地方,可以马上再去问。录音前一定要告诉对方,这首先是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同时对方知道已经录音,就不用停下来等我记笔记了。我的经验是,不用担心对方因为在录音就改变讲述的内容。一个好的访谈,对方会逐渐投入,眼睛也会不再不断地瞥那摆在显眼处的录音笔了。这里说的都是一般的田野作业,如果是做语言学人类学研究,高质量的录音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读过书的人多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听自己说话。况且,有些平时能说会道的人,一旦被你访谈,也会变得木讷,受不了冷场你自己的话就越发会多。对这一点我这个读过书还教过书的人深有体会。曾经有一个基金会知道我是人类学家,又在做跟艾滋病有关的研究,就给了我一个项目,让我去采集感染者生活与治疗的口述。我自信逗人家说话是我的看家本事,我常常能让出租车司机说得痛快,忘记我的目的地,发现后再关掉记程器向我道歉。于是就把这活接了下来。兜里有钱是好事,可以带还没有做过田野的学生跟着我去体验一番,访谈录音也不用自己整理。没想到,没有充分田野准备就做访谈,我还真不擅长。回头学生整理录音时向我报怨,说录音里听到的多是我在说话,人家的话比我少,很难连贯成章。所以,做田野时一定要记住克制自己爱说话的毛病。倾听远比提问重要。
其实,集中的访谈最好是放在已经开始书写“人志”或论文之后,这就自然转到是我想说的第四点:没有必须把田野与书写在时间上划出截然的界线。随着田野的进展,有思考的田野笔记应该十分自然的就变成你最后要写的东西。这个建议不仅仅为在我们的学制下田野时间不充足而提的。写就是思考最好途径,在田野里就开始写,则可以参与不忘观察,观察不误参与。这样不至于做田野时只是一门心思地收集,回到家里该动笔的时候面对一大堆未经烹煮的生食不知如何下嚥。
最后,如何跟人打交道。人类学是个职业,但人类学研究者的职业对象不仅仅是“报告人”。社会中很多的人际关系都可以而且应该职业化,比如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乘务员与动车乘客。这些关系都有起止,在起止之间不应该有其它关系的渗入。而人类学却很难界定明确的起止,一旦你把人家定位成“报告人”,相应的社会沟通也会变得单一苍白。既然你要走进人家的生活,你就应该做好跟人家长期做朋友的准备,也应该让人家了解你的生活。你在人家面前编故事,人家也会给你编故事。当然,有时你再坦诚,人家对你有戒备,还是在一开始会给你编故事。只要你的记性好,相处时间久了,人家的戒备解除了,故事背后的故事也会在平日交谈中点点滴滴地自然浮现。
生活层面上的沟通交流还只是打交道的一个部分。田野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不妨把我们初步的想法、分析与结论拿出来跟我们报告人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与批评。这种做在影视人类学中早就有人尝试。Tim Asch在南美拍摄的雅诺玛诺(Yanomano)部落的系影片时,就经常让镜头前的部落成员走到摄影师的位置上,或让他们参与后期剪辑,把当地人的视角带进镜头。我自己通常没有他这么花哨的用意,做田野时说出自己的分析、解释或结论,主要还是要确定我的想法没有太不靠谱,让他们笑话。即便他们读不到我写的东西,总会有知情的人读到。再说,你的人类学分析与解释不管如何高明、深奥,你不能用你研究对象听得懂的话说出来,让他们听明白,那你一定自己还没完全想明白。我并不要求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也从来不曾想过要说服他们,但至少不能让他们听了就发笑。
四、人在做,天在看
这句俗语最近经常听到。或许人们是在表达对道德力量的信念,或许是在召唤缺失的道德。天也好,神也好,上帝也好,雷公、雷婆也好,人类学不会停留在这些观念的面值之上。神明的眼睛就是人的眼睛,是人的社会眼光的异化与投射。没有这个社会眼光,也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与他的不同与沟通。人类学田野就是用这种眼光去从事的自觉的社会实践。也可以说,田野是一种态度,不是一套操作程序,不限于一个场所,一段时间,一种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