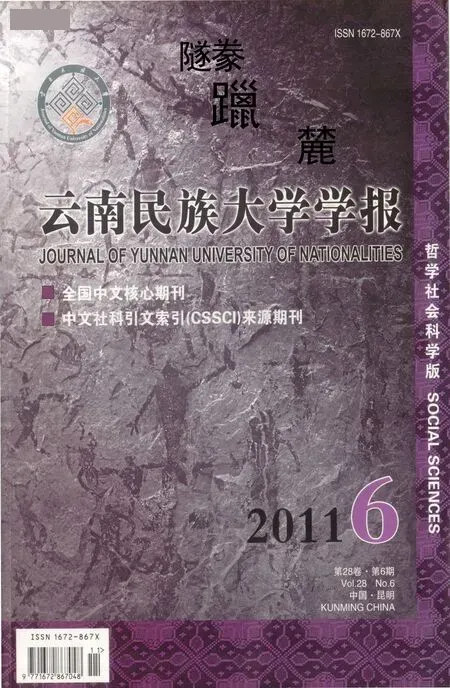“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
范可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3)
迄今为止,人类学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有其自身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可以通过它所关注的问题体现出来。同时,这些问题也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也就是说,一定时期的人类学研究旨趣往往与当时国际氛围有一定关联,与特定时期的思想界风潮有一定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由于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学术旨趣的影响,所以也有了一些差别。就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早期古典学派的一些人类学主要是通过文献工作来收集资料之外,①最典型者当属弗雷泽(James Frazer)。人类学在这方面与其它学科有着很大的差别。人类学研究的资料主要在实地进行收集,它们主要来自民众的每日生活。但这不等于说图书馆工作或者历史研究就不重要。研究中国的已故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曾经在他的一次主题演讲中强调,人类学研究还应当“采访死者”(interview death),②Maurice Freedman,1979,“Rites and Duties,or Chinese Marriage,”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ed.,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255-72.言下之意当然是文献与历史的重要性。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伊万斯-普里查德甚至认为,人类学如果不是史学的话,那就什么都不是。③见E.E.Evans-Pritchard,1962,Social Anthrop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The Free Press,pp.172-191.当然,他的这段话可以有很多重意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但是,无论怎么理解,有一点是确定的,在研究方法上,人类学者需要有历史维度,人类学的作品一定要有历史感。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素材主要的还是来自田野考察。
一、“他者”的田野
人类学之所以如此强调田野工作与这门学科的历史有关系。这一历史造就了人类学的学科特色,自然也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人类学产生的动力与那些一直困扰着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有关——人们总是希望能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但毋庸讳言,人类学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殖民主义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海外殖民地的开拓,西方人接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文化。有好事者遂将此逐一记录在案,这是人类学滥觞的由来。当时欧洲人遇到的许多有着不同文化的社会都是无文字的,因之,无论是传教士或是其他有文字工作能力的人在面对这些不同于欧洲人的民族时,只能通过观察来记述。这是一种与其他倚重于文献的研究完全不同的一种实践。这后来导致人类学研究基本要求之形成——研究者必须到活生生的生活中寻找资料。所以,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手段与人类学传统上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直接关系。过去,人类学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异文化”。今天,人类学者往往喜欢称自己的学科的研究对象为“他者”,④当然,对此也有持有异议者。见George E.Marcus,2007,"Collaborative Imaginaries,"i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vol.5,n.1,pp.1-18。也就是与自己的文化之不同者。
诚然,大部分西方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都是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而且更多地到国外进行研究,所以,尽可以理直气壮地称研究对象为“他者”,或者“异文化”。这一“规定”在其他国家里也有些影响。例如,在日本,人类学者都是到国外进行研究。研究本国文化则被称为民俗学。费孝通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度不愿意说他自己是人类学家,其心结也在于此。过去的西方人类学家把人类学定义为研究“异文化”的同时,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拉德克利夫-布朗和伊万斯-普里查德都公开宣称,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原始社会”,①见E.E.Evans-Pritchard,1962,Social Anthrop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The Free Press,pp.172-191.言下之意,这些社会在文明程度上低于欧洲人。今天,即便在人类学发达如美英法诸国也没人敢如此称呼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原始”不符合平等待人的原则。但是,人类学主要研究异文化的传统乃然在这些国家延续下来。②这绝不是说这些国家的人类学者完全不研究本社会和本文化;也有研究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者,但比较有限。但另一个变化日益醒目,这就是越来越多地人类学家直面当下,研究那些直接影响人类生活与延续的各种涉及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国际金融、政府治理实践等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课题。
人类学既然以研究“他者”为己任,那进行工作的田野必然是“他者”的。由是,从方法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研究异文化的田野称之为“他者”的田野。传统上,它应是异国他乡的某地,无论在城里,或在乡间。就方法论而言,如果研究对象为“他者”那就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他者”意味着与己不同,同时也意味着陌生和新鲜。比之于在本土进行参与观察,“他者”的田野必然对一个外来的研究者有着全然不同的刺激。虽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研究者首先必须对所研究对象的语言有所熟悉,但来自异文化的新鲜感与刺激感,还是能使研究者仅凭肉眼观察便能感受到许多与自己的文化全然不同的东西。我们说的“旁观者清”是很有道理的。许多人也许会纳闷,为什么有些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研究时,会从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里找出些道道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更有学识,而是更多地在于我们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反倒有点“不知庐山真面目”了。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教科书经常强调人类学者所从事的是跨文化研究。一个人有跨文化生活的经验,对自己(本文化)和他人(异文化)的看法一定与没有异文化生活经验的人有所不同。所以,美国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倾向于招收有异文化生活体验者攻读博士学位是很有道理的。
在“他者”的田野里,研究者与当地人的距离感始终存在着,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会使田野工作者保持清醒。这种距离感不应当是田野工作者的优越感所引起的。早期人类学者的优越感显而易见,今天的人类学者是否在异文化面前完全没有优越感?这就不好说了。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田野工作,研究者必须克服自己的优越感。你凭什么觉得你比你所研究的人优越?就因为你的教育背景,你的身份,或者你的富有?其实,在田野里你得设想你是贫穷的,因为田野里的民众说不定是你日后的衣食父母!你得设想,他们将成就你的研究,成就你的博士论文。所以,你在田野里既是研究考察也是学习。英文里有关研究的一个字——study,其另一层意思不就是学习(learning)么?因为某种优越感而保持与被研究对象的距离,这不是人类学者应有的态度。我们所说的保持距离就是得始终记得我们来田野里是来发现新的问题,是带着问题来寻求回答,是带着问题或者假设来进行验证。因此,需要保持清醒。美国人类学历史上有人类学者最后被所研究的文化所“化”——被印第安社区收养,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生涯。在人类学研究上,这是失败的例子。人是情感的动物,与一群人生活久了自然会产生感情,产生对他们的依恋,甚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其例之多,在现实生活里不可胜数。研究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如果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固然可以得到更为准确,信度更高的第一手资料,但也必须清楚:一旦失却了对研究对象之主观世界的客观探查,资料的信度会大打折扣。而如何才能保持客观?关键就在于提醒自己:我们虽然努力通过“他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思考问题和看待外部世界,但不等于我们自己必须同意和接受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他者”的田野里,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还是容易给外来的研究者提供大量的研究素材,即便在语言不过关的情况下,也能通过观察获得许多资料,但在如何理解自己观察的一切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主、客位的问题。在语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理解所观察的一切只能是一种“想当然”。所以,资料的获得是一回事,理解和解释资料又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说的是“他者”的田野可能更具刺激,信息量也就显得大了。这是与田野里的“他者”的不同之处。
二、田野里的“他者”
由于中国人类学者大多在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熟悉的社会里进行研究,所以把研究对象定义为“他者”不免有些难言之隐,至少不会象欧美学者那般自然。①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倒是派送学生到海外进行研究,并命名为“海外人类学”。其实,这倒是复归人类学“正统”,谓之“海外”反倒令人生疑。在熟悉的环境里从事田野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敏感度,因为熟悉的社区和周遭环境对研究者不陌生,自然也就没有了新鲜感。这点堪称田野工作一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在本土做田野研究还真是一个挑战。每个人都不愿意讲些别人都谈了无数遍的东西,所以有个如何在熟悉的环境里发现新东西的问题。总而言之,本土田野工作者必须克服的首先是那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的状况。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最迫切的需要就是阅读,而且多了解一些社会理论。
当今的人类学成果已经少见过去那种事无巨细都记录在案的民族志了。那样的研究建立在这么一种假设之上,即:所研究的社区与外界完全隔离,因此必然有自己的存在法则。事实证明,这样的社区在当今世界根本不存在。所谓与世隔绝的社会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很早就与外界有了接触。这样,问题就来了,他们所受的影响来自哪些地方?这些影响是否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社会与文化形貌?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很多人类学者反思这门学科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也使得人类学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这些反思的一个后续发展便是人类学研究越来越趋于课题取向了。从那以后,许多学者的田野工作可以说是以问题为基础,即所谓的topic based。于是,在田野里发现的问题也往往是所研究的问题之中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个环节。
带着课题下田野不见得就不会发现其他更值得关注的问题。许多人类学者田野工作之后的研究成果与他们原先准备做的课题完全不一样,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田野中发现新的,对研究者个人兴趣而言,更为有意思的题目;当然,另一种原因也不能排除,那就是研究者发现新的兴趣点资料的潜质,或者信息更易于获取。但是,千万不要认为你有足够的信息就已经够了。关键的是,你获得的信息或者资料的信度如何。人类学方法,严格地讲,是所谓的“定性”或者“质性”研究,资料的信度可能无法按照量化研究的一套东西来衡量。因此,就人类学者而言,尤其是对在自己熟悉的社会里进行参与观察的人类学者而言,资料的信度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的是你的解释力度。这种解释力不是简单地清理出因果关系或者其他相关关系即可,而是必须用自己的能力来解读被研究者的主观世界。
在本文里,“田野里的‘他者’”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在本土的田野里,本土研究者应尽量使自己从自认为熟悉或者熟人状态中摆脱出来,力图以一种“外来者”的眼光来审视引起兴趣的一切。这种努力寓意于本文的题目里,即:我们应该把自己设想为你所研究的社区的“他者”或者把自己想象为“外来者”,并将此作为一位本土田野研究者的立场。这并不是说无需与社区人士建立真正的友谊或者情感。而是,在参与的过程中,观察者应该心有旁骛,用自身储备的异文化知识来进行比较,并且也设想,如果自己是外来的人类学者,所看到的事项对你可能意味着什么。总之,把自己视为田野的“他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新鲜感,保持自己头脑的“冷静”,而不是要有意识地与被研究者疏远。比之于前述的“他者”的田野的状态,田野里的“他者”更需要保持一种能进能出的状态,因为自身的文化更容易把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遮蔽掉。
在本土的田野里,田野工作者比较容易与所研究的对象成为朋友,这对收集资料有好处,但有时也可能会是制约。譬如说,如果我们参与观察的社区内部关系复杂,存在许多矛盾,这时候,作为田野工作者,你在社区里与什么人关系较近可能会影响到你与其它人的关系,从而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社区里从事考察就得站好“立场”。当然,这不是说你加入社区内的某一派别,而是,尽量使自己不要让人把你归入某一派别。在这样的社区里做田野,在清楚社区内部关系之前,最好自己找个地方独自居住。待到把内部关系梳理清楚之后,再考虑住到社区内部不同的人都能接受的人家里去。
“自我的他者化”还有这么一层意义。我们在田野里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没有什么事是不能理解的。其实,情况可能完全不是这样。以我个人为例,我选择做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田野点就在我的家乡闽南,但是我到了之后不久就发现,许多事情对我是闻所未闻的。我虽然成长在闽南,但生活的背景与我所研究社区的人们完全不同。我在城市里的大学社区里长大,无论在各方面都与所研究的社区极不相同。当时,我所研究的社区虽然在经济上已经十分富裕,大部分人已经不再务农,文化上已经是很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才会有的那种状况。但是,当地人的每日生活基本还是保留着原来农业生活的惯性,许多农人的习惯还保留着,如四时节气、婚丧嫁娶的各种仪式。可供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且,许多想当然的看法都遇到了挑战。所以,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地方可能对我们其实也是很陌生的。
三、田野工作方法
尽管早期的人类学家有一个“安乐椅上的人类学者”的雅号,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还是做过某种程度的调查。泰勒就曾因为养病到过北美,对当地的印第安人留有印象,也曾对美洲的古代文明遗址怀有浓厚的兴趣。摩尔根也曾走访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并曾被当地人收为养子。而哈登和里弗斯组织的托列斯海峡探险队,也进行过考察。但是,他们究竟如何进行实地考察却鲜有记载,许多细节问题更是无从了解。摩尔根虽然有过所谓的调查,但是我们知道,他更多地是通过当地的传教士、保留地和殖民地官员来收集信息。这些人类学家总的来说,主要的还是通过文献来获取信息。
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研究是从马林诺斯基那个时代开始的。马林诺斯基的田野研究被公认为典范。他在田野里住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三年间,他甚至连离开那个地方都不可能,因为他虽然是波兰人但却是奥匈帝国子民。①当时波兰被普鲁士、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大强权所瓜分。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敌对国家澳大利亚所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生自由。这一歪打正着的半囚徒式生活成就了他的田野工作。他不仅能流利地操当地的语言,而且还熟悉了当地所有的一切。他可能没与当地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有些人类学者不无揶揄地描写,他在所研究的村子外搭帐篷居住),但他深入的程度无疑是其他人类学者难以做到的。所有批评他的后世学者,没有一位在田野考察中像他那么深入。
对马林诺斯基而言,田野研究无疑是有一套方法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家》的第一章,就是介绍民族志方法。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公推为田野工作的祖师。就常规意义上的人类学而言,马林诺斯基在他的导论里讨论的方法无疑很经典。对于研究一个社区的方方面面,他的工作方法堪称指南。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对于了解被研究者内在世界的重要性并没有太多的认识。更遑论后来的什么“复调”、“多音”——这类涉及所谓民族志知识权威性的隐喻与修辞,以及与当地人共同生产人类学知识这样的觉悟了。尽管如此,马林诺斯基的方法论还是成就了现代文化和社会人类学。②即使是对马林诺斯基的方法多有揶揄和批评的乔治·马库斯(Gorge E.Marcus)也承认这一点。马林诺斯基说,他研究的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经济学现象,其重要性是当地人的实践。当地人的观念、抱负、欲望,乃至虚荣心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库拉”交换所决定。③Bronislaw Malinowski,1961[1922],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E.P.Dutton&Co.,INC,p.2.
马林诺斯基田野工作的缺陷在于把社区预设为与外界隔绝的场所,当地人的生活空间被库拉圈所规定。这样的观照必然忽视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应当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难道当地人从来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冲击?显然当地人不是与西方文化没有接触,但在马林诺斯基的书里,我们好像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痕迹。对于特罗布里安人而言,时间仿佛是凝固静止的。这一现实的遮蔽实际上是被他自己对“他者”的想象 所导致的。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谈,单就对“他者”文化的描写而言,马林诺斯基的著作近乎完美。我们没有权利苛责马林诺斯基。今天我们关心的许多问题当时要么不存在,要么没被发现或不是问题。因此,如果考虑到大部分人都无法避免历史局限性的话,马林诺斯基则在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下,做出了令后人永远无法忽视的成就。
今天,这个星球已经没有任何社区、任何地方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交往早在殖民主义兴起之前就已开始,更遑论处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个各种现象聚集,各种问题也全球化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产生了太多的问题,人类学也就无法仅以理解“他者”自命。我们依然在寻找alterity,但它已然是各种各样的与全球化有所关联的问题,哪怕并没有明显的迹象与之有直接联系。如此一来,似乎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仅关心的只是问题了。与这种情况显然不无关系的是,在许多美国大学的人类学系里,田野或者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methods)成了一门最容易“混”、成绩以pass或者no pass了结的必修课。说是课,其实只不过让学生们在那里侃,想象自己如果在田野遇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以及可能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凡此种种。但要说它完全没用却也不尽然,因为课上总有些影像资料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参与观察”。教授会要求你对观察的影像片断进行描述记录,并予以讲解,告诉你还有哪些重要的情节被你遗漏。但对如何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则颇为强调。记得有一门课叫“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其实是教学生如何写课题申请要钱的课程。虽然也是pass和no pass,但却比较较真。值得玩味的是,教授这门课的教授仿佛完全无视方法,而是反复要求学生构思和写好第一段。就这样,学生们反复改反复写,大半个学期都用在构思和写不足三百字的第一段!为什么第一段如此重要?也许有人说,那是门面。不错,确实是门面,但这一门面不是徒有其表没有内容的门面,而是突出内容的门面。如何突出,那就得靠你所考虑的问题来支撑了。
四、民族志与问题
有了问题自然就好开展田野工作了。具体的田野工作程序如何,这是每一个从事人类学的人都知道的,许多学者都有关于自己田野工作的经验之谈。李亦园先生的《田野的图像》里的有关章节很值得一读。他告诉了我们一些技巧,以及有关资料的信度和效度的问题等等。说来有趣,李先生的一些经验也是我在田野中曾经有过的。譬如在一些场合不经意地得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①李先生的书提到曾经躺在村里的庙里休息与老人攀谈,得到了很多信息。见李亦园《田野的图像》,1999,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第106页。田野工作中最常用的是深度访谈。在这种场合,除非你已经与访谈对象特别熟,征得同意后,才有录音设备和做笔记,否则,还是尽量不要用这些设备。但是在攀谈中一定要让谈话在可控的范围内。这样做的话,每天就必须写田野笔记。无论多迟,都得完成这个任务。田野笔记很有用,你可以把瞬息即逝的思想火花即时记下,这对日后成文真是大有裨益。而且,在写田野日记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信息比较模糊。对此,你应当做好标记,第二天或者有机会时,进一步核实。总之,在田野里,最重要的是与人沟通,而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则可能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比较腼腆,不善沟通,那就得努力改善。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问题,尤其是好的问题。
但是,提出问题并不容易。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接受一项任务,接受一个命题作文,要比你自己寻找问题来进行研究容易得多。韦伯说过,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困难,道理就在这里。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和好的研究方案,除了个人敏锐的洞察力之外,关键的是要有一定的理论储备。马林诺斯基在他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家》一书中,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从事研究要避免理论先行,但问题一定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下田野之前有问题在胸虽是要求,但并非一成不变。你带到田野的问题未必比在田野里发现的问题更有意义,所以,不要担心日后的研究成果与原先考虑的问题不一致。我的导师原先想做有关家庭的研究,但田野工作却令他写了关于中国人信仰的博士论文。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每个从事过田野工作的人都知道,为了准备进行田野研究,都得进行储备,阅读许多相关的书籍与论文。其实,这就为我们在田野当中改变主意打下了基础。因为我们改变主意通常都是遇到一些觉得更有意思、更有意义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上,问题通常都是在学术积累的过程中发现的,理论积累越深厚,发现的问题可能就越有意义。如是说并不是鼓励任意改变自己原先的设想,而是提醒不要担心改变主意。在田野工作中,除了投机取巧,主意的改变往往是问题意识在起作用。
好的民族志通常有较好的问题意识。尽管过去的民族志不一定是今天常见的做法,即所谓topic based的,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预设。米德的研究就是个例子。米德去萨摩亚从事研究时已经有了个关于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nature or nurture)。美国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人们总是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人特殊的生理阶段所致。换句话说,也就是荷尔蒙的问题,是自然的,先天的。但如果青少年犯罪是先天的因素所致,那就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现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得考虑其他的原因。米德因此到萨摩亚从事田野研究。她的结果认为,青少年反叛犯罪不是什么先天的原因所致,而是文化的结果。[1]但是,我们从她的民族志,即《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来看,她还讨论了文化上的许多其他内容,好像并没有一直在先天或者后天的问题上进行辩论,好像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这在方法上有什么启迪呢?其实,无论她如何行文,讨论什么,先天还是后天才是她研究的基本问题。她的其他描写和分析,都是对回答这一基本问题的铺垫。这里,涉及到人类学的一个哲学命题和基本观照,也就是整体观(holism or holistic view)。所谓的整体观,在马林诺斯基的著作里表达得很清楚,也就是强调文化各部分都有联系,有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这种看法的哲学基础是马赫(ErnstMach)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其基本看法就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或者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思想在当年德语思想界里影响很大,而马林诺斯基和博厄斯都受到德国传统的思想统绪的影响。米德是博厄斯的学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还有一个例子来自非洲研究。我们都知道社会人类学上几本非洲研究的书很著名。其中有伊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这本书所回答的主题并不在于努尔人社会怎样,生活怎样,而在于告诉人们,当地人已经在那个环境里有秩序地生活了很长时间了。作者实际上是反殖民政治的。所以想解决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一定得生活在国家制度下。这个国家(state)在那里就是殖民地当局。而在当时英国社会,有关对殖民地间接管理(indirect rule)是一个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论的议题。[2]
有些人类学者喜欢把问题划分层级,他们认为第一层次的问题应当是涉及人类本质,在哲学上属于本体论的问题,诸如,从哪里来到到哪里去这类的问题。早期的人类学者都是在这一层面上进行讨论。无论是古典演化论或者是传播论讨论关心的都是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如何发展而来的问题,无非前者试图从时间的维度上来勾勒发展的谱系,后者从空间上来进行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研究渐被放弃了,因为原先所相信的欧洲文明是人类文明顶点的神话,被战争的残酷现实所粉碎。社会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转入了较为微观的研究。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兴趣的问题,同样还是涉及到人类的本质所在。这种思考方式体现了人类学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特点。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就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他研究台北三峡地区童养媳多年,目的在于解决所谓乱伦禁忌(incest taboo)为什么会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位学者的著名假设,一位就是有名的弗洛伊德;另一位是芬兰人类学家威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
在威斯特马克看来,人类之所以会有乱伦禁忌乃在于一起生活的亲人之间会产生性嫌恶感,自然而然地会排斥与一定范围内的亲人发生性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的假设。正是因为有这类情结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会有禁忌来杜绝近亲之间的性关系。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武雅士的研究就是想要看看这两人的理论究竟谁有道理。这是他的研究的出发点。所以,童养媳研究看似是一个小课题,但它却与人类本质的一些命题有关。
武雅士所研究的台北三峡,其居民祖先来自福建安溪一带。安溪与同安县接壤,两个地方过去都地瘠民穷,长期流行童养媳的习俗。为什么这种习俗在那个地方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多半的人认为是经济上的原因。但有意思的是,闽南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条件类似这两个县,却未必有这种习俗。童养媳的存在为武雅士探讨的课题提供了素材。他设立了一些假设来加以验证。比如说,离婚率、所生子女多寡,等等。但仅靠验证童养媳与养父母家的儿子成婚(他称之为“小婚”)无法得出结果,所以必须同非童养媳通婚者(称为“大婚”)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比较才能说明问题。通过二者的比较,他发现,小婚的离婚率远高于大婚者,而且这种情况在养父母双亡的家庭里尤甚;另外,小婚者所生的子女也普遍比大婚者少。武雅士认为这些证明了威斯特马克的近亲之间的“性嫌恶”假设,因为童养媳与她未来的丈夫从小便生活在一起,情如兄妹姐弟,但成为夫妇后却难以白头到老。[3]
人类学上小题大做的例子很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及其对世界各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东西原来我们没有的现在有了,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景军编了一本很好的书——Feeding China's Lit-tle Emperors,主要讨论儿童食品的问题。许多人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但这本书的作者们就从中发现了很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里,是没有儿童食品之说的。在传统时代,大人吃什么孩子跟着吃什么,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但现在很不一样了。儿童食品的目标就是孩子。孩子开始有选择了,这时候家里的亲子关系可能就会起变化,事实也确乎如此。孩子成了餐桌的主人,人人围着孩子转,过去的家庭权威在这样的氛围里遭到了挑战。[4]而这种亲子关系的问题也是传统人类学所关怀的问题,是很本质的。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从亲子关系展开推衍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很多。很多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和学者,都担忧全球化可能会危及人类的文化多样性,这就成了个问题——全球化究竟会不会给人类带来同质性的文化?华琛(James Watson)和他的一些学生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Golden Arches East,从跨国连锁快餐巨头麦当劳入手,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研究证明,甚至标准化生产的跨国快餐业都得在许多方面与当地的文化相调适,所以这些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麦当劳连锁快餐店在许多方面都与在美国的不同。华琛因此认为,所谓全球化会带来同质性的文化的说法完全是一种现代神话(a modern myth)。[5]
以上例子说明,问题在田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的产生来自我们日常对周围发生一切的关注。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的各种问题也全球化了,这就要求我们扩大视野,时时考虑到你所兴趣的事情究竟与外界有没有联系,有多少联系。当然,发现问题更需要我们大量地阅读,因为只有对各种研究和理论了解多了,才易于发现学术上问题。学术工作不能完全如同象牙之塔,所以,应当充分关心社会民生,因为有许多问题恰恰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急剧的社会变迁也给我们提供了发现问题的空间。
本文初稿系在“云南大学2011年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生实地研究暑期学校”的讲课稿。笔者谨向何明教授致以谢忱,他的诚邀促成笔者写就此文。
[1]范可.重读米德的意义(代译序)[M].玛格丽特·米德.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Adam Kuper.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J].in Social Anthropology,vol.13,no.1,pp.2005.
[3]Arthur P.Wolf.Sexual Attraction and Childhood Association:A Chinese Brief for Edward Westernarck,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Jun Jing(ed.),Feeding China's Little Emperors:Food,Children,and Social Ch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James Watson.Introduction:Transnationalism,Localization,and Fast Food in East Asia[J].JamesWatson ed.,Golden Arches East:McDonald's in East As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