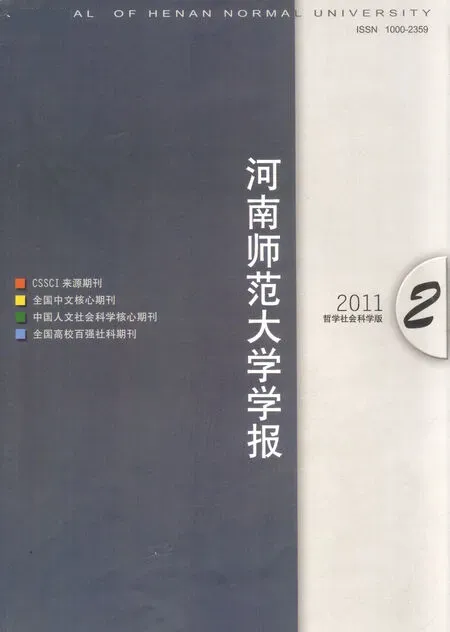《诗人玉屑》的唐诗观
孙 向 召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7)
《诗人玉屑》的唐诗观
孙 向 召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7)
《诗人玉屑》的唐诗观可以从它对盛唐诗和晚唐诗的理解来梳理,表现为盛赞“李杜”典范,重点是扬杜抑李,并且推原汉魏,诗法盛唐。总体上它的唐诗观,设立了双重目标,崇尚盛唐李杜为首的汉魏古诗气象,认为这个目标遥不可及,是个理想,因此转而设立晚唐目标,并发现晚唐诗含蓄讽喻价值,从而与宋代诗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契合。
李杜;诗格;晚唐风味
魏庆之的《诗人玉屑》(以下简称《玉屑》)是南宋最后一部总结性诗话汇编。作者不仅遍览诗歌、诗话、笔记、杂著,而且广泛学习诸家思想和言论,从而对整个唐代诗歌发展史,表现出了深刻的见解。《玉屑》卷十四、十五、十六分列唐代重要作家和作品,其关于唐诗的认识和体会主要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三卷,散见于其他卷中对唐诗的看法亦不少,如第十二卷中“品藻古今人物”对唐诗也有深刻的领悟。《玉屑》的唐诗观,对唐诗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一)盛赞“李杜”典范
《玉屑》唐诗观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注重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歌,高度评价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按条目讲,第十四卷是对李白、杜甫的评述,“草堂”、“谪仙”辑录条数在所选唐代诗人中条目最多,分别是33条、21条。诗论开篇即引用严羽的论评表达对李、杜诗歌的高度赞誉:“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1]卷1显示出《玉屑》对二人高超神妙、独领诗坛的崇拜。
《玉屑》赞赏李白的诗歌“千载独步”、“气盖一世”、“惊动千古”,并引用黄鲁直言:“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1]卷1对杜甫,《玉屑》则强调其“诗史”精神和“集大成”成就。如“宋子京赞”:“……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诚可信云。”[1]卷1又如“少游进论”云:“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子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呜呼,子美亦集诗之大成者欤!”[1]卷1杜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的精神不仅在唐代,在宋代也同样具有典范作用。可以看出,《玉屑》对李白、杜甫表现出来的盛唐伟大精神是高度赞誉的,这是其唐诗观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 )“李杜”优劣论
关于李杜二人孰优孰劣的问题自唐代开始就已经被文人们关注。李杜之后的中晚唐,人们或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这个问题到了宋代仍然被广为关注。

太白:“辞粟卧首阳,屡空饥颜回。当代不饮酒,虚名安在哉。”……此类者尚多。愚谓虽累千万篇,只是此意,非如少陵伤风忧国,感事触景,忠诚激切,寓蓄深远,各有所当也。子美……忠义所感,一饭不忘君耶。
世俗夸太白赐床调鼎为荣,力士脱靴为勇。愚观唐宗,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者哉。其意急得艳词艳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就使滑稽傲世,然东方生不忘纳谏,况黄屋既为之屈乎。说者以谋谟潜密,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1]卷1

《玉屑》还从“义理”角度评价,认为杜甫优于李白。“白不识理”条借苏子由之言:
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画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去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1]卷1
可以看出,李白一味豪放的诗风,超出了儒家所涵定的微言大义和忠君爱国的要求,这成为《玉屑》借以批判的着眼点,从而在深层含义上肯定了杜甫“一饭不忘君”的儒家精神以及“感事触景、寓蓄深远,各有所当也”的诗歌内容和表现手法。总之,《玉屑》在总体承认二人各有优势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杜优于李”的诗史观。
究其原因,这大概与宋代理学思潮,以及魏庆之本人深受理学影响有关。众所周知,宋代理学勃兴使“诗史”理论融进义理学说,促使诗歌叙事抒情与教化相互结合。在理学观念的支配下,一些批评家对杜甫“诗史”的关注逐渐向诗篇“诚实”、“义理”、君父意识等内涵倾斜。魏了翁希望“笃意”学杜甫“诗史”的人,“沉潜于义理,奋发乎文章”,不要在分韵摘句上玩雕虫小技[2]。刘克庄认为,注杜诗而将诗歌与具体史事一一对应实在不恰当,他指出:“杜公所以光焰万丈,照耀古今,在于流离颠沛,不忘君父”[3]。苏轼也对杜甫评价极高,原因在于杜甫“一饭未尝忘君”[4]318。以上说明,《玉屑》关于李杜优劣的论述是宋代的主流叙述。
(三)推原汉魏、诗法盛唐
《玉屑》关于盛唐诗的理解还体现在大量征引的《沧浪诗话》及其他言论中,如“诗辨”门引“沧浪谓当学古人之诗”:“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人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1]卷1“诗评”门引“沧浪诗评”:“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盛唐人有似拙而非拙处。”又“考证”门:“前卷读之尽佳,非其选择之精,盖盛唐人之诗,无不可观者。”[1]卷1认为盛唐诗紧承汉魏五言古诗,皆为诗歌第一境界。这里有几层含义:第一,虽然汉魏诗歌“不假悟”,盛唐诗歌是“透彻之悟”,但严羽标举的以盛唐为法正在于盛唐诗歌以兴趣为尚,有“莹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妙处,像汉魏古诗一样不可句摘,“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这是《玉屑》所以标举以李杜为首的盛唐诗歌的根本原因所在。第二,严羽认为诗歌境界有等级性,汉魏境界最高,属于“不假悟”。其他诗歌由于没有实现情景交融的境界,都不如汉魏盛唐诗,这说明《玉屑》认可诗境存在着等级差别。第三,“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这句话中转折词“而”表示语气的转折,它代表着观点的转换,反映出严羽根本上是宗唐的,因为在他看来,汉魏古诗是高标准,高理想,根本无法实现,而且年代太久远,不足以引起人们重视。认识到这一点,他于是干脆从唐人着手,“截然”二字鲜明地展现出他的态度。客观地说,李杜诗歌与汉魏古诗相比,还是有迹可循的,尤其杜甫诗法可学。盛唐诗歌处处可观,这在宋代人眼里已达成共识。《玉屑》在摘引宋人诗论时,也内含着这样的思想。第四,确立盛唐诗观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这是借以回应今人的不足。它指出今人治经的功夫太甚,偏离了诗歌本来之途,希望能够扭转今人诗歌追求上的偏邪的风气,认为应该用今人研读儒家经典的功夫认真熟读汉魏以来的古诗,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就是魏庆之借《玉屑》拯救今人也即给江西后学和四灵、江湖诗人偏离诗学之途指出的一条正确之路。当然,这样的理想是否能实现,他没有把握,只是提出希望和具体做法、记载有关诗论而已。
二
(一)晚唐别称
《玉屑》除了视盛唐诗歌为楷模外,对晚唐诗歌也很关注,体会颇为深刻。从“唐之晚年”条开始至“晚唐”,论及有孟郊、贾岛等12人,其体认的晚唐诗意义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呈现出较长的时段。从对晚唐指称术语来考察,《玉屑》辑录有“晚唐”、“唐人”、“唐末”、“唐之晚年”不同的称呼,均指言晚唐诗人或诗作。从引录内容上辨析,可以看出《玉屑》对“唐人”的意义还没有明确的意义,有的泛指唐代诗人,有的指盛唐,还有的指中唐,也有指晚唐的。这说明,晚唐的意义范围不甚明确,但是《玉屑》对唐诗发展史进行有意识的划分和定位是有价值的。
(二)晚唐意义
总的来说,《玉屑》对晚唐的评价贬中有褒,客观公允。贬的方面,认为晚唐诗歌风格寒俭、鄙俚、卑浅。如引录杜牧“品题”评李贺诗“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六一居士诗话”条评贾岛诗“枯寂气味”,“隐居诗话”条评孟郊“陋于闻道”,“高斋诗括”条评杜荀鹤“鄙俚近俗”,引“诗史”及“室中语”条评(晚唐)“浮艳无足尚”、“格致卑浅”。概言之,《玉屑》对晚唐诗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多采用批评的口吻和判词。其价值在于写出了晚唐诗歌较盛唐时期的变化和衰落。如“诚斋论晚唐诗”引《文集》:“然则谓唐人自李杜之后,有不能诗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论也。谓诗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灵实哀梨之论也。”[1]卷1
晚唐诗歌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用词精工、词意深妙上。如“高情远意”条、“词意深妙”条引录“谈苑”评李商隐诗用字精深,“古人措辞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不失为好的方面。“诗评”门引用“诚斋评为诗隐蓄发露之异”:
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近世陈克咏李伯时画宁王进史图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是得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污秽乎!惟李义山云:“侍燕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矣。[1]卷1
“晚唐”门“诚斋论晚唐诗有三百篇之遗味”引《馀话》:
诚斋序顺庵刘良佐诗稿云:……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云:“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战场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云云)。先生此序,深造作诗宗旨,故录之。[1]卷1
上面两段话均为《玉屑》引录诚斋诗评,第一条从微词婉意传统梳理出《国风》、《小雅》、《左氏传》一脉相承的关系,最后引用李商隐《龙池》诗,表明对晚唐寄托比兴作品的推崇。第二条指出晚唐诗承继了诗三百“怨而不怒”、含蓄不露的传统,肯定了晚唐诗“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的风范。魏庆之通过对诚斋诗论的引入,指出晚唐诗歌具备含蓄不尽的韵味与寄托遥深的特点,认为这是晚唐诗值得欣赏的地方。
综合《玉屑》的盛唐诗观和晚唐诗观,它一面崇尚盛唐诗,奉之为理想,一面又看好晚唐诗,连魏庆之本人所作诗歌也多具晚唐格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宋人在对盛唐诗难以企及的情况下,只好转而效法晚唐。宋初晚唐体的盛行,南宋中后期四灵、江湖诗人复归晚唐风的创作,实际上都在具体创作中与晚唐诗风有所联系。而杨万里等人对晚唐风味的揭示,也可以说明晚唐诗歌成为宋人一直效法的隐在原因,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是宋人诗学选择的结果。更明确点说,总体上宋人宗唐,设立了双重目标:先是以盛唐李杜为首的汉魏古诗气象,这个目标是个理想,不易学,因此,宋人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转而设立晚唐目标,并发现其含蓄讽喻的价值,于是晚唐地位就突显出来。《玉屑》发现了宋诗的这一特点并赋予其各自应有的地位,是对宋诗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变化的很好总结。
[1]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魏了翁.鹤山集:卷52 [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G]∥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0.四部丛刊本.
[4]苏轼.苏轼文集: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86.
I206.2
A
1000-2359(2011)02-0174-03
201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