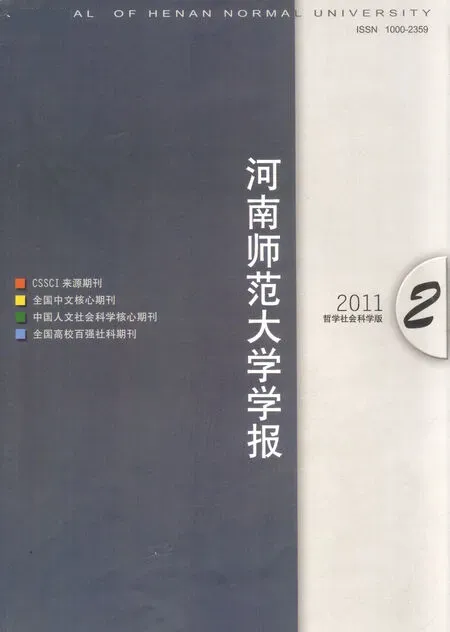汉代诗教思想之形成及其特殊内涵
郑 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汉代诗教思想之形成及其特殊内涵
郑 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汉代诗教是从古老的乐文化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它被用以强调《诗》的“谏政”功能和“修身”之效,还不具备创作论的内涵。汉代诗教话语保留着乐教的文化因子,这是它的某些表述令人疑惑的重要原因;其美学意义在于以道德、礼义的教化价值作为评判美的依据,确立了封建时代意识形态审美的基本范式。
乐教;诗教;意识形态审美;话语建构
将诗教定位在文学创作论的范畴中,认为它表达的是关于作诗的规定性,这大概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其实这个看法更加适合于魏晋以来文学独立的时代,而和汉代经学语境中的诗教概念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一、诗教与乐教
古人所谓教化,乃是“礼”内化为人之心性的种种途径,人们遵道循礼,仿佛是率性而为,便是得于教化之功。若分而言之,则“教”、“化”自有别,《增韵》曰:“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教;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教”是凭借言说的力量,将道业外烁于人,其本意“通谕告之词”;“化”是行为、环境的浸润和熏陶,臣民身处其中,对秩序的亲切认同感油然而生,其优点是“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1]。在古代,“教”与“化”对应于诗教和乐教这样两种教化形态。孔颖达注《礼记·经解》云:
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教也。
诗教与乐教在理论上的分别就是如此,而就思想史的一般情形而言,它们实在是纠缠不清。因为诗为乐章,备受推崇的三代诗教严格地说就是乐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诗教独立以后每每显示出向乐教回归的趋势。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儒家要从学理上为“礼”寻找人性论的根据,力图将一种外烁的价值规范内化为人的自我生成。在宋代理学氛围中,诗教已经脱掉了耳提面命式的严峻面孔,读《诗》仪式化了,《诗》的领受心灵化了,儒家教义的施行日常化了,洒扫应对亦可体认天命,循礼守义仿佛自乐为之。这非常符合乐教的精神实质,因为乐者,“中心诚乐而为之也”[2]。

古代中国人如此崇拜乐的力量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这自然与华夏先民的思维定势与心理积淀有关。但就意识形态的建设而言,乐教委实有着它的长处。周代是理性文明跃动的时代,周公制礼作乐或许正是取其长处。宋人郑樵说:“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举三达乐,行三达礼,庶不失乎古之道也。”[3]这里的“古道”,其精髓是礼、乐相须为用,以乐助成礼的施行。用今天的话讲,乐是一种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它不以纯粹的观念形态存在,而是融汇在政治制度中,借助仪式的操练实现其功能[4]。还以上引《周礼·春官》一段话为例,贾仲彦疏云:
大祭祀之际,“言‘帅瞽登歌’者,为下神合乐,皆升歌《清庙》”;“此大飨,谓诸侯来朝……其在庙行飨之时,作乐与大祭祀同”;“射节,王歌《驺虞》”。
《清庙》是周初朝廷所作颂诗,“祀文王也”;《驺虞》用以表征文王之化,“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周礼》记载的是当时官方用乐的情景,诗歌在祭祀先祖、诸侯朝会以及天子享射等场合被演奏,已经成为“礼”的一部分。礼者,别异也,首先是在天子与诸侯之间辨别贵贱尊卑,而观礼的主体正是周天子与诸侯。所以说,演奏《清庙》、《驺虞》,并非仅仅是表达对于先祖的怀念敬仰之情,而是要向诸侯灌输“礼”的观念,强化他们同神共祖的信仰以及对于国家的深切认同感,以确立周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可见,在周代礼乐文化氛围中,诗乐舞的表演过程实质上是礼义精神的发散过程,接受者在类似于艺术的欣赏中完成对秩序的领悟。
乐教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趣味,也规定了后世精神文化的秩序和法则,那些构成诗教规定性的话语表述起初从属于乐教的范围。李泽厚说:“孔子之前的关于乐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讨论乐与和的关系,一个是讨论乐与德的关系。”[5]除此之外,乐与天道、乐与性情、乐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是很紧要的问题,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严密的乐教感应系统。感应是古代乐教理论的逻辑,音乐与宇宙、性情、治政三者间是一种直接和透明的关系。音乐是人心感物的产物,通过音乐教育同样能够唤醒人的良心,起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效果。所以古人定要辨明正声与奸声、古乐与今乐,这是乐教能够发扬的基础。
后来,汉儒将乐教理论的相关思想移入《诗》论,把原属于乐的教化功用归属于《诗》,于是,儒学的教化便改由《诗》来承担了。《毛诗大序》中还保留着乐文化的因子,它对诗歌抒情言志本质的强调以及关于诗歌与时代关系的论述,显然是借用了《乐记》的话语形式。问题是,乐和诗毕竟有着各自的规定性,文字诗也缺乏音乐的那种亲近自然的本性,于是,当有些在乐教中不言自明的表述移用到诗歌理论时,便有了“隔了一层”的感觉。比如《毛诗大序》说诗具有感动天地鬼神的能量,具有移风易俗的强大功效等等,这些说法令人匪夷所思。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儒的诗说生硬套用了乐教的逻辑,将音乐的自然本性赋予诗歌,导致了理论上的隔阂。
二、汉代诗教理论的形成轨迹
从乐教到诗教的转变贯穿了西周后期以来礼乐崩坏的整个时期,其间经由先秦士人的努力,最终定型在汉代的经学语境之中。历史地看,乐教的衰微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礼乐文化凝聚着周代宗法封建政治格局中的尊尊、亲亲之义,它也只有在这样的伦理氛围中才能持续下去,所以,“上下相倾”、“纪纲绝灭”的政治情势必然会导致制度之礼的废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依然进行着诗乐舞的表演,但由于失去了“乐德”的支撑,这种表演就不免褪变为一个豪华的“过场”。二是面对春秋中后期以来新乐的冲击,雅乐的演奏越来越稀少。如《国语·晋语》载晋平公好“新声”,《乐记》载魏文侯好“郑卫之音”,《孟子》载齐宣王“好世俗之音”等等。这些新声以其新奇刺激的娱乐效果迅速迎合了国君们的口味,而那些过于正经严肃的雅乐则被抛弃。加之战争的破坏,统治者无暇经营,乐师散走四方等因素,乐教事实上走向了衰落。乐教的崩坏标志着那种曾经作为活生生的政治生活内容的礼乐本身已经终结了,乐教的衰落为诗教崛起提供了契机。
“诗教”是一个后起的名词,有着特定的内涵。《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注云:“《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在汉人的理解中,“诗教”并不是教人如何作诗,而是以诗为教化的工具。乐教的衰落导致《诗》演唱功能的逐渐丧失,孔子后来就得到一大推重复、错乱的文字《诗》。文本性的发现是诗教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春秋中叶以迄战国时代,乐教的文化空间逐渐收缩,诗的文“义”逐渐凸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和士人乌托邦建构的资源。从先秦到两汉,诗教观念的形成大致上沿着《礼记》和孔颖达揭示的两条线路展开。
其一,关于“讽谏”的用《诗》传统的形成。以《诗》谏政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臣子们用《诗》所承载的历史经验和德政思想引导君主的行为,用《诗》所实录下来的“风衰俗怨”的图景表达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其目的都是为了教戒。后来,诸子们将这种实用主义的用《诗》行为纳入到自己的思想构造之中,并结合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对《诗》之所以用的学理依据做了有力的揭示。在子学时代,士人从创作论的角度体认诗歌的“言志”内涵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孔子和七十子“诗无隐志”的思想、荀子和庄子“诗以道志”的思想都是从作诗的角度理解诗歌抒发怀抱的本质的。“他们虽然还不承认‘诗缘情’本身的价值,却已发见诗的这种作用;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那么缘情作诗竟与陈志献诗殊途同归了”[6]。朱自清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古代采诗制度,指出先秦儒家“缘情”与政教间有本质联系,就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今天看来,根据新出土文献整理而成的《孔子诗论》能够为这个推论提供更为直接的证据。《孔子诗论》是战国中前期的作品,它完全贯彻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比如它说《小雅》“多言难而怨怼者也”、《邦风》“民之有疲倦也”、《小旻》“拟言不中志者也”、《关雎》等七篇“童而偕贤于其初者也”、《葛覃》“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等等。学界从多方面论证了它和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甚为可信。这里要说的是,从最初实用性的讽谏行为到汉代美刺理论的形成,《孔子诗论》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从学理上看,《诗》三百政教功能的实现有赖于《诗》文本的支撑,而《孔子诗说》对《诗经》“怨情”内涵的发掘,关于“人欲”、“民性”的体认和赋予,则为《诗》功能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源于社会心理层面的依据,这样,采诗说、讽谏说及美刺说就获得了逻辑上的合理性。而后来孟子将《诗》三百和“王者之迹”与“春秋之义”联系在一起,则为美刺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源自历史经验方面的依据,从而奠定了汉儒历史化解《诗》的理论基础。汉儒继续努力,将三百篇都与民俗风情挂钩,又坐实为“为某公而作”,于是有“正变”说与“六义”说的产生,《诗》三百转化成了“政治教科书”。
其二,关于修身的学《诗》传统的形成。所谓“诗教”也是强调学《诗》对于培养道德人格的重要作用,因为汉儒“依违讽谏”的目的就是为了“格正君心之非”。最早将学《诗》和道德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是孔子,他认为《诗经》是“无邪”情性的呈现,具有感发志意、导人向善的教育功能,即所谓“兴于诗”也。春秋时期,《诗》演化成一种用于“专对”的外交辞令,是贵族社会通行的话语方式。只有孔子才赋予《诗》以修身之具的意义。他教育伯鱼要多读《二南》,启发子夏从《硕人》中悟出“礼后”的道理,引导子贡从《淇奥》中领会“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生境界,这些例子都说明“兴于诗”是孔子确定的《诗》学教育纲领。春秋时期,礼义精神逐渐失去了制度之礼的支撑,转而在《诗》文本中寻求寄托,所以在孔子那里,诗歌对“礼”的演示转而为对礼所蕴涵的道德精神的高扬,这是孔子“乐云乐云”之叹的真实含意。
萧公权这样总结孔学之宗旨:“其最大的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7]这是不错的,后来的荀学与孟学虽然见解不同,但是思想进路都大致如此。因为儒学后生学成以后是要“仕进”的,所以诸子的学术话语都有一个“隐含的读者”——未来的统治者。儒家的教化是要将天下人改造成为具有有教养、守礼数、有同情心和秩序感的意识形态的人,需要统治者先行具有正心诚意的君子人格。在先秦儒家学术中,如果说孔子是就《诗》论及道德修养的话,那么到孟、荀那里则开始了以君子人格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建构。孟学自然是如此。关于荀子,其学术的确有明礼、重法的倾向,这是他就时势而立说的结果,但是荀学是根本不同于法家学术的,因为它还继承了儒家的乌托邦精神。荀子始终将“德政”置于“霸政”之上,将以德致位的“君子儒”树立为理想君主的原型。《荀子》一书以《劝学》和《修身》开篇,而学习的目的即在于“自美其身”,有“美身”斯有“美政”和“美俗”。所以,儒家士人的《诗》学一旦牵涉到“王道”,《诗》的修身进德的价值就必然会凸现出来。在今天看来,孔子“为汉制法”不仅仅是指其“乘殷辂,服周冕”的思想为汉初郊祀车服制度的草创提供了参考,更深层的意义上,先秦儒家对于修身政治功能的论述开启了汉人“格君心之非”的致用方向,给出了汉儒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基本思路,从而也奠定了汉儒道德化、伦理化说《诗》的基本原则。
三、汉代诗教思想的美学意义
诗教是从古老的乐教传统中独立出来的。《诗》本来是周礼的歌词,后来逐渐失去了演唱的性质,演变成为一种可以被阐释的文本。阐释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赋予”的过程,先秦诸子基于讽谏的用《诗》传统和他们对于诗歌修身功能的新拓展,将《诗》三百视为民风民俗的一面镜子,并开启了历史化、伦理化的《诗》学阐释思路。在汉代,先秦儒学话语的“隐含读者”以更独断的法家专制者的身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的一流士人弱化了先秦那种“以道制势”的恢弘气势,转而更加依赖于通过学术话语的建构来间接表达这种隐密的政治诉求。在汉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的政治文化格局中,《诗经》的沟通功能和政教内涵被突出地加以强调,并以诗教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因此,汉代的诗教概念主要是一个经学的范畴,用以强调《诗》的“谏政”功能和“修身”之效。
我们不同意学界批评汉儒以《诗》为用、将《诗》中审美因素消失殆尽的观点,也不大认可在一个狭小的审美自律的天地中发掘“诗经汉学”之文学性的做法。因为汉儒的诗说主要是一种政治价值的呈现形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学。他们从诗之本质论、功能论、表现手法及风格,以及诗歌与时代的关系等方面铺陈出来的诗教理论,是将适合儒家教化原则的某些先验的规定性赋予《诗经》,是用认知形式装点起来的思想信仰。这种信仰的真理性取决于它与真理本身相契合的程度。如果我们从“审美经验”而不是从“无功利”的抽象观念出发来体认美的真理,那么汉代诗教的美学意义在于以道德、礼义的教化价值作为评判的依据,确立了封建时代意识形态审美的基本范式。所谓意识形态审美是说人们的审美经验处处打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具体地说,它并不是要将直接的政治实用性树立为艺术美的准则,而是认为理想的艺术应当符合某种超越权力政治之上的文化关怀。就汉代《诗经》学而言,毛宣国先生指出:“汉儒中许多人强调《诗》为政治教化服务,主要还是因为一种政治责任感,有一种积极参与与干预现实的道义理想和政治关怀,有一种对黑暗政治和不良政治的批判精神,这正是汉人以《诗》为教,将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传统。”[8]这种意识形态美学观念与司空图、严羽等人构造的纯粹美学体系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将历史感、道德感、政教价值及士人的担当精神糅进审美经验之中,从而使得外在的价值规定性由理性层面渗透到感性层面,并获得某种美学品格。
汉代诗教思想是一个大的话语构造,它的基础是儒家制衡君权、重建秩序的道义担当精神,它的言说逻辑是通过“比兴”、“正变”的阐释策略强化或再造诗歌与历史、与道德价值的关联,从而将诗性话语转化成政治话语,适应其“以三百篇当谏书”的心理需要。当然,汉代诗教话语中也存在着少量的认知性阐释(比如诗学情性论),但是认知精神并没有成为诗学的基本言说指向,我们宁愿相信是汉儒的《诗》学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诗的真理。所以,汉儒说《诗》并没有将审美因素消失殆尽,更没有以文学观念来解读《诗经》。这样两种相反的观点实际上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审美自律”的观念。至于它是否一定就比汉儒的意识形态美学观念更为真实合理,这还是一个问题。
[1]王安石.原教[G]//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卷32.成都:巴蜀书社,2005:1102.
[2]苏辙.孟子解二十四章[G]//栾城后集: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郑樵.通志·乐略总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
[5]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07-108.
[6]朱自清.朱自清自选集:卷2[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127.
[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8.
[8]毛宣国.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文学院,2007:195.
[责任编辑海林]
AresearchonthePoetryTeaching’sformationandspecialmeaning
ZHENG Wei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Poetry Teaching i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from the ancient music cultural tradition. It was used to emphasize “remonstrance political “func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effect, did not have the cont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Poetry Teaching in Han Dynasty retained the cultural factor of Music Teaching, which was important reason that its presentation puzzled many people.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Poetry Teaching in Han Dynasty was that using the enlightenment values of morality and Ritual as the standard of judging beauty,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paradigm of Aesthetic Ideology in Feudal era.
Music Teaching;Poetry Teaching;aesthetic ideology;discourse structure
I206.2
A
1000-2359(2011)02-0159-04
郑伟(1979—),男,湖北枝江人,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基本理论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51055);山西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0809012)
2010-11-12
——长春市第一中学学校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