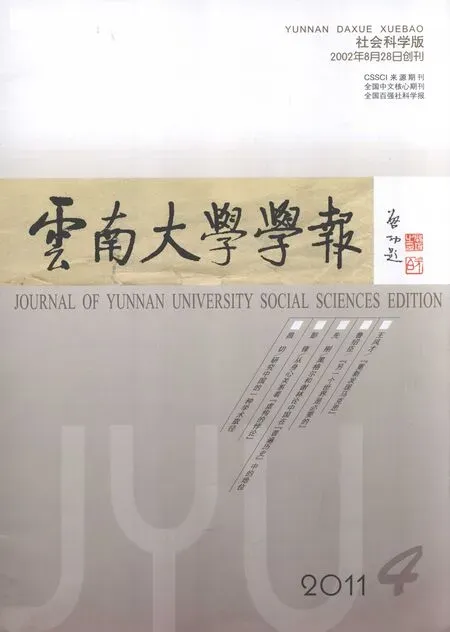试析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几种证明
赵 林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众所周知,近代哲学是从培根和笛卡儿那里开始的。黑格尔评论道:“我们可以借用西塞罗形容苏格拉底的话来形容培根:他把哲学理论 (从天上)带到了世间的事物里,带到了人们的家里。”“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 ‘陆地’。”[1](P59)如果说培根所开创的经验论哲学是植根于对自然世界的经验观察之上的,那么笛卡儿所开创的唯理论哲学最初则是建立在对自我意识的反思之上。
和培根一样,笛卡儿也把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怀疑当作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他比培根的怀疑论(“四假相说”)更加彻底。他为自己确立的四条最基本的逻辑规则的第一条就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2]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对一切已有的知识都进行了怀疑和否定,接着又对物质世界、上帝甚至自己的身体也进行了怀疑,最后只剩下怀疑本身 (即思维)是无法怀疑的,从而由怀疑这个内在的经验事实推出一个怀疑着的“我”,确立了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 “我思故我在”。
然而,这个被笛卡儿当作整个哲学的出发点的第一原理,同时也将可能成为笛卡儿哲学的囚笼,因为除了自我意识之外,一切其他的东西 (包括物质世界、身体和上帝)都已经在此前被怀疑掉了。因此,要想走出狭隘的自我,在第一原理的基础上重建整个世界,就必须放弃怀疑论,以独断论的方式确立一个比自我更加具有权威性的新理论根据。在宗教信仰氛围浓郁的17世纪,这个新的理论根据只能是那个老的信仰对象——上帝。因此,为了实现从自我向上帝的过渡,笛卡儿不得不以更新的方式重现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
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来进行的,其具体的论证过程在《方法谈》、《第一哲学沉思集》和《哲学原理》中都有表述,①分别参见笛卡儿的《方法谈》第四部,《第一哲学沉思集》“沉思第三”和“沉思第五”,以及《哲学原理》第14、18、20、21条。下面就这三种证明作一点分析。
1.第一个证明——从上帝的本质分析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的第一个证明是一种先天证明,它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基本上是对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老调重弹,即从上帝的本质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 (这个证明后来又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人再次重复)。笛卡儿说道:“当我更加仔细地思想到上帝时,我却明显地发现存在并不能与上帝的本质分开,就像三角形的三只角的和等于两直角不能与它的本质分开,或者山的观念不能与谷的观念分开一样;因此,设想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亦即设想一个没有什么完满性的最完满的实体,是和设想一座没有谷的山同样的不合理。”[3]
很明显,笛卡儿在这里是把上帝的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当作一个分析命题来处理的,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本质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存在。所谓分析命题,就是主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谓语的命题,例如“黄金是黄的”、“三角形有三只角”,“物体是有广延的”等等。在这些命题或者判断中,谓语都已经内在地被包含在主语的字义或定义之中了,因此只要一提到主语,就可以必然地分析出谓语来。
但是,关于一个东西是否存在的判断,却显然无法仅仅通过对这个东西的概念进行分析来得出。诚如康德后来所指出的,存在只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概念的属性;任何东西 (包括上帝)是否存在,不能由逻辑来推论,只能由经验来确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认为,存在不能作为分析命题的谓语,也就是说,存在这个事实是不能从一个概念中分析地推论出来的。说某一个东西存在,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综合判断了,而综合判断不具有必然性。因此,任何东西 (包括上帝)的存在,都具有或然性,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它的不存在并不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康德举了那个一百元钱的著名例子来反驳笛卡儿的本体论证明,他嘲笑说,仅仅从一个东西的概念中分析出这个东西的存在来,就如同一个商人试图通过在他的账簿上添上几个零来增加他的财产一样可笑。[4]
许多人都认为康德的这个批判是很有力的,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康德的这个批判实际上并没有针对笛卡儿的形而上学理论。也就是说,康德的这个批判,仅仅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用经验的论据来驳斥形而上学,就如同用形而上学的论据来驳斥经验论一样,都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一般事物的存在都是由经验来加以确定的 (包括作为内在经验对象的“我思”),但是上帝却属于形而上学的对象,他的存在是超验的,与他的本质是完全同一的,这种同一性是靠着信仰来保证的。因此,康德用经验的论证 (如一百元钱的论证)去否定超验的或形而上学的本体 (上帝)的存在,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上帝”作为一个超验的本体,其存在当然不能成为经验的对象,如果仅仅凭着经验就可以对上帝的超验性存在进行置疑,那么上帝就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普遍信仰。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儿坚持上帝的超验性,直接从上帝的本质中推论出其存在的做法,是一种信仰主义的结果;而康德坚持从经验出发,反对由上帝的概念中直接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虽然笛卡儿是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开创者,但是在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上,他那貌似理性的论证就如同安瑟尔谟的论证一样,实际上是以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作为前提的 (即坚信上帝的本质与存在是先验地统一的)。就此而言,康德基于经验理性的批判是无法真正反驳笛卡儿基于信仰的本体论证明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儿与康德也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一者是形而上学的,另一者则是经验论的;一者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先验同一,另一者则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面对二者之间的这种分歧,黑格尔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他一方面指责安瑟尔谟和笛卡儿等人直接从上帝的概念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做法,另一方面也对康德割裂概念 (思维)与存在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基本的倾向上来看,黑格尔似乎更加同情安瑟尔谟和笛卡儿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黑格尔强调,存在虽然不是概念,但是它却是“概念的外在化”,概念不仅仅停留在自身中,而且还要超出自身而走向存在。显然,黑格尔强调的是运动和过程,是概念自身的辩证发展。他针对康德的一百元钱的例子反驳道,一百元钱的概念固然不等于真实存在的一百元钱,但是一个人如果总是停留在二者的区别上也不是健康的常识,重要的是如何扬弃二者之间的对立,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百元钱的概念本身并不包含存在。同样在一百元钱那里,观念与存在的对立的绝对性也是要被扬弃的……思维、概念必然地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示自身为客观的东西。”[1](P285)而这个扬弃对立的过程就表现为从头脑中的一百元钱 (经过艰苦的劳作)进展到真实存在的一百元钱。事实上,黑格尔的整个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就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重演的本体论证明。在他那里,最初的东西是逻辑学,即纯粹的思维或概念,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逻辑学中演变发展出来的。正如安瑟尔谟和笛卡儿从上帝的概念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一样,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概念中推论出整个世界的存在。
当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本体论证明不同于笛卡儿的上帝的本体论证明,黑格尔强调的是过程,概念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存在,它只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转化 (或外化)为存在;而笛卡儿的上帝概念则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存在,因此上帝的本质 (即概念)与存在是先验同一的。但是,无论是笛卡儿还是黑格尔,都表述了一个同样的重要思想:存在之为存在,只是由于概念的存在。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时指出,由于黑格尔是从存在的概念而不是从存在本身开始的,因此存在与思维只是在思维本身之中形式地对立着,思维可以轻而易举地产生对立而又扬弃对立,因为存在仅仅只是思维的存在,同一性也只是思维自身的同一性而已。“在黑格尔看来,。”[5](P114)也就是说,存在不再是客观的经验事实,而只是主体的自我意识,是思维的存在、意识的存在。与黑格尔一样,在笛卡儿那里,思维或意识就是能动的,就,而自我意识本身含有一种要求存在的冲动,它只有在被表述为时才是自我意识。在这里,思维与存在是完全等同的。正如从自我意识的概念中分析出自我意识的存在一样,笛卡儿同样也从上帝的概念中分析出上帝的存在。由此可见,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过是“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第一原理的一种重演而已。
当然,笛卡儿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不愿意识到这一点。他本来完全可以把上帝证明为仅仅就是自我意识,但是他却通过一个悖论把上帝从自我意识变成了客观本体。这个悖论就表现在他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二个证明中。
2.第二个证明——从结果性的上帝观念推出原因性的上帝存在
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二个证明在形式上不同于本体论证明,它不是通过对上帝概念的分析,而是通过因果关系的逻辑推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个论证所依据的大前提是这样一条公理:原因必须“形式地”或“卓越地”包含结果,①在这里笛卡儿借用了经院哲学的两个概念,所谓“形式地”是指原因的实在性等于结果的实在性,“卓越地”是指原因的实在性大于结果的实在性。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结果不能大于原因。笛卡儿的论证表述如下:“我的任何一个观念,如果它的客观实在性 (或完满性)居然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种实在性 (或完满性)既不是‘形式地’在我之中,也不是‘卓越地’在我之中,因而我自己不能是它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必然地推论出:我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东西,还有另外某种别的东西存在,它是这个观念的原因。”“因为实体的观念虽然因为我是一个实体而存在于我心中,可是我是一个有限的实体,是不会有一个无限实体的观念的,除非是由一个真正无限的实体把它放进我心中。”[3](P169~170)也就是说,我心中有一个上帝的观念,但这个观念的原因却不能是我,因为我是一个有限的实体,不能产生一个无限的实体的观念 (结果不能大于原因),所以这个观念一定是被一个无限的实体放到我心中来的。简言之,依据原因必须“形式地”或“卓越地”包含结果的原理,从我心中有一个无限实体的观念,可以推出一个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客观存在。
笛卡儿的这一证明,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曾经被奥古斯丁论述过。初看起来它似乎很有道理,然而细加分析却可以发现它本身包含着一个悖论:如果有限的“我”不能产生一个无限的上帝观念,那么有限的“我”何以竟能包含一个无限的上帝观念呢?尽管无限的观念来自无限的存在,但它毕竟被包含在有限的“我”之中。如果有限能够包含无限,那么有限也同样可以产生无限,无限也就不是无限,而是有限了。当笛卡儿说在有限的“我”之中有一个无限的观念时,他只是从有限的意义上去表述无限,无限只不过是对有限的否定而已。因此无限只是有限中的无限、具体的无限、相对的无限。由于自我意识本身是有限的,所以一切观念作为意识对象也都是有限的。当“我”对自身进行反思(“我思故我在”)时,“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不完满的东西 (因为怀疑本身就是不完满性的表现);当“我”对上帝的观念进行思考时, “我”实际上只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把上帝的观念当作无限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有限的“我”的否定而达到无限的上帝。①尽管笛卡儿对此不予承认,他辩解说,如果我不是先知道了一个无限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呢 (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三个沉思”)?但是事实上,我们永远只是通过对有限的否定才得出无限的,因此无限实际上是一个缺乏确定内涵的空概念。因此,当笛卡儿说上帝的观念是一个无限的观念时,他只不过是按照“我” (有限的存在)所想象的无限性和完满性来理解上帝的。伽桑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按照我的里边的那些完满性的程度产生、做成一个观念,这个观念适合我们的渺小,也恰好适合我们的用处,它并不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不包含我们以前在别的事物里边所没有认识到的或从别事物里边没有知觉到的任何实在性。”[3](P210)也就是说,所谓无限的、完满的东西,并未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能力,说到底还是由有限的“我”所产生、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作为原因,并不小于作为结果的上帝观念。如果这样来理解上帝观念的无限性(正确的理解只能是这样),那么笛卡儿的那个有限包含着无限、却又不能是无限的原因的悖论就可以被克服了,笛卡儿的论证就可以避免自相矛盾了。
但是,悖论的克服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上帝观念的无限性只不过是被有限的自我意识理解为无限的有限性,那么上帝的观念就不是被客观实在的上帝加到我们的意识中,而只能是自我意识的杜撰。这样一来,且不论在神学上会导致渎神的可怕后果,仅从哲学上来说,这一论证就无法达到它所预期的结果,即证明上帝的客观存在。伽桑狄幽默地讽刺道:“假如上帝就像我们所理会的那个样子,假如上帝只有像我们看到在我的心里那么一点点完满性 (尽管我们理会的这些完满性在上帝里更为完满得多),那么上帝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3](P209~210)但是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上帝到底有多么了不起,在这里甚至连上帝的客观存在也都无法保证了。
然而,笛卡儿需要一个上帝!否则他就无法从狭隘的自我意识过渡到广阔的心物二元论世界。因此,思维一向清楚明白的笛卡儿宁愿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一个自我矛盾的悖论,也不愿放弃上帝的客观存在这根理论上的救命稻草。在这里,笛卡儿的目的与他的第一个证明一样,就是要从自我意识过渡到上帝,从主观过渡到客观,从认识论过渡到本体论。只要能够从自我中推论出上帝来,任何风险笛卡儿都敢于承担。
在笛卡儿的认识论中,自我意识就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一切东西都要在自我意识的清楚明白的标准面前接受检验。但是,自我意识毕竟是一个狭小的主观世界,是一个相对的和有限的东西。为了保证自我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的可靠性,以及自我意识所依凭的清楚明白的标准本身的权威性,笛卡儿必须在本体论上确立一个绝对的和无限的实体,这个绝对实体当然只能是上帝。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从认识论中的有限的自我意识过渡到本体论中的无限的上帝?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一个逻辑上的转换,即把认识论上的自我意识―上帝的顺序转换为本体论上的上帝―自我意识。而这个转换恰恰是通过上述悖论而完成的:笛卡儿一方面从自我之中引出上帝的观念 (认识论);另一方面又依据“结果不能大于原因”这条基本原则,从自我之外来说明上帝观念的原因,从而推出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上帝 (本体论)。这个客观存在的上帝不仅是自我之中的上帝观念的原因,而且也是自我 (精神)和世界(物质)这两个相对实体的终极原因。笛卡儿就是这样通过“有限包含着无限、却不是无限的原因”这个悖论,实现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从有限的自我向无限的上帝的过渡。
尽管笛卡儿的上帝只是一个被有限所包含和所理解的无限,但是他却把上帝当作一个绝对的无限,或绝对实体。所谓“绝对实体”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主语,这个主语是对一切宾语的否定,对一切相对的有限事物的否定,因而它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这个抽象的“绝对实体”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纯存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规定性或内容,仅仅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语而已。可见,笛卡儿从自我中所推论出来的这个上帝实际上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概念。但是只要有了这个至高无上的概念,哪怕它是一个空洞无物的虚概念,笛卡儿就可以把它作为逻辑跳板而走出狭隘的自我意识的藩篱,走向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相互并行的二元论世界。
正是因为上帝作为绝对的无限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只是一个缺乏具体内容的纯形式,所以笛卡儿可以在逻辑上不顾悖论的危险而把它从自我中推论出来。逻辑论证注重的是形式,讨论上帝这个概论的内容,那是神学的任务。而笛卡儿要做的仅仅是证明上帝的存在,确切地说,证明上帝在形式上的存在。黑格尔精辟地指出,在笛卡儿的时代,“宗教所假定的东西被抛弃了,人们寻求的只是证明,不是内容。这是无限的抽象主观性;绝对的内容不见了。”[1](P69)上帝究竟是什么,这不是笛卡儿所关心的问题,他所关心的只是必须要有一个上帝存在,以作为整个心物二元论世界的基本保证。正因为如此,笛卡儿才不惜通过一个悖论,来把上帝从自我中推论出来。
由此可见,笛卡儿的第二个证明实质上是把有限的自我偷换成了无限的上帝,通过一个悖论,把上帝观念的原因由自我意识变为上帝本身。尽管这个偷换已经被伽桑狄在《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中揭穿了,伽桑狄明确地指出,笛卡儿的上帝其实就是自我意识本身,但是笛卡儿却仍然坚持这个证明的有效性。我们很难猜测,笛卡儿本人是否明明知道自己在逻辑上把自我偷换成了上帝,却仍然煞有介事似地进行着证明。但是笛卡儿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超出自我意识的小圈子。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奥秘,这一点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中就已经被注定了——笛卡儿如果不愿意像一个唯我论者那样被束缚在自我意识的襁褓中,他就只能借助于一个名义上无所不能、实际上却空洞抽象的上帝跳出自我意识的陷阱。因此,笛卡儿进行上帝存在证明的动机完全不同于安瑟尔谟,他不是出于宗教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出于哲学理论上的需要。
在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三个证明中,这一个证明是最具有笛卡儿特色的。它从认识论的自我意识出发,通过有限与无限之关系的悖论,推出了本体论的上帝。它表面上是通过结果去推论原因,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不证自明的——尽管笛卡儿试图说明一个客观存在的上帝是“我”心中的上帝观念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是那个含而不露的自我意识。笛卡儿就像一个玩弄障眼术的变戏法者,他拿起了一块顽石,在人们眼前晃动了几下,就变成了一块黄金。但是这个变戏法者自己心里却非常清楚,那块黄金是他事先就已经藏在道具下面的;至于那块顽石,无论怎么变,仍然还是一块石头。
3.第三个证明——从不完满的自我推出完满的上帝
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三个证明实际上只是对第二个证明的一种补充,即从不完满的“我”的存在推出完满的上帝的存在。笛卡儿从两个方面表述了这个证明:(1)我是不完满的存在,不能是自己存在的原因,这个原因只能是外在于我而存在的东西。(2)同样,我不能是自己继续存在的原因,除非有一个外在的原因使我继续存在,否则我将停止存在。这个外在的原因只能是上帝,所以上帝存在。[6](第20、21条),[2](第四部)这个证明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颇为相似,即从被动的、他因的、偶然的、不完满的存在推出能动的、自因的、必然的、完满的存在,从上帝的创造物的存在推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儿和托马斯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从自我的存在推出上帝的存在,后者是从宇宙间万物的存在推出上帝的存在。这个差别无疑再次向我们表明了笛卡儿的证明的主观性——自我意识仍然是整个证明的出发点。恰如费尔巴哈所指出的:“笛卡儿不是从物体、即感性之物中,而出上帝、引出上帝。”[7](P180)
笛卡儿的这一证明虽然是以一个内在经验的对象 (自我)作为出发点,但是它和第二个证明一样,仍然预设了一条先验的原则。第二个证明预设的先验原则是“结果不能大于原因”,而第三个证明所预设的原则是“不完满的东西必定不能成为自身的原因”。说一个东西不完满,只是就相对的意义而言,一个相对不完满的东西与他因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完满性是一种相对的属性,一个事物可能比另一个事物更完满一些,但是这种完满程度上的差异并不会涉及到事物究竟是自因的还是他因的。除非我们事先设定了“不完满的事物必定都是他因的”这一条先验原理,否则我们无法根据事物的完满性来推论它们的原因。况且,所谓“完满的”这一概念就如同“无限的”和“绝对的”等概念一样,都是一些没有具体内容的空概念。世间任何事物,都或多或少有着一些不完满的地方,一个没有任何缺憾的完满的存在物只能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理想。这个理想(即上帝)由于什么都不缺乏,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是,它只能是一个绝对的否定概念,即“纯存在”或“无”。诚如黑格尔所言:绝对的光明就是绝对的黑暗。
当然,由于这个证明涉及一些复杂的形而上学问题,涉及关于世界原因的根本分歧,即外因论与内因论之间的分歧,在此不便展开讨论。笛卡儿与牛顿一样,作为近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奠基者,其在世界万物的原因问题上是主张外因论的,这种外因论的机械论世界观使得他必然要把信仰中的上帝作为整个自然因果链的开端。从这一意义上说,笛卡儿从经验的自我推出一个超验的上帝也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要求他接受内因论的立场。但是对于笛卡儿的这个证明,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他仍然是从一个不完满的自我之中推出了一个完满的上帝。
纵观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三个证明,可以看出,笛卡儿极力论证的上帝不过就是自我意识而已。他宛如一个波希米亚的巫师,对着自我意识念了一通惑人耳目的符咒,然后大喝一声,自我意识就变成了上帝。就如同那些天性乐观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然而又对这些神明顶礼膜拜。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宙斯、阿波罗、雅典娜、阿佛洛狄忒等神明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外在化了的自我意识,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对宗教的自然本质作过深刻批判的费尔巴哈在谈到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时说道:“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就其真正含义而言,只不过证明:自我确定的、自我意识的思维的本质就是上帝的真正本质。”[7](P180)
如果说笛卡儿哲学的第一个环节即“我思故我在”表现了自我意识的确定过程,那么他的第二个环节即上帝存在的证明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和异化过程而已。这一点,在笛卡儿那里还是一个自在的过程;然而到了黑格尔那里,则成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自觉的过程。
4.笛卡儿哲学中自我意识与上帝的关系
上帝的存在一经证明,笛卡儿的自我意识就立即获得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这时它就不必再像在证明上帝存在时那样谨小慎微,而可以在心物二元论的世界中自由驰骋了。因为这时它已经不再是赤裸裸、孤零零的自我意识,而是披上了一件令人目眩神迷的上帝的外衣。既然上帝是无限的绝对实体,他无所不能,所以从上帝那里,笛卡儿就轻而易举地引出了两个有限的相对实体——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它们各自的属性分别是思维和广延。
这样一来,曾经在普遍怀疑的过程中被否定掉了的外部世界又被重新建立了起来。上帝是自我意识借以重建外部世界的必要手段,是实现认识主体 (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 (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的重要中介。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以后,不仅自然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有了一个终极性的根据,而且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也有了一个可靠性的保证。笛卡儿明确地表示:“上帝一方面把这些规律建立在自然之中,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我们对此充分反省之后,便决不会怀疑这些规律之为世界上所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所遵守。”[3](P152)于是,一个相互平行并且协调一致的心物二元论世界就在上帝权威的保证之下建立起来了。
在笛卡儿的哲学体系中,上帝的意义也仅限于此,上帝是为了自我意识对于客观世界的建构和认识而服务的。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韦伯教授在谈到笛卡儿思想的逻辑程序时说道:“那么,我知道:(1)我存在;(2)上帝存在,上帝的必然存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真理确定性和正确的知识都基于此。没有它,我就不能越出‘我思故我在’的范围,我将除了认识自我之外永远不能认识非我。正是上帝使我能够打破我的怀疑在思维与外界事物之间设置的障碍,它使我知道:(3)物质世界存在。”[8]笛卡儿本人也坦陈:“因此我非常明白地认识到,一切科学的确实性和真理性,都只是依靠对于真实的上帝的认识,所以我在认识上帝之前,是不能够完备地知道任何东西的。现在我认识了他,我就有办法获得一种关于无量数事物的完备知识,不但可以认识在上帝之内的东西,而且可以认识 (别的理智对象,以及)属于有形体的本性的东西……”[3](P176)
笛卡儿借用奥古斯丁、安瑟尔谟、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先贤的各种证明方法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其动机更多地不是出于一种宗教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出于一种理论建构上的需要。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不借助于上帝的中介,笛卡儿就会像休谟一样被局限在怀疑论的狭小天地中。正是由于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一个心物平行的二元论世界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保证,从而成为知识的对象。笛卡儿从建立在内在经验之上的自我意识认识论出发,经过向形而上学 (上帝)的跳跃,然后才能转向二元论世界观和物理学,并且用上帝的名誉来担保“天赋观念”的真理性,再由“天赋观念”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演绎出整个观念体系,从而建构起唯理论哲学的宏伟大厦。
笛卡儿虽然论证了上帝,但是从方法论或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上帝是从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是自我意识的结果 (尽管在本体论上,上帝被说成是自我即精神实体的原因)。由于近代哲学的重心就是认识论,因此笛卡儿实际上是把自我意识置于上帝之上,只是在理论需要时才借用上帝的权威来确保从自我意识向二元论世界体系的过渡。就此而言,笛卡儿和牛顿、贝克莱等人一样,只是利用上帝这个“大阴沟”(黑格尔语)来排除哲学和科学上的理论困难而已。正如在自然神论中,作为创世主的上帝在丰富多彩的自然界面前不过是一个形同虚设的傀儡一样,在笛卡儿的哲学中,作为绝对实体的上帝在桀骜不驯的自我意识面前不过是一个过了河就可以拆掉的跳板而已。汉斯·昆评论道:
由于笛卡儿,欧洲思想在一种批判的发展中达到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原本的确定性已不再寄予上帝,而是寄予人。换句话说,中世纪从上帝确定性推到自我确定性的方式被近代的道路所取代:从自我的确定性到上帝的确定性。
这是一个哥白尼式的转折点,相当于地球和太阳的关系的重要性。取代上帝中心论(Theozentrik),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人类中心论 (Anthropozentrik)。人站在中心,真正地以他自己的双脚站立着。笛卡儿以其最大的精力、决心和磨炼,在方法论上,从人出发,从主体出发,从他的自由、理性、确定性出发,因此他是第一个在哲学上证明科学自足性的人。他被恰当地称为“近代哲学之父”,“近代思想之父”。[9](P29)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笛卡儿.谈谈方法 [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M].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6]笛卡儿.哲学原理 [M].
[7]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一卷[M].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8] Weber.History of Philosophy [M].trans.by Frank Thilly.New York:Scribners& Sons,1908.
[9]汉斯·昆.上帝存在吗?——近代以来上帝问题之回答(卷上)[M].孙向晨译.香港:香港道风书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