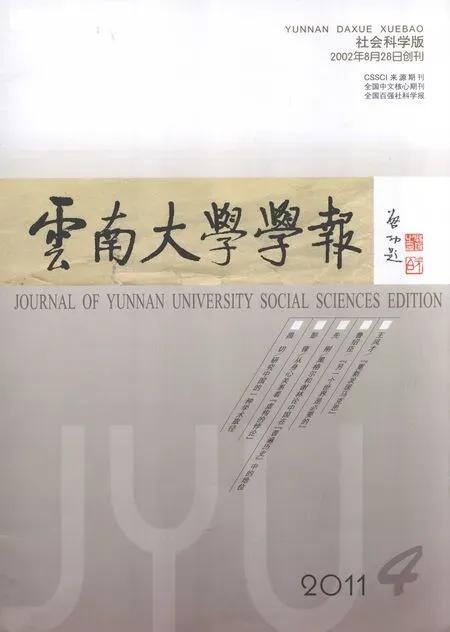研究中国的一种学术取径
——写在卜松山教授即将荣休之际
昌 切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研究中国的一种学术取径
——写在卜松山教授即将荣休之际
昌 切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中国研究;异;同;同情的理解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中国研究以我为主,是一种为认识、进补自我而平等看取中国之“异”的中国研究。这种研究思路也可在另一德国汉学家顾彬那里得到印证。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不同,卜松山认为西方不应自居文化霸主的地位,用西方的概念对中国作同质化处理,不应只“予”不“取”,而应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研究中国,辨识“异”而明了“异”之价值所在,以弥补自身之不足。
在卜松山教授即将从特里尔大学汉学系荣休之际,回想近十多年来与他的学术交往,感受最深的不是从他以及其他欧美汉学家那里知道了一种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另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文化如何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成和呈现,而是知道了在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汉学所存在的不大为人注意的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径或类型。
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卜松山教授,是在位于武汉大学人文馆的中文系那间不大而简陋的办公室里。他为中文系的师生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讲的是杨炼、刘宾雁和李泽厚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看取屈原。当时就觉得他的选题和切入方式很新鲜也很巧妙。杨炼初涉文坛以写朦胧诗成名,不久便转向“文化寻根”,写有《飞天》、《敦煌》和《大雁塔》等赞颂中国传统文化的诗篇。刘宾雁和李泽厚在青年时代就有了文名,“文化大革命”后,刘宾雁仍然以“写真实”为宗旨,著有《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等轰动一时的纪实文学作品,李泽厚则以《批判哲学的批判》等一系列哲学、美学和思想史论著极力倡扬启蒙思想。这三个人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风云人物,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在屈原那里各取所需,使屈原以三种面孔复活在二千多年后中国的思想文化论坛上。现在看来,这样做实际上是自况,是借屈原以确证自我:在杨炼是激活屈原的浪漫诗魂,在刘宾雁是从屈原身上提取有别于“第一种忠诚”(歌颂时政时事)的直刺时弊的“第二种忠诚”,在李泽厚则是把屈原美化成“向死而在”的追寻自由和美的孤独个体。不论对谁来说,屈原都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其意义所在完全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精神诉求。而经由屈原所见证的他们的精神诉求,多少能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卜松山教授所作的这个报告题为《屈原和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原是很贴切的,论述具体实在而不拘泥粘滞,未因论域大而流于空泛。
那时还不知道卜松山偏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体现出“天人合一”特质和“性灵” (自然)葆真的部分。后来接触得多了起来,对他的学术经历和作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知道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他更倾心于未经“西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对于一味追随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化则多有不满之辞。他在德国读大学时由学地球物理转攻汉学,触因是他读到一本介绍中国禅宗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向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神秘世界。随后他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随汉学家米列娜教授深造,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是为人疏淡放达、作品格调峻奇的清代书画家郑板桥。他曾经到郑板桥的家乡江苏踏访郑板桥的踪迹。不知我的记忆是否有误,在特里尔大学他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郑板桥手书的“难得糊涂”的拓印件。他还十分欣赏辞官归隐田园的东晋诗人陶渊明,把陶渊明的作品译介给了德文世界,并曾在德国的一个葡萄酒节上专就陶渊明与酒的关系做过一个充满“诗情酒意”的漂亮演讲,对陶渊明酒中存真意的人生姿态倾慕不已。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卜松山最感兴趣的恐怕是追求大道无形、自然神韵的一路 (李泽厚所谓庄禅美学一路),他所撰的《死法与活法——中国文学与艺术中的法与无法的探讨》和《论叶燮的〈原诗〉及其诗歌理论》两文,论述了从唐代司空图经宋代严羽到清代叶燮和王士祯的诗论,梳理了自“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到以禅喻诗再到诗求“别才”、“别趣”和“神韵”的诗学脉络,其重心显然落在“至法无法”之上。何谓“至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最高的法则。最高的法则与自然同一,是大道。大道无形,无所不在,寓于“无法”之“法”(技法,art)之中。道为法中之法即“至法”,非“至法”之“法”则只是次一等级的技法。《庄子·养生主》里面的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刀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恢恢乎游刃有余,当可视为“至法无法”极佳的范例。梁惠王赞叹地问:技何以达到这等地步?庖丁答: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里的“进”当“超过”讲。可见庖丁看重的是道而不是技,他得道解牛,循的是“天理” (自然法则),得到的是“至法”,技(法)是不值一谈的。古代有“雕虫小技”一说,现代有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的说法,所传达的都是“至法无法”的意思。
卜松山在中国现代文化方面也做过出色的工作。李泽厚的美学史专著《美的历程》,刘纲纪评述德国美学在中国的长文,以及部分朦胧诗人的诗作,就是由他或由他主持翻译成德文发表的。他还写过若干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论文。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他进入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特有的一个视角,也是他给出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尺。与中国学者解诗的趣味大为不同,他从毛泽东的诗词里面可以读出一种内在的威严聪慧与大度的气息,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相互酬唱的雅趣。他研究中国现代诗歌,选评的是杨炼的《飞天》、李小雨的《敦煌》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认为这几首诗追慕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赞扬《飞天》完全把自我融入到描写对象中,达到了“物我两忘”、“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在他看来,这种艺术境界对于只顾追求个人利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西方来说,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的。他论及儒学的现代意义,认同海外新儒家对于“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酷待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造成中国文化断裂带的指责,认为儒家文化“天人合一”和“厚人伦”等优良传统值得珍视,尤其是值得正处于深重的现代性危机之中的西方人珍视。
一个是现代西方的需要,一个是古代中国的文化,由现代西方的需要溯及古代中国的文化,发掘古代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我以为这是卜松山研究中国的一个基本思路。十年前写《文化间际对话:卜松山眼中的他者》一文时我就有了这个认识。在他那里,不同文化之间交际的理想状态,不应该是一种文化压制、吞没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化在屈从、效仿中迷失、丧失自我,而应该是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看待另一种文化,取对方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按他的说法,把西方文化的价值绝对化是不合适的,西方应该自觉地批判反思自己的文化霸权立场,不要在世界上搞“文化一言堂”,不要奢望把自己的文化价值普世化,使世界变成一个无差异的乏味的同质化世界,而要看到文化的相对性,看到人文价值的不同取向,平等而非盛气凌人地与其他文化展开富有诚意的对话,从其他文化的优良传统中汲取现代西方所需要的“共同价值”。这其实也就是他多次表述过的“与中国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对待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无论是对待中国古代文论还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他都十分注意开发其中所隐含的现代西方所缺少的“异”的优质元素,对于其中“同”的成份往往置而不论,而对于一味追随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化则大不以为然。
说实话,在几年前读到卜松山的德国同行顾彬教授的两篇文章以前,我并不清楚卜松山的研究思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不清楚这个研究思路与美国汉学相比有什么区别。顾文一篇发在《读书》杂志上,一篇发在一个研究德国的中文专刊上。 《读书》上的文章谈的是波恩学派。作为波恩学派的传人,他在文中回顾和描述了波恩学派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分辨波恩学派以及欧陆汉学与美国汉学的重大歧异。他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视为波恩学派的理论骨架,认为与美国汉学把西方概念强加给中国,对中国作同质化的处理不同,波恩学派以及欧陆汉学特别重视“异”样的中国,因为在跨文化对话中,只有“异”才能体现其相对存在的价值。世界原本是一个差异互生互形的存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唯有以其独特性才有资格通行于世界。无“异”不成世界。西方研究中国,要的是“异”而不是“同”,“求同”无助于西方认识以至提升“自我”。
后一篇文章谈的是如何研究中国,理论立场与前文如出一辙。文章开篇就坦率地说,经常有中国人说他是外国人,不可能切身体验中国复杂幽微的内情,因而无法深入理解中国,强作解人无非是雾里看花。他对这种自以为是的论调非常反感,说越是外国人越能深入理解中国,甚至比自以为熟悉中国内情的中国人更能深入理解中国。他的理由是: “异”文化是一面镜子,“自我”只有在这面镜子里才能看到自己真实的面目,反过来说,身在其中,见木不见林,见“同”不见“异”,反而看不清自己。苏轼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雅俗两端都能支持顾彬的看法。在跨文化对话中,顾彬是见“异”无视“同”,但不是“为异而异”,而是为认识“自我”而见出“异”之价值。这里的关键是“认识你自己”。不找到差异面或参照物,怎么可能更好地“认识你自己”?波恩学派研究的要点,用顾彬的话说,就是承认作为差异存在的中国文化,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这正应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把顾彬与卜松山的中国研究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西方这个“自我”,为认识以至提升“自我”而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研究中国,辨识“异”而辨明“异”之价值所在,以弥补自身之不足。如顾彬所说,这种研究思路与美国的中国研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隐含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的,据我了解,是一种西/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架构。中国在这个思维架构中,总是成为西方概念的“跑马场”,传统中国的现代变迁是由西方概念推论出来的,中国的形象是由西方概念描绘出来的。这是“予”而不是“取”。也许根本就无“取”可言。美国以前的中国研究如此,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出道以来的中国研究也不例外。现在时兴反西方中心论,说以前西方研究中国扭曲了中国形象,这与以前说西方同化中国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也还是强行把西方概念套在了中国的头上,中国无论如何也无从挣脱西方概念的紧箍咒。我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曾读过一些美国学者和美籍华裔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述,对此深有体会。如“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和“民族国家”等等概念,都是源于西方并用于中国的,不用它们好像就不可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为何物。 “民族国家”本来是典型的欧洲问题,经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移用,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了。身在美国的刘禾教授想换一种思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可以称作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中国的学者、学生喜欢跟着风向转,一时间把这个概念弄得满天飞,论晚清文学,论女性文学……论什么好像都离不开“民族国家建构”这个热门概念,好像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殊不知作为文化概念的“民族”与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在“五四”文学中实际上是分裂的,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学因被认为有碍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而遭到“五四”作家的痛斥和遗弃。看看“五四”新文学,查验它的文化内容,不是“个性解放”就是“价值重估”,哪里有中国固有的文化可言?顾彬和卜松山的做法与此大异其趣,当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008年9月,卜松山应邀来武汉大学讲学,在哲学学院做了一个《佛教中的笑》的学术报告。与前文提到的在中文系做的那个学术报告相似,这又是一个很新鲜也很巧妙的论题。在报告会结束后,报告会主持人、哲学学院的吴根友教授对卜松山说: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题目?这种题目我们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后来问卜松山,他语气轻松地告诉我,将佛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较,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题目。佛教在它的原产地印度是一种悲苦的宗教,在中国却可以转化出快意人生的内容来。他的文字报告附有一些图片,我对其中一张摄于浙江的巨大的弥勒佛石像印象最深。在那尊袒胸露怀、心宽体胖、笑容可掬的弥勒佛石像的大肚、大腿和手臂上,跃动着的是一些扎着小肚兜神态各异的极其可爱的胖小子,画面中似乎还有一些鲜果。中国老百姓历来讲究“民以食为天”、 “多子多福”,雕刻家富有创意地把中国老百姓的愿望融入“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的中国化、世俗化的弥勒佛石像,创造了这么一件好作品。这尊弥勒佛石像,与它在印度的原型和在中国的初型相去甚远,彻底地褪去了悲苦的色彩,完全被中国现世实用的“乐感文化(李泽厚的概念)同化了。据许多中国佛学研究者说,大肚弥勒佛的形象,甚至连原型也许都不是出自印度,而是脱胎于传说中唐末的那个成天嘻嘻哈哈、疯疯癫癫、四方游走的布袋和尚。由此便明白了为什么卜松山会关注佛教中的笑。他的兴奋点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异”上。他关心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佛教,而是经中国文化重塑的佛教人物形象。我推测,可能是这种佛教人物形象所凝聚的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打动了他。
卜松山就要离开他心爱的岗位了,但是我相信,他绝不可能离开自接触那个禅宗小册子时开始的中国研究生涯。他在一封邮件中对我说,他退休后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中国。我想,到那时,以他那种“求异存同”的研究取径、自省平等的对话姿态和新奇别致的眼光,他一定会发现更多让我们中国人感到很新鲜也很巧妙的论题,做出更老到也更优异的成绩。
G04
A
1671-7511(2011)04-0090-04
2010-04-14
昌切,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林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