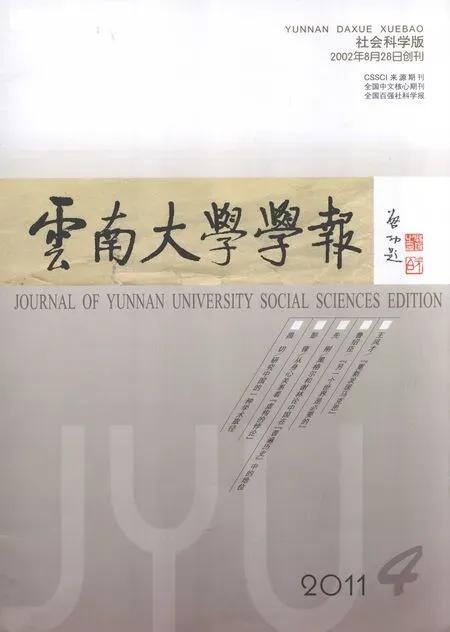关于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一个再思考
——在哈里·G.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框架内
段素革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 300191]
伦理学
关于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一个再思考
——在哈里·G.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框架内
段素革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 300191]
哈里·G.法兰克福;相容性;可供取舍的可能性;自主性
法兰克福在关于相容性问题的讨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就是通过法兰克福反例对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进行的批驳。但是,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所表达的那种必要性似乎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难以消除的直觉。尝试在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框架内找到一种对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解释,或许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直觉和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同时提供支持。
一
法兰克福在当代相容论讨论中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在于他通过法兰克福反例对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principles of alternate possibilities,下文将简称为PAP)进行了有效的批驳。所谓PAP,指的是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称,一个人只有在他本来能够采取其他行动的情况下,才能为他当时所采取的那个行动负责”。[1](P1)这个原则通常被作为不相容论的一个论证前提。
对PAP的反驳集中体现在《事关己者》(the Importance of What We Care About)一书中的多篇论文中,尤其是《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与道德责任》、《意志的自由与人的概念》、《强迫与道德责任》、《自由行为的三种概念》等。法兰克福最初对于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相容性问题的思考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我们在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上的直觉是否可靠;(2)如果实际上在我们关于道德责任的主体条件的考虑中,真正被我们作为必要条件的并不是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那么是什么条件;(3)这个新的作为道德责任赋予之必要条件的自主性(意志自由)说明能否容纳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道德实践的直觉,也就是说能否为那些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说明或辩护。
在对PAP的批评中,法兰克福反例实现了对这样两种情况的澄清:1.缺乏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在常识中被认为可以免除行为者的责任,但这源于一个误解,即没有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行为者被认为受到了强迫,或者说是非自愿的行为。但情况不一定是这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无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有无,而是说明行为者的意愿和行为的关系。2.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缺乏并不等于“行为者不能够采取另外的行动”。如果后者表明行为者具有某种内在能力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行为者进行了不同的选择,他就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并且的确是对行为者所具有的一种能力的表达。就此而言,行为者事实上不能采取另外的行动,并不排除行为者具有一种自我引导的能动性,因此,实际行为可能是在行为者的自我引导下实现的,所以是不能免除责任的。因为如果行为者事实上不能采取其他行动的原因是行为者自己的选择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与行为者的能动性和责任有关的事态。
依靠对这两种情况的澄清,法兰克福对上面提及的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回答:在限定的范围内实现了对PAP的反驳,并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对意志自由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澄清,提出了著名的层序动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意志自由的相容论理解。他指出,对自由意志的考虑,仅限于对行为者行动意志形成机制之特征的考察,因为意志的自由不是行动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是在人的行动意志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我一致的特征。这样的自由表明了人的自我引导的能力,是人的自由和能动性的体现。相对于对PAP的拒绝,法兰克福认为,在我们关于道德责任的主体条件的考虑中,这个意志自由的概念才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恰当的道德责任要求行动意志和行为是这样一种“自由”的行动意志和行为——即行为者自己认同的意志和行为。
这样,法兰克福就建立了一个内在主义的自主性和意志自由的概念。这个概念排除了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必要性,而仅仅以行为者意志形成的内在结构特征为标准。
二
尽管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对PAP的反驳,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似乎仍然无法彻底地消除我们在思考自由与道德责任问题时的一个直觉: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评价的实践中,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似乎总是被我们不由自主地拿来作为行为者的自主性的一个标准。即使在法兰克福本人的反例中,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对行为者来说,仍然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也许不能够十分清晰地把那个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描述出来。说我们的某个错觉太顽固了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关于道德评价的哲学思考不应该回避实践,当然也就不能够回避实践当中存在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关于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必要性的直觉是如此普遍和顽固,使我不禁想,是否能够在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框架之内找到一种对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理解,以便能够容纳我们的这个直觉?
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2]1978年7月5日,在劫持一辆用于抢劫银行目的的汽车时,罗伯特·奥尔顿·哈里斯和他18岁的弟弟丹尼尔遇到了两个高中生,哈里斯在逼迫两个高中生将车开到偏僻之处后用他的手枪杀害了他们。随后,哈里斯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对于罪恶的内疚感或不适,他若无其事地吃掉了他们未吃完的汉堡,还对他的这个“事迹”谈笑风生。同一天,他还完成了他的抢劫银行计划。在被抓住之后,人们曾经为哈里斯的残暴、毫无人性感到愤怒。随后的调查显示,哈里斯有个极其不幸的童年:据他的姐妹说,他曾经也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孩子,但是其父母亲都酗酒,并且父亲经常在大醉后残暴地打骂妻子和孩子们,哈里斯是受害最多的一个,甚至在娘胎里的时候他就已经遭受这种虐待了。有专家认为,哈里斯母亲的酗酒以及在怀孕期间遭受暴力可能导致他出生前即受到神经方面的损害,因而导致其在感受正常情感方面的缺陷,以此为由,他们向州长申请免除哈里斯的死刑。但是州长拒绝了这个申请。当1992年4月21日哈里斯被处死的时候,他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州25年来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罪犯。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在社会学、刑法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被广泛地引用和讨论。
可能有更多的人会认为哈里斯残暴无情,罪有应得;但是也有人会提出质疑:如果哈里斯真的是在生理上先天地受到了母亲酗酒及父亲的暴力的影响,对一些事情的正常感受能力受到了损伤呢?或者如果哈里斯确实除了自己生活的环境外,从未有机会接触和感知过爱和尊重,因此在他的头脑里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些概念呢?
这个思路可以典型性地反映出一些学者对法兰克福的非历史的、内在主义的自主性标准之充分性的质疑。因为在我们的眼里——包括在拒绝免除死刑的州长眼里——哈里斯是一个有自我反思能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采取某种态度的人;然而如果上面的两个假设能够成立的话,我们的观点是否会有所动摇?与此例类似,还有许多可以设想的情况似乎可以对法兰克福的那种纯粹内在主义的自主性概念造成冲击,如神经控制、催眠、洗脑等。因此,从机会与控制的角度对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原则进行一个再思考也许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假定行为者的自我引导是我们对于道德责任条件的真正考虑,那么,从机会和行为者对行为的控制的角度看,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有无实际上是否会影响到行为者实现自我引导的机会和控制?
我认为,说法兰克福的理论对PAP的反驳在以下任何一个方面取得了成功,可能比说它有效地证明了PAP对道德责任赋予的无关性更加谨慎和没有争议:1.法兰克福证明了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与每个具体的道德赋予情境直接相关的考虑,因此,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并不是每一个具体情境都需考虑的必然条件;2.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并不是决定道德责任赋予的唯一因素,因此,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缺乏并不是免除一个行为者责任的充分条件。这两个结论的成立,要求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缺乏并不剥夺一个人对行为的控制和在这个控制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引导能力。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也许不是道德责任的一个直接的必要条件,但是却有可能是自我引导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是自我引导的真实性的必要条件的话,仍然有理由说某种理解之下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是道德责任赋予的必要条件。
罗伯特·凯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3]他认为,一个自由的决定或其他自由的行为,是一个行为者能够为其承担“终极责任”的行为。终极责任或者要求行为不是被因果地决定的,或者要求如果它是被因果地决定的,那么它的任何决定性的原因要么是行为者的某个不被因果决定的行为,要么是那样一个行为的结果。因此,他同意,终极责任并不排除一个由行为者的某种性格特征所因果地决定的行为的责任。但是为了行为者能够为那个行为承担终极责任,要求在这个行为者的这个性格特征形成的历史当中,必须至少曾经存在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不是某些具体情境下的道德责任赋予的必要条件,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却是一个行为者获得道德主体资格的必要条件。然而决定论排除了这一切可能。
因此,当我们直觉地认为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是将一个道德行为归于某个行为者的必要条件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有可能是,这个可能性是表明那个选择的确是行为者的一个选择的必要的对照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说明一个行为在自我引导的意义上是属于行为者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就不必是不相容论所要求的那种所谓的“真实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首先,我认为,就人类实践的目的来说,不相容论者框架内所要求的那个所谓“真实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如果将那个概念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可以说世界是一个凝固的铁板一块,任何的变化、过程、区分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都会像我们对意志自由的感觉一样只是一个假象,因此,若假定这个决定论概念的话,不仅意志自由是不可能的,我们常识中的一切世界观和自我观念都是不可能的或者无意义的;即使决定论的世界观最终表明是真的,也依然无法在实际上影响到我们行为的日常方式,也即以恰当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为前提信仰的行为方式。在此意义上,决定论与我们试图在意志自由的问题当中所表达的自我关注是无关的。其次,以表象形式向行为者开放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却是必要的,并且足以表明一个行为的真正自我引导的性质,足以帮助我们确定选择是否是出于行为者的自愿。一旦确定在某个具体的情境下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即使在行为者的意识中——以概念或想象的方式——也不存在,就没有任何一个这种情况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赋予责任。
法兰克福的意志自由观点不仅能够、而且的确涵盖了我所说的这种表象意义上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它就体现在法兰克福所描述的行为者在不同的欲望之间以认同的方式进行选择的情境中,体现在他所描述的在相互冲突的欲望间进行认同的选择的情境中。它仅仅被限定在行为者的意识活动内部,但是这种以表象的形式向进行实践推理的行为者的意识所显现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行为者处于一个选择情境的时候,所有进入他的思考权衡范围的可能性——包括他对于自身能力、个性的反思、判断,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对于客观环境的判断而认为被允许的所有选择——并不因此就是一种不真实的可能性。它对于说明人的实践推理的活动机制,以及因此确定行为者如何可以被说成是一个选择的发动者,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并且,行为者不是在行为阶段而是在意志活动阶段实现在这些可能性之间的取舍,这一点更能够说明意志自由的内涵。也就是说,意志自由或者说自主性的真正标准是行为者的控制,这种控制就是法兰克福所说的那种认同意义上的控制。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动机、行动的控制,通常需要一个参照才能体现出来,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就发挥着这一作用。但是,这个参照无需是不相容论者的那种所谓的“真实”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在对未来进行展望时在行为者的意识中所呈现出来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
在暂时搁置决定论与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相容性问题的情况下,让我们先来考虑如下的这个对照。假设选择的情境就像面对许多岔路,就现实来说,总是存在许多条道路,然而,限于一个行为者的视野、认知能力、或其他的意志能力,他只可能选择其中的一条,而其他的道路或者是他看不到的或者对他来说选择它们是不可想象的,那么这些道路的存在对于他的意志自由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选择其中之一是就他的个性而言是必然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那条道路的选择一定是被动的、无责任的?作为对照,我们也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情境:事实上开放给行为者的道路只有一条,他此刻就站在那个路口。他认为如果他不选择走这条路,还会有其他的道路向他开放;但是实际上不存在其他的道路。他进行了权衡,认为这条道路是他应该选择的,因此他向这条路走去。我们会认为他之所以走这条道路是不得已吗,还是会认为走这条道路的确是他的自由的、自主的选择?我想会是后者。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不相容论者所谓的那种“真实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是无关的,但是表象中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却说明了行为者的选择是否是自主的。
在我们的道德处境中,此类例子并不少见。展现一个人的品质,并不需要选择情境的“真实”存在。在一些道德品格或心理测试、犯罪测试中,虚拟的甚至欺骗的选择情境的设置,都足以实现确认一个行为者的内在品格,这当然是以那些选择展现了行为者的自主性为前提。法兰克福的反例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行为者多少是有选择的并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像法兰克福本人所特别指出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把那种可能性彻底去除,那个例子需要的,本质上是操纵和未来都是行为者所不知道的,他面对的是在他的意识中以表象的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及后果,他在概念中对这些可能性进行比较和权衡,然后做出抉择。这种描述可以说是最符合我们的实践推理概念的,也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表明行为者选择的实质。
在提出这样一种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可以指出,对于这个必要性的理解,能够为法兰克福的自主性标准提供一个补充。将法兰克福所主张的自主性理解为仅仅是要求一阶意志与二阶决心的形式的符合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法兰克福不仅要求一阶意志符合二阶决心,而且要求这个符合是在有一种恰当的内部活动机制的保障下实现的。这个机制始终是激活的,因此行为者能够针对确定的目的对其中出现的偏差进行调整。这种概念形式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存在,是这样一个动态的能动性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表明了作为能动者的行为者与作为目的的行为之间的真实、可靠的联系。
这种理解之下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容纳经典相容论试图以条件句分析的形式表明的自主性的内涵,以及表明那种分析的真正意义所在。“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与“如果他当时选择了,他就能够已经采取不同的行动,尽管他事实上不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毕竟还是不同的。后一句陈述在我看来还表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一个人的行动与他的主观动机间的必然性联系,这就是“如果他当初做了不同的选择,他当时就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的含义,这一含义在前一陈述中毫无体现,而这一含义并不像不相容论者所说的那样,“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而毫无意义。它在行动和行为者之间建立的那个联系是我们的自我概念所不能够消除的,只要我们对象性地“看”自己,我们就不可能消除那个行动最后的关节是由我的选择所保障的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对于上面提到的两个陈述,在自由(指的是不相容论者所要求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意义上进行理解,那么,的确也就像不相容论者所说的,后一个陈述对于阐明自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控制”、“自我引导”的意义上看那两个陈述,他能不能实际上做出另外的选择,与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就是无关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概念形式的存在,一方面并不要求行为者的选择确实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可以表明行为者与那个选择的内在联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下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才是支持PAP之必要性直觉的理解,并且是真正与我们关于意志自由的思考以及道德评价、责任赋予等实践相关的考虑。我的意思是,即使决定论是真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只有一条——事实上不论世界是否是决定论性质的,其结果都是如此,但是在我们迈出人生的每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肯定未来总是展现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看”不到、不确定,因为未来对我们是有限开放、也有限遮蔽的。这样,虽然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必然最终只有一个,但在选择时它却总是展现为许多道路;当我们回顾往昔时我们只看到一条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当我们向前看时却总是有许多条道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描述,即使不以“道路”为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正是我们自己的有限性,使得世界和我们自身之间的关系在认识当中呈现出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矛盾状态。我们对于自我、对于自由意志、对于责任的思考究竟应该立足于何处呢?我们永远是站在那一条按照决定论的说法已成为凝固的一条的道路与未来的许多条道路的相接口,我们是应该面向那一条已经凝固的道路来看待、思考自己,并以此指导自己未来的脚步,还是应该转过身来?前者只会让我们寸步难行。而如果我们决定继续前行,我们所面对的必然是后者,我们只能那样看我们自己、看呈现给我们的世界。简而言之,不相容论的论证或许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与我们对于自身的思考无关的;或者说,它根本算不上是一种思考或考量,而是一种以一个概念否定一切现实差别和实践可能的独断。
三
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解决。一是,应该把传统上所理解的那种所谓的“真实”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理解为什么样的条件?它应该在什么样的意义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道德责任?或者说它在何种情况下才影响我们对道德责任的判定?二是,如何避免我们上面所描绘的那种含义可能导致的主观主义指责?
通过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如果将意志自由定义为法兰克福的那种方式的内在自由,那么它就无需不相容论者所要求的那种可供取舍的可能性。而且,通过法兰克福借助于意志自由与行动自由的对比所做的说明,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意志自由的定义是更加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相容论的论证所要求的那种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应该是在作为一种外在条件的意义上与自由和道德责任的考虑相关的。或者也可以说,不相容论者所说的那种作为自由之必要条件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应该是作为自由“行动”之必要条件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如Peter van Inwagen所举的打电话报警的例子,[1](P96)显然涉及的就是行动自由的例子而不是意志自由的例子。法兰克福说得很对,当我们以本文所描述的那种理解方式来考虑意志的自由的时候,在打电话报警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就可以很恰当地认为行为者仅仅因为他所作的选择就是有道德责任的。假如他选择了报警(出于自由的意志),但由于电话系统崩溃而未能实现自己的选择(行动未获得自由的实现),那么他毫无争议地无可指责(从道德上说);如果他选择了不报警,而且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电话系统崩溃),即使他选择了报警也不可能会通知到警察,这个结果并不能撤销我们对他的道德品格的谴责和责任的判断;如果他决定不报警,可是在周围的人(或者同行的朋友)的相反意见的压力下最终还是拨打了并且打通了这个电话,那么我们仍然会对他最初的抉择持一种保留的否定态度(此态度上的肯定或否定是道德评价的必然内涵之一)。
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人的道德责任可以意志自由为前提,而意志自由是法兰克福的那种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人的确具有这样的自由,而且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先验地具有(因为它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先天结构而不是经验的内容);行动自由也是经验性地考虑道德责任时必须纳入的因素,它会影响我们对于道德责任程度的考量,而这种考量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否遭受强迫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遭受强迫的问题,它仍然与不相容论者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无关,相反正是经典相容论所理解的那种自由。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样一种理解之下的PAP无可避免地依然是一种内在主义的理解,它如何避免主观主义的指责?也就是说,如何避免使自主性的有无变成一件完全依行为者个人的感受(感受自己是有所选择还是走投无路)而确定的事?我已经表明,法兰克福路向的意志自由定义,仅仅以人的先天的意志结构为条件,因此与决定论的问题是无关的;同时,某些决定论者的观点实际上等同于以决定论否定人类实践的一切差别和意义,甚至否定人的存在的独特性。综合这两点,我认为法兰克福的意志自由概念(建立在本文所考虑的这种内在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存在之基础上)是更加可取的。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前提下,我们在道德责任以及自由的考虑中,并非完全不考虑外界为行为者提供的可能性的意义。如上所述,外界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可以在承认意志自由的存在和道德责任赋予的依据的基础上,恰当地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同时,一个行为者是否具有我所主张的那种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由行为者所决定的,它需要面对一些具有普遍性、可沟通性、可操作性的标准,尽管我们还不能很完美地运用这个标准。这样,我就建立了一种次序,道德责任的赋予和考量是这样一个被分为两个步骤的过程,其中只有在满足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第二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就是:1.具有自由意志,即能够正常地进行法兰克福自主性概念所描述的那种认同的活动,因此是道德责任赋予的一个恰当对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或全有或全无的条件,先验地确定道德资格。2.从认知和行动的可能性的层面,外界(包括自然,更主要地是社会环境)为行为者提供了一定的抉择范围。这是一个人在经验世界中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或全有或全无的,而是允许程度上的差别的,它影响着我们对道德责任大小的判断。
由于意志自由在这里被规定为道德责任赋予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同时,一个行为者是否在意识中面对可供取舍的可能性,这些并不由行为者所决定,法兰克福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以及本文在他的概念框架内对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所做的阐释,都不会导致关于自由和道德责任判断的纯粹主观主义的错误。
综合以上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在法兰克福所阐明的意志自由概念的基础上,以及以此为核心建立的相容论的框架下,找到一种可理解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含义,来阐释和辩护我们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之必要性的直觉;并且,这个相容论框架内的理解,是一个比不相容论的理解更加与我们的实践、道德心理相关的理解。当然,这样的理解,就像法兰克福所提出的自主性(意志自由)概念一样,必然导致对于道德责任甚至道德本身的观念的一系列相应转变。
[1]Harry G. Frankfurt. the Importance of What We Care abou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Robert Alton Harris[D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Alton_Harris:2011-02-25.
[3]Robert H.Kane.Some Neglected Pathways in the Free Will Labyrinth[A].The Oxford Handbook of Free Will[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82-02
A
1671-7511(2011)04-0058-06
2010-10-20
段素革,女,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道德与文明》编辑部编辑。
■责任编辑/袁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