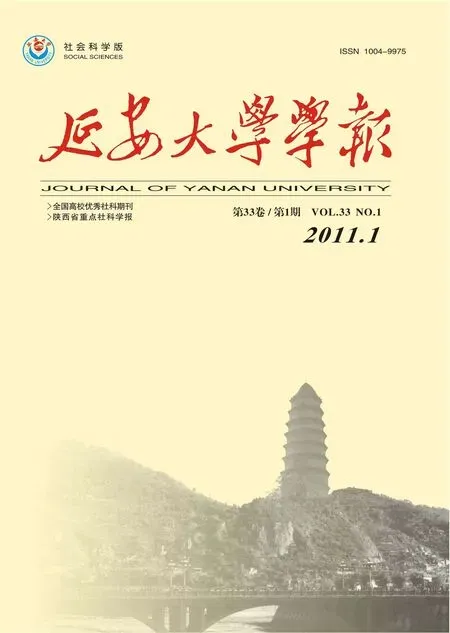民族认同与文学建构
——以阿来小说《格萨尔王》为个案
樊义红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问世后,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将从“民族认同建构”的角度对之作新的考察,这不仅是为了从认同理论的角度来探究作为个案的文学作品,也是希望在个案的研究中获得理论的突破和新的发现。
一、作为建构认同手段的文学
作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认同 (Identity)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许多学科的论域中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何谓认同?这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术语。“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 (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1]465追究其思想根源,一方面,它是现代启蒙哲学的产物。启蒙哲学“赋予现代人以理性甘露与批判利剑,向现代主体提供了强大反思能力,所以说,启蒙即反思,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反思,对自我的反思,对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思。”[1]466另一方面,它也是新近兴起的文化研究的产物。
传统的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是对某种本质性和中心之物的“归附”,是一个稳定的、单一的和确定性的过程和状态。当代的认同理论对之进行了相当程度的颠覆。比如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在认同理论的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霍尔就说:“在通常的做法中,认同过程 (或译成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的实践是在对某些共同本源的体认后建构起来的,或是与他人或群体所共有的某些特征,或是共有某种理想,共有某种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自然封闭的团结和忠诚。然而,与这种界定的‘自然主义’相反,话语研究方法则把认同过程视为一种建构,一个从未完成——总在‘进行中’——的过程。它始终是‘赢得’或‘失去’、拥有或抛弃,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确定的。尽管有其存在的确定条件,包括维系它所需要的一些物质的或象征的资源,但是,认同过程是无条件的,处于偶然之中。一旦它得到了,它就不会抹去差异了。它所暗示的整合事实上只是一种统合的幻想。”[2]185在这段话中。霍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也是现在广为接受的观点:认同的建构性。那么,通过什么来建构呢?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文学就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无数的文学作品已经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事实根据。笔者将要探讨的是,文学是如何建构认同特别是民族认同 (认同之一种)的?这种建构能给我们的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什么新的启示?鉴于民族作家文学中的“民族认同”现象特点突出,故下文将主要以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为个案来展开这方面的思考。
二、《格萨尔王》对民族认同的一致性建构
早在 2005年,由英国的坎农格特出版社牵头启动了一个全球性的“重述神话”项目,它是一个世界各国出版社联合参加的全球性出版项目。所谓“重述神话”,按照坎农格特出版社出版人杰米·拜恩的解释,即以神话故事为原型,融合作家的个性风格,重构各国的传统神话,从而重述影响世界文明中积淀了数千年的神话经典。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就名列国内首批出版的“重述神话”系列之中。
格萨尔王是西藏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其传奇故事主要来源于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格萨尔王传》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享誉世界,至今在西藏各地广为传唱。小说《格萨尔王》对此也有生动描述:“不止是上演——草原上,农庄中,千百年来,都有说唱艺人不断讲述这个故事。”[3]13《格萨尔王传》内容及其丰富,它融汇了不同时代藏民族关于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艺术的大量知识,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在此意义上,笔者以为,可以把《格萨尔王传》看做西藏民族的一部“传记”。那么,阿来为何要对这个流传千古的格萨尔王故事进行“重述”呢?这里面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动因。作为一个存在了一千多年、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民族,长期以来藏族文化保持着很大稳定性,却在近些年来受到汉族文化和其它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强大冲击,民族文化心理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和发展中的选择困惑。笔者以为,正是对于民族文化转型和重建现状的敏锐感应,使得阿来选择了回到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通过重写《格萨尔王传》来表达自己的文化思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正如个人在对早年记忆的“疏隔之中产生了一种关于人格的概念,也就是因为不能被‘记忆’而必须被叙述的认同这个概念。”[4]193“适用于现代人物的‘叙述方式’,同样也适用于民族。直觉到自己深深植根在一个世俗的、连续的时间之中,并且直觉到这虽然暗示了连续性,却也暗示了‘遗忘’这个连续性的经验 (这是 18世纪晚期的历史断裂的产物)——这样的知觉,引发了对‘认同’的叙述的需要。”[4]194而“民族的传记”就是满足这种“民族认同”的需要而产生的。根据安德森的观点,阿来对《格萨尔王传》这样一部类似于“民族的传记”的“重述”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民族认同”的冲动而被叙述出来的。从内容上看,小说《格萨尔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神子降生”、第二部“赛马称王”和第三部“雄狮归天”,其中以第二部内容最为详细。而在叙述格萨尔王的辉煌战绩时,又把重点放在了其四大降魔史上,即“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和“门岭大战”。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相当充分地表现了格萨尔王超人的力量、智慧和胸怀。此外,小说反复喻示了:魔鬼分为心外之魔和心内之魔。心外之魔可以借助神力消灭,而更为可怕地是心内之魔,比如“搜罗财宝,渴求权力,野有贫寒而锦衣玉食,都是心魔所致”[3]89,要消除这心内之魔就只有求助于佛法了。以上这些,都与史诗《格萨尔王》的艺术安排基本一致,从而保证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建立在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基础之上,这也构成了小说能够激发民族认同的有效保障。
人物形象是文学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之一。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在现实主义文论看来,能够塑造出成功的典型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作品的成败。而我们发现,有些典型人物因为其身上负载着丰富而强烈的民族特征,事实上已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比如格萨尔王的形象。作为《格萨尔王传》的主角,格萨尔王是天上的神子下凡,为人间降妖除魔,一生戎马,扬善惩恶,是西藏人民家喻户晓、引以为自豪的旷世英雄。小说《格萨尔王》对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有着充分的艺术表现。可以想见,阿来在小说中通过重新温故格萨尔王的故事必然会激发起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故事情节也是文学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之一。作为小说的三要素之一,故事情节在小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许多优秀的作家都认为,能否讲出一个好故事是小说成功的关键。比如当年果戈理就因为找不到一个好故事而向普希金抱怨和求助,认为自己不缺才华就缺好故事,后来果然以普希金提供的好素材写成了名作《钦差大臣》。进一步看,有些故事因为广为人知,如果重新讲述也许缺乏新意,但也正是因为故事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重述故事可能就产生了另一种功能——认同。这一规律特别适用于作家对民间故事的讲述,比如阿来重述格萨尔王的故事。《格萨尔王传》作为一部活形态的史诗,从其诞生之日起至今一直在青藏高原广泛流传。特别是其中的 30部左右,被称之为“奇人”的优秀民间说唱艺人,以不同的风格从遥远的古代吟唱至今。阿来以一个民族作家的笔墨,对一些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讲述,那种因为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会油然而生。
民族认同作为作家的一种思想观念,不仅借助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加以建构,必然还会影响作品的文本形态。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6对“民族”这个“共同体”的想象“最初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字 (阅读)来想象的。”[4]9比如我们通过齐唱国歌来想象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存在。笔者以为,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暗指了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必然带来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因为在对这种共同体的想象中,想象的主体事实上是把自己归属于一个更大的集体概念并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这个集体的归属感。而且,民族的想象的作用——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甚至诱发人们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也证明了对民族想象带来的认同确实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综合以上思想可以得出:通过语言想象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可以带来民族的“认同”。小说《格萨尔王》中经常通过说唱人晋美和其它人物之口来带出史诗《格萨尔王传》里的语言,比如“雪上之上的雄狮王,绿鬃盛时要显示!森林中的出山虎,漂亮的斑纹要显示!大海深处的金眼鱼,六鳍丰满要显示!潜于人间的神降子,机缘已到要显示!”[3]126等。而有时候,则是叙事者语言对说唱人的语言进行了巧妙的化合,比如“天哪,还没有说完,那就继续往下说,嗡!智慧的长者有格言,要把参天大树认,光顾树干怎周全?必得脱了靴子往上攀,捋遍所有分支与枝蔓!嗡……列位看官耐烦点!”[3]39小说对史诗中语言直接或间接地保留,实际上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媒介,借以重现一种典型的、共时性的说唱场景的“仪式”,这种作为民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情感指向就是民族认同。因为在认同理论看来,“仪式”在建构民族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的功能。正如康纳顿所言:“所有的仪式都是重复性的,而重复性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6]也就是说,借助于语言所想象的说唱场景的“仪式”,实际上起到了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使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民族传统的作用。
由此可见,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文化给与藏族作家独特而宝贵的馈赠,阿来真心地接受了这一馈赠并通过自己的重述实践表达了自己对藏民族的认同。可以说,以上分析不仅让我们认识了阿来作为一名藏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事实上也为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民族文学作家和作品提供了一个重要标尺,那就是是否具有民族认同。
三、《格萨尔王》对民族认同的差异性建构
以上所言,还只是涉及了小说《格萨尔王》建构民族认同的一个方面。毕竟,小说《格萨尔王》不同于史诗《格萨尔王传》,透过小说的表层,我们会发现其建构“民族认同”的另一个方面。
首先,从内容上看,目前搜集整理的《格萨尔王传》共有 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而小说《格萨尔王》只有 33万字。显而易见,小说对史诗进行了重大的取舍,这种取舍不是一种对后者的简单压缩和简写,而是经过作家的艺术构思,构造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作家文本。
在这个新的文本里,作者实际上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讲述的是格萨尔王的故事,一条讲述的是神授的说唱人晋美四处流浪说唱《格萨尔王传》的故事,其中格萨尔王的故事又是由晋美在梦中看到、听别人说唱和自己唱出来的。这两条线索平行地往前发展,又不时地交叉 (通过晋美与史诗中人物如格萨尔王的对话等),由此展开了神话与现实、历史与今天的鲜明对比。比如小说写了神话中的赛马大会格萨尔王骑着神马比赛获胜称王,又接着写现实中的赛马大会“墨镜人”诱骗晋美治好骏马,妄图以高价出售给商人。前者的崇高对比出现实的卑琐。又比如小说写了格萨尔王的爱情又接着写晋美的恋爱,前者的春风得意对比出现实的情场失意。
在作品的主题表达上,小说抓住了格萨尔王“半人半神”的身份特点,在表现其神通广大的“神性”一面时,又着力表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上的诸多困惑。而这些困惑正是作家阿来要借重述这一神话来加以追问的。比如关于战争。小说借一位喇嘛之口说道:“正是战争给了他那么多荣光!人们传诵他的故事,不就是因为那些轰轰烈烈的战争吗?他是战神一般的无敌君主!”[3]281但是小说中的格萨尔王却越来越厌倦无休无止的战争,因为在他看来,战争除了给他个人带来荣耀给贵族带来利益,带给百姓的更多的是贫穷和家破人亡。一个真正伟大的君主应该以天下苍生为顾念而不是迷恋于杀戮和声威。比如关于佛教。史诗《格萨尔王传》具有浓厚的宗教 (藏传佛教)色彩,这与藏族僧侣曾介入《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和传播有关,比如格萨尔王在藏族的传说里就是佛教连花生大师的化身,史诗《格萨尔王传》也宣扬了不少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观点。而小说《格萨尔王》对佛和佛教表现出一种辩证的态度,比如小说既写到上天诸佛的加持使格萨尔王获得通天的神力,又写了一些僧侣们入世的野心,小说甚至通过晋美和学者之口来质疑格萨尔王故事的真实性。这些艺术处理,使得小说有意地疏离了“神性”和“佛性”,而更多地关注了文学表现的根本对象——人和人性。
霍尔在谈到认同的建构性特点时说道:“认同是通过差异而非外在于差异所建构的。这引发了完全令人不安的认识,即只有通过与他者的关系,与其所不是之物的关系,与其所缺乏之物的关系,与其构成之外在方面的关系,任何术语的‘肯定’意义即它的‘认同’才能被加以建构。”[2]67可以看出,无论从作品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看,阿来作为一个民族文学作家对本民族的认同都不是一种单纯的“顺应”,毋宁说是一种“同化”,是在认同中的批判。这实际上反映出阿来作为一个民族文学作家的民族认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阿来对民族认同的这种态度在民族文学作家中很有代表性,姑且称之为“感情加理智型”:一方面他们对待本民族怀有真挚的热爱,另一方面又能以自己的理性和现代精神看到民族的痼疾并试图给民族开“药”治“病”,以求得民族的更大进步。关纪新和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对这一类民族文学作家有精彩的论述:“以扬弃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少数民族作家,大多是些富有个性和主见的人。他们知道本民族以外的世界文明已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也知道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份已经并且还要带给自己民族的是什么样的危机。他们对此怀有深深的无可派遣的忧患意识,并把忧患意识化为个人的历史负载,要为自己心爱的民族重新做出长远的命运抉择。他们不再以讴歌民族文化的美好因素为自己的心理满足,而是满含痛切地去揭露传统的缺陷,指出民族魂灵深处包藏的弱点,激发全民族疗治痼习的觉悟。”而从文体上看,这也是因为小说毕竟不是一种安德森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的传记”。[7]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理论发现——小说和传记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所能引发的民族认同倾向的不一致性:传记所引发的往往是一种简单的无原则的民族认同,而小说所引发的民族认同则要复杂得多,往往是在认同的同时还有反思和批判。
总而言之,作家阿来以小说为文体媒介,通过“重述神话”的策略,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这种建构是了不起的,但也不会是唯一不变的,因为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必将永远处于多元变化之中。
[1]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 [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阿来.格萨尔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61.
[6]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0.
[7]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