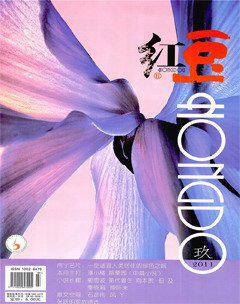旱子的荒腔和烂漫旅途
郁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疆八零后的这一批詩^横空出世,搞得我目乱神迷,好长时间都无法把他们的詩歌和他们炫目的名字对上号,且大多是一些“惊世骇俗”网络笔名,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旱子的名字应该是“悍子”,至今我的手机里存的还是这个“悍子”。直到前不久,和旱子一同参加了一个时间不短的采风笔会,才把这“悍子”的名字平反昭雪为了“旱子”。
今天,当我应约为旱子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才认真地想了想,竟一时想不起和旱子是怎么相识的了。记忆里一直是闹轰轰的一片,忘记了是哪一年的“新春詩会”,还是另外的一场詩歌或者文学的聚会上,我端着酒杯子,晃晃悠悠地走到这帮子詩歌的狂徒跟前,倚老卖老地说,小兄弟们,老哥敬你们一杯酒!谁曾想到没过去几年,这帮小子便一个个口无遮拦地叫起我“郁老”了。真是世事变迁,风卷残云,往事不堪回首。
旱子这一代人的詩歌,我似懂非懂,也不能不懂装懂,所以就不敢在这里妄加评说了。好在旱子还是一个有趣味的人。这些年,他还没有被那一顶“詩人”的头衔给砸晕了,表面上看去,还不像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青年詩人”。生活中,旱子的角色是一家都市报的文化娱乐名记,事实上,我也更喜欢那个名叫巩亮亮的光头记者。小伙子略带甘肃口音的普通话里,偶尔还会有一些愤世嫉俗的“微博”言论,常常遭到我等革命前辈的不屑和击打。
嬉笑怒骂之间,最能看清楚一个人的真实性情。这几年和旱子有过一些零星的接触,由于我的“不正经”作风,也慢慢地影响了旱子、去影等一帮子本来很正经的年轻人。上个月,在北疆的一次采风活动中,这两个家伙为了“讨好”郁老,即兴把坐在我前排的两位如花似玉的年轻女记者,送给我做了宫女。我一时高兴,本想封他俩个一官半职什么的,却由于准备不足,临时起意,竟脱口封了他们两个人为“御用太监”。当车上众人一阵哄笑之后,才觉出不妥,本想改口,想这等时刻,哪能朝令夕改,再一想,虽是太监,但贵为御用,也是待遇不低了。
旱子和去影虽对“御用太监”的任用多有不满,但也没有太过计较。我端坐在面包车的最后一排,正是浮想联翩,享受着“宫女”在前,“太监”断后的美好时刻,很大的可能是,我靠在后面,在颠簸中晕晕乎乎地睡着了。被这两个坏小子钻了空子,只听得两个“太监”齐声高呼:“郁老归天了!”
想想新疆这样的漫漫长途,若没有这等生活的荒诞轻喜剧,该会是多么的寂寞。而要演好这样的剧目,旱子这样的“演员”是不可或缺的。我喜欢和旱子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不分老少地纵论古今,当然也会谈到詩歌,但我们是那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谈论,也就是不再拘泥于詩歌和文学本身的那一种热烈探讨,没有一本正经的学究气,也就不会有惹人生厌的酸腐气。所以一般来说,我和旱子等人在一起的时候,多半还是热闹的。
也有一次,供职于某晚报的一个朋友在酒桌上向我告状,说有人在网上出卖我的“色相”。我一听这还了得,谁知出卖我“色相”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旱子。那是我仰面躺在赛里木湖畔的草地上,被旱子用相机给偷拍了。他回来后在微博上与人交恶,就拿了我的这张躺在草地上的毛毛草草的老脸来顶替自己。我听后忍俊不禁,声称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权,谁知没过几分钟,就被旱子用酒给灌晕了。
表面上看来,旱子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酒后言行更是夸张,虽然插科打诨的能力有待提高,但后生可畏,前途不可限量。还是在赛里木湖边上的毡房里,主人有一场盛大的招待酒会,主人由于连日来招呼客人,已几近失声,诺大的毡房里,好几十号人,众声喧哗,主人的号令全被淹没了。这时旱子在众多年轻后生中脱颖而出,负责代替主^、行酒场号令,也就是主人敬酒时,先是趴在旱子的耳朵上,用沙哑的声音小声地告诉了旱子,然后再由旱子对着众人大声朗读出来,其声势浩荡,其威风八面,甚是了得。
我写了这么多旱子的表面风光,如果旱子仅仅只是这些表面上的浮华,那也就只能是浮华了。其实不用深入到旱子的詩歌和文字之中,他偶尔闪现在瞬间的忧郁和落寞,你就应该知道了这个总是要大声说话的年轻人,骨子里还是那样深刻的孤独着。我们也总是需要一些生活的道具,来遮掩了我们内心的那些剧烈的动荡和不安。
旱子的詩歌里,总是充满了怀疑和游弋,这是生活不能被确定的真实境况,还是他内心的纷繁无法抵达。他试图向生活开掘出更深的矿藏,但这世界坚硬的表面,总是让他屡屡受挫。从旱子詩歌的系列化写作和宏大的愿景里,你可以感到这个年轻^对这世界的不安和不满,但是,时机还是运气,总是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来。
在今天,我们或许再也不能用“坚持”这两个字,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期许和梦想了。但是在这里,我还愿意对旱子说,没有坚持的梦想,还叫梦想吗?我想说的是,旱子的詩歌还需要时间的打磨,正如他不断到来的人生,还需要拨开重重的迷雾,找到一条上升的阶梯。
没有一场比赛是完美的抵达,同样,我们都还需要在命运的这场僵局里,学会在艰难的妥协中有所坚守。
而对于詩人而言,这不仅仅只是一场道义上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