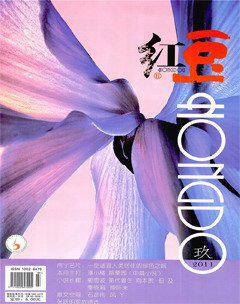我就是那个行走在河岸上的孩子
潘小楼
我是在父亲的工厂里长大的,那是一个上千人的水泥厂,毗邻右江,对岸是村子,溯江而上,是小镇。小时候,我常一个人到河滩上拾荒,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你永远猜不到水流会给你带来什么:瓷片,浮木,甚至是一只彩色的玻璃球……
一个孩子孤独地走在河岸上,这个情境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它更像是一个隐喻。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一条长河,有太多东西是茫茫不可知的,但有时候,一些碎片还是会被冲刷上岸,那是一个个你无法释怀的片段、场景,甚至是一闪之念,它们具体、形象、触手可及。为什么偏偏是它们?你无法解释。
然而,对我来说,这就是小说的发端。
我第一个中篇《端午》(发表于《芳草》2010年第三期)源于一个画面:一个男孩站在阁楼的窗边,楼下,一个女人躺在一张竹椅上,半眯着眼,她的腹部微微隆起;将这两个人联系起来的是男孩手里的一面小圆镜,镜子的反光在女人身上逡巡,她却浑然不觉。这个谜一样的画面我说不清是何时何地看到的,抑或只是我脑子里的臆想,它折磨了我很多年。2009年年底,我把它植入了靖西边陲的端午药市,一个潮热、带有生命感气息的小说便开始抽发枝芽。
2008年年底,父亲过世,我与母亲回厂里办相关手续,这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光一时的厂子,因为连年亏损,即将停产。我站在厂里的宣传栏前,眼前尽是一张张讣告。老一代的人一个个去了,却没有新人补充进来,沦落为空城,已经是这个厂子不可避免的命运。一个时代转身了,但我发现自己还停留在它的喧闹里。这个场景纠缠了我一年多,后来才有了第二中篇《秘密渡口》(发表于《广西文学》2011年第6期)里一个关于自渡的故事,地点,就是在世界尽头的一座空厂。
中篇《小满》取自和我同学了十五年的森的生活片段。小时候,他有着我们既妒又羡的搬家经历,这一切,要归结于他的母亲。她像个吉卜赛女人一样,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凭借着一门独家的烧卤手艺,沿着右江河谷,从这个工厂辗转到那个工厂,而她所做的种种努力,只是为了让一家人能够吃上饱饭。
《罂粟园》是我的第四部中篇,它直接来源于我中学时代,我高中曾有一段类似于插班生的经历,那是我最为阴暗的记忆。后来我又接触到不少类似的人和事,我忽然意识到,会不会我们都曾经这般聪明过:为了使满足欲望的过程体面而堂皇,会站在制高点上,对道义进行逆用。这一做法是如此成本低廉,而又回报丰厚,以至于它像瘟疫一样,在伤害者和被伤害者中迅速传播,并在种种社会生态中蔓延……感谢这部小说,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并有可能摆脱其中的毒素。
在这四部中篇之前,我从未写过小说,因为我曾偏执地认为,自己有严重的叙事障碍。自虐式地看了上千部电影,其中,吉赛贝·托纳多雷和沃特·塞勒斯的代表作看了不下十遍,然后,我才开始动笔。很意外,我开始可以以一种自由的叙事姿态来面对我一直以来生长的南国:白亮的日光,色块浓烈的大地,空气中似乎随时都在冲击饱和极限的水分子……对此时的我来说,它竟是如此叵测、风情,而迷人,就像西西里岛于托纳多雷,拉美大地于塞勒斯。但更让我着迷的,还是这块土地上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主宰,立体而多维地去呈现出这样一种力,是我终极的文字理想。
从真正动笔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有过焦虑、惶恐,和困惑,但庆幸的是,有太多给予我温暖和鼓励的人,让我坚持了下来。谢谢你们,让我找到了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最适宜的方式一以一个孩童的姿态,在河岸上行走、拾荒,对未知心存敬畏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