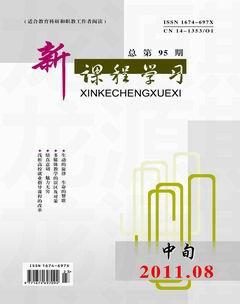简论校文学社的“疏导”功能
刘悦
摘要:从古诗论“诗言志”说起,引出“文学即人学”的观点,继而阐发对文学“宣泄”和“疏导”功能的认识。在对当今我校高中生青春期心理状态的分析中,将文学社的功能及意义重点落在“疏导”上。以反映社会黑暗面的文章为疏,以励志青春的文章为导,导占绝对优势,如此,达成文学社在学校教育中教化导引、缔造幸福的氛围里所能起到的一点作用。
关键词:诗言志;文学即人学;疏导;幸福
古有“诗言志”之说,虽然后世将功利性的“诗言志”和艺术性的“诗缘情”相对立,但检索“诗言志”的古义以及文学史中对其理解的主流意志,情志并重应该是比较确切的。即是说,文学(“诗”为代称),既应该注重社会性功能,又需要体现人的主观情感与
思想。
情志并重,虽然文学有其功利性,但无论怎样做“传声筒”,毕竟作品中浸润了作者的视角、言说方式、言说目的,所以,纯然客观的“自然主义”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才有了一种说法,“文学即人学”。
我赞同“文学即人学”,因有了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种种经历、思想情感的嬗变,有了言说的冲动和目标,才有了文学。在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那里,文学本就是宣泄人的性本能的主要方式。中国古代有“物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说法,这其中都包含有文学的宣泄功能之义。那么,作为一个校园的文学社团,校文学社,就不仅承担了学生在文学创作中的宣泄功能,而更应体现作为一个教育园地一定程度的教化功能,即进行“疏导”。
高中生是一个有着自己年龄阶段特点的群体。他们不同于初中生的简单叛逆,也不同于大学生的初涉社会,他们正处在一个似懂非懂,似乎有了比较定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并不牢靠,时时处于观望、徘徊和犹疑的时期。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是一个人生的关键时期,更别说高考在他们的人生中所占的不可否认的分量了。因此,他们都会经历一个意义重大的思考阶段,在思考中,感知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方向,放弃自己曾有过的美好但天真的幻想,让自己在现实中完成那纵身的一跃。
在这些试探和确定中,早恋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亲情和友情。尤其在我们这样的住宿制学校,亲子关系的种种问题在一周才能回家不到两天的学制中被无奈地放大。高中生们不是继续怨叹,不再继续挑衅,而是选择了接受甚至是理解,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孩子比父母还要成熟、深沉。他们知道,现实就是这样,自己已经看淡。父母是不能选择的,而朋友,则成了最体贴心灵的救命稻草。高中生相当敏感,他们基本已练就了只和气味相投的人相处的能力,这时候交到的朋友,基本都可以延续很久。只有那些特别寂寞的人,才会选择用早恋来体现自己的魅力和价值。早恋的孩子,明知没有结果,但也要投入,也要维持,因为心灵其实比较空虚。然而,早恋的后果往往是更加的寂寞和空虚,更加的惆怅。
对社会更是时有偏激之论。社会之种种诡谲、阴暗,在高中生的心灵中也被无比敏锐的感知放大了。他们看社会,就像看污泥浊水,像黑森林。比如,前两年校文学社刊物上登载了一篇《老杨之死》,写负责任而憨厚忠诚的老杨最后被社会的几只黑手合力绞死的故事,竟受到了大家的追捧。每期校刊登载的文章不下几十篇,一两篇是揭露阴暗面的,那余下的几十篇文章我就都留给了美好光明的心灵。或抒写青春的烂漫,或展现年华的感伤,或歌颂清明的智慧,或寄托高远的志向,让学生们读了,受到启发和鼓舞,让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上可爱美丽的一切,并不因几丝阴霾就否定人生常在的晴朗。励志之中,亦不失真性情,真感想。
所以,疏为先,导相继,疏为辅,导为主,大禹治水的古训,而今依然有效。作为文学,我希望文学社反映学生们真实的心声,作为社团,则寄予了我教化导引的衷肠。
我热爱文学,虽不至像鲁迅先生那样相信文学能改变国民之精神,但自信文学之能濡染心灵,有其卓然独具的魅力和影响。文学社,作为长春市实验中学的一个小小社团,也为“幸福校园”的建设发挥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作者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