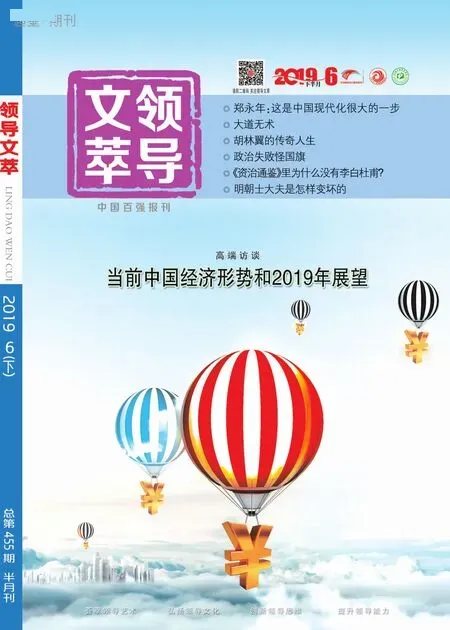李斯的顿悟
□李国文
李斯的顿悟
□李国文

人生道路,对平庸的人说,走对走错,是无所谓的。对,也好不到哪儿;错,也坏不到哪儿。而对李斯这样一个敢下大赌注,敢冒大风险的强人,就很难说他入秦是对是错了。他到秦国以后,历任廷尉、丞相等重要职位,为秦王上“皇帝”封号,废分封而行郡县制;统一六国文字为“秦篆”,禁绝私学及百家论著, “以吏为师”,以免文人儒士颂古非今,谤议朝政。铸铜人,收缴武器,以防造反;坑儒生,焚《诗》《书》,箝制文化。这一系列的暴政,大多是这位上蔡县小人物的点子。因此,秦始皇视之为膀臂,授之以重任,官运也就亨通起来。从此顺风顺水,一路发达,他的官也做到了极点。按说,他这一步路是对的,然而,他最终得到的是一个腰斩的下场,到底是对,还是错,又得两说着了。
李斯,人聪明,太能干了,但聪明能干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智清醒的人,秦始皇死后,他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阿顺苟合于赵高,那是一个心毒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坏蛋。贪恋高官厚禄的李斯,利欲薰心,竟与魔鬼结盟,两入密谋矫诏,立胡亥而逼死扶苏。秦二世当权,自然宠信赵高,于是,李斯向二世拼命讨好,怂恿他肆意广欲,穷奢极乐,建议他独制天下,恣其所为。赵高哪能容得那个指鹿为马的胡亥成为李斯手中的傀儡,任由操弄。便不停地构陷诬告,加上李斯的儿子李由,先前未能阻击吴广等起义农民军两进获罪,新账老账一块算,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那是公元前208年。
李斯在被腰斩前,对与他一齐俯首就刑,一齐奔赴黄泉的儿子,说了一句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话,那就是有名的“牵犬东门,岂可得乎!”
死在当头,能有心思说出这番言语者,你还真得佩服,他还真是一位非常人。我觉得李斯死前对儿子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实际上是对他一生所追求的价值,作出重新的评估。
说出这番话语,我认为是这位走出上蔡的河南汉子,对其追逐权力的终身选择,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全面否定。
李斯直到腰斩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为时已晚。如果一直纵狗猎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干馍,喝糊糊,听梆子腔,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看着法场上像砍玉米秸杆似的,倒下一排排子女亲属的尸首。
他杀了一辈子人,如今,轮到他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的结尾处,写到了这次残酷屠杀。“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所谓“三族”,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他明白为他权力狂人的一生,要付出多少代价。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与其父子同时同地遭到屠灭。
这位法家(按“文革”时的封号),当他作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时,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此刻,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场面,大概唤醒了他早已泯灭的人性,这位秦国丞相, 《大秦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这个残酷暴虐的政府痛心疾首。此时此刻的李斯,该多么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牵着咻咻嘶叫的猎狗,出上蔡东门,在秋日衰草丛中,追逐成群狡兔的无忧岁月啊!
后来的文人墨客,就把李斯这句死前名句,缩成“东门犬”三字,既表示恨不如初,也表示对自己的彻底决绝,在人鬼交替,阴阳分界的这一刻,作出俺错了的悔愆。
其实,司马迁说李斯不过是“为郡小吏”,一个相当寒伧的土老冒。他所担任的那个职务,粮仓保管员,在一群乡巴佬中间,也算得上是出人头地的区乡干部了。
据说,他是这样感到自己其实的渺小,真正的不足的,据《史记》,有一天,管库员李斯例行检查粮库,“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来讲,就是“厕”而不是“仓”了。
楚国这个“仓”,再大,也大不过秦国,那里才是他这样有抱负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干的所在。权力基因驱使着他“西说秦王”,他相信,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弄个一官半职,当不难。就在这种权力场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脱颖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权力顶峰。
李斯在他最得意时,曾经“喟然而叹”:“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农,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令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税驾”,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任何处也。”
重新阅读这段尽人皆知的秦亡史,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精明老道,如此能言善辩,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计高谋深的李斯,在秦始皇沙丘驾崩后,在赵高、胡亥策划的宫廷政变中,忽然成为一个处处挨打,事事被动,步步失着,节节败退的完全无法招架的庸人?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纵横捭阖,兼吞六国,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来,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能事先无远见卓识,猝不及防;事中无应变能力,仓皇失措;事后无退身之计,捉襟见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赵高,基本白痴的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
每个人任其一生的道路上,总有拐不过去的死角,当李斯告别上蔡县乡亲父老,往西大步流星走去的时候,对这位野心家而言,渴求权力的必然结局,或许就已经注定了。
司马迁这样写到他的最后一幕:“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历史是不相信眼泪的,曾经辉煌一时的秦相李斯,只有伏在刑场上专为腰斩而锻铸成的铡刀上,把命交代给刽子手了。
(摘自《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