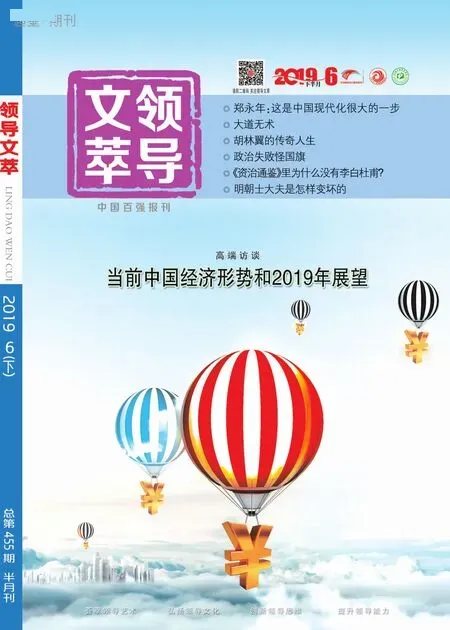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冯锡刚
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冯锡刚

“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安排,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
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国际友人。其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祝贺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这当然是不无夸张的说法,但是诗词确实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独特武器。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年6月5日,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殊,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示 “不熟悉”、“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虚相比较,江青似咄咄逼人:“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就在称赞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这样的疾言厉色恐怕与江青质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不会全然无关罢。
除了京剧现代戏,对于其他一些艺术形态,毛泽东都予以利用。10月6日,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0月8日,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0月13日,毛泽东在8天之内第三次去剧场,观看歌剧《江姐》。这一系列的举动,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京剧要革命,芭蕾舞要革命,归根到底,人们要革命。革命成了6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
中苏大论战中的小插曲
就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决眦裂眶的一刻,人们大出意外地在1964年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读到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竟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经验告诉人们,这只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3月17日,也就是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氏70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据吴冷西回忆,10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氏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说,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定的友好之意。
4月14日,毛泽东审定贺电,在加写的诸多文句中,最具个性色彩的就是“亲爱的同志”。祝寿电文可以视为大论战中的一个插曲。
这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不无巧合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与赫氏下台的消息刊登在了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这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一上一下的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无疑为毛泽东赢得了极大的威望。毛泽东此刻的心情应该是一喜一忧:喜的是“豺狼”已除,忧的是继承者是否更坏。毛泽东迅速决断,指派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以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名,与苏共新领导接触,作现场考察。在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已将赫鲁晓夫撤换了,你们也应该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报告和请示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党政代表团应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抗议。随后,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道歉,但周恩来未予接受,并强调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结果不欢而散。
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历数赫氏执政11年来的12大罪状。毛泽东总结赫氏下台的原因,除社论所说的,还有一条未便公之于世,那就是1965年1月9日在回答斯诺提问时所说的:“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对原因的洞察可谓别具慧眼。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吐真言”对于毛的刺激之深是不难想象的。紧接着发生的作出“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定,当然是毛多年来反复权衡的结果,但也不能低估毛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总结。
“接班人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
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毛刘分歧固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开始,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两人还是步调一致的。即使是社教运动,在1964年春夏之前,也还是基本一致的,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毋宁说刘比毛更“左”。在笔者看来,引发毛泽东强烈反应的真正原因,还是对“大权旁落”的担忧。
6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发表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备战,二是培养接班人。
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在谈到高岗问题时,毛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刘少奇。毛这番关于接班人讲话的最后,指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
这一年,毛泽东在部署和准备接班人上,采取了重要措施。1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的这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与上届相比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林彪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
1964年的毛泽东,思虑所及,渐由国际反修转入国内反修(社教),由运动重点之争及于接班人的替换,选择的突破口在文艺和教育两界,而确保既定路线的推进,要依赖对军队的掌控和对个人崇拜的鼓励。这一切被有机地组合在了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两年之后开通的“文革”之路。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