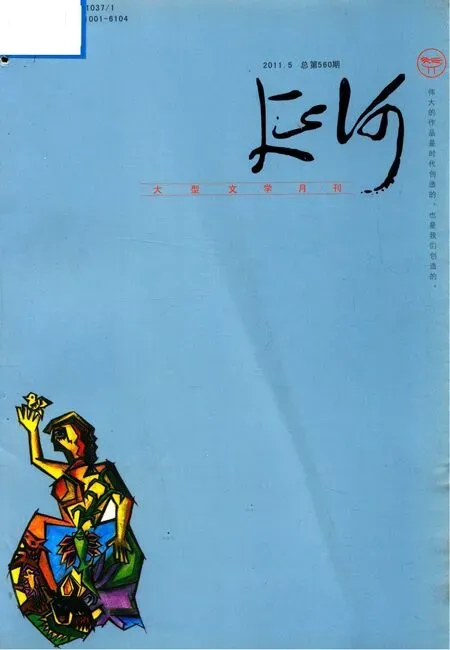民国建筑与今日阅读
高星
民国建筑与今日阅读
高星
西城民国建筑
西直门圣母圣衣教堂
1723年的西直门
有运水的马车在这里经过
时间像树丛一样浓密
意大利人德里格在这里弯下身躯
太阳从高粱河上折射出他的身影
正好等于哥特式教堂的高度
教堂像《圣经》的书脊一样
窄小 节制且精装
但历史的文字
总像力大无比的刀枪
一次次冲进这本书中
厚重由此而来
嘉庆皇帝捣毁过它
义和团也捣毁过它
文革时在这里生产纽扣 中药 电扇
今天重又修饰一新的塔尖
那光芒依然有些惊恐
相邻的高楼 却是异样的反光
我的母亲 此时拖着血栓的身躯
住在对面的老年公寓
在小屋里 一个人面对着电视
期待着那里展现的一个平等的未来
我每次和母亲分别在街上
都会正好与教堂打个照面
成为一种注视死亡的礼节
它像一个巨大空荡的背影
在打开的棺材中穿行
有一天 我会和母亲一样死无葬身之地
此时 还有更大的灾难临头
人们在一致地排队购物
习惯于物与物之间转换的兴奋
还有我那没着没落的爱情
教堂在积极向上 如同
抛开一切的塔尖
教堂的四周堆积着黄昏的尘埃
像我一辈子所见的黄昏
丰厚的历史就是它的感染力
灰色的天空和街道
像它的墙壁一样灰
拥堵的车辆穿行的电线
让教堂里面的辉煌更加遥远
当年城外的庄稼和布衣的人
才正好仰望农业社会的信仰
教堂伸展着细细的塔尖
像瘦小的鸟 收紧了翅膀
在天空的挤压中 如何向上飞离
白塔寺人民医院
两个女儿先后在这里看过眼睛
但她们现在都戴上了眼镜
在这个几乎看不见医生的院落里
我每次都要提早去挂号
寻找一位叫吴夕的女大夫
1918年 伍连德成为了这里的首位院长
当时叫北京中央医院
本来刻在碑上的博爱、精微、醇良的院训
如今真的成为了口碑的相传
维多利亚式的小楼院落
主楼的门厅如突出的羽翼
罗马圆柱撑起巨大的玻璃窗
东西两端的燕尾式楼道
被藤架上的丁香遮掩
亚麻地毯上曾经摩擦着
逆光中的修女轻轻摆动的裙裾
1956年9月24日
诗人顾城在这里出生
所在的妇产科是来自协和的材巧稚创办
他的父亲抱着他 穿着一身严肃的军装
出生在城里的顾城
时常在夜里拿起铅笔
在睡床旁的墙上涂写着成名的诗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女儿在这里指着“E”的方向
大夫直接用灯光将眼睛照亮
这个小而安静的院落
抽象得更像是一座幼儿园
更像是一只被无限放大的瞳孔
如今我居住在西直门的西侧
这里是人民医院的新址
巧合的是地理位置的联系
但我深信 女儿的眼睛
都将从那个小院失去记忆
西交民巷中国银行
1976年 清明节的时候
我曾在这座楼旁的邮局上过厕所
后来盖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
拆除了它旁边的那座老楼
1989年慌乱的春天过后
我走进了它对面的22号院落
开始了保险杂志的编辑生涯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职业
我的父亲1952年在相邻的前门大街
鲜鱼口胡同口的52号
义盛珠算厂学做木匠
这一年他只身迁徙北京
我在简易的办公室里
情绪像夕照的阳光透亮笔直
隔着朝东的窗户可以看见广场上的华灯
感受着习以为常的心脏跳动
院中是金城银行的旧址
木楼梯绿铁皮柜和雕花的铁艺栏杆
如今都已消失
记得那里的一只老鼠
吓坏了一位傲气的医务室医生
我每天中午到钟楼下的食堂吃饭
也到那里打开水 洗澡
那时不用打卡 不用电脑 不用登陆OA
我的目光总会习惯地越过这座钟楼
向北面的广场望去
就像我会隔过雕饰的门扉
抬头看一眼顶端钟楼的指针
我每天都会像欧阳江河一样傍晚穿过广场
都会像西川一样走过广场上的落日
都会像阿坚一样昂首穿行到广场的东侧
2008年 广场开始施工
我没有收藏一块广场上的水泥方砖
哪怕是拆掉的一小块
因为它太普通而且太沉
在钟楼的中国银行营业大厅
曾经有一位高个的女孩 气质非凡
她的高傲比钟楼的拱顶还要
高昂 还要辉煌
有一次在前门地铁的站台上
她终于对我点头微笑
我没有受宠若惊
明白这是她的礼貌和面熟
那些年的爱情 全是片段的记忆
就像圆顶上的时钟
每一个刻度都是一种际遇
这座建于1924年的仿英建筑
花岗岩的基座还有挑出的檐口
三层拱门镶嵌的劵柱
映衬着两侧的科林斯壁柱
去年 它终于挂上了文物保护的牌子
西皇城根北京四中
一座灰砖牌坊式的门楼
一座典型的民国风格的栅栏门
成为了北京四中孤单的旧物
成为了北京四中的标识
它是北京所有学生的一道门坎
也是我1977年中考时
一座遥不可及的目标
1965年 北岛考上了北京四中
如同摸进了天堂的大门
他每天骑着永久牌的自行车
沿着德内大街穿行
他惊吓于一位女老师用剪刀割断了喉咙
只是为了剪断自己的阶级身份
他暗笑一位女学生检讨的大字报
上面讲出了有关乳房的想象
他曾要为四中做个大个的铝质徽章
他从这里出发去天安门见到了毛主席
在我送女儿上幼儿园的平安大街路上
我总会一遍又一遍指给她看
那就是北京四中
它似乎早已成为视觉形象的定式
成为了一座不可跨越的大门
她们惊讶狗子也毕业于这个学校
就像我惊讶白脸也上过这个学校
狗子当年在教室的门框上
放过水桶和扫帚
吓跑曾经教过我画画的老师
丁榕老师那种朴素的美如版画一样
可以让今天的彩照变成黑白相片
在丰台少年宫灰色的小院里
为我们展开一片奇形怪状的云彩
后来,她来到了四中执教
1983年的夏天我们几个昔日的画友
在四中的门前和丁老师合影
照片中的我十分尴尬
四中终于和我发生了关系
这里曾是最早成为废除高考的革命中心
如今成为了北京高考升学率的典范
这里曾宣扬过血统论、贵族论
如今成为了北京高考状元的摇篮
今日阅读
同样——仿卢梭
很久很久以前
这样开头很像童话(就是一个童话)
一个没心没肺的国王
脑子里装着许多生活幸福的理想
大臣的眉眼 要和他长的得同一模样
一个爱讲道理的王后
走路的时候 经常打碎所有的东西
拥抱所有的路人 并且心思不在身旁
国王和王后一直没有孩子
绝后会让全体子民绝望
后来王后终于怀孕的喜讯
竟让路人窒息 敌人死亡
医生说 多亏了他们的药剂
僧人说 多亏了他们的圣物
子民说 多亏了他们的祷告
国王说 多亏了他的爱
任性的王后 以为自己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
疯狂的国王命令只能准备男孩的衣裳
一个人一旦有了疯婆娘
就不可避免先要做个傻瓜
要想疗救妻子的荒唐
最好的办法是和她一起荒唐
请教慧星 仙女传言
讲究秩序的项链 镶着宝石闪闪发光
就像有了太阳 还有月亮
王后最终生了一个女孩
国王同时得到了一个男孩
两个各自属于自己性别的那个孩子
相互相反的天性和模样
男孩叫任性王子
女孩叫理智公主
王子拥有女人的全部美貌
公主具备君王的全部德行
国王有时抱起王子 其实却抱着公主
王后有时跟着儿子 结果踩着了女儿的脚
掌
王子在国王去世后继承了王位
同时也继承了父亲有关幸福的全部理想
公主最终嫁给了临邦的国王
因为他会玩单脚跳 而且胡子长得最长
王后最后死于消化不良
而那时,国王正引诱着她上床
一天——仿洛谢夫的《布罗茨基》
1962年1月9日 就在这一天
母亲一个人手提铁皮的脸盆
挺着大肚子 但乳房并不充盈
来到丰台医院 将我生了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前一年
21岁的布罗茨基见到了阿赫玛托娃
他坐在塞得满满的电气火车里
为她写下了祝寿的诗
公鸡在鸣叫 倾斜地书写
那时对阿赫玛托娃的造访
风流伴着风险
在聋哑的宇宙 获得话语的天赋
就在这一天的前几天
布罗茨基刚刚与女画家巴斯马诺娃相识
阿赫玛托娃说她就像一杯冰水
布罗茨基说她是手持苹果的维纳斯
她的絮语、呼吸还有身姿
创造了他的耳朵、口腔和眼睛
他曾为她割断静脉
让血流向大海
让爱得以永存
政治永远是荒诞 只有爱情才构成悲剧
在流放的诺连斯卡亚村
他的诗有一半献给了不在场的她
就像他身体的一半
在获准回到列宁格勒的路上
他一心一意的是想回到她在的莫斯科
在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
布罗茨基在美国又为她写下了三首情诗
他不仅戏仿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冬夜》
还暗自改写了但丁的《神曲》
爱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群星
世界就这样被创造 被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