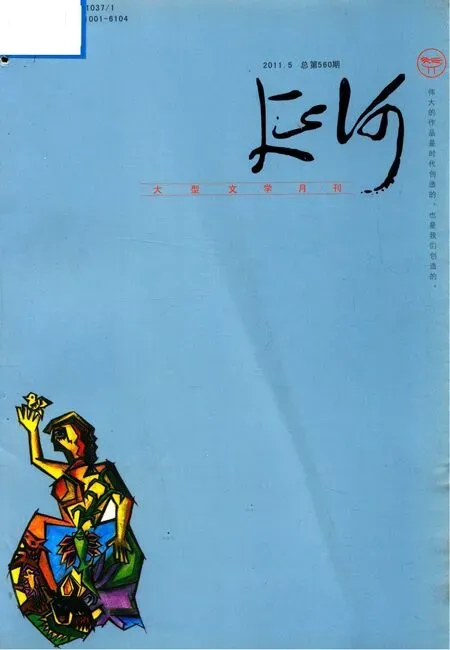新时尚:一种文学的政治写作
黑丰
新时尚:一种文学的政治写作
黑丰
现在早已没有纯文学可言,只有一种文学的政治。较真地说,是文学的政治,不是政治的文学。文学的政治写作,是现实的文学化,是从政治的冰中汲取冷的火,从政治的鸠中提取止渴的毒酒(文学的嗉囊必须吞下),是一种危险的表达,是对文学的一次内部引爆!新生即涅槃。
这就是我的和我认为的现代写作。它是一次指向疫区的免疫写作。
每一个词都昏厥,每一个词都贫血!每一个词都亟待针灸!
只有从世界的午夜进入词语的午夜,从午夜的政治进入词语的政治,只有穿越文学中的政治碱性,只有“杀”生,只有血祭,词语才得以拯救;只有喋血,词根才得以复苏;只有“自杀”(“自杀”是作者亲死,亲历时间的断裂,亲历时间的停顿和永夜),物与词的复眼才得以共同复明,让生命和词语一再碰撞冰凉的石镜,磨砺出词语的光亮和锋刃。这就是我的文学的政治写作——一条血路的写作。
“一次纯粹的(也许是不朽的)写作是惨无人道的。在寻索美构与人性的栈道上,伤害甚至摧毁了人的存在——这就是代价。”(1993年,拙作《灰烬的飞行》)
政治有时像一台粉碎的机器,送进去的不仅仅是时间的金色麦秸,还有我们自己。谁是被粉碎的麦渣瓤,谁是活蹦乱跳的我们,已难分清,血肉模糊。有时血肉模糊都不是,脱离出来的只有一团干干的粉末,一阵风吹来,什么都不是。
文学的政治写作的残酷性,需要将我们散布到空中的粉末,收集成像,再度纳入,再次粉碎。
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境遇中,我有一种绵延不绝的颤栗,一种说不清的惧怕、惶惧,我的心中有一个卡夫卡的世界,有一种悬浮的等待,一种不期而然的等待,就像等待雷击和过电的那一刻。人一直悬浮着。一种不具象,不具体,无方向,无源心的力,它从前后上下左右四方扼住你,扼你的心、喉、四肢。一辆永远的警车一直在我的附近啸叫,大雾弥天,我看不清,找不到方向。一种“境”始终压榨你。我并不惧死。死倒安静!而自然死亡也是可鄙的,这是一种“在最可鄙视的条件下”的死亡,“这种死亡并不是自由的,在该死去时它并不来临……”但我也不愿认可在“境”的压力下死,这种死同样苍白。很多时间,我感到人生的苍白,写作失效、无可救药。但我需要一种顶住压力的写作,一种有锋芒的写作,就像一种完全不同的自杀一样,“自由的和有意识的”,绝非“偶然和意外”,这更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和热爱。所以这种写作就像这种死亡一样是可能的,它给出了空气、空间。这就是文学的政治写作。在写作中去“死亡”,在写作中“通过死亡成为自己的主宰”,同时,“也将是通过死亡而降临于我们的那种强权的主宰”,“使这种强权沦为一种死去的强权”。在一种准备赴“死”的写作中去“活”,“使人类无需再自杀”,“使人的生命完全地成为人的生命”(布朗肖语录)。这也许是一次晦涩的或晦暗不明的写作,但这绝对是一次“纯理想”的写作——一种极权写作或黑色文学写作。
写作不是交流,而是抗拒。用文学的政治消解之,消解我们永夜中的魔鬼。
时代再一次出现了危机——信仰危机,这是一个神迹与高贵空位的时代,市侩与功利成了当下最大的“病”,人们过早地失忆,或习惯了失忆,或自动放弃记忆。一场又一场的“血崩”也无以唤醒,只有血的暗寂,人们完全忘记了大地、天空及诸神的召唤。
一个人为的真空出现。
整个中国全部成了一个市场,充耳的只有市声。只有掮客、商人、政客和流氓的横行,只有势利,只有交易和买卖;没有尊严,没有公正,没有神圣的东西;只有龌龊,只有用过就扔的方便袋、纸桶,擦过就丢的纸巾。核心价值观、公共道德全部沦丧。没有最后的底线,只有无耻的卑鄙和交易;只有面具,只有假话、空话、套话,只有阿谀奉承、尔虞我诈,只有上级上司老板老总,只有权力、权贵和金钱,只有歌星影星球星;没有灵魂。大街上、大型广场、公共场合,会议室、办公室、家里,全是无“灵”人。到处是行尸走肉!人们被驱赶着、牵引着,搔首弄姿、矫揉造作。沉天忙忙碌碌,也不知干了些什么,呆头呆脑的。灵魂仿佛被摄走,被“吃”掉,诺诺连声。
世界和时代越来越严峻,越来越陡峭,越来越不知道是个什么。剩下的只有恐怖,只有一个虚拟的、网络化的幸福。
大师满街走,大奖随便就砸着一个人头。明明狗屁不通,明明结结巴巴、句读不准,明明是空的,明明是泡泡、泡沫,可是一下子“火”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砸住了他,庄重文文学奖砸住了他,鲁迅文学奖也砸住了他。怪了!连发原创都不够格,选刊只眼不看的人,一下就撞了个鲁奖,撞了个庄奖。——这就是中国!现实中国!
鲁迅,一个多么严肃、纯粹的人,一个多么嫉恶如仇,一个死后“血肉”即使“该喂动物”也“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的人,这下可好,喂的几乎尽是一帮癞皮狗。啊嚏!鲁迅地下有灵也该打喷嚏了。——完了,我感觉这个时代完了!
——这是一个瘪壳的时代,一个欠收的时代!一旦大风吹过,大多将被吹走,没有多少谷粒留下的。
没有。
这个时代,让你丧失写作能力;在这个时代活着,让你感到“脏”;这个时代,让你感到“活着”是一种耻辱……我感到孤单和无助,我强迫自己慢下来,安静下来,与大师一道温习功课,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存,重新检点我们的写作。
我们还仍然生活在一个蒙蔽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去蔽、敞开、启蒙。历史的积淀和污垢太深。
这个时代不需要小说家,不需要广义叙事的作家。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大思想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亟需的。我们目前没有,时代没有给出,十分悲哀!嘤嘤嗡嗡到处都是,蝇屎到处都是。这里没有创作,只有生产,“抓革命,促生产”式的,“文革”狂病复发式的。
中国不需要小说,中国需要启蒙,需要彻底的启蒙;中国不需要故事,中国需要创造自己的精神启示录和贯穿历史的忧思录。
中国的小说写作、散文写作、诗写作,都一样,都是“生产线”,都是泛工业写作,都是白开水。没什么艺术含量,没思想,没有文学价值。全是劳动密集,大兵团,全是落伍的装备。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室。只有工厂。工厂,工厂,工厂,工厂……除了工厂,还是工厂。林立的工厂。人们像自己的祖宗一样在“田间”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守时勤奋。每天一轮红日西沉,每日一模一样。产量惊人,但只有重复。如此这般,一个大师,一支笔,足矣!
——中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造!
一个作家衣食无忧,一个作家住小洋楼、别墅楼,一个作家脑满肠肥,一圈一圈地叠摞赘肉……靠他们能写出什么?那堆积起来的文字,那一本本码起来的开本近乎书籍模样的东西就说明他们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吗?——垃圾!!不定是毒品!这种千篇一律的波普的东西,只会导致人性和生活方式的平面化、审美趣味的肤浅化、粗鄙化。被秋风吹破的茅屋何在?冷江破船漂泊的踪迹何在?“三吏三别”何在?人民的哭嚎何在?
无影无踪。
一个作家的苦难是必须的。一个写作者必须对现实说话,必须面对自己的文学良心和艺术良知,必须揭示感观中的残酷真实。但揭示不是止于镜像式的,“揭示”是艺术的凸视,是使残酷的现实变得更富意味和发人深思。“艺术的目的是给予事物的感受以幻像而不是认知;艺术的手段是陌生化的手段和给感受以难度和广度的困难形式的手段,因艺术的感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并且应该伸展下去……”(施克洛夫斯基语录)所以,文学写作,必须遵从艺术自身的规律。在此前提下发展文学。我的文学的政治写作是遵从这个前提的,这是一种最简洁、最形式、最疼痛的写作,是一种疼痛的“痒”,是希望中的绝望,绝望中的希望。但这种很形式的政治写作是残酷的、自杀式的——是以血祭词。是一种冰面燃烧,冰火相融。本质是最形式化的。而一切形式必须具体、深刻、可感、直观,具体而抽象,经验而观念,垂直、深邃却无限开阔。实在、具象、物质却蕴涵思想和精神的向度。比现实更现实,比残酷更残酷,但残酷中有一种艺术光照的温馨。清晰、清白、永恒,却瞬息变化。根本而虚构。不识,却似曾相似。是时间的一次阵痛,一次断裂的绵延。晴明,明明白白却依稀朦胧,清晰清白却是一个梦,清晰清白却雾气弥漫……
我的文学的政治写作,还体现在另一方面——一种冷酷的考古学意义的地层发掘。“在纸上的漂泊中,我呼唤并期望寻索一种新的地理。我提倡人的不灭,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认为文学实则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我们不仅要善于从人使用过的器物中,从历史的的遗迹与印痕中,从空间的迷局中给祖先和易失的人类按脉,还要善于从当代人的身上发掘我们的祖先,从而发掘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从而开启另一扇人的生存之门,进而拓展一种神性的文学新疆界,让比我们更古老的词语重新开口说话。”(拙作《灰烬中的飞行》)
现在看来,仍然是对的。这个认识在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中得以认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研究时间中的“空间”,历史中的“档案”的。他认为空间为外化了的时间,时间不单纯是“绵延”的,也是沉淀的。“博物馆”看起来保存的是“物”,但其实是时间的“遗迹”,使用它们的人虽然不在,但使用的印痕、生命浸注的印痕和时间沉淀的“遗迹”还在。物就像一个“贮放人性的容器”(里尔克语)。时间虽然从死亡的零界、从握着“烟斗”(福柯)的手上断裂,但消失的时间会在“烟斗”上一层层“冷冻”下来,同时它也会在今人身上“沉淀”,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发掘。“烟斗”的所指具有意义,它的能指同样具有意义,或许更为本质。德里达的《文字学》也有进一步的表达,《文字学》是一部强调“写”、“轨迹”、“文本”的书。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皆是“时间——历史”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直线的“绵延”,而是层层覆盖。现在“覆盖——删改”着过去,透示着未来。眼前的事物,大多为昨天的事物,事物在“延续”中“自身同一”,但今日的事物,已非昨日的事物,今非昔比,“同”中有“异”。这就是德里达的“延异”。
所以,我的写作“考古学”的意义,是空间的,遗迹的;“人虽不在场,却完全存在于景物当中。”(塞尚语录)所以,我重视“物像”,重视罗伯•格里耶,重视他的《嫉妒》。物体和词语中存在“一种非有机体的生命的力量”,“消亡的是有机物,不是生命。”(德勒兹语录)
我的文学的政治写作不仅强调时间中的的“遗迹”,强调“冷冻”、“沉淀”的时间,同时强调从词语开始我们的写作,从句子开始写作(有时甚至从汉字的奇特、繁复的笔丛开始)。一看就陌生、新颖,一看就与众不同,一看就是激进的,一看就刻骨铭心、深入骨髓。我们需要这种效果,不需要“慢”到一件事的过程结束。我是说,一旦摔成碎片,仍然是光芒四射,金光耀眼的。这里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因为一切写作都是语言的,一切语言都在纸上。这是大道,必须悟清的。语言是晶体。内容是语言的,语言是内容的。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客观的、外在的最终都是语言的。而这种语言不是想破脑壳都不识,查遍字典词典都不识的语言。首先它们的词素都是普通的,但都显出不同寻常的光芒。让你识,也让你不识;让你查,也让你无典可查。它的意义在典中,也不在典中。
它通过一件事来贯穿,但它不一定要通过一件事颠覆你。写中有神奇,词中有光芒。它不是故事篓子。写出的也不一定是故事。故事是平面的,线型的。它写出的是创造性本身。
故事篓子作家是这样的,倒,倒,倒,一旦倒空,就黔驴技穷。
这与作家的观念有关。艺术观决定艺术形式。
传统意义的写作主要强调的是经历、经验、教训和创伤(记忆),强调的是思想和血肉的感觉。传达的是道。语言不过是载体——包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们强调从细部开始、从词的政治开始,从词语中的黑夜开始,从文学的碱性开始。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新的出发,每一次写作都将推到临界。写作就是向困境推进,写作就意味着冒险。
传统性作家依恃的是人生经验、经历,坎坷,认为有了丰富的积累就可以动笔了。这种写作主要是将他们的经历经验、思想及世界观记录下来,形成文字。
我认为写作主要是未知的。也在乎人生经验、经历的形成,但这只是一方面,不是全部。我们并不摈弃生活摈弃经历摈弃血泪与思想。我认为深刻性无大小,不以物小为小,不以物巨为大,不一定占据很大的体积、很长的阅读时间和空间。但讲求“核”能。即使很屑小很微不足道也仍能体现深度长度和广度;一滴水、一只蚂蚁、一片树叶也能体现世界的残酷性、荒诞性。
我的写作首先想到是一种形式,一种语言。我热切地心潮澎湃地想望着,一种乌托邦式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一个均一的系统,而是一个不均衡的,永不均一的系统……它的“主句与从句之间”,甚至词与词之间“必须有一种张力”。我的世界尽在语言中;而我的语言尽在虚构中。写作使我疼痛;疼痛产生我的写作。我的写作,昭示着一切华辞丽藻死去,一切伪语言写作死去,一切伪现实伪现代死去。语言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困境,也是我们的前景。
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
我时常想象一种虚构的笔,一种像一把多面的、全方位的刻刀的笔。一种想望中的作品难说有正确的道路和安全的通途,不是迷宫,却胜似迷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上有地,地下有天,影在水里,水在云中,云在天上走,也在地下行;是上也是下,是前也是后,是左也是右,是东方也是西方,是北方也是南方,是白天也是黑夜;一切都在变,渐变,变形变异变大变小,变成你变成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艾舍尔的画《白天与黑夜》。
语言是一种再生能源,是一种魔性黄金。它收容卡夫卡,收容卡尔维诺,收容博尔赫斯……
借用让•理查的话,再说一下,语言是石化作用的泉水,石化泉水是液体的石头;语言在流动不居的液体内部重新聚合……写作是深入这些深处,从中发现这种凝固的运动。……写作就是把缓慢积聚成的、分散在全部时空中的整个固体性集中在唯一的一点和唯一的时刻上。写作犹如一种生活的自然运动的入侵:把本性、本能和习惯在生活的遥远的深处积聚下来的存在之物汇聚在现在,在这里、在句子里,写作就是一种存在的恢复和回收。
(本栏目图片都来自互联网,相关作者请与本刊联系。)
栏目责编: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