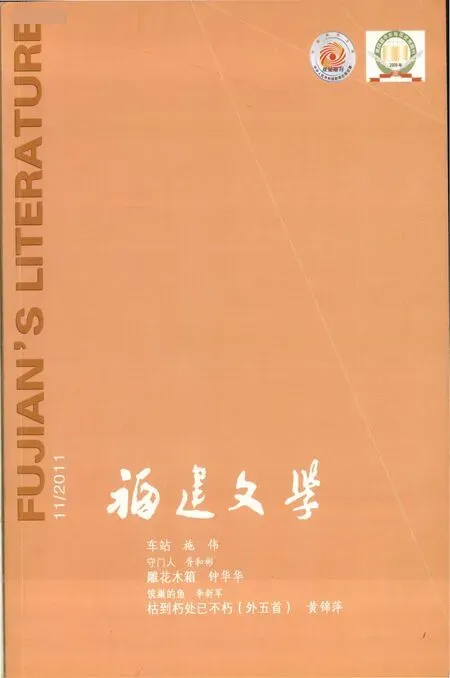雕花木箱
钟华华
瓦兰又做梦了,梦里总是出现那只雕花木箱。
瓦兰梦里的河涨满了水,雕花木箱像道鬼魅的影子,从河上游漂来。瓦兰光着脚板,朝河边跑去,她拼命想捞着雕花木箱,可河面突然变得特别宽广,她无论如何也够不着。就在瓦兰焦急得哇哇大哭时,她身上像挨鞭子抽一样疼痛起来。
钻心的疼痛惊醒了瓦兰,她揉了揉烂桃一样红肿的双眼,才发现是个梦。而自己,是被刚才男人抽打的伤口痛醒过来。男人来宝打完她,早已到镇上的柜台里喝苞谷烧去了。
来宝打女人,像打条牛一样狠。
那天清晨,就为了那只雕花木箱,瓦兰天不亮就起床了。头天夜里,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只要下过暴雨,这条平常极温顺的河,就会变得汹涌咆哮。只要河水涨上来,上游就会冲下来各种有用的东西:比如木料,棺材,衣服,鲜鱼或是发胀的粮食袋子,甚至是死人。瓦兰不喜欢那些东西,她觉得那些东西从洪水里钻出来,始终带着一股死亡的味道。她只去等待一件物品,那就是雕花木箱。
自从三年前瓦兰从河的上游嫁到躲雨镇来,每次涨水,她都会去河边守候,寻找梦中的雕花木箱。可每次她都无功而返。涨水时节,村里的人,人人眉飞色舞,高兴得快要发疯。谁见到那样的场景不会发疯呢?涨水的河里漂满各种各样有用的东西,这些东西要是河边的人自己造,不知要花多少钱呢。
瓦兰每次去,目光总是掠过那些与雕花木箱无关的物品,朝河里张望着。男人来宝裹在洪水一样汹涌的人群里,不断打捞。瓦兰就负责站在岸边,不断听从来宝的吩咐,朝家里搬运木料啦什么的。每次洪水一来,瓦兰就觉得那些木料多得堆放不下。她心里嘀咕,捞那么多木料干什么,不就是卖几个臭钱打酒喝么?喝了酒,又把怒气发到她身上。因此,每次搬运木料时,她就心里来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别的女人,都在男人的唆使下,像牲口一样朝家里搬运着。
瓦兰到达河边时,天刚蒙蒙亮。她努力朝河的上游宽阔水面搜寻着。就在一眨眼工夫,那只雕花木箱,泛着油漆的红光,从上游漂荡而来。就在这时,村里的柳翠翠,也来了到河边。柳翠翠是村里最可恶的女人。她的嘴皮子翻得像两片弹簧一样快。要是骂起架来,谁也不是她的对手。瓦兰看见她,原本想躲开,可是心爱的雕花木箱眼看快漂到跟前来了,她舍不得。
柳翠翠也发现了雕花木箱。瓦兰踩进水里,水流太急,雕花木箱被她用一把铁耙狠狠逮住了,却无论如何也捞不上岸。这时,柳翠翠急急地赶了过来。瓦兰看见她眼里泛动的绿光,就知道这只雕花木箱变得复杂起来。
“好一只雕花木箱呀!瓦兰,瓦兰,我来帮你。”柳翠翠老远就喊起来。
瓦兰本想说声感谢话,可看见柳翠翠那老鹰一样的眼神,就说,“河里的东西多着呢,不用了嫂子,我自己能把它捞上来。”
柳翠翠有些不高兴了,“哟,嫂子是贱呀,找上门帮你忙,你也推辞,真是把嫂子当外人看了。”柳翠翠说着,裤管也没卷,呼地一下就跳进了河里。柳翠翠也抓住了瓦兰手中的耙柄,一起奋力朝岸边拖着。
瓦兰本想拒绝她,可是没办法了,柳翠翠真是热心过分了,甚至站到了自己跟前,先前在自己手里极不听话的雕花木箱,正乖乖地朝她靠拢。瓦兰一下子变得心里虚脱起来。自己发现的雕花木箱,突然变得那么不真实可靠。柳翠翠一边拉,一边惊喜地说,“好漂亮的雕花木箱呀,上等的红豆杉木料,一流的木匠,不知做了多少功夫呢,啧啧啧!”柳翠翠说的时候,口水都快掉下来了。
瓦兰故意不屑地说,“一口普通得很的木箱呢,嫂子家里多的是,有什么好珍贵的?”瓦兰的意思,是贬低雕花木箱,让柳翠翠主动放弃抢夺。
柳翠翠却说,“弟媳呀,你说的那里话,嫂嫂想这雕花木箱,都想到命里去了,再说,你嫁过来三年,一直不开怀,也没落下一儿半女,雕花木箱你拿回去屁用也没有!”
“你拿去就有屁用?”瓦兰有些生气了,每次和柳翠翠搭腔,柳翠翠总是揭她心头的伤疤。
“我用处大着呢,给娃装虎头鞋呀,装衣帽呀什么的,不管装多久,都不会有异味,打开就会闻着一股清香呢。”柳翠翠说这话的时候,简直就把眼前的雕花木箱视为己有了。柳翠翠说完,突然扭头凑近了瓦兰的耳朵,“弟妹呀,这雕花木箱,还可以装女人的内裤和胸兜呢,那香味儿,可以熏得死男人!”柳翠翠边说,边像只小母鸡一样“咯咯咯”大笑起来。
正说间,雕花木箱已经被两人拖上了岸。真是一口漂亮的好箱子。柳翠翠已经扑在上面,做势要把它扛回家了。瓦兰心口疼痛起来,她也顾不着平常在村庄里人见人爱,口口称赞的形象了。她也扑到了雕花木箱上,“嫂子,雕花木箱是我发现的,应该归我,你不能抢!”
柳翠翠冷笑了一声,“瓦兰呀瓦兰,村里人都说你是少有的乖媳妇,没想到那些人真是瞎眼了!这箱子明明是我拖上来的,你偏要说是你的!你真是横不讲理了!”柳翠翠说着,就把箱子扛到了肩上。瓦兰去夺,可不是柳翠翠的对手。
瓦兰急了,大声喊起来,“不要脸的柳翠翠,活抢人了!”这时,村庄里正涌来不少打捞的人群。来宝也夹在人群里,一副气鼓鼓的喜气样子。柳翠翠突然耍了花招,人一下子倒在一面湿漉漉的草坡上,呼天抢地般哭起来。“瓦兰抢人了,抢我的雕花木箱了!”她边装模作样地哭喊,双手却死死地抱住雕花木箱不放。
来宝就在这时听见了呼喊,人群像群疯子一样奔了过来。来宝气得吐血,当时就左右开弓抽了瓦兰几耳光,把瓦兰嘴里的血也抽出来了。
瓦兰拼命咬着嘴唇,不哭。只是狠狠地盯着雕花木箱,幽幽地说,“是我先发现的雕花木箱呀,恶人先告状呀!你们不信,那箱子底儿还涂着蜡呐,专门为我做的雕花木箱呢。”
瓦兰说完,才发现乱子越捅越大。柳翠翠趁机换了一副讥讽的笑脸,“哟,来宝媳妇还知道这雕花木箱底儿涂着蜡呢,莫不是桐花岭上的高山毛特意为瓦兰订做的?哟,你这看心眼细得,还涂上蜡呐,啧啧啧,来宝一定比他差远了。”
柳翠翠骂完,围观的人群哈哈大笑起来。来宝一张丑脸气得像猪肝。他又抬手给了瓦兰脸上几下。瓦兰就被打得天旋地转起来。柳翠翠趁火打劫地挖苦来宝说,“来宝呀,嫂子猜想,一定是哪个高山毛为瓦兰做的雕花木箱,嫂子我不要了,这是贱货呀,嫂子要了丧一辈子的霉气!
柳翠翠说着,作势要把雕花木箱递给来宝。来宝气得脖子上青筋暴绽,扬手就推开了。柳翠翠见状,扛着雕花木箱,飞也似的逃走了。瓦兰理也不理来宝,她的目光跟随着雕花木箱那道暗红的影子,追出去老远。可她无能为力了,丢了心爱的雕花木箱不说,还挨了男人一顿耳光。这还没完呢,来宝东西也不捞了,丢了家伙,拖着瓦兰,就朝村子里跑去。
来宝把瓦兰打得鬼哭狼嚎时,柳翠翠正在门口的瓦顶上晒她的雕花木箱。柳翠翠真是可恶,抢了别人的雕花木箱不说,还要把它晒到瓦顶上,让整个村里的人眼气,更让瓦兰眼气。
村里女人都到柳翠翠家里,去看那只漂亮的雕花木箱。柳翠翠真是精过头了,她怕雕花木箱被人们摸坏,或是抢走偷走。她竟然想出了个万全的法子,把湿淋淋的雕花木箱放到高高的瓦顶上。鲜红的雕花木箱放到漆黑的瓦顶上,经过强烈的反衬,愈发显得妖娆迷人。
人们团团围住柳翠翠,啧啧称赞。她算是出了不少风头。
柳翠翠提了根棍子,就坐在坝子里,守着她的雕花木箱。柳翠翠对围观的人气鼓鼓地说,“瓦兰这不要脸的,还说是她的呢?真是死不要脸了。这不?来宝只像打条牛一样抽她,这就是不要脸的下场!”围观的人不敢多言多语,只是夸赞几句,就悻悻离开了。女人们散开时,还在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的样子……
来宝打得实在没有力气了,才放下鞭子和拳头,朝镇上走去。他每次打完瓦兰,总会去镇上的柜台里买苞谷烧喝。喝醉了酒,他不是在大路边睡上一天,就是又歪歪倒倒地窜回家里,拉着瓦兰接着打。打着打着,他也可以呼呼睡去。
瓦兰哭累了,小睡了一会儿,她在睡梦里总是梦见那只雕花木箱。她还梦见了姆妈,姆妈总是一个劲儿地说,“瓦兰呀,雕花木箱从河里漂下来了,你快去捞吧。”姆妈说完,就像缕青烟一样消散了。而瓦兰在梦中奔跑着,快要到河边时,却总是够不着那雕花木箱。于是,她常常会在梦中惊醒,然后,独自一人带着无限惆怅的心情,面对这浑噩的世界和人群。
第一次看见雕花木箱,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姆妈还在世,姆妈家住在这条河的中游,也是住在河边。爹早就死了,他是水鸭子,喜欢在河里捕鱼。而他却在一次追逐鱼群的过程中,死在了河里。瓦兰很小的时候,姆妈就给她说过,爹不是淹死的,而是被鱼害死了。爹杀了太多的鱼,鱼对他深怀仇恨,在爹一次炸鱼后,钻到几丈深的水去抓鱼时,一对桃花色的大鱼,把爹带到了更深处。
瓦兰的姆妈说,那两条桃花色的大鱼,其实就是要了爹命的鬼。鱼群被爹放的炸药炸晕后,躺在深水的河床里明亮亮一片,像天上的星星泛着光。爹的水性好,每次在水底抓鱼,他都要穿满胳膊长的两串鱼儿,才浮出水面。
和爹一起下水的,还有一个“高山毛”叔叔。在河流的这一带,人们喜欢把水边的人分为三类人。高山毛人,半山腰人,和矮处人。有必要解释一下,矮处人在这一带,地位最高,他们住在河的下游,是鱼米之乡,穿得光鲜体面。而半山腰人,往往住在山脉的中游地带,缺水和植被,但有杂粮解决温饱,总是抽着一种烟子烟,嘴臭气熏天。高山毛人,就是住在桐花岭山脉的顶部,常年住在云雾里,不出产多少庄稼,却可以有木材和野物享用,常常披着蓑衣,裹一身棉裤和跳蚤。这里人群的地位,一处比一处低。
深山里来的高山毛叔叔,是爹要好的朋友。他是个出色的木匠。他做了米柜,衣柜,梳妆台,脸盆架子,或是雕花木箱,爹就去山里运下来,到躲雨镇上卖掉。而躲雨镇上接头的人,就是来宝的爹。正是这个原因,雕花木箱从小就填满了瓦兰的梦。也正是这个原因,她长大后才嫁到了是女人都想去的躲雨镇。
那天高山毛也跟随爹潜到了河底。爹的死,就是高山毛叔叔后来向姆妈描述的。姆妈说,那两条桃花色大鱼让爹兴奋不已。爹懒得去抓躺在河床上那些普通不过的鱼儿了,他瞄上两条大鱼,追了过去,没想到,两条鱼儿把爹带到水的最深处,然后闪进了一条石缝里。爹伸手就探了进去,没想到当爹想拔出来时,却怎么也拔不出来。高山毛叔叔也无能为力,就在最后一口气快没了时,他只好拼命地浮出了水面。而瓦兰的爹,却被两条大鱼害死在了河里。
当然,事情发生的时候,瓦兰没在现场。她一个小丫头,此刻,正在和高山毛叔叔带来的“小高山毛”在门口,用瓦片呀,树叶呀,小虫呀什么的办“锅锅宴”,还装模作样地吃得“叭叭”作响呐。
埋爹的时候,村里人议论纷纷,说爹死得很蹊跷。爹那么好的水性,怎么可能被淹死呢?这真是这条河上的笑话。可爹偏偏就死了。瓦兰听村里人悄悄嘀咕过,怕是高山毛搞的鬼。
告诉瓦兰的,是村里一个老婆儿,她对瓦兰说,“你姆妈嫩得像朵花呐,怕是高山毛心痒痒想掐了。”当时瓦兰太小,没懂,也没放在心上,自然也就没把这秘密告诉给姆妈。当然了,瓦兰也不明白姆妈是否知道。她只记得,埋了爹,高山毛叔叔就带着小高山毛走了。小高山毛走的时候,还哭哭啼啼呢,他的二分头被风吹得一甩一甩的,让瓦兰当时就看得入迷。
高山毛的雕花木箱,打造出来相当漫长和艰难。瓦兰从小听村里的女人说,雕花木箱,不是村里所有女人都可以享受的福气。姆妈告诉过瓦兰,做一口上好的雕花木箱,首先是红豆杉这种木材难找。等找着了红豆杉,又要择日子砍树,砍完不能暴晒,要用阴干的方法,然后才是做工。等做完箱子,雕花的功夫就更长了。这样一算下来,一口雕花木箱,要花上一年半载才能做好。而且在桐花岭上,只有高山毛叔叔才有这门手艺。
当年,爹仗着和高山毛要好,才弄得了三两口,不过瓦兰的姆妈也只是在夜晚摸到过几次,转眼就被爹和来宝爹,倒卖到了躲雨镇外面更远的地方去了。瓦兰想,那几口雕花木箱,肯定被城里尊贵的大家闺秀买去做嫁妆了。爹在世时,姆妈就向爹央求过,给她弄一口。可爹不干,爹说,那要卖很多钱呢。姆妈背着爹,暗地里咒骂了他好几次,无非就是骂他水鬼牵呀,短阳寿死呀什么的。
爹后来果然就被水鬼牵了,也短阳寿死了。
瓦兰在没有看到雕花木箱前,雕花木箱鬼魅般的影子,就开始光临她的梦境了。爹死后不久,瓦兰就央求姆妈,带她到高山毛叔叔家,去看雕花木箱子。其实瓦兰除了想看雕花木箱的样子,还想看看小高山毛。她老想着他的清秀的二分头和腰间总是拴着的一根草绳子。
去看雕花木箱那天,瓦兰记得清清楚楚,姆妈精心打扮了一番。姆妈用两根线,对着镜子在脸上扯着汗毛。等她脸上,额头上的汗毛扯得光溜溜了,她的脸也变成了月亮般明媚。然后姆妈又取出一张两面红的纸样的东西,放到唇间轻轻地长长地抿了一下,她焦渴的双唇就变得鲜红欲滴了。姆妈也没忘收拾瓦兰。她给瓦兰换了一身新衣,头发也扎成了两条辫子,还一边扎了朵花儿。
母子两像一对走亲的人,朝山里走去。村里人看见瓦兰母子,都驻足观望,然后啧啧夸赞姆妈和瓦兰漂亮。那时,柳翠翠还是村里等着出嫁的大姑娘。可她已经变得像个婆娘一样尖酸刻薄了。瓦兰记得,当她们从柳翠翠家走过时,她穿着一身破衣烂裤,斜着眼嘲笑说,“哟,大娘,相亲去啊,整得像个新媳妇儿!”
当时姆妈没吭声,拉着瓦兰,急急从柳翠翠家门口走过了。柳翠翠却还不饶人,又赶到路边,对姆妈喊起来,“大娘,记得弄口雕花木箱做嫁妆呀,你开口,高山毛叔叔肯定给,还不用付钱呐。”挖苦完,柳翠翠就满意地“咯咯”笑开了。瓦兰当时想扭过头去骂,可姆妈一把捂住了她的嘴,把倔强的她硬生生拖走了。
等走远了,姆妈才对瓦兰说,那丫头嘴里有毒,我们招惹不起。瓦兰却气鼓鼓的,一脸不高兴。瓦兰从柳翠翠的眼神里,看出她是眼气瓦兰家。瓦兰爹虽说走得早,可多年买卖,给她家留了些钱财,虽然孤儿寡母,可在村里也过得像模像样。
瓦兰那次去看雕花木箱回来,柳翠翠就嫁人了,远远地嫁到了下游的躲雨镇上,那是山里女人,人人向往的富足之地。嫁到那儿去,女人就是享清福的命了。
瓦兰记得柳翠翠出嫁那天,她在亲人的簇拥下,从大门口走出来。瓦兰看见她手里拿着双筷子,猛地朝后甩去,然后装模作样地哇哇哭起来。村里的女人出嫁,朝身后甩筷子,意思是从此不吃娘家的饭了,从此嫁出去后,凭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活。瓦兰出于好奇,跟在围观的人群里,也许是她好看的新衣很惹眼,柳翠翠透过捂在脸上的指尖,一眼就看见了她。
柳翠翠一下子捉住了她,又伤心地哭起来。村里的人都说,柳翠翠好心善呀,连村里的小孩子也这般留恋。柳翠翠却在瓦兰耳边哧哧一笑说,“瓦兰呀,你好福气,你早晚也要嫁到躲雨镇上,来宝可是个丑八怪呢。”说完,她没等瓦兰发火,又站起身,用手捂住脸,佯装伤感起来。爹生前让瓦兰就和来宝订了娃娃亲。听说自己将来的男人是个丑八怪,瓦兰伤心得呜呜哭起来。
送亲的人听到瓦兰哭,纷纷又夸赞柳翠翠。瓦兰觉得,柳翠翠那声音,不知是哭还是笑,她偷偷地从指缝间,拿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嘲笑着哭得伤心欲绝的瓦兰。就这样,柳翠翠在伤感的气氛里,体面地离开家,嫁到了躲雨镇上。
瓦兰和姆妈走了一天,总算赶到了高山毛叔叔家。瓦兰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小高山毛的家。几间土坯房子,上面顶着茅棚。倒是房前屋后,堆了无数木料和家具。高山毛叔叔正弯着腰割木头。他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架着一支铅笔。
高山毛叔叔背对着她们,撅着屁股,一下一下,卖命地锯着。瓦兰只听见“呼,呼,呼”的声音从木料和锯齿间传来,然后是木料的锯屑纷纷扬扬洒到地上。从粉白的锯面上看,这不是做雕花木箱的木头。
姆妈只好用手背摁着嘴巴,站在不远处,假装轻轻地咳了一声。姆妈的意思,她不是闯进来的,她要埋头干活的木匠请她和瓦兰进屋。而且想通过这声意味深长的咳嗽,看看木匠扭过头来的神态。听见响动,高山毛叔叔果然弹簧般迅速扭过头来,同时停下了手中拉动的铁锯。
瓦兰看见他几乎是愣怔了一下,又惊又喜的样子,一口吐掉口中的烟屁股,朝姆妈和她死死瞅着,一步一步地走来。瓦兰回头看了姆妈一眼,她发现姆妈嘴角扯动着,眼底眨着泪花,似笑非笑的样子,突然变得像个害羞的姑娘一样不知如何是好。高山毛叔叔嘴角也扯动着,他的笑了起来,有点怪怪的味道,他冒了句,“您终于来了,等得好苦哟。”
高山毛叔叔说完,就低下了头,也变得一副很害羞的样子。姆妈这才扭动了步子,瓦兰也跟在姆妈旁边。高山毛叔叔她很熟,她一点也没觉得别扭,只是姆妈和高山毛叔叔的举动,让她变得有些不自在起来。她只好赶紧问,“小毛哥哥呢?”她刚问完,正要进屋的两个大人就咯咯笑起来。高山毛叔叔瞅了姆妈一眼,说,“知道我们的瓦兰要来,小毛哥哥在屋后山里捡蘑菇呢,你快去喊他吧。”说完两人相视一笑,瓦兰就边喊边朝屋后面的森林里跑去。
瓦兰记得,那次在高山毛叔叔家住了很久。映像中一向冷漠无语的高山毛叔叔,变得开朗了。他成天哼着曲儿,在门口做家具。他一会儿去屋后的森林里,在树干上这儿拍拍,那儿拍拍。一会儿又耳朵上架着铅笔,在一根木头上忙活起来。姆妈也像走进了自己家里,在屋里屋外忙活,打扫呀,烧火做饭呀什么的。瓦兰和小高山毛,也像久违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有做不完的游戏。小高山毛把她带进森林里,森林里到处是铺满的落叶和松针,还有四处鲜艳夺目的野花。山风也一阵阵,像洪水漫过森林顶端。空气中泛着各种树脂的清香。
俩人坐在地上,小声聊起来。
瓦兰突然说,“小毛哥哥,你姆妈呢?”
“姆妈早死了。”小高山毛幽幽地说。
“你爹这么年轻,她怎么会死呀?”瓦兰觉得有些奇怪。
“谁知道呢?她本来可以不死。”
“本来可以不死?”瓦兰问了一句,“说话有半句没半句的,把我说蒙了。”
“是呀,要是她不想死,她是可以不死的。”小高山毛甩了甩二分头,鼻子抽了几下,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
“是她自己死的?”瓦兰不知怎么和冒出了这一句。她像脑袋开窍一样,突然明白了死亡的方法很多。
“是呀,是在森林里上吊死的。”
“森林里?你成天在森林里瞎转悠,莫不是想碰见你姆妈呀?”
“是呀,想碰见她,可怎么可能。”小高山毛叹了一口气。又说,“要是像你一样,有个年轻美丽的姆妈活着,该多好呀。”
“那,她是为什么死呀?”
“不为什么。”
“死总得有个理吧?”
“就为一只雕花木箱死的。”
“怎么会呀,你爹不是木匠吗?做雕花木箱是他的拿手好戏,怎么会守着鱼池还没鱼吃呢?”瓦兰歪着头,去看一脸忧伤的小高山毛。小高山眉清目秀,瓦兰只觉得看上去舒服。再加上他不经意看你一眼的那种神情,叫人心疼。
“爹不给她雕花木箱,他总是做着其它家具,偶尔做一口雕花木箱,要不是你爹来取走,就是他人预订了。姆妈等了很多年,没等着一口雕花木箱,那天她实在想不通了,就给我们做好了饭,说是去林子里捡蘑菇,却在一棵红豆杉树上吊死了。”
“就是那种做雕花木箱的红豆杉?你妈妈死得好奇怪。”瓦兰一脸迷茫。
“是呀。姆妈死后,爹就极少做雕花木箱了……”
“平常你一个人在森林里,你就不怕遇上你妈妈的魂魄?”
小高山毛幽幽看了瓦兰一眼,嘴角像高山毛叔叔那样扯动了一下,然后轻轻笑着说,“有什么好怕的?那是自己的姆妈呢,想遇着还来不及呢。”小高山毛说完,停顿了一下,又莫名其妙地说,“世上有谁怕亲人的鬼魂呢?”
两人聊了一会儿,天色就暗下来。黑暗像墨水,从森林的深处洇染而来。瓦兰不是怕黑夜,她是担心黑暗里会跳出些魔鬼。于时,两人手牵着手,从森林里跑了出来。
瓦兰一直记得,在高山毛叔叔家做客的最后一晚。那天高山毛叔叔活也不干了,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地抽着烟,一眼一眼地往姆妈的脸上瞟着。她和小高山毛在灯下玩,佯装没去关心两个大人的事,可却总拿一只眼睛瞟着两个大人。姆妈坐在高山毛叔叔身边,虽然没挨在一起,但很近。高山毛叔叔一脸忧愁,不断吞吐着烟雾。姆妈轻轻地说,“他叔,你别那样。”
高山毛叔叔还是不吭声。倒是一旁的小高山毛急了。看样子父子俩感情很好。瓦兰来的很多天里,她也真切感受到父子俩像兄弟般开着玩笑,互相咒骂着对方。灯下的小高山毛愣了高山毛叔叔几眼,气鼓鼓地说,“你倒是开口说话呀,三碇子打不出个屁来的家伙!”
没想到,这样的玩笑话,竟然叫高山毛叔叔火了。他猛地一巴掌扫掉了面前的油灯,朝小高山毛吼了一声,“闭嘴!”很久以来,瓦兰一直觉得高山毛叔叔脾气很好,几乎不发火儿。姆妈及时地支了一声,小高山毛就气咻咻地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睡觉去了。瓦兰也磨磨蹭蹭不想走开。姆妈也把她支开了。瓦兰走进堂屋里,却在门边停了下来,她想听点两个大人聊点什么。
高山毛叔叔开口说话了,“瓦兰姆妈,你能不能留下?”
“不能呀,我留下,村里人怎么说,还有瓦兰呢,怎么办?”
“别管人们怎么说了。瓦兰的事,要是看上我家娃就……”
“不可能呀,她和躲雨镇的来宝定下了,那可是媒妁之约,我们不能毁了他爹留下的诚信。再说他爹死了,我更不能这样,要不然我怎么活呀。”
高山毛叔叔看了看姆妈,他低下头,沉默不语了。高山毛叔叔隔了好一会儿,才又把头抬起来幽幽地说,“那我不强求吧,您想要我做点什么,您就说吧。”瓦兰看见高山毛叔叔的眼神里,充满了忧愁。
姆妈开口了,露出了一口雪白好看的牙齿。她轻轻地拢了拢耳边的垂发,轻轻地,喃喃地说,“给我口雕花木箱吧?”
瓦兰看见高山毛叔叔瞅了姆妈几眼,摇摇头,使劲地摇摇头。姆妈一下子扑过去,抓住了他的大手,几乎用哀求的语气说,“他叔,求你了,就给我做一口雕花木箱吧。我想它,都想到命里去了。”
高山毛叔叔愣怔了一会儿,才点了点头。“我一直给您做雕花木箱吧,到时候,您也不用再来,只需在河边等着就好了。”姆妈张口想说什么,高山毛叔叔用眼神制止了她。她也就只好抿着嘴唇,一句腔也不开了。瓦兰就在他们的谈话里睡着了,等醒过来,她和姆妈已经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来宝是在姆妈死后不久娶走瓦兰的。那时,瓦兰已经十七了,山里的姑娘,十七岁就足以嫁人了。从高山毛叔叔家里回来,姆妈就常常去河边等雕花木箱出现。可是,很多天过去了,雕花木箱一直没有出现过。后来几个月过去了,听说有雕花木箱出现,却被其它村的人捞走了。就这样一直等了很久,瓦兰陪在姆妈的身边,一直等到了她十七岁。
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雕花木箱已经像道魂魄一样缠上了姆妈和瓦兰。姆妈总是在河边徘徊着,她夜夜梦见雕花木箱。就在离开高山毛叔叔家的头一年,河里出现过三两次雕花木箱的影子。后来很多年间一直没有出现。在雕花木箱连影子也没出现的那些年,姆妈还是照常去河边。瓦兰也总是跟在她身边。那时候,村里人纷纷议论说,姆妈是不是让爹的鬼魂附上了,怕是要疯了。
瓦兰担心姆妈,只好跟在她身边徘徊。
没隔多久,山里传来消息:高山毛叔叔死了。他也是上吊死的,同样死在那棵小高山毛姆妈吊死的红豆杉树上。当瓦兰姆妈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变得木然无声了。只有去搜寻雕花木箱时,瓦兰才发现姆妈的眼神变得异常明亮。
就在瓦兰出嫁前不久,下了一场七天七夜的大雨,整条桐花岭山脉,被天上来的大水烧湿透了,河里的洪水滔天而来。第八天清晨,人们都在休息时,姆妈却不见了。瓦兰一觉醒来,朝她熟悉的河边跑去。这时,天地像冒出来的一个新世界,到处充满了洪水。
瓦兰很快在河边发现了姆妈。远远地,瓦兰就看见姆妈双脚已经踩进了洪水里。瓦兰顺着姆妈奔去的方向,看见了梦里时常出现的雕花木箱。那雕花木箱,像道可怕的红光,在那儿闪烁浮沉。洪水咆哮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眼看雕花木箱泛着的那道红光奔到了跟前,姆妈尖叫着不顾一切地朝它扑去。瓦兰高声喊叫起来,她边喊边哭,心都快冒出了嗓子眼……
事儿还是发生了。就在姆妈快要够着雕花木箱的当口,更大的一个浪头呼地卷走了姆妈。瓦兰跑到河边时,洪水快淹没了姆妈的嘴巴。姆妈伸出一只手,摇晃了一下,喊了声,“瓦兰,快捞你的雕花木箱呀!”她话音刚落,一阵巨大的咆哮声就把姆妈带走了。
瓦兰后来想,那叫人心疼的雕花木箱,一看就没有高山毛叔叔的手艺那般老到。于是,她想到了小高山毛。想到了他忧郁的眼神,和被风吹起来一甩一甩的好看的二分头。
村里人等瓦兰妈一安葬,就急着把瓦兰嫁走了。村里的亲人说,那只雕花木箱就是条勾魂摄魄咒语。为了避免这噩梦般的诅咒再次缠绕活着的人,就让瓦兰出嫁冲冲喜。柳翠翠裹在前来迎亲的队伍里,幸灾乐祸地看瓦兰家的热闹。瓦兰原本灰暗的内心,又贴上了一道难解的符。
嫁到来宝家的第二年,瓦兰看见来宝第一次打了牛。瓦兰嫁过来快两个年头了,一直没开怀。第二年里,她就常常听见村里的挖苦。特别是柳翠翠,总是带着他胖乎乎的儿子,从瓦兰家门口走过。每次走过,都故意高声地问,“瓦兰呀,你怎么还不开怀?是你不肯?还是来宝不行呀?”说完,她就嘎嘎笑着,扭动着肥嘟嘟的屁股走远了。
就在这一年开春时,瓦兰跟随男人来宝,在田里耙田。男人牵着牛耙田,瓦兰就在田坎边上捞泥糊田埂。瓦兰在家时,很少在田里干活。糊田埂的活儿,不不好拿捏。如果捞的泥稀了,糊不上去。如果捞的泥干了,又糊不匀称,田埂糊出来也不保水。瓦兰正想着心事,稀泥糊上去,立即就垮了下来。来宝在不远处斜着眼瞅着她。他越看越不顺眼,加上牛累坏了,站在那儿不肯耕田。
来宝立即火冒三丈,手持赶牛的鞭子,狠狠地打起牛来。牛是头老牛,来宝像抽仇人一样抽着它。来宝先是在屁股上抽,不解气,干脆往牛头上抽。牛累了一个春天,瘦得皮包骨头。坚硬的荆条鞭子落上去,很快就抽出了黑红的血。那鞭子坚硬如铁的声音,一下一下抽在上面,像抽在瓦兰身上一样。老牛实在不行了,只好趴在水田里,闭着眼让来宝抽。来宝边抽边骂着。
瓦兰听得出,来宝其实是在骂她。瓦兰实在看不过了,可怜的老牛啊,她真想跑过去,抱着她痛哭一场。
后来,老牛就在来宝的皮鞭下,痛苦地死去了。最可恨的是,来宝竟然还剥了老牛的皮,熬了他的汤。杀老牛喝牛汤那天,村里来了好多人。瓦兰躺在床上,无论村里人怎么劝,她就是不肯喝一小口老牛汤。倒是村里人吃得红光满面。
那天早晨,当瓦兰和柳翠翠吵了架,被来宝拖回家抽打,她就是受的老牛那份罪。只是自己年轻力壮,没有被打死。她在迷糊中,梦见那只漂亮的雕花木箱漂下来,不断地漂下来,扰得她心烦意乱。瓦兰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只从未拥有过的雕花木箱。她猛然间想明白了什么,决定去柳翠翠家把雕花木箱看个够,然后彻底把它忘掉。
瓦兰想通后,起身朝柳翠翠家走去。
柳翠翠听说瓦兰要看雕花木箱,她几乎笑掉了大牙。
她对瓦兰说,“要看我的雕花木箱可以,但得付钱。”
瓦兰二话没说,立即掏了张钱给她。柳翠翠小脸立即笑得稀烂,张口就朝村庄里喊起来,“瓦兰花钱赏我家雕花木箱了!”她生怕村里的人听不见,声音加大了好几倍。村里的人匆匆围观而来。
瓦兰嘴角扯动着一丝神秘的笑意,心满意足般走了。
她看过了雕花木箱,那是一双年轻的手做的雕花木箱呀。从它的楞角和墨缝间,还可以看出些许粗糙和焦虑不安。这雕花木箱出自一双没有女人爱抚的手。瓦兰黑暗的心头,瞬间像洒上一缕光明,让她透彻得眼泪汪汪。
她头也没回,再也没有看雕花木箱一眼。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很多天里,柳翠翠家挤满了掏钱看雕花木箱的人群。有人劝柳翠翠说,“柳翠翠呀,你把那宝贝箱子放到地上来,让大家掏钱观赏,不是一个样?”柳翠翠小母鸡一样,咯咯一笑说,“哪能一样呢?要是放到地上,就便宜大伙了,我柳翠翠哪能赚钱?再说放到高处,大家涂的就是个稀奇古怪!”
大家不得不佩服柳翠翠的历害,可又忍不住掏钱上房去看几眼。就这样,柳翠翠天天都在门口忙活,生意好得不可开交。
没想到,几天后的傍晚,正沉浸在发财梦中的柳翠翠,终于出事了。她照例上去收雕花木箱,想把它扛进屋里收藏好,第二天再放到瓦顶上去。没想到她刚爬上去,没踩稳,从上面摔了下来。柳翠翠头先着地,躺在地上还有几分气息,她只吐出了句,“我的雕花木箱呀……”然后就一命呜呼了。
瓦兰看见柳翠翠这一幕遭遇时,是在来宝又一次抽她之后。这次抽打,瓦兰同样在伤心中捂在被子里睡了一觉。她梦见了那只漂亮的雕花木箱。
来宝打完她,就到镇上去喝苞谷烧了。瓦兰在傍晚时分醒来,正好看见了柳翠翠从漆黑的瓦顶上,像头牲口一样栽了下来。当时,瓦兰分明看见了像夕阳反光一样的东西刺中了柳翠翠双眼,然后她才从高高的瓦顶上摔了下来。
柳翠翠的死,同样与雕花木箱有关。瓦兰一下子大彻大悟了。
天刚麻麻亮,瓦兰就离家出走了。这时候早起打捞河流施舍礼物的人们,也三三两两地朝河边赶去。没有人在意瓦兰的存在,都把她当成了个等候雕花木箱的傻女人。瓦兰轻快地在岸上走着,两岸浓烈的大雾,正飞快地撤走……桐花岭深处带来的山风,吹起了她额前的长发。她任长发飘飞着,懒得去捋它一下。她心底不断涌现出小高山毛的样子,这也是她后来人生中常常出现的梦境。
等河边的大雾彻底退却后,瓦兰就在躲雨镇上消失了。当来宝一梦醒来,光着脚板,跑向河边找自己的女人时,在河边打捞的人才告诉他:瓦兰走了。
有人说,瓦兰是去捞一只雕花木箱失了足,掉在洪水中冲跑了。也有人说,瓦兰往上游去了,可能是她娘家的方向,也可能是小高山毛家的方向。
疯癫的来宝不断地把瓦兰找呀找呀找。
又过了两三年,一场更大的洪水后,有人又说,在躲雨镇下面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具怀孕女人的尸体,样子很像瓦兰,可洪水太大,没有人会愿意为打捞一具怀孕女人的尸体而冒失去生命的危险。
就这样,这一切都成了传说。
传说终归是传说,瓦兰和雕花木箱,再也没有在躲雨镇上出现过。